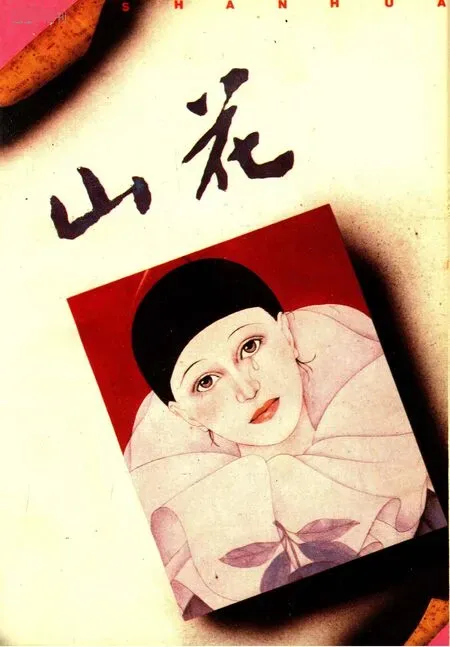记忆中的“蝴蝶效应”
2005-04-29翟大炳
人们之所以喜欢回忆,就心理机制说,是由于那些已逝去情景带来的深刻的体验常常是难以忘怀,并且对眼前有借鉴意义。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的回忆经常是抚今思昔的对比。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说它是“断片”。为什么这些“断片”能打动我们,是因为他起到了“方向标”的作用,“起了把我们引向失去的东西所造成的空间的那种引路人的作用。”
(一)一句话惹祸
1954年,我考上了当时安徽省最高学府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今安徽师大)学习。这在大学生还比较少的年代实在是特大喜悦,何况当时的录取方式是“金榜题名”,所有录取学生名单都刊登在华东区首席报纸《解放日报》上。
然而不久,这欣喜心情就灰飞烟灭了,原因是入学不久就遭遇到突如其来的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先是武装的公安人员进校抓人,虽然被老革命的校长方向明制止了,但不久就传来中文系教授曹冷泉和艺术系的一位著名版画家被隔离的消息。又过几天,教授的夫人因惊恐而悬梁自尽,一时间乌云密布,山雨欲来。学校除了维持上午上课外,其余时间都是学习文件、检查和揭发。试问,当时大多数学生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最小的只有16岁,他们对胡风的作品压根儿都没有看过,又怎知他的罪恶。不过,经过几周对人民日报上刊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编者按的强行灌输。终于使他们有所认识:这是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企图与党争夺青年的反革命集团。不是吗?报纸上报导了一个19岁天津青年侯红鹅就是在名利思想引诱下一步步投入他们怀抱走向深渊的。
出于真诚,在一次小组学习会上,我率先检查自己名利思想,并说:“幸亏这场运动及时开展,否则我会成为第二个侯红鹅的。”不料此话一出,会议主持者立即要我交代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关系,紧接着有人拍案而起,大喝一声:“翟大炳,你要老实交代给胡风写了几封信。”小组其他人也一哄而起,说我已走到危险边缘。就这样,我就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挂上了钩。直到30多年后的1985年,一次偶然才知道这侯红鹅正是活跃于当今文坛的天津的诗人,小说家林希。时光进入了2005年10月,当我读了他的新著《百年记忆》,才知道他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他不可能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安徽芜湖的一个青年学子也因此付出了代价。这不是有名的“蝴蝶效应”吗?所谓“蝴蝶效应”,是说一只蝴蝶在巴西煽动翅膀,就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引起旋风。它可以是正效应,也可以是负效应。它可以是美丽的,也可以是残酷的。现在我们还进一步知道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骨干分子,不仅是创造了名垂史册的“七月诗派”的大诗人,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如绿原、曾卓。在当时,从未见过这阵势的我,一下被吓得嚎啕大哭起来,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政治运动的威力。
也许当时的班领导视我年龄还比较小,用现代话说,尚未成年吧!再说彻底检查了日记也没发现什么,经过几天折腾后便放我一马,我获得了“解放”。可是班上有几个平时爱和干部顶牛的同学,尤其是爱和其中一位来自山老区的民兵队长姓阴的同学碰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被关进了失去自由的“老虎队”,说他们已是反革命集团了。以后虽也被“解放”,已是一年之后,只好留级了。1957年,这些同学自然为此愤愤不平而“鸣放”,他们又成了“右派分子”。那位3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革命的院长也成了包庇坏人的大右派分子,其妻也成了右派分子,儿子流落街头,几乎家破人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后果真是不堪回首,这已是后话了。
时隔50年,但一切好像就在昨天,历历在目。我们真羡慕当今青年,他们逢上了可以读书的盛世了,只要他们愿意。可是在当时,偌大的中国是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我们要倍加珍惜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啊。
(二)一次奇特的辩论会
改革开放后,大学生辩论会成为新兴事物为人们所称赞。其实,早在40年代就有过。据青年学者谢泳说:“时为1948年12月28日。这次辩论的题目是《和谈是可能的吗》?正方:和谈是可能的;反方:和谈是不可能的。经过两小时的辩论,同学公断结果,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为目前和平不可能,反方获得大胜。”①对这次辩论会,他给以极高的评价,说他有深度,因为他们辩论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辩论双方才真正投入智慧和判断。而不是像当前的大学生辩论会上所显示出来的“秀”(show)。他认为这次辩论,从双方的语言、逻辑和辩论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学生所望尘莫及的。
对上述看法,我们认为必须有所辩正。首先要说明的,解放后的大学辩论会并不是80年代才有的,早在50年代初期的大学中就有了。笔者就全程参加了我所在的安徽师院(今安徽师大)一次辩论会。辩论的题目为“什么样的教师受到尊敬?”正方的基本观点是只要是教师就要受到学生尊敬;而反方的基本观点则认为一个受到学生尊敬的教师必须是有条件的。由于双方观点是如此明显信息不对称,在同学心目中是不辩自明的。但为了认真、严肃地对待这次辩论会,反方的同学还是作了精心准备,并公推有出色口才的曹鸿儒同学为首辩。在辩论会上,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举出大量事例,说明一个受到学生尊敬的教师必须是有条件而不是五条件。什么样的条件?诸如品格高尚,精通业务,有敬业精神等等。在他义正词严的强大的攻势面前,正方的辩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常常是张口结舌。他的辩才不时博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就在大局已定、群情激奋的欢乐氛围中,会议主持人在做总结了。他首先声色俱厉地宣布正方获胜。理由是反方所说的条件在我们这所学校根本不存在,仅仅是一种假设,因而是诡辩,而正方所坚持的观点正是热爱学校的表现。他再三说明,班领导之所以安排这次辩论会,是对同学是否热爱学校的一次真正的考验,一种检测。顿时,大家目瞪口呆。此时大家方明白原来它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教育方式。为什么采用如此方式,说来话长:我们所在的安徽师范学院,50年代并不像今天安徽师大这样的红火,不少芜湖人将它说成“芜湖市一中附大”。而当时进入中文系的学生分属两种类型:一是经过统考进来的,一是保送来的。前者学生不免就有一些优越感,常有些牢骚怪话。为了教育并挽救这些落后的同学,便有了这次辩论会的安排。为帮助他们,班干部确是煞费苦心。但同学们对此总觉得不是滋味,似乎吃了变味的食品。刚好教中国通史的陈鹏教授不久前给我们讲了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大家嘴上不说,但内心不免就有了上述联想。当时看来似乎是班干部别出心裁的创造,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大气候的折射。据老共产党员、诗人绿原回忆,胡风当年在写作“三十万言”时,“为了确保自己在理论方面万无一失,曾经多次与朋友们在太平街寓所的客厅里,就林默涵、何其芳两篇批判文章
所涉及的所有理论要点展开过模拟答辩,他是以必胜的理论确信,而引来上书事实上的惨败。”②再认真地想又想,它与后来文革中出现的“无理判断”,所谓“理解的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是否有内在的联系?我们知道,社会语言应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可证性原则:话语者的语言必须是可证明的,必须具有充足的理由,即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文革中,无论是赞扬什么,打倒什么是不需要充足理由的。如一首歌颂文革歌曲,开头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再如:“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的得力干将陶铸就是‘袁世凯式人物中的一个。袁世凯式的人物都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也是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家。他们第一个特征就是千方百计贬低毛主席,贬低林副主席”。(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1697年9月14日)凭什么理由得出上述结论?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一种语言强权。现在看来,这语言强权实滥觞于此。
现在看来,我们把20岁左右的青年说成是一个孩子,因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还会在不断碰撞和比较中认识并纠正自己的错误,对他们应持宽容态度,这才是以人为本。我们班上一位名叫张士魁的同学就是极好的一例。他是从江苏徐州考进来的,由于是填了服从分配志愿而进了学校,他对芜湖市和学校都存有偏见,因而怪话就特多。如说“你们芜湖人说它是一中附大,我说它是徐州市一小附大”、“什么教授,我看是草包”,“芜湖的赭山怎么能和我们徐州的云龙山相比,它只配跪在云龙山面前,我们徐州的云龙湖比你们镜湖至少大8倍,和云龙湖比,镜湖是‘小儿科”等等。可是在多年之后,当我俩再次聚首徐州时,他为自己青年时代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一再忏悔不已。他先后花了几年时间,耗费了大量精力联络上到江苏工作的安徽师大的学生,成立了“安徽师大校友会”。谈起已逝去的宛敏灏、张涤华、卫仲藩、陈鹏等教授和健在的祖保泉教授赞不绝口,为他们学术造诣所折服并以他所工作的徐州师大加以比较,流露出深深的眷念之情。
也由此,我们认为同为大学生辩论会,80年代所举办的,就水平和规模而言是大大地超过50年代。它的自由空气和个性化的发言是前者不可比拟的,确也涌现出不少人才。时代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尤其是三中全会之后。现在的青年人,面对我们这些6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看到的都是些老头、老奶,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对当代青年说,经常温故而知新对促进他们珍惜美好的今天无疑有极大的帮助。
注释:
①《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过去的大学生辩论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
②《读书》2004年6期,《反省大事件,复活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