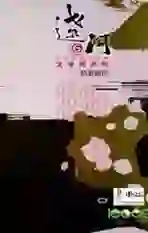记忆中的树
2005-04-29王志宏
王志宏
三叔的梨树
三叔,我是怀念的!就在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我的眼睛和心里含着浓重的泪意。然而,我是不愿意让母亲看到这些文字的,因为她忌讳提到二叔。她固执地认为是三叔导致了我今生的残疾,这也是令她自己伤痛不已的。
所以,小时候,我也是恨三叔的,如果没有他的好心帮忙,我会跟所有的孩子一样的,不会在此后的经历中,遭受某些人的奚落、嘲讽,甚至恶意的中伤。
我没有想到,没有想过,会怀念三叔,怀念分给他的梨树。夜已沉寂,只有我敲打电脑键盘的声音响彻屋宇。我希望三叔可以在远处的某个地方看到我,能够谅解我曾经对他的仇视。在茫茫人海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谁像三叔,也许,我早已忘记了他的音容,无从辨识。我惟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我还记得三叔的梨树。
那时,三叔刚刚和二哥分了家,而三叔的二哥是我的爸爸。日子很艰难,大家分得的东西都少得可怜。我很失望,我家没有分到井台旁的那棵大梨树,不过,小孩子总是极易满足的。不久,我就释然了,因为,那棵大梨树虽然分给厂三叔,但是,它依然耸立在井台旁,依然在我的视野之中。我依旧可以在它的荫蔽下玩耍,依旧可以吃到梨,没有熟透的梨虽然很涩,但是对于那时的孩子来说已经是很好的美味了,整个村子里只有这一颗梨树啊!我和三叔家的堂弟、堂妹是倍受邻居的孩子艳羡的。
那棵梨树叫做红盖梨,现在似乎早已绝迹了。秋后,把梨卸下来,捂得软了是好吃的。树极高,极壮,树荫极大,枝繁叶茂的。祖母和邻家的老太太们都爱在大梨树下做针线活儿。那棵梨树是我们一群孩子的乐园。
我不记得自己有几岁了,穿着一件花的小背心儿,坐在青石板上,祖母说:“回家穿件长袖衣服吧,你已经长大了,你是一个女孩儿家,要注意自己的衣着。要离男孩子远一些。”
也许我的孤独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不过,祖母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依然很快乐,绕着那棵大梨树与孩子们疯。只是,没有哪个孩子能够爬到那棵大梨树上去,想梨吃的时候,我们只是拿着遍地的石头扔到枝叶间去击打,所以我们吃到嘴里的梨没有一个不带伤口的,伤口中还夹带着一些泥土,尽管如此,这依旧让我们兴奋不已。
有时,我从梦中醒来,吃吃地笑个不止,原来,我刚刚躲在梨树上偷吃末成熟的梨,被三婶吼,可是我并不爬下树来……
没有想到,我真的爬到梨树上了,坐在粗粗的枝上荡着,微风从枝叶间轻轻拂过,吹动着朴素的花布裙儿,细长的角辫儿仿佛细的树枝。这并不是梦,也不是我爬到了直立的梨树上,而是梨树被三叔砍倒了。我们觉得真好玩儿,尤其是梨树被锯锯过,在即将倒的瞬间。三叔和帮忙的人给树拴上了绳子,往一边拽着,喊着一种激荡人心的号子,一边轰着我们这群看热闹的孩子。
当红盖梨树轰然倒下,我们迅速地抢战自以为最有利的枝杈,晃荡着孩子们的乐趣。那一天,我并没有意识到,随之而来的秋天,我们将吃不到梨子。也不知道三叔为什么要将长了几十年的老树砍倒。他似乎用砍倒的树,做了几个菜板,也许还做了木头锅盖什么的。我知道,梨树做的锅盖一定比松树的好,因为父亲用过松树的,有松树油子味儿,不经过一年两年,味儿是去不掉的。
门前光秃秃的,老井没了梨树的荫蔽,多了些泥土味儿,似乎不如从前清澈了。看起来敞亮了不少,可是,少了遮拦,总觉得空旷。不久,三叔病了,住进了沈阳的医院,后来,爸爸也去陪护了,这样过了很久。一天傍晚,爸爸回来了,背着一个小口袋,他把它放在大门口原来红盖梨居住的地方,进屋子里来告诉我们三叔去世了,那个小口袋里装着三叔的骨灰盒。
我不记得我是否哭了,那时,对于生命我还没有切身的感受。没有电话,写信邮路太远,爸爸突然的归来,突然的关于三叔的噩耗,令妈妈惊心不已。三婶没有同归,她不会回来了。埋葬了三叔,妈妈沉默了许多。我知道,妈妈是善良的,她谅解了三叔。我的残缺已是无可挽回的,何况三叔也是一片好意,才请错了医生,而事实上,关于我的病,三叔请来的大夫扎下的一针仅仅是一个诱因而已。
三婶另嫁了,嫁得很远,带走了我的三个堂弟堂妹。去年冬天,堂弟回老家,我也赶上正在乡下,他“姐呀姐呀”地呼唤着,我的心里充满了爱怜和酸涩,他帮他的二伯扛大米,一袋子大米压在他个子不高的肩背上,让我不由地心痛。晚上,他没有住在家里,而是住到了邻村的姥姥家,因为,他的继父在那儿。
看着暮色中堂弟渐渐远去的背影,我不敢远送,我怕他看到我的眼泪。我站在红盖梨曾经生长的地方,目送他,仿佛也在目送我们已然远去的童年。似乎我们还花枝招展,无忧无虑地垂着双腿,在三叔伐倒的梨树上悠荡着……
刘堡的花椒树
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美丽的小村子,她不是我的家乡,可是她带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那个小村子是妈妈的家乡,村子的名字叫刘堡。当然了,是因为世代居住着刘姓的土著居民。在妈妈的家里,姓刘的是外婆,而不是外公。
外婆家的房后是一座不太陡峭的大山,山上长满了一种滑滑的草,外婆们叫它“房苫草”,顾名思义,这种草是用来苫房子用的。那时,刘堡的房子几乎都是草房,外婆家的也是。冬天的檐前结着长长的冰凌。
秋天的时候,我们一群伙伴互相牵扯着爬到山上,然后,坐到房苫草上往下滑,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滑梯,房苫草又软又滑,那种感觉极其美妙。秋后,房苫草已经失去了夏日尖尖的绿色,枯柔着,在阳光的抚照下,我们贴在房苫草上的感觉仿佛贴在温柔的猫身上一样。
一天,我们又去玩草滑梯,换了一个稍陡的坡,待滑到山下才发现已然远离了外婆家。山脚下有一棵高大的树,结着小小的果实,果实的大小就像我们在深夜遥望到的星星的模样。这使我莫名地惊讶,在这小小的村子里,这棵树竟然结满了花椒!这棵树竟然是一棵花椒树!
幸亏我是认识花椒的,这得感谢外婆。外婆家的花椒面是买了花椒粒,包好,放在炕席下面烘干,然后,放到桌子上,用擀面杖擀,直到那些花椒由颗粒变成了细细的面儿。而这个活儿基本上是由我来完成的。
也许我太讶异于满树的花椒,事后,无论我怎么回想,都想不起来花椒树的叶子形状,实在没什么印象,恍惚觉得花椒树也许是不长叶子的。
此后,每天放学做完作业,玩过了草滑梯,我们都要去花椒树那儿玩一会儿,选定一个树干做秋千,荡够了,开始摘花椒。那树花椒,我们摘了好久,似乎总也摘不完,也没有大人来过,仿佛那棵树是我们探险探得的。那些干透了的花椒被我擀成面儿后,终于用来炒菜了,每一盘简简单单的青菜都被我吃得津津有味,吃饭的时候,我似乎也感到那么一点儿自豪。
后来,我离开了刘堡,可是,我依然牵挂着她,牵挂着外婆,也牵挂着那棵花椒树。我回去看望过外婆,然而,那是冬天,大雪封山,我没能去看望花椒树。再后来,外婆举家搬迁,离开了刘堡,去了城里,我彻底告别了那棵花椒树。
二00一年的五月二十八日,在外婆离开刘堡十二年之后,我们把外婆送回了故乡,让外婆长眠在南山上。山下流水潺潺,山的对面就是当年我们玩草滑梯的地方,那棵花椒树还在山脚下。那时,满山的绿草凄凄,每一棵草都似乎是我对外婆的思念。
从刘堡归来后,每夜,我都在长满房苫草的山坡上滑行,一直溜到长了花椒树的山脚下,草是绿的,中间盛开着紫色的毛骨朵花,外婆有时背着我,像小时候背着我去哄那样,吟唱着:“毛骨朵花儿,真奇怪,毛朝里,根儿朝外……”
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