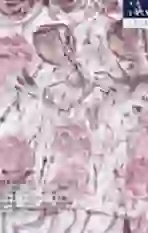记忆中的兰草
2004-04-29西门马格.郑阳
西门马格.郑阳
好多年以前,花卉,只是作为一个词汇,出现在书页里,还不曾作为植物的任何一种进入人们的家居生活。那时,人们也还没有那份闲情和需要去抚弄花草,并把它作为日常生活不可或却的一个仪式。如果偶有这种兴致,也只是去别人家的菜园子里要一枝偶然长在墙角边的花骨朵——鸡冠花,玫瑰呀什么的,或者在外面的溪沟边信手摘回一枝,拿回家弄一个空墨水瓶一插了事,等花枯萎了就丢了,一般不会再有心思再去哪里再摘一枝回来再插在瓶里。既没有人会去专门栽花,也没有人会拿花去街市上卖。倒是小孩子会煞有兴致地去老远的地方拔回几棵,一门心思的撮些土去栽,也不管那是些什么花。
好多年以前,在那个春日的午后,伙伴们跑来告诉我:二道沟里有兰。于是我们就带了小挖锄去挖。那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这在滇东北乌蒙高原上还是很难得的好天气。四五个人怀着像是挖掘宝藏一样的兴奋一路赶去,其乐融融。那时的公路上很少有车,四下里很静,只有阳光在头顶晒着,跳麻蚱在路边上的草叶里猛地飞动的扑翅声——那是一种很纯净的时光——慢慢地,沟谷里传过来汩汩的流水声,从公路的一边下去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最先发现兰的那个伙伴一路上津津乐道地向我们叙说他的发现经过,弄得那兰草在我们心里像电影《马兰花》里的马兰花一样的神秘了。那个时候也只知道兰草会开花,但从来没有见过它开的花是什么样的,更没有听说过兰的名贵与稀奇,一路兴高采烈地前去,仅仅只是图好玩。
走了老远,下到二道沟的沟谷底,我们看见了兰,它生长在一边坡上,一坡都是,一盏一盏的,绿茵茵的叶子向外挑着。大家一涌而上。伙伴中的一个在行的说:那些叶子宽的不是兰草。我们这才看清那一坡上的点点翠绿差不多都是宽叶子的,既而我发现真正的兰草大都长在那些石缝里。石缝虽然不高,但挖起来还是比较辛苦,因为得尽可能把根保留住。到了后来索性把那些不是兰的宽叶子草也挖了些回去。那个时候既不懂栽插常识也不懂气候水分,弄回去的兰草当然不几日就萎败了,那四处探花的兴致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了。
二十年后,在那旧时的山坡上,兰花肯定是再难找寻的了。但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这种分布在温带和寒带的兰花却已一跃而成尘俗炙手可热的尤物。一本本关于养兰鉴兰赏兰的书籍充斥在大大小小的书店,兰花协会蓬勃发展颇具规模,兰花展定期举行,每到此时,各色人等游离其间,交头接耳,可谓盛况空前。面对如此强势的潮流,我对兰却所知甚少,只知道中国是兰花资源最广的国家。想想自己也是爱花之流,再看见别人把兰养出一朵花来,难免会有一份落寞,但也不以为然。
总以为世人之爱兰,别有用心:有仰其高贵的,有爱其圣洁的,有仅供把玩的,有填补空白的,有别有寄情的,有视若生命的,有急功近利的,有盲从随流的……若问是谁栽兰花最多,那肯定非卖兰者莫属了。一棵兰花的价格可以上百万,如此天价,岂有不栽之理。一时间,挖兰者多了,因为养兰者甚众;卖兰者多了,因为买兰者养兰大多是为了更好地卖兰。兰花慢慢地变得不是兰花了,不是兰科植物了,不是空谷幽香的奇花异草了,甚至已经不是花了。作为花,它的欣赏价值已在那金钱铺就的阶梯上被残酷地灭杀了,它变成了人们股掌中的一件奇货可居的商品,成了人们贪欲与妄念的牺牲品——从这一方面来看,真是兰之灾疫和亡世。但是,如果一家一户都养了兰,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人都不爱兰,兰就回到它的深山,不见人世了,人间又少了一种花色,这岂不有些可惜。看那养兰者终日忙乎,竟为卖之,这世人的妄念竟不经意间铸成了兰的繁盛,这倒也值得欣慰。而那一买一卖之间也确有不少真正的欣赏和交流,这当中最为贵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交流,这是令其他花所望尘莫及的,兰花完成了它彰显其色成就经济的价值,也正赖于此。
总还在幻想有一天能够回到记忆中的山坡上、沟谷里,再去挖一次兰,从那些泥巴和石缝里——而不是从塑料盆瓦盆瓷盆里——再看见兰;总幻想有一天,人们都不再栽兰花了,而是唱着那首“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的歌大老远地跑到深山里去看兰花,享受那一种纯粹的与自然的亲近和接触,而兰花也就在人们的一仰一俯,一凝一盼之间重现了它的空谷之幽,王者之香,将那些溪涧的流水声和山峦上的清风带给那些顾盼流离的眼睛和心灵,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壮美……
想虽这样想,最终还是忍不住在热闹过后买回一株栽将下去,然后就少不了经常仰观俯查,暗暗期待,期待什么呢?
期待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