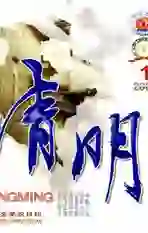钵盂峰的悲愿
2003-04-29藏学
藏 学
悲世间多苦难,发大菩提造地藏圣像,力救群萌;
觉人生若大梦,愿力虽宏奈众生业重,空劳往返。
——净空法师悼念仁德大和尚挽联
一
医生发现您的病情我正在四川峨眉山游玩,我是趁您不在时出去的,您去了北京开政协会,我计算好时间,在您开完会之前赶回佛学院。当得知您在北京住院时,无知的我止不住高兴,我对同去的法师说:“我们用不着急着往回赶。”当时,我不晓得您得了什么病,我只以为北京天凉,您不适应。
4月初我去了北京,在中日友好医院里见到了您。那天上午,我找到了您住的病房,却不见您身影,我问医生,医生说您刚做完手术,在危重病房,怕细菌感染,不能见人。我的心不由地惶惑,医生的谨慎是否表明了您的病况?我找到圣富法师,他一直守在您身边。圣富法师住在医院对面的一家旅馆里,他憔悴的脸上显现出多日无眠,我不便再问什么,也不敢再问什么,我害怕知道您的病情。
圣富法师说下午五点给您送饭,可以在窗口外看您一眼。
我捧着饭盒跟着圣富法师,沿着医院的走廊拐了几个弯,上了几层楼,来到您的住处,我刚要进去,被看门的护士拦住,圣富法师回过头来跟她打了个招呼,说我是同他一道来的,她才放我进去。进门又是一道幽深的走廊,这时,我的双腿突然沉重起来,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我是去看您的,却像是走向另一个世界。
静立在病房外,透过玻璃窗望去,室内苍白一片,白的墙壁,白的床单,您坐在床前的一张没有靠背的椅子上脸色惨白。您将双手搭在膝盖上,像是在静坐,又像是要挣着站起来。我心头酸楚,双眼模糊,您能看清我吗?您我近在咫尺,我却无法走近您……
您的病势已到晚期,大家都为您焦虑,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您的病情,我想您是知道的,您只是装成不知道的样子。您到底得了什么病?圣富法师嘱咐过,要我们瞒着您,只说您的食道里长了个东西,摘除就没事了。于是,大家都说您的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可您总是默不做声,您自己似乎更知道您自己。
我们围坐在您身边,静静地坐着,您不能多说话,您因食道癌做了手术,声带受损。“再过几天就可以回去,铜像的招标已经完成,土地的批文也下来了。”这是您手术后我第一次听到您的声音,也是您最想说的话,您情绪蛮好,只是声音嘶哑,像是受了风寒,伤了嗓子,谁都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的。
二
您是6月上旬回九华山的,一到山上您就投入到地藏铜像的各项论证工作中,北京来的医生劝您万事放下,要多休息。您说没人能够理解您,您的弟子,十方信土,当然也包括医生。您住持一方,可您孤独,您没有属于您自己的时间,也没有一方真正属于您自己的乐土,您把您自己关在一间逼仄的寮房里,医生却建议您到室外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您在上客堂回廊里来回走动,可那巴掌大的地方,您又能走到哪里。您只好回到您的房间,伫立窗前,凭窗远望,您像是在寻找什么,寻找几十年前引您上山的那条小路?您眼前却满是房舍,山问的小路与小路上的野趣只能永远深藏在您的记忆里。
已有好些日子,上客堂走廊里再没出现您的身影,我去您房间看您时,您跏趺在床上,形同槁木。您见我进来,没有说话,我由您的目光领着在写字台前坐下,写字台上放满了有关地藏铜像的审批材料,上面有您的审核及签名,您已心力交瘁,可每一个细小的环节您都马虎不得。写字台上方的那面镜子不知何时被何人揭走,灰暗的墙壁上凸现出一方空空的白。
您看着我,我知道您有话要对我说,您一定放心不下佛学院的事。我是个懒散的人,在学修与工作上不思进取,您让我管理佛学院,要我以身作则,我却秉性难移,我常以工作为名逃过上殿、过堂。我对您说:“佛学院一切正常,您不用操心。”说这话时我已下了决心,我不能再“洒脱”了,我要尽我的职责,尽我的全力,话刚出口我的心却不安起来,学院里千头万绪、理还乱的事务已搅得我乱了方寸。我无法向您诉说我的苦衷,为了不让您挂念,我只能报喜不报忧。您没有在意我话里的真伪,您一定看穿了我的内心,可您没有责备我,您只说您明天要去上海医病。
您是从合肥乘火车去上海的。午后三点从九华山出发,您躺在汽车后排椅上,司机怕颠着您,车速放得很慢。车默默前行,偶有车鸣,在寂寥的山路上,显得分外凄切。到合肥火车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您的身体极为虚脱,圣富法师说已找来了单架要抬着您上车,您不同意,您要自己走上车,众法师无奈,只好左右搀扶着您,您颤颤巍巍地往车上走去……
三
我去上海看您,在您住的医院附近的招待所里见到了圣明、慧庆、圣富、道源等九华山各大寺院的住持,他们日夜守护在您身旁,已有十余日,我本来担心看不到您,我怕看望您的人多了,干扰了您的休息,谁知众法师一见我,就叫我赶紧去看您。我是傍晚时分到达上海的,还没来得及吃饭,祗园寺的住持道源法师就把我带到了您的身边。
离开招待所时,我向众法师深深地鞠了一躬,以示感激。
十几年来,我在您的呵护下成长,从一个小沙弥直到今日,是您给了我一切,从物质到精神,我无法估量,也无以回报。我坐在您身边,陪护着您,尽管您已认不出我是谁。
上海的夜晚似乎有点儿疯狂,霓虹灯搅乱了夜的祥和与宁静。我拉上窗帘,把日光灯关了,只留下您床头的那盏小灯,您躺在病床上,病床像只无系的小船,在肆意的大海里漂泊,没有航线,也没有目的地,谁也不知它会飘向哪里,唯有那盏小灯在黑暗中延伸。您说您难受,您要坐起来,我和道源把您扶起,道源问您哪儿不舒服,您用手艰难地指了指您的腹部,您的病症已从食道转移到肝部,是肝腹水而胀痛。道源用手轻轻地抚摩您的背脊。您说您累,我们又扶着您,叫您躺下,您却茫茫地望着我们,问:“就躺在这儿?”
您每隔十多分钟要躺下又坐起,直到天明。查房的医生问我们您昨夜休息了没有。我们告诉他,您一夜没睡。医生又问您能不能吃点东西,道源说您什么都没有吃,只喝了几匙清水,也不知咽下去了没有。您又要坐起来,医生叫您把腿伸直,不要盘着,盘着腿血液不流畅,您不依,您无论是坐着,还是躺着,您总盘着双腿,您习惯了您的生活,您似乎已做好了归去的准备。
四
救护车载着您的身体,也载着您的病痛与灵魂,从上海至九华山这条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公路上,您没有驻足停息,您顽强地走过一程又一程。车进入九华山盘山公路时,远方传来几声隆隆的雷声,我们惊奇地看车窗外,只见天阔山明,一轮红日悠悠西沉。
您躺在祗园寺方丈室内,您的神情显得异样的安宁,医生要给您扎针,您轻轻摇头,让他走开,您知道您已不属于这个世界了,您已经听到了遥远的呼唤,您从哪里来?您要到哪儿去?您感觉您的床前总有好多的人,您不知道他们是谁,您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在您的世界里,一切是那样的恍惚,一切又是那样的清晰。
8月23日上午,风尘仆仆赶回来的圣辉法师刚到您床前,您突然
伸出手来,他赶紧握住您的手。您气息微弱,嚅动着双唇,却不能成声。“师父,您是不是想说99米地藏铜像?您放心吧!我们会完成您的心愿。”圣辉法师的声音有些哽咽,眼里强忍着泪水。您的手从圣辉法师手中滑落,脸上留着浅浅的笑,跟孩童一般天真。
五
远在新西兰念书的延续法师也赶了回来,在您出行的那一天,他却要我陪他到山里走走,我问他不参加您的追悼法会?他没回答,他转过身去,可我分明看到了他眼里闪动着泪水。我们避开前来悼念您的人们,落落地往山里走去。
他对我说他有好久没在山里走了,走着走着,他突然伸出双臂,做拥抱万物状,他专注而忘情,全然醉于山中。山青如黛,静然肃立,我心头不由地一震,这么多年,我一直被琐事所困,不曾好好看山,真有负于山的神韵。我对他说:“我虽生活在山里,却不知山的面目。”他说:“人爱山而无我,人无我才能与山相亲。”他像是在回答我,更像是自言自语。我顿感怅然,他却转过话题,说:“我们去钵盂峰看看。”
钵盂峰是99米地藏铜像的选址,1999年9月9日在此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庆典,此时只剩下一片荒凉,残破的山体,让人徒增伤悲,我怕他难过,我说回去吧,他却执意不肯,他对我说,他突然感觉到了您的存在,就在这里,他说在他的前方有您刚刚走过的足迹。他的话让我心动,让我心碎,我渴望见到您的足迹,可我又害怕见到您的足迹,我抬头看远方,这时,山谷中传来一阵唢呐声,回荡在钵盂峰上空,凄婉而悠长,像是在倾诉一个伤感的故事,又像是在表白一种亘古难变的心声。
释仁德:江苏泰州白马镇人。11岁随泰州太尉庵依松琴长老出家,1948年于南京古林寺授三坛大戒。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安徽省暨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住持地藏菩萨道场,祗园寺方丈。1990年创办“安徽省九华山佛学院”,任佛学院首任院长。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8月23日安祥示寂,世寿76岁。
藏学法师:1969年出生于湖北的一个乡村,20岁时,至九华山寻找出家多年的母亲,随母进入空门。同年,入九华山佛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迷恋文学、艺术。1996年,应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邀请,跟随仁德院长在新加坡举办了“九华山佛教学院历届学僧书画展”,此后,又跟随仁德院长出访了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地。1998年底开始散文创作,先后在《佛教文化》、《散文》、《美文》、《天涯》等杂志发表过文章。现任九华山佛学院副院长、天柱山三祖禅寺住持。
责任编辑陈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