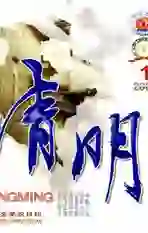连襟
2003-04-29凌可新
凌可新
1
朱世安和朱子才相好的时候还不是连襟。
那时候他们都还不大一点儿。不大一点儿的孩子都贪玩儿,就天天在一起玩儿。跑街窜巷的找年纪差不多的孩子打石头仗开火,打得你死我活的样子。要不就钻苇塘摸雀,堵水沟捉鱼。反正闲不住。夏天里常常是泥猴一样溜回家,断不了惹得家里大人骂,有时还得挨上几苕帚疙瘩。
朱世安别看人长得比朱子才大,胆儿却小,挨过骂就老老实实地舀几瓢凉水洗洗身子,打几下也憋着不哭不嚎。穷人家的孩子夏天里不穿衣服,出去磨的是自己的皮,回家挨打的是自己的肉。朱世安的娘敲过后摸着儿子鼓起的包又后悔,心想傻儿子咋就傻等着挨呢?
朱子才就不傻挨。进了家门见家里大人的脸色不对,撒起脚丫就往外跑。他娘就拎了一只苕帚疙瘩在后面撵,一边撵一边骂个不停。他娘是小脚,跑着的时候扭扭怩怩的,快不起来。朱子才的一对小腿倒是风快,转来转去就转到了朱世安家,回头见他娘也跟着转来了就往里一钻,躲进朱世安他娘的身后,嘴里一口一个二奶奶一口一个二奶奶地叫。这一叫朱世安的娘就过来劝朱子才的娘。劝来劝去朱子才就免了一顿皮肉之苦。黑天里回家早就把身子洗得干干净净的,跟个好人似的,大人的气也慢慢消了,想继续施展威风也没了充分的理由。要不就干脆睡在朱世安家。朱子才乖巧,叫罢二奶奶又叫小叔,挺讨人喜欢的。二天早上回家,大人就像是没有过那事一样。
总之朱子才没挨过几回大人的揍。
玩儿到八九岁,有点钱的人家的孩子都进草泊学堂念子日子日了。朱子才家里有十几亩地,算是有些钱的人家,不免也跟着去念了几声。朱世安就不行。他爹死得早,没撇下什么家产。家里就他和他娘两个相挨着过日子,三亩薄田刚好能糊了两张口度日月。他不想去。其实就是想去也去不了,早早就帮娘田里家里地做活。做来做去就把自己给做大了,身子骨也做结实了,才十五六岁就像条汉子了,力气也足足的,一拳差不多能打趴下一头牛。
朱子才念了三年半子日子日也念不下去了。他爹开头还算是本分,可当不得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的鼓动,这年冬里就到草泊赌场去赌。他是个什么水平,能玩儿得了人家那些个专业人才?一个冬天不到,就把家里的地输了个精光,差一点儿把老婆孩子都给输掉了。这么一弄,他就穷光蛋了一个,想死死不了,想活又活不好,就不让朱子才再去念什么鸡巴书,租了草泊当铺的几亩地,要他也下地刨食。朱子才做不来庄稼活计,一做就手脖子酸软,东倒西歪的。他人长得细细挑挑,像是一棵没发育好的豆芽菜。
不过他和朱世安还是相好。念书时疏了几年,没书念了又常找朱世安玩儿。白天胡乱做上几锄头,挡挡他爹的那双长满鸡屎的眼,夜来就和朱世安瞎掰些他听到的外面的乱事。掰晚了还是睡在人家炕上。常了就觉得自己家不好,很烦他爹那张狗屁股似的破脸。说是要是他爹不让鬼给迷了心窍,不去草泊冒充什么有钱的大爷,这会儿他就是上蓬莱念书也早就念过半本了,还用得着这么天天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朱世安听他埋怨到这里就插上句话说,“念书有啥好?”
朱子才说,“念书当然好了。”
朱世安说,“念书到底有啥好的?”
朱子才说,“你不懂。”
朱世安还是弄不明白念书到底有什么好的。书不就是在一些灰蒙蒙的纸上印着些鸡屎一样的字么?念和不念都当不得饭吃。等朱子才再说起念书来,他就又插上那么一句。叫朱子才也觉得他笨,这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了。
没出息的朱世安二十二岁那年冬天要成亲了。倒是有出息的朱子才还没有个媳妇的影儿。
2
朱世安娶媳妇的日子定在腊月初六。
腊月初六是朱世安的娘拎了两盒点心,求村里比较有名的读书先生三爷爷给定下的。是黄道吉日,最适合娶媳妇了。说是这一天娶的媳妇,能白头到老,两口子恩恩爱爱,子孙满堂,富贵平安。
成亲前朱世安娘儿俩一心一意地操办着这事儿。朱世安身强力壮的,知道有个媳妇儿的日子才能往好里过,他娘守了小半辈子的寡,总是想早早地抱上个孙子,过过当奶奶的瘾。这么着就把日子俭省着过,苦苦地攒巴。等约摸着攒得能娶回个媳妇时,他娘就开始张罗了。媒人给介绍的是二里半外的黄家庄的闺女,也是穷人家出身。亲订的还算顺当。订亲不到一年光景,这就往回娶了。
还没进腊月门儿,朱世安就照着娘的吩咐,去草泊集上买鱼呀肉呀菜呀的,买回来自个儿动手拾掇,一样一样,条理分明。小户人家的,娶个媳妇儿也不敢多么铺张,但必得有轿子的。他娘就叫朱世安去了一台二人花轿,还有四个吹手。临快到日子时又算计着请客的事情。那一天朱世安是新郎,穿新衣陪客人,不能端盘递碗,得找个把帮手做这事。
朱世安先就想到了朱子才。
这几天朱子才也过来玩儿。冬天没甚事就生了盆炭火烤手。见朱世安张罗着娶媳妇,朱子才就没眼儿地羡慕,又总想帮帮忙啥的。朱世安的娘也挺喜欢他,朱世安跟他一说就应了。朱子才听了脸上挺高兴的样子,说是小叔娶小婶儿,这个忙怎么说也该帮。
腊月初五阴天,一整天了也没出来个太阳。这天朱世安家也准备好了。又买了些红纸裁了,待要央人给写写喜字,一边的朱子才吃地一声笑了,说,“小叔要是不嫌我的字丑,我就给写了。省得求别人还得一份人情。”
朱世安瞅着朱子才说,“你会写?”
朱子才脸上还是那么着笑,“娶媳妇就写一个字,喜。小纸写单个的喜,大纸把两个喜并起来写就行了。喜和双喜,都不难的。念书时先生教我们写大仿,也写过这字。”
朱世安是一副不相信的表情,“这字可不是胡来的。要是丢条胳膊缺条腿的,人家来的客人里碰上个认得字的,那就让人笑破肚皮了。”
朱子才这时不笑了,“要不我先写出一个你看看。你看中了我就往下写。你要是看不中,再找人也不迟。”
朱世安想想也是,就把买回来的墨汁倒出一些在碗里,让了毛笔给朱子才。朱子才也没客气,铺开一张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红纸,把笔尖上蘸足了黑黑的墨汁,提起一口气,慢慢那笔就落到了纸上。手腕左来右去的,才放屁大一点时间,那纸上就出现了一个方方正正的黑字。
朱子才把提起来的那口气慢慢放下去,手也跟着一软,抬了眼问朱世安,“小叔你看看,是那个字不是?”
朱世安虽说不识字,可这喜字谁家娶媳妇都要往门上墙上贴的,见多了也就面熟几分。这会儿瞅着,的确是那个字。不光是那个字,竟还比村里常写这字的那个三爷爷写得还要周正些。他就面上一松,说,“成,是那个字。子才,那就劳动你给写写了。”
朱子才没再说别的。不过在写的时候想起了朱世安以前说过的话。他说念书有什么好。念过书和没念过书的就是不一样。这不就显露出来了?当然朱世安那脑子,这会儿肯定早就把说过的给忘到脖子后面了,要不
就在吃哪顿饭的时候当咸菜吃进肚子里又屙出去了。
朱子才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把所有的喜字都给写得方方正正。尤其那几个大双喜对子,更是写得像用模子刻出来似的。
这大双喜对子是预备初六早起封大门的。小喜字则要从家门口一直贴到村子外面,相当于引路的标志。到时候认识家门和不认识家门的客人,都能跟着这些小喜字找到喝喜酒的地方。
傍黑天朱世安一家一家撒了帖,都是要请的亲戚本家。又特意叫朱子才明天早半个时辰过来,好和他一起去贴小喜字。朱子才没口地应允了。朱世安留他一起吃顿饭,朱子才没吃,说是快些回去睡上一觉,好弄足了精神。
“等明天你娶回小婶儿时,我再好好吃上一回。”
朱子才这么一说,朱世安就不好再留了。
一夜无话。第二天娘儿俩早早起身下炕,点燃了两盏麻油灯和一对小儿手腕粗细的红烛,把三间已经收拾好了的屋子映照得亮亮堂堂,真像是个要往回娶媳妇的样子。朱世安呵着白气打开门,却见天和地一片的纯白,回头说,“娘啊,外面下雪了呢!有几多厚了。”
他娘也走到门口往外看,果然是下雪了,就说,“下吧下吧。下雪天吉利。能白头到老呢你们!”
朱世安听着有理,也觉得下雪好。老人们会说瑞雪兆丰年,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心疼他还没过门的媳妇儿得在雪里过一遭了。
没过上一会儿,朱子才就踩着白扑扑的雪过来了。朱世安见他的两只眼睛都红红的,就问,“你眼这是咋了?”
朱子才开始不说,朱世安又问了一回才说,“我是怕起来晚了,误了事,一宿没敢闭眼。”
朱世安就很感动的样子,忙舀了一碗热水叫他喝。
喝了几口朱子才就自己夹了一摞小喜字,端了只盛满糨糊的碗出去贴了。朱世安要和他一起去,朱子才不让,说是这一天里新郎得有个新郎的样子,他自己也一样贴得完的。
回来时朱子才就一身白白的雪,脸冻得通红,鼻尖像是成了冰,都没有颜色了。朱世安给他拍打掉身上的雪,要他坐炕上暖和暖和,搁火盆里烤烤手。他不,又忙这忙那的不闲着。
忙着忙着订下的轿子来了,吹手也腋下夹了吹打的家什来了。进了屋领头的就要朱世安把钱再加加,说这样的天都得加加的。冰天雪地,不加就不好做了。讲讲好了加半块银元,他们才坐下吃些饭菜喝盅烧酒动身抬人去。
朱世安说,“子才,你领着轿子去抬你小婶吧。我不好去,昨个黑里跟我娘商量了,还得叫你吃趟苦。不好说,谁叫咱俩相好的呢?”
朱子才往门外望了几眼,说声行,就领着轿夫和吹手们出了门。
朱世安他娘说,“子才跟你,真像是一对亲兄弟。”
朱世安说,“可不是么。”
他娘又说,“可惜比你小一辈儿,算来算去还是个侄子。”
朱世安就不吱声儿了。
很快天亮了。朱世安走出家门,走进白扑扑的雪里去。雪花纷纷扬扬,一片一片的都挺铺张,也都带着一些喜气。村里的街道上这时还没有别人,朱世安顺了贴着小喜字的街走到村头,向东南黄家庄方向张望。一里半地外有一个土岭。过了土岭就是黄家庄了,就是他媳妇的村子了。这一望远远近近都是那么白白的一片,很能开阔人的心。过不上一会儿他媳妇就得让人给抬着从岭上的那条小道下来了,就得抬进他的屋子里了,那也就成他的人了。这么一想朱世安忽然有些羞,像做了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悄悄循了街回屋猫了起来。
听见岭上传过来一阵吹手日弄出来的声音,朱世安又让前来看热闹的人披红挂绿地簇拥到村头。望见一顶红红的小轿在雪白的岭上逶迤,朱世安的心就别别直跳,眼也有些花里胡哨起来。他想逃回去,可那些看热闹的怎么也不容他,把他给推到最前面,说是你娶媳妇,咋个好不出头露面呢?朱世安也只好一手按着胸口,让自己平静下来了。
把花轿远远地迎到门口,几挂鞭炮就脆脆地响起在雪里,吹手们的手艺也响成一片。轿子落下,朱世安才看见了跟在后面的朱子才,就冲他笑笑。朱子才也笑,只是笑得有几分怪。不过朱世安没在意,在别人的强迫下,把媳妇驮在背上,一口气驮进屋,小心翼翼地放到炕上,直了腰瞅。新媳妇蒙块红盖头,看不见脸面。光听别人说俊俊俊的,又不能立马掀了盖头看个虚实。心里就急急庠庠的,想,这块破布真碍事。
一个白天朱世安的心思都在新媳妇一人身上。直恨这天还不快快地黑下来。一黑下来他就会知道自己的媳妇儿到底长个什么样子了。
好不容易熬到夜来,偏偏又有好些人在洞房里嘻嘻哈哈着闹新媳妇儿。见朱世安从外面进来,就毫不客气地再把他给轰出去。出到大门外却看见朱子才一个人在雪地里站着。
朱世安有些奇怪,问他,“咋了子才?”
朱子才笑笑说,“不咋了。”
朱世安说,“进屋去坐坐吧。累了你一天了。”
朱子才说,“不进了吧。里面人多,外面凉快。”
两个人就站在雪里说几句话,有一搭无一搭的,像是都在有意地消磨时间,过了一会儿闹洞房的三三五五地出来了,把地上的雪踩得吱吱作响。朱子才也道了声别回自己的家去了。不知怎么,他脚下的雪不响,朱世安没听见声音。
朱世安用眼睛把朱子才给送到了一个拐弯处。朱子才一闪,就没有了。
估计人走得差不多了,朱世安就忙忙地进了屋,见新媳妇坐在喜炕的中央,头上还蒙着那块红布。就剩下娘一个在一边守着。朱世安想,这块布也不知让人给揭过多少回呢。那些闹房的,手下一点也不会留情。想,真是亏了,自己的媳妇没捞着先瞅瞅,倒是让别人看了个够。又想,到底俊不俊呢?
他娘见他进来了,就下了炕到另一间屋子里歇息着了,留洞房给一对新人使用。娘的脚刚离开,朱世安就忙不迭地闩上门,伸手就去揭那块红布。揭开就着亮亮的烛光一瞅,果然是俊。细细弯弯的眉儿,黑黑油油的发儿,红红小小的嘴唇,白白嫩嫩的脸蛋儿,身子结结实实,果然是好。想想自己这么个家里没有几亩田地的人,能娶回这么俊个媳妇儿屋里守着,朱世安就像是连灌了半斤老白干儿,眼睛都有些直了。
这新媳妇儿在炕上坐了一个白天加上半个夜晚,心里也在时时地惦念着自己男人的模样儿。往屋里炕上背时觉得这人怪有力气的,就想不会差到哪里去。可丑不丑的,光从力气上看不出来。她是担心男人会丑了。要是个丑男人就没劲了。这会儿叫人揭了红盖头,偷偷地一瞅,是个浓眉大眼的汉子,个子也不矮,样子不光不丑,还有几分英俊呢!就放下了心,低了头吃吃地笑。
她这一笑,使朱世安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儿都跟着酥了个透,再也顾不得脸皮薄薄什么的,把嘴鼓起,憋足一口气,对准那一对站在柜上跳跳跃跃的红烛,猛地一吹,噗地一声,屋里立刻就变得漆黑一团了。
新媳妇呀了一声,像是受到了突然的惊吓。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声音了。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又啊呀了一声,有什么跑进了她
的心里似的。
3
朱子才想,我是叫朱世安给害苦了。他不该叫我给他押轿。
朱世安叫朱子才给他押轿去的那会儿,朱子才愣了愣。倒不是害怕外面的雪下得大,路不好走,他是奇怪事先朱世安咋不打个招呼,不早些跟他说。当然奇怪归奇怪,他还是二话没说,一猫腰,就领着轿夫和吹手钻进雪里。
地上的雪还不很深,能有一尺半吧,走上去有着一种比较特别的感觉。这么走着,好像娶媳妇的不是朱世安,而是他朱子才了。待上了岭望见雪里的黄家庄了,朱子才就想,都说小婶俊呀俊呀的,可不知是怎么个俊法。这下就能先瞅上一眼了,看看朱世安福气大不大。
再俊,总不会比天仙还俊吧?
天仙朱子才没见过,不过村里人都把最俊的女孩子叫做天仙了。
下了岭就是黄家庄。人还没进村就有人迎了过来,领着一行人轿入了村。七转八转的,转到一幢旧屋前,那人说声到了,轿夫就把轿子搁门口一竖,人进屋暖暖手脚。吹手里就有人忽地吹弄了一下家什,一惊一炸的,惹得人都笑。朱子才也笑,拱拱手跟人家客套几句,吊几行从学堂里拎来的酸文字装点门面。子日子日的,终于又有了一回用武之地。
屋里窄窄巴巴的,人也甭想躲着个人。进了屋朱子才就拿一双豆荚眼瞄来瞄去的,企图看看小婶儿的模样。
先一眼见了一个姑娘家的身子苗苗条条地在外屋忙活。这姑娘大概也就是十五六岁的样子,头发蓬蓬松松地梳成一条独独的大辫子,乌油油地在后背上晃。辫梢还扎了根红头绳。额上是齐齐整整的刘海儿。她的脸蛋儿圆里略长,红口白牙,一笑两酒窝,是十分地招惹人的长相。
这模样叫朱子才倒吸了一口凉气在肚子里转悠,转来转去也找不到出来的地方。想不到连天下最大的字都不识一个,只知道出力气的朱世安竟会有这么大的福气。有这么一个媳妇儿,就是一辈子给她当牛做马也值了。忽然想到他自己,和朱世安年龄不差上下,小也只小了半岁不到,却是连个媳妇的影儿也没有,不由心里一酸,差点就流下些眼泪来。
正胡思乱想着,忽听耳边的她唤了声姐,里屋跟着就有一个女的应了声。她冲着里屋说,“姐啊,人家的轿子都停在门口好半天啦。冰雪天,你还好意思磨蹭呐!”里屋的不说话,她就伸手挑开粗布做的门帘,身子闪闪地进去了。
朱世安的丈人迎了人进屋就忙忙着张罗。递一支卷巴好的旱烟给朱子才吸,朱子才竟忘了接。他的一对眼睛紧紧盯着里屋的门不放。他当然看不到里面,满眼都是布门帘的花色。门帘是旧的,花色也陈旧了好些,可朱子才的心情一下子明亮了许多,跟云开日出了似的。
原来这女子不是小婶,不是朱世安的媳妇儿,是小婶的妹妹,是小叔朱世安的小姨子。朱子才心里一明亮,就暗暗地松了一口气,端起一碗放了糖的热水也喝得出甜味,吸一口旱烟也品得出那辣来。不过他那眼还是紧紧地停留在门帘上,一心一意等着她再出来。
再出来她就陪了姐。姐款款地走,像是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她走的就俏皮,跟还没完全长大的孩子似的。朱子才望着她,这时早就忘记看小婶的丑俊了。仿佛那已与他毫不相干。而他来这里,为的就是看她一样。
见朱子才一副痴痴的表情,她忍不住噗哧地一声笑了。这一笑,朱子才的心就杂乱无章地胡跳了一通,慌慌张张地低下头,不敢再看了。
不敢再看,心里却还是紧紧地想着人家。
新媳妇打扮整齐,蒙了红盖头,由她和她的娘扶着入了轿。两名轿夫起轿,吹手们把各自的手艺亮出来,朱子才这才不得已押了轿子走。走一步一回头,走一步一回头的。上了岭看不见什么了还是回头。
他叫一个小姑娘给唬住了。他把自己的魂儿丢了一大半在她身上。
有两个字这时突如其来地进入了他的脑子。连襟。是这两个字。里面他虽然也只会写一个连字,可它们连到一起后,一下子就把他的整个脑子全给塞满了。
一路上他就只是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两个字。一个白天都是想。见了朱世安的面就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不敢和他直直地对眼神儿。有时还躲开人的影子,去想那个有着一条长长辫子的女子,朱世安的小姨子。
黑夜里从朱世安家回到自己的家,躺在冷冰冰的炕上,朱子才一宿没睡着。心里装着一个人,他怎么能睡着呢?翻一个身再翻一个身,像是在烙饼,又像是身上什么地方在疼。
第二天早上朱子才就觉得身子有些发软,头也有些发烧,好像是生病了。朱子才起了几起又躺回去。他想,我是叫朱世安给害苦了,硬是叫他给害苦了。他望着灰暗陈旧的屋顶出神。
家里人都不知道他这是咋了,问他他也不说。问烦了他就把一双眼给红起来,像是要把谁给一口吃掉一样。吓得谁也不敢问了。
4
好日子过起来飞快,跟不光长着腿脚,又一下子生出一对翅膀似的。连跑带飞着,这才一眨眼,就到了春上。
这一个冬天,自从成了亲娶回了媳妇儿,朱世安就没出过几回门,天天在家里守着媳妇儿。他媳妇叫喜俊,姓一个黄字。名儿起得好,人也长得俊,脾气更不用说了。朱世安和他娘都喜欢她,宠着她,不要她做什么家务。她不,争着抢着做。做起来手脚也麻利。
过了正月十五,地慢慢开始化冻了,朱世安把在岭上自己家的半亩春地送上几车粪,吭吭哧哧着刨了。预备过些日子栽几台子地瓜,再种上些花生。地瓜是农家冬天的口粮,花生换了油,也是一家人一年的油水。这两样都少不了。
朱世安到岭上千活,喜俊也跟着来。刨地两个人一人一张三齿镢,肩并了肩刨。朱世安一次刨快三尺宽,喜俊力气小,就只有刨一尺半才能跟得上。朱世安不让她做这力气活儿,怕累坏了她,可又挡不住,只好在刨的时候时不时地帮她几下。这样白天一齐干活,夜里睡一铺炕,日子过得也蛮有滋味儿的。
他们上山干活时常碰见朱子才。这一个冬天朱子才瘦了不少,人就更像一棵豆芽菜了,眼圈还是有点儿青。见了面跟他打招呼,他总是弄出着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喜俊一跟他说话他的脸就红。私下里喜俊跟朱世安说,“你这个大侄儿还挺腼腆呢。你说他像不像个大姑娘?”
朱世安说,“不知这是咋了。过去他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过后朱世安也想这是咋个了?他不知道朱子才心里老想和他连一回襟,想把喜俊的妹妹弄成自己的媳妇儿。岔开这个理由,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头绪,朱世安就不想了。
有一回朱世安一个人在岭上做活,朱子才就慢腾腾着走过来。朱世安把手里的家什一丢,两个人就搁地头坐着。岭不是很高,说起来也就是一个大土堆。坐在顶上往这边能望见他们的村子,往那边能望见黄家庄。都不远不近着的,像是一个人挑着的一对水桶。
坐了一会儿朱子才说,“不知咋,过去上你家就像是回自己的家,脑子里不用想,抬脚就去了。这会儿得盘算老半天。”
朱世安说,“我也说是你不常去了。我家那门坎又没往高里长,人还是那些人,面生了咋的。”
朱子才笑笑,“不知是咋。”
朱世安说,“当咱们打光屁股那会儿就相好着。以后你常来。咱们过去还不是跟一家子似的。”
朱子才想了想,问,“你还当咱们跟一家似的?”
朱世安想都没想,说,“可不是。”
打那起朱子才又去坐了。白天田地里忙就夜里去坐坐,随便说些话。不到很晚就回去。那晚朱世安送到门口,朱子才住了脚步,说,“你没看出来这些天我心里装着些啥?”
朱世安的心猛地一跳荡,“你心里装着啥?”
朱子才又不说了。黑黑里朱世安看不清朱子才的脸。可他真怕他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
停了停朱子才才说,“那天你真不该叫我去给你押轿。”
朱世安问,“押轿咋了?”
朱子才又不说了,两条胳膊垂着,一个人在黑黑里走远去,把个朱世安给闪在了那里,一头雾水。
回了屋躺在媳妇身边。屋里也黑黑着,糊纸的窗户透不进一点星光。朱世安想睡却睡不着。翻个身睡不着,再翻个身还是睡不着,跟身上生满了虱子似的。喜俊说,“你咋了这是?”
朱世安嗡声嗡气说,“不咋了。”
“不咋了又咋了?”
“我就觉得子才跟过去不一样了。今天黑里我出去送他,他跟我说他心里装着个啥。”
喜俊不以为然着说,“人家大小伙子一个了,有二十一二了吧?还不兴有个心思啥的?人是人,又不是根木头。”
朱世安忽地把自己坐起来,酸溜溜地说,“不是这回事。他还说咱成亲那天不该叫他押轿去。”
喜俊听了,也吓了一跳,不知道朱子才是什么意思。难道……难道他也看上了自己?她不敢再往下想,脸面热热胀胀着,黑黑里不敢说话,只拿眼睛瞅着糊着白纸的格子窗户。
久久朱世安才说,“我寻思着得弄个明白。别叫他钻了牛角尖出不来。到头来也不知会害了谁。”
喜俊也说,“是得问问。他可别是那么一种人。”
那么一种人是哪么一种人,不用说也都知道。
两个人一夜都没睡好,各自怀着一个鬼胎。二天见了朱子才,朱世安就说,“子才,你心里有啥你就直说。就是说过了头我也不会怪你个啥。”
朱子才瘦瘦的脸上是古怪的表情,一对不大的豆荚眼定定看着朱世安。看了半天摇摇头,“不说吧。说了也是白说。”
朱世安有些发急,说,“你说。别焖我了子才。我这人心粗,抗不住焖。”
朱子才说,“我说了,你可不能怪我。”
“怪啥怪。不怪。”
“那回我给你押轿……”说了半句朱子才又闭了口不说。
朱世安咬咬牙问,“你也看上了她,对不对?”
朱子才点点头,“我寻思着咱俩能扯上个连襟最好了。”
这一句话叫朱世安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原来他担惊受怕的全然不是。不过朱子才的想法也稀里古怪。他知道喜俊有个妹妹,也见过几回面,长得跟喜俊各有千秋。但这话他不好说去。望着朱子才那副古怪的样子,朱世安想了想才说,“要不,等我叫喜俊回她娘家问问吧。”
回家跟媳妇说了,喜俊也松了一口气,说,“是这么一回事儿呀。那天你咋叫他给押轿?”
朱世安说,“咱这儿不是不兴新郎押轿么,我又没个亲兄弟帮这忙。再说我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儿。”
“子才是你侄儿,要是我妹妹嫁了他,不得跟着他一块叫我小婶儿啦?一叫,辈儿就乱了套。这事儿可犯不得。”
“子才这人不错。就是他那爹差些成色。日子么,过还是过自个儿的,他爹能跟他几年?可这辈儿又不好乱了。难呢。不过得了空你回去给问问吧。兴许你爹他一高兴就应了呢。”
过几天喜俊真的就回去给问了。回来脸上一片愁苦的样子,跟朱世安说,“还是不行。我爹就两个闺女。他说俩闺女嫁一个村庄不好看。又说是什么远了香近了臭的。这还差了一辈儿,应不得。”
朱世安说,“一点门儿都没有?”
喜俊说,“想吧。”
朱世安就找朱子才去。朱子才正躺在炕上,瞅屋顶吊下来的灰串儿。见了朱世安进来也没做出什么表示来。朱世安说,“子才你咋了?”
朱子才说,“不咋了,头有些发烧。”
朱世安就坐到炕边上,停了停把喜俊捎回来的话说了一遍。
朱子才说,“我就知道说了也是白说。”
朱世安说,“子才,你也别上火。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要是我能做得了这个主,还不就成了。”
朱子才笑笑,“话还不是这么说。”
朱世安劝他,“这天底下的好女人多得是,也不在一个上面。”
朱子才说,“话还不是这么说。”
话不投机,朱世安也不好再说什么。胡乱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几句别的,就起身走了。
从那天起朱子才又不来朱世安家坐了。朱世安想,一来是忙了,田地里有的是活儿要做,不得空闲;二来子才他脸皮儿薄,有些过不去。停些日子还会来的。相好了十几年,不信会因了这就不来了。
可是好长时间也不见朱子才的影儿,田地里村子里都不见。到他家里问问,他爹说他当兵去了。朱世安一时呆在那里。他不知道朱子才为什么要去当个兵。都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他是不是不拿自己当个好男人了?再说时逢乱世,弄不好还得和谁谁打上几仗,一般的人遇上这事儿躲还来不及呢,谁又肯自己送上门去呢?
5
刚收拾罢了秋,朱子才果然穿了一身军装挎了一把匣子枪回来了。他身子瘦瘦的,穿上这一身黄衣裳还挺提神儿。不仔细着看,没几个能认出是他来。而且他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回来的。那车子有七八成新,村里再没有第二辆了。给人的感觉是风风光光着的。
朱子才进了庄没回自己的家。他推着自行车,在街道上三转两转的,就转到了朱世安那里。
正好朱世安在门口收拾玉米秸子,要垛成个垛子,见了面挺高兴,把手里的活计一放,说:“子才,你回来啦。”
朱子才把车子支起来,伸手弹了弹军装上看不见的灰尘,说,“刚回。这不,先来看看你。”
朱世安说,“走,进屋扯吧。”
进了屋朱子才从怀里掏出一盒白皮儿上下一般粗细的烟卷,弄出一支给朱世安抽。他自己也点上支抽。抽了几口见喜俊腆着个大肚子进来,朱子才就问,“小婶儿快生了吧这是?”
这烟很好抽,朱世安猛抽了几口才说,“早呢。得过了大年。”把一口烟雾慢慢吐出去,又问,“子才,你真当兵了呀?”
朱子才笑笑,“不当兵做啥。总得混个出路,好娶一房媳妇呀。”
朱世安听出他那话里的口气,不好说什么,就岔下了话头,“你这一出去,当的啥兵?”
“救国军。”
朱世安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以前有这么个军没有。光知道这地面上有八路九路的,再还听说有中央军。就问,“打小日本儿不打?”
朱子才伸手摆弄着匣子枪把手上的一绺
黄缨须,脸上古古怪怪地说,“打日本做啥,日本人又不坏,都规规矩矩着在城里住着,见了人都笑眯眯的,还掏出些糖给小孩子吃。”
往下都没有什么话说,场面上仿佛弄得挺尴尬。喜俊烧了两碗热水,递一碗给朱子才。朱子才搁手里瞅瞅碗边上的那一圈黑印,用嘴唇沾沾就放下了。他没喝里面的水。
临走朱子才说,“家里要是有啥活计就快些忙忙吧。只怕是过几日就不得清闲了。”
“咋了?”
“不咋。过几天就知道了。”
朱子才走后朱世安猜不出过几日咋个就不得清闲了。怪他不把话给说完了再走,外面放一半,怀里掖一半。就跟喜俊说,“他说他不打小日本儿。都这世道了,不打小日本儿叫啥的救国军?”
喜俊说,“就是。还不如当个胡子呢。胡子要是碰上了小日本,也敢照着他们放几枪。巧了还能打死个把的呢。”
朱世安也知道南边山区里有胡子,听说还去蓬莱县城搅闹过小日本的好事儿。喜俊这儿一说,他心里就有些瞧不起朱子才,觉得一个大男人的,当这种兵才没个出息呢。就是挎把匣子枪在屁股后面丢当着也还是没个出息。就庆幸幸亏没叫他给套上个连襟。
6
过了几日果然就不得清闲了。日本人来岭上修什么炮楼子,把周围十里八村的男劳力都弄了去。朱世安当然也让弄了去。日本人光管饭不给工钱。吃白面馍。吃了几天改成二道面的。还有肉吃。白花花的肥肉一个劲儿地肥,一咬一呲油。好些人都觉得不吃亏。就是改成三道面的馍也不吃亏。从蓬莱城里下来的日本人脸面上和朱子才说的那样,都那么笑眯眯的。他们经常伸了手去拍劳力们的肩,嘴里说些鬼也听不懂的鸟语。朱世安也叫一个小个子日本人用只粗短的胖手给拍了一回,感觉很不舒服。那块地方连着几天老是痒痒,像是那么一拍,给拍得生出来了一块牛皮癣。
从蓬莱城里下来的不光是七八个日本兵,朱子才也在。朱子才领了二十来个骑自行车的救国军来当监工。这些个救国军也都挎枪装弹的,威风自是不必说。来了不几日朱子才就升了朱世安一个小工头,还叫朱世安的丈人也做了小工头。小工头不用下死力气干活,背着个手溜达着腿儿,嘴里吆喝着别让人偷懒耍滑就行。不光这样,每四天还有一块光洋好拿。朱子才说他认识字,一去城里就升了小队长,这会儿已是副中队长了。将来炮楼子修好了日本人不一定能来,估计着还得让他领人守着。守家在地的,不图别的,就为了防止八路和山沟里的胡子来祸害老百姓,让家乡的父老能过上个平安日子。
朱世安没见过八路九路的,不知道八路怎么个祸害老百姓法。不过胡子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倒是常听说过。当然了,在这有几百号人的工地上,有朱子才这般照顾着,朱世安心里也挺受用的。
朱子才的脸在这里就大得不得了。他没啥事操心,得空就往黄家庄转悠。这岭离黄家庄才一里地不到的样子,跨上自行车顺着道儿,放个屁的工夫就到了。朱子才脑瓜快记性好,转了几回就转到朱世安丈人家里去了。
朱世安的丈人就俩闺女,没儿。有时朱子才去家里是娘儿俩。朱子才就装做是渴了讨碗水喝,表现得还挺正经的,连头上的那顶黄帽子都戴得端端正正,衣服上的扣子更是都系严实了。这么看上去,还真是个正经军人的形象。
有一回只有朱世安的小姨子一个人在家。进了门朱子才一下子就放松了,脸上不用弄就自然地亮出一层笑来。他站在朱世安的小姨子面前,咽了一口什么才说,“知道吧你。这会儿我不是以前的我了。”
朱世安的小姨子名叫喜梅,见过朱子才几回,也不怕他,叫他坐椅子上,拿装盛了旱烟的烟笸箩给他押。他不要,从怀里摸出自己的白皮烟,点上吸,一吸一股烟一吸一股烟,看着比旱烟冒出来的好。
喜梅哧哧着一笑,说,“怎么个是不是以前的你了?我瞅着就外面的一套衣服不是以前的。”
朱子才也笑,“不跟你说明了你以为我是蒙你。在工地上,你爹黄国仁的工头是我给升的。你姐夫也是。在这里,连人生地不熟的日本人也得听我的。我说升谁就升谁。”
喜梅就说,“谁叫你和我姐夫相好。不升他升谁。”
朱子才鼻孔里冒着两股发蓝发白的烟,冒到了头顶就慢慢形成了一片景色。他故意不去看喜梅,眼睛一斜斜到上面,说,“我可不是因了这个。”
“不因这,那因了啥?”
“那回来抬你姐,是我押的轿。大雪扑扑的日子,你记了吗?”
“怎么记不了?那回你个掉了魂儿的样子,一双眼睛都不知往哪儿搁放了。这会儿想着,也真是叫人好笑呢。”
“还有一回你姐回来跟你爹妈两个商量了啥事没有?”
这一句话说得喜梅一张俏脸红到了脖子处。她抬手打了朱子才一下说,“我就知道你来是没安了个好心。”
朱子才趁机抓住了她的手,把她硬往怀里扯。喜梅力气小,很快就叫朱子才给抱住了。朱子才很得意,盯着喜梅好看的脸蛋说,“谁叫你姐夫叫我押轿,谁叫那天你对我吃吃着笑。我非娶了你不可。”
“我姐夫他不会依你。”
“这阵子我还怕他?”
本来喜梅对朱子才就没有多少坏印象,想想这阵子他确实不会怕谁。他屁股上吊着枪,腿裆里跨着自行车不说,还有胆量,光天化日的,竟敢一抱就抱住了她,还不肯松手。她就红着一张粉脸不吱声儿了,故意扭怩了一下,由着他啃咬够了才罢。
过了几天朱子才就找了个媒人来黄家说媒,说是他看上了喜梅,要娶她回家做媳妇。这媒人不用说是三里五村最能说会道的,而朱子才也不是个一般的人。朱世安的丈人黄国仁自然就拿不定主意,问喜梅,喜梅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就是把一张脸给弄得红红着,像是早已和朱子才好过了一样。黄国仁就找了朱世安来商量。
朱世安想了半天也很是犯难。他倒不是怕谁不怕谁。不过朱子才想这事儿不是一天半天了,回绝了显然他是不会甘心的。等炮楼子修盖了他就住在这儿,他手里有枪有炮的,说不上就会弄出什么不好看的事儿来。到那时后悔也晚了。
这天傍晚收工时朱世安跟朱子才说,“子才,你是真心要娶了喜梅?”
朱子才说,“狗才不是真心。”
朱世安说,“以前咱们相好,以后的日子还没来,不知道会是啥样子的。要是你能保证不做坏事,我就不管差辈不差辈儿子,替他们应下来这门亲。我想了好半天,就这话。”
在西边还红着的夕阳里,朱子才的脸上又有了古怪的表情。他望了朱世安一阵子,说,“算了吧,我不用你替他们家应。你不是说过你说了不算?这事儿你也真说了不算。我也不向你保证什么坏事好事的。不信我就娶不上她。”
朱世安有些生气,说,“那你娶去。”就走掉了。过后想想不对头,夜里跟媳妇说,喜俊也拿不出个什么章程来,光知道叹气。
转天朱子才就撤了朱世安的工头职务,叫朱世安跟别人一起出苦力,意思是好好打磨打磨他,让他知道知道土地爷爷的鸡巴是
石头刻出来的,不是尿泥捏的。朱世安咬着牙不肯服输。不服归不服,还是得眼睁睁地看着朱子才把聘礼派派场场地送到了他丈人黄国仁家,把亲事给定下了。
冬天刚刚到,朱子才就娶回了媳妇。成亲那天把场面弄得挺大的,比朱世安那回大了不止几个来回。头一天朱子才打发人给朱世安送了请帖,请他去喝喜酒。朱世安心头的弯儿转不过来,一赌气没去,也没上岭上搬石头,就躺在家里守着媳妇儿望屋顶发愣。
喜俊是个大肚子,这样的场合当然不敢露面,怕冲了人家的喜。朱世安不去,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说不过去就不说。
下回碰见朱子才,朱子才的脸色就很不好,古怪里透出些青来。也不和朱世安打招呼,只把一支匣子枪外面的木头板套弄出几声脆响来,像是要立马拔出里面的真家伙给人一下似的。朱世安不由觉得自己的头皮冷嗖嗖的,心想不如当初什么都应允了。反正小姨子又不是自己的,给谁不是给,连谁不是连。
7
娶了亲的朱子才黑里就不出门了。白天上岭上工地反背了手溜达,指挥手下的好好看着做工的,别出了漏子让日本人不高兴,回屋就把枪摘下来顶上火压到枕头底下,腾出手脚和喜梅打打闹闹,早早就搂着喜梅的光身子睡觉,做些男人和女人间常做的那种事情。
有时候半夜睡醒过来,听着身边媳妇喜梅匀称的呼吸,感受着一团温热,朱子才就胡思乱想一通。想想他羡慕朱世安那阵子,心里急急痒痒的有劲儿没地场使唤,天天黑里瞅着屋顶,瞅瞅就伤心伤情的,只差没拔根毛上吊了。这会儿就比朱世安强。当初朱世安可是凑了黑瞎摸的媳妇儿,凭的是个命,万一是个瘸子瞎子麻子脸呢?那还不得死守着这一世,不开心着这一世?自己就不一样,是先看中了意先迷了魂,再使法子娶了回家。这就不瞎。朱世安不是说念书有啥好的么?念了书识文断字就是有用。不瞎。就在心里笑话朱世安,笑他没个出息,连个小工头也当不长远。
想过了就鼓捣醒喜梅,要她和他再好一回。
两口子干柴烈火样,过得还恩爱。冬天天冷,炮楼子工地上的活儿基本上停下来了。有救国军的兄弟和各村分派的人看守着,朱子才就没多少事可做。逢上草泊赶集朱子才就骑自行车带喜梅去。道路不是很好走,车子摇摇摆摆着就很是招摇。救国军的车子都在岭上,喜梅看看满集人多的是,可这么好的自行车却没二辆,就很知足,脸上总是一片笑意盎然着,觉得十分光彩。
嫁给个手里捏着枪的人,当然是十分光彩的事情了。
就是一条不好,朱子才不让她时不时地上朱世安家去。那天朱子才没事,在灯下瞅着喜梅,剔着牙缝里的肉丝说,“别看朱世安表皮厚道,跟个好人似的,里面可没啥好下水。”
喜梅笑着撇一下嘴,说,“你们可是连襟呐。俗话说连襟连襟,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呀。”
朱子才心里有些酸溜,“什么连襟不连襟的。你不听人家说什么小姨子是姐夫的半个屁股这话吗?他不愿你嫁我,他是想自己留着用吧。”
喜梅听了这话脸上就臊,就用一对不大的拳头捶他,又顺嘴骂他,说人家正经着哩,可不是那样的人。过后却也不敢随便去了。就是偶尔去坐坐也不敢让朱子才知道了,怕他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朱子才和朱世安的关系一时弄得很僵。正月初一早起朱子才也不上朱世安家拜年,初三上丈人家见了朱世安的面也不说话。中午喝酒就呕气。朱子才不给朱世安敬酒,朱世安也不给朱子才敬酒。在酒桌上朱子才想,要是朱世安不又臭又硬,跟个茅坑里呆了一百年的石头似的,肯说个软和话,看在相好了十几年的份儿上,也就不计较了。可朱世安就板着张黑脸,跟是朱子才欠了他什么一样。朱子才看他一副没打磨好的模样就生气,心想还是得继续打磨他,像玩弄麦芽糖那么,直到弄软了他才算完。
也是活该有事。这大正月的才过去了一半儿,有一天晚上几个救国军的兄弟来敲朱子才的门。朱子才开始以为是来了八路,要敲他的脑袋呢,待拎了压足了火的枪出去,才知道是他手下的发现一个人影偷偷摸摸进了朱世安家的门。黑灯瞎火里进入门的,定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朱子才二话没说,带人就破门而入。果然逮了个陌生面孔的男人。拉回去三审六问,这人还不承认他是八路,硬着嘴巴说他是讨口饭才去的,没做别的勾当。
逮了个八路兄弟们都十分振奋,磨拳擦掌,要求把朱世安也一起抓了来。朱子才寻思着治治他也好,不过自己不好出面,就让手下的连夜抓了朱世安关起来,自己回家睡觉。
回家喜梅问他做什么去了,黑灯瞎火的,弄得个人也冰凉。朱子才说逮了个八路,“你猜在谁家逮的?朱世安!”
一句话说得喜梅没了睡意,爬起来急着问,“姐夫呢?”
朱子才一脸的得意,说,“也逮了。眼见他茅坑石头,看他再往哪里臭硬。这下摊上事儿了吧?”
喜梅说她姐眼看要生了,别这么太凶,要朱子才放他一马。朱子才不依,说当初我叫你给迷得都快上吊了他咋不放我一马?喜梅说你还不是如意了?把人家睡也给睡成陈年旧事了。朱子才笑笑,说,“我如意是靠我自个儿。我能睡了你也是我自己的手段。他又没帮我啥忙。他要是有本事也靠自己洗清了身子。”就躺下把脸往边上一侧,睡了。
不道喜梅一夜没睡好,二天早上起来先上姐姐家看。姐姐和她婆婆两个都坐在炕上一把一把地抹眼泪,抹一把往地上甩一把,地都给甩成湿的了。见了喜梅进来也不敢说是朱子才不好,异口同声地说那八路不是个东西。说一个村子百十户人家,大门小户的都有,明窗亮瓦的也有,去哪家讨吃的不好,偏偏来这家。这倒好,给惹出事来了。
喜梅听了也流出来几颗眼泪,说,“来了就来了。那人的腿脚长在他自个儿下面。谁也不知道会有这事儿。子才和姐夫相好了十几年,又是连襟,不信他能把姐夫给咋样了。”
话是这么说出来,可连喜梅也弄不准这事儿到底会咋个样了结。
摊上八路,事儿就不会是个一般的事儿。这一点谁都清楚。
8
想想朱世安也挺冤枉的。
那天黑里吃过晚饭,他和往常一样着出去闩门,抬眼见门外站着一个人的影子。这人见了他就开口叫了声大哥,说是在家乡过不下去了,上烟台寻工做。走到这儿,有一天水米没沾上牙了,想讨一点口,充充肚子。朱世安心好,也没往深处想,就让他进屋了。
这人有三十来岁的样子,外表很是有几分不俗,脸也是方正的,眉毛也粗,嘴唇也厚,不像是个给人惹事的坏人。朱世安给他舀了一碗温水,又拿了两个苞米面做的饼子和一碟咸菜。这人一边吃喝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拉家常。拉着拉着就拉到炮楼子上去了。
这人说,“大哥,门前岭上黑糊糊地戳半截的是啥呀?打老远看着像是个黑老怪。”
黑老怪是一种方言。朱世安也弄不明白具体指的是什么。不过他知道这人说的是炮楼子,就说,“还能是啥,日本人修的炮楼子。”
这人一副迷迷糊糊的表情,说,“日本离咱这儿十万八千里的,要是拿一双腿来走路,走上十年二十年也走不完,累死了也走不来的那个远,他咋上咱这儿修个炮楼子?”
朱世安说,“听说是防八路。”
这人笑笑,说,“防啥的八路?”
朱世安也弄不清楚是防啥的八路,望他一眼,摇摇头。
停了停这人又说,“修这黑糊糊的东西,个子赛得上小半个村子。咱这十里八村的乡亲吃了不少苦了吧?”
这些日子朱世安就生朱子才的气。一个工头四天一块的光洋泡汤了不说,吃的也一天不如一天,满碗里连个肉丁丁也难见到了,光是些萝卜白菜的,吃起来寡淡得很。几个日本人撤回城里后,救国军也慢慢变坏了,个个吹胡子瞪眼的,拎着鞭子抽人棉袄踢人屁股蛋。还有修炮楼子占了他家半亩麦地,才给了三块半大洋。三块半,也只够买半分地的。他和日本人讲讲,日本人听不懂他的话,可那中国的翻译却说不少了,说是再说,连一分一毫也不给。不给是小事,还要弄进城里去办个通匪罪。这么朱世安就吃了一回大亏。吃了亏也只好咽在肚子里。不过二年里种不上地瓜花生,他家里的日子肯定不会多么好过了。
这人的话一下子触动了他的心事。他把眼一瞪,愤愤着说,“修那么个鸟玩意儿,还不是祸害咱老百姓!”
这人像就等着这句话似的,这时把手里吃了一半的饼子一丢,啪地一声一巴掌拍在了自己的大腿上。他的眉毛乍煞着,眼睛里放射出好些光芒来,说道,“着呀老乡,你这话说得可是太对头啦!你想日本人来咱中国是为了做啥?是为了咱中国好吗?非也。是来杀咱中国的人抢咱中国的宝贝,顺便还操咱中国的女人,连七八岁的小女孩子也不放过,七八十岁的老人也得跟着受辱。不说别的地方,单单一个南京城,日本鬼子就杀害了咱几十万的中国同胞。几十万呐,就是叫你一个一个数,只怕也得数上十天八天……”
朱世安吃了一惊,“真的么?那么多人,得拿什么才杀得完呐。就是几十万只蚂蚁,也不是那些日本人能踩光的。”
他有些不信。
“这还有假?日本鬼子有枪有炮,还有飞机炸弹。这些东西杀起人来就跟老牛喝水一样,一下一片一下一片。南京那边,早就有消息传出来了。那长江里的水,都让人血给染红了,尸体堵着江水都不流了……”
朱世安哦呀了声,像是叫这人说的场面给吓住了。连屋里的喜俊和朱世安的娘也都跟着脸色青青着。
“日本鬼子来咱中国,那可是无恶不作。这岭上的炮楼子要是盖成了,住上了日本鬼子和狗腿子们,那方圆几十里的百姓就没个好日子过了。”这人站起来,沉痛地说,“可是我们的一些同胞,还在天天给敌人卖命呢!这是什么道理?我们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
这人还想再往下说,就让朱子才领人给抓走了。望着外面的黑暗,朱世安恍恍惚惚觉得这人很可能就是专门和日本人作对的八路。他有些担心和害怕。可细想想人家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比朱子才那帮子人强多了。
正胡乱地想着,他也让人给抓走了。
岭上工地边上垒了十几间简单的房子,有些是供救国军的人住,有些是放东西的。那些抓他的救国军把他塞进了一间没留窗户的屋子里面去。他们用的力气大,他跌在地上,好半天才明白过来,他是让那个人给带累了。
屋子里潮湿而冰冷,原先是存放洋灰的。现在洋灰没有了,那种难闻的味道还是那么重。朱世安摸了条装过洋灰的袋子垫在屁股底下,心里有了一些慌张。听人说私通八路是要砍头的,用磨得锋快的大刀砍,嚓地一下,一个人就没了。这些日子他和朱子才僵着,不给朱子才面子。当了兵的人的心都狠,不是肉长的。要是朱子才不看过去的情分呢?他伸手摸摸头,等明天天亮了,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在脖子上长着不能。
迷迷糊糊着过了一夜,二天早上进来两个兵一人一条胳膊拖了他出去,一个挎着比朱子才的枪还要小许多的枪的救国军问他话,问不上三句五句喊声打,就挨了一顿鞭子。再问,问不上三句五句又喊声打。这回是剥了棉袄打,鞭鞭见血,鞭鞭都有声。打够了就再拖回小黑屋关起来。
这一天朱世安硬是一口水一口饭也没捞着。
傍黑天朱子才过来看他。朱子才站在门口,背着一双手,口气木木地说,“那人给你都说了啥?”
朱世安身上的皮肉疼肚里的肠胃饿,嘴里也干得厉害。他有气无力地说,“说啥?没说啥。一个出来找活儿做的能说出啥来?就是些家常话。”
“你再想想。那人可是全招了。白天来的那个是我们大队长,坐的是三轮摩托,不是自行车,一走屁股后面直冒烟儿,屁屁屁屁着响。”朱子才吸了一口烟,说,“这个案子可不小呀,城里的日本人都知道了,说是要严办的。咱们相好了十几年,又扯了个连襟,我不能见死不救不是?”
朱世安不信朱子才说的话。那八路要是全招了,他们也就不用问他了。听说八路的骨头都是硬的,一般软不了。再说那人也只不过是说了那么些话,说得又都挺有理的。他就摇摇头,“那人没说啥。就是讨口饭水么。”
“你再想想。”
“再想想也是没说啥。真没说啥。”
朱子才气哼哼地把背在后面的手伸出来,砰地一声扔过来一包东西,扔在朱世安身上,说,“到了这地步你还死硬。我不管啦!”转过身就走掉了。
朱世安摸摸朱子才扔下的东西,是一块布里包着的两只热馒和一块煮牛肉,热馒一个有三四两,煮牛肉怕不有半斤。朱世安顾不了那么多,忙忙着就吃。吃着想朱子才坏是坏,可还没坏到家,也就不那么恨他了。不过那八路是条好汉,也不能卖了人家。一时间好生为难。
二天白天朱世安又挨了几回臭揍,傍黑天又给拖回了那屋。朱世安身上皮肉都疼,不过活动活动,筋骨还没伤着。他靠墙坐着,正想着这么做值不值,自己是不是在自找倒霉,想着想着竟就睡了过去。
天黑定了许久朱世安让人给拍醒了。来的人先是嘘了声,不让他说话。朱世安听出是朱子才,就哼了声。
朱子才悄悄着说,“小叔,你这么死抗着抗恼了大队长。明儿个他要来辆车把你给弄到蓬莱去。蓬莱那可没我说话的地方,日本人对私通八路的人也不会给条别的路走。一去你肯定就没命了。说不说也一样是没命了。”
朱世安的心铮地一响,有些发懵起来。
朱子才叹了一口气,说,“这年把的我挺恨你的,恨你不帮我个忙什么的。可让你丢了命我又不忍心。相好了十几年,今儿个我就豁上自己了。你快逃走吧。越远越好。逃出一条命就是。不过可别当啥的兵……你也不用像我……”
朱世安的心一下子热热,黑黑里看不清朱子才的脸面。不过他知道了朱子才的心,热热地叫了声子才就说不出别的话来。
朱子才说,“你快别说什么了。我是偷着上岭来的。家里的事你也别去管啥了,能帮的地方我尽量让二奶奶小婶她们不吃着苦。你这就走。要是叫兄弟们见了你还咋个逃。”
说着朱子才一推把朱世安给推出屋,往他怀里塞了一包吃的和衣服。再一推把他推到黑黑的夜里去了,直至没了顶。朱世安很快就被这黑给化了去。无声无息。
9
时间总是长着腿的,走起来飞快。这一过,一下子就过去了十年。再回来时朱世安瘸了一条腿,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他穿了一身洗得发白了的军装,扎了一条宽牛皮带,也背了一把朱子才背过的那种匣子枪。他的身子比以前瘦了不少,脸也黑瘦,胡子拉拉的。帽子上面还顶了一颗用布铰出来的红五星。他到底没听朱子才的话,还是当了兵。当来当去的,把一条结结实实的好腿也给当瘸了。
这一走十来年,村子都面目全非了,岭上朱世安走时才盖了一半的炮楼子也早就成了一片废墟。
进了村子朱世安很激动的样子,急急忙忙地一拐一拐着找自家的门。找了几个来回没能找到,拽一个乡亲问问。乡亲先是认了好半天没认出他是谁来。认出来后脸面上很复杂的一片表情,哼哼哧哧着说是他家早就让日本人给一把火烧了。再问他娘和他媳妇喜俊,说是死了六七年,坟上的青草都绿六七回了。
朱世安懵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问朱子才怎样了。那人很是不屑地说,打炮楼子那阵子早给炸成了一堆肉酱,连个尸骨都收拢不起来了。那狗日的汉奸败类,提他不怕脏了嘴!
人去楼空,物是人非。朱世安一时很是颓然。他想不到急匆匆着回来,得到的却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倚着一棵刚刚长出新叶子的老树,朱世安把一对拳头攥得格格作响。
很久他找到了朱子才的家。还是原先的那幢旧房子,不过是更破败不堪了。推开门进去,朱世安看见院子里站着个十来岁的男娃,怯生生地正拿一双眼睛望他。他站着向屋里喊,“屋里有人吗?”
里面应了声,慢慢走出个三十多岁样子的女人。这女人也是怯生生的一副表情。朱世安望她。从她满脸的憔悴里面,他还是找到了他小姨子喜梅从前的一点点影子。
“喜梅……”
那女人怔了半天,才哇地一声哭了,也不顾身边的娃,一扑扑到朱世安身上,说,“姐夫,你咋才回来呀……”
朱世安眼里也有了泪。他扶喜梅坐下来,递一块自己带的毛巾给她擦泪。喜梅哭了一会儿不哭了。她拉过那男孩推到朱世安怀里,说,“小安,这是你亲爹。叫爹,快叫呀。”
那孩子还是怯怯着,不敢叫这个身上带着枪的陌生男人是爹。朱世安很动情,一搂搂住了他。
许久喜梅说,“你这一走十来年,也不回来救救大妈和我姐。”
“她们是咋个死的?”
“还不是日本人。你自己走了倒好,她们咋个过。你走了才五天姐就生下了小安。不多久,日本人说她们是共属,硬是一把火给烧了房子。三个只好拖了棍讨饭。我姐月子里落下了病根,大妈年纪大了,不上三年就都死了。小安还是商量了子才才领回来的。”喜梅低着头,慢慢说,“姐姐临死时嘱咐我帮忙拉扯大小安,说是有一天等你回来还你。还好,你总算是回来了……”
说完这些话,喜梅显得疲惫极了,仿佛是刚刚走完了一千里的路途,刚刚卸下一千斤重的担子。
朱世安的心里酸酸一片。他知道喜梅拉扯着小安,这几年定是受了不少的苦。尤其是朱子才让八路给炸死了后,村里人更是得给她白眼看的。他无法谢她,但他决定留在村里不走了。他跟喜梅说,“以后就好了。我回来了。有我在,不会再叫你们受苦了。”
“姐夫,你……不走了?”喜梅眼里忽然露出一些惊喜。
朱世安点点头,大声着说,“不走啦。到家啦我。喜梅,难道你还想叫我再走么?”
“……不想……”
那晚朱世安就住在那里。他的家没有了。他想有一个家。夜里他搂着儿子。喜俊留给他的骨血使他的心重新充实起来。而且他发现这时的喜梅很有些像当年的喜俊。
第二天他跟喜梅说他决定娶她。小安已经叫惯了她妈妈,改不了口了。他要娶了她。开始喜梅的脸红了一下,但忽然间很是恐惧。她拒绝他。她叫他领着小安走,越远越好。她说她是汉奸家属,她不能连累他们。
朱世安挺固执,说,“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我不怕连累。”
喜梅又说,“你不知当初子才是咋个说的,他说……”她说了一半就不说了。朱子才说的小姨子是姐夫半个屁股的话,她还说不出口。
朱世安不管,“子才爱咋说就咋说,我不听他的。再说他也不在了……”
喜梅一整个白天都痴痴着的,给小安不停地缝补衣服,也不和朱世安说话,夜里就悄悄去跳了井。
又过了三天,朱世安领着小安走了。他一拐一拐地走在家乡的泥土路上,心里面尽是无限苍凉。走前他给母亲和媳妇上了坟,又把喜梅埋在了朱子才的坟边。他知道朱子才的坟里只有他枕过的一只枕头,和他用过的一支毛笔,一本书,几张纸,可他还是把喜梅埋在了那里。
10
许多年后的一个冬天,一个面目清瘦的老人找到了早已退居二线闲赋在家的朱世安。尽管过去了那么多年,他们仍旧很快认出了对方。
“子才!”
“姐夫!”
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久久久久不松开。
朱世安沙哑着嗓子问,“你咋没死?”
朱子才说,“你不是也活着么?”
因为都老了,也就没有了太大的冲动。两个人坐下来,平静着说话。朱子才说四三年八路打炮楼子那阵子,他趁夜侥幸逃了出来。人是逃出来了,可也不敢回家了,就只好往远里逃,迷迷糊糊竟逃进了国民党的队伍里去了,后来又迷迷糊糊地跟着老蒋上了台湾。朱世安说他逃出去后没处可去,干脆就去找到八路,钻山沟子钻了好几年,腿瘸了才转到地方上来。问起部队的番号,他们竟然还交过几次火。只是当时都不知道对方里面有自己的连襟罢了。
停了停朱子才忽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到蓬莱去当兵吗?”
朱世安说不知道。
朱子才说,“我虽说认得了一些字,可在村里什么也不是。你嘴上不说,心里定是瞧不起我。我当兵,是想通过这个和你连上襟呀。”
朱世安相信朱子才说的是真的。他们心里也都明白,要是当初喜俊回娘家商量那事儿时,她家里人当时就同意了,那么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将肯定会是另外的一个样子。
可到底是哪一个样子,他们又都说不出来了。人世沧桑,白云苍狗,有些事情,谁又能说得清呢?
责任编辑陈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