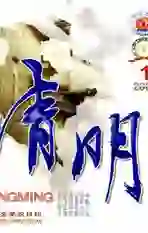小城世相
2003-04-29聂鑫汉
聂鑫汉
小巷的灯
我的家就住在筷子巷。这条巷子那样长,那样窄,真像一根横放着的筷子。不,它像一根筷子挑着一只小葫芦,因为,在巷子中间的那段,突然“鼓”出一块圆形的地盘,立着一根水泥电杆,上面挂着一盏亮瓦瓦的路灯。
小巷的路面是麻石铺成的,每一块都被磨得溜光溜光,像镜子一样。雨天,木屐的铁钉敲击着麻石,“嘀叮,嘀叮”,像琴声一样好听哩。而在最热最热的夏天,小巷却像一条幽深的峡谷,清凉极了。这是因为巷墙很高,太阳怎么也晒不到巷里。“过堂风”穿过长长的巷道,发出呼呼的响声,刮在身上格外的爽人。
夏天的夜晚,筷子巷是我们“小把戏”的乐土。我们可以玩“捉特务”的游戏,可以在路灯下占一块地盘,放上一条方凳,走“跳子棋”,或者做作业。
而筷子巷的大人们,也十分珍惜每一个凉爽的夜晚。路灯下,总是坐得满满的。除了乘凉的外,有的还借这不花钱的灯光,赶一赶活计。
那些老爷爷、老奶奶,喜欢躺在竹睡椅上,一边喝着又浓又酽的茶,一边唠叨一些陈年古话。那些大婶大嫂,则不停地织毛衣,或者纳着鞋底。住在巷子前的刘伯伯,脚边放一只大篮子,篮子里放着鸡毛、麻绳、小竹竿,两只手飞快地扎着鸡毛帚,一会儿就是一只,像变戏法一样。住在巷子尾巴后的张满爷,常在灯光下,用雪亮的篾刀,削竹筷子,听爸爸讲,他的手艺很好,自己削筷子自己拿到街上去卖,蛮受人欢迎。最有意思的是那个剧团退休的王师傅,兴致好的时候,还爱拿把月琴,“嘣咚嘣、嘣咚嘣”地弹起来,边弹边唱,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啦,什么“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啦,听得人不肯动脚,嘴巴不停地咂着。
每晚来得最早的,就要数唐娭毑啦。她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头发像雪一样白,满脸的皱纹,又深又密,像刀刻的一样。背已经弓了,而且是个瞎子。虽然灯亮不亮,对她来说都是一个样。但是,唐娭毑爱坐在这盏灯下,尖起耳朵,默默地听着。听我们的谈话声、笑声、棋子敲击棋盘声、麻线拉过鞋底的“唰唰”声、扎鸡毛帚的“嘶嘶”声、削筷子的“哒哒”声、月琴的“叮咚”声……只有在这时候,她才不感到孤独和寂寞。
又是一个美丽的夏夜。唐娭毑拿着椅子,迈着颤巍巍的步子,朝路灯下走去。从她家到路灯下,是二十七步;从灯下到她家也是二十七步。巷子里,哪里有个坑,哪里有条沟,她像熟悉自己的手指头一样熟悉。
她坐在灯下,静静地等候大家来。干涩的眼窝里时常流着泪水。唐娭毑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女,孤单单的,真可怜。听人说,她本来有个丈夫,还是个当“官”的哩,在教育局做事。文化大革命中,在一次批斗大会上,被活活地打死了。那时,唐娭毑是个小学教师。丈夫死后,她哭了几天几夜,把眼睛哭瞎了。以后经常流泪。后来,她退了休,在小巷里安下了家。筷子巷的左邻右舍,都很同情她,帮她洗洗浆浆,帮她烧火做饭。唐娭毑见人就说:“筷子巷的人,都是好人啦,要不,我这瞎子婆婆真不知怎么活下去!”
粉碎“四人帮”后,教育局的领导劝她搬出小巷,住到教工宿舍大楼去,唐嫉毑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她说,她舍不得这条小巷子,舍不得这些邻舍,舍不得这盏路灯!
真怪,一盏路灯有什么舍不得的?哪儿没有电灯呢?我不懂!可今天,我真希望我像神话里的仙人一样,有无边的法力,能让白天不断地延长,能让夜晚永远永远不降临!但是,夜晚毕竟还是悄悄地来了。
筷子巷热闹起来,大家呼喊着,召唤着,朝路灯下走去,杂乱的脚步在麻石路面上响着。
我看见唐娭毑的脸上,浮出了笑容,她努力睁大眼睛(其实,她什么也看不见),朝着巷子的两头来回望着,用耳朵聆听着。她对这些脚步太熟悉了,她准知道来的是谁。
扎鸡毛帚的刘伯来了,他的脚有些跛,脚落地,一声重,一声轻。
唐娭毑问道:“老刘,鸡毛帚子生意好不好?”
“好得很哩,今晚打个夜工,多扎几只看看。”
削筷子的张满爷来了,他的脚步缓慢细碎。
唐娭毑笑了,“满爷,听说你领了执照,发了大财啰!”
张满爷“格格”地打了几个哈哈,“托党的福,一切都还顺心顺意。”
李二婶来了,手里拿了一只打了一半的鞋底。在我的记忆中,她的鞋底是永远打不完的,又厚又结实。
哦,我的同学小明也来了,他在灯下摆一把方凳子,对着我快乐地喊道:“小石,来,下一盘!”
我吞吞吐吐地说:“不……好,下就下吧。”
王师傅腋下夹着月琴,一摇一摆地走了过来。唐娭毑笑得更欢了,问:“王师傅,今晚是讲‘三气周瑜吧?”王师傅用手指在月琴弦上拨弄几下,顺口唱道:“就等路灯放光明,我把那‘三气周瑜说一轮!”逗得大家笑个不停气。
我默默地站在旁边,望着大家兴高采烈的样子,望着唐娭毑用手绢不断揩泪水,脸上闪现着一种期待光彩,心里就一阵阵地难过。白天,一只小麻雀栖在灯罩上,我扯起弹弓去打,麻雀没有打到,却把电灯泡打碎了。唉,我真该死!
这时,街上的路灯亮了,一片金黄色的光照在巷口。李二婶惊喜地说:“街上的灯亮了,我们的灯快亮了!”唐娭毑兴奋起来,问:“亮了吗?”
于是,大家都抬起头望着装电灯的电杆,把颈脖伸得长长的。一分钟、二分钟……。
王师傅说:“平常街灯一亮,我们的灯也亮,今天怎么搞的?”
因为夜色很浓,灯又挂得高,谁也看不清楚灯泡已经碎了。
张满爷急躁地用篾刀敲了敲木墩子,用命令的口气说:“石伢子,去拿手电来照一照,你家住得近。”我很窘,脸上直发烧,像欠交了老师的作业一样不好意思,又像捉迷藏怕被人发现时那样紧张。我连呼吸也变得急促了。
我无可奈何地跑回家去,拿来了手电。张满爷接过手电,往上一照,灯罩下的灯泡已经碎了!
张满爷忍不住骂起来:“哪个作的孽,把灯泡打掉了!耽误我的工!”他气呼呼地把手电往我手上一塞,拿起篾刀、木墩转身就走。
路灯下,一阵骚动,李二婶用手拍着鞋底,气愤地说:“回去打鞋底去!缺德的家伙!”
扎鸡毛帚的刘伯,把拳头晃了晃,大声说:“我要晓得哪个打的灯泡,不打他两个嘴巴不算角色!”
小明收起棋盘,有意无意地瞪了我一眼。是的,我们两个平素玩得最好,只有他知道我有一只弹弓。他准怀疑上我了!
人们陆陆续续地走了,仿佛我打碎了一盏路灯,也把筷子巷的欢乐打碎了。是的,谁又愿意坐在黑咕隆咚的地方呢?
王师傅见人们都回家去了,也夹起月琴,叹了口长气,没精打采地对唐娭毑说:“唐老师,回家去歇歇吧。”说完,一摇一摆地走了。
唐娭毑对这一切似乎都无动于衷,依旧坐在那儿,眼里的泪水流得更勤了,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忽然,她对着我,不,是对着筷子巷,自言自语地说:“唉,在灯下,我还有个
影子,回到家里,连影子都没有了!”
我知道,唐娭毑的家里,是没有装电灯的,因为她不需要电灯,一切都靠用手去摸索。
我心里一阵阵发痛,我想哭!我从口袋里摸出弹弓,狠狠地把它丢得老远。我走到唐娭毑身旁,搀扶着她,拧亮手电,一步步走向她的屋子。
唐娭毑的屋子空落落的,摆着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五屉柜。
我把唐娭毑扶到床沿坐下。我用手电在屋里来回照着,仔细地打量着一切。
五屉柜上立着一个木镜框,里面嵌着一个老爷爷的像。木镜框上的漆,已经被磨得溜光溜光。看得出,唐娭毑每天不知道要去摸多少次。不用问,那一定是唐娭毑的丈夫的像片。我相信,她一定能看见这个爷爷的模样,要不,她为什么总要去摸、去看呢?
手电微弱的光,又落在书桌上。书桌上,摆着一本《班主任手册》,纸页的边角都卷了起来。唐嫉毑一定常常坐在桌子边,翻着这本手册,回忆着她教学生的情景,怎样备课,怎样家访;她一定能叫得出她的学生的名字,也能记得她的学生的模样。
这是一个寂寞的世界,陪伴她的只是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她多么需要新的欢乐,来不断填补她今天的生活啊。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每晚爱坐在路灯下,听大家说话,听大家笑。人是害怕寂寞的,小孩子怕,大人怕,老年人更怕。
我打碎了路灯,筷子巷失去了一个美好的夏夜,唐娭毑失去了一个美好的夏夜。失去的,我能去偿还吗?回到家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捂着被子,轻轻地抽泣,泪水打湿了枕头。
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梦里,我依偎在唐嫉酏的怀里,反复地说着一句话:“我错了!我错了!……”
惊醒后,我把电灯扯亮。一骨碌跳下床,把自己储蓄零钱的竹筒劈开,数着一个个晶亮的分币,一分,二分,三分……
第二天早晨,我跑到百货店,买了一个100瓦的灯泡。
回到巷子时,人们都上班去了,老人们还挨在家里,巷子里静悄悄的。在巷口,我碰到上街去卖筷子的张满爷,他问我为什么还没去上学,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一溜烟就跑过去了。
我把家里的梯子架在路灯下,敏捷地爬上去,把打坏的半截灯泡子取下来。
这时,唐娭毑拄着竹棍,提着菜篮子上街去买菜。她的竹棍碰到梯子时,说:“又是哪个调皮鬼在掏鸟窝,莫跌倒哟。唉。”
我屏住呼吸,不吭声,一直等到她走过去,才开始装新买的灯泡。
灯泡装好后,我像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任务,心里感到特别的舒服。
我眼前又幻现出这样的情景:闪亮的灯下,人们围在一起,一边听王师傅讲“三气周瑜”的评弹,一边扎鸡毛帚子、削筷子、打鞋底、下棋。唐娭毑端坐着,满脸带着笑,凝神地听着、听着……
放好梯子,我拿起书包就往学校跑。今天我迟到了!
假如老师问我为什么迟到,我会把这一切告诉她,也告诉我的同学,关于筷子巷,关于那盏路灯,关于唐娭毑……,请他们千万不要用弹弓去打路灯!
宋老师
宋老师,自然姓宋,名什么,我一直没有打听过。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宋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
宋老师个头不高,额头上皱纹很多,清瘦的脸上总是平平和和,慈慈祥祥。齐耳的短发,修剪得齐齐整整的,不枝不蔓,青发里掺着不少白发、灰发。一双眼睛很有神,流出清清朗朗的光。她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士蓝布衣。士蓝布衣剪裁成列宁装的款式,穿在她身上很得体,胸左有个口袋,插着一支英雄牌的粗杆钢笔。她当班主任,还教语文课。每天她很早就到了教室,坐在讲台边看书和备课。我们清早来到教室,很自觉地早自习,谁也不会到操坪去玩。班上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的前几名。
宋老师到我家家访过,知道我家生活很困难。每学期的学费减免,她总是首先考虑到我。我心里很感激她。
有一个下午,我吃过午饭就来到学校,学校的大门虚掩着。很厚很重的两扇校门,门轴竖在麻石凿成的石臼子里,门上用黑漆写着“临丰小学”四个字。大门一打开,就是一个很大的礼堂,礼堂是青砖铺地,二十四根石柱撑着屋顶。屋顶上盖的是青瓦,每隔两行青瓦,就镶着一行镜瓦。光线从镜瓦里透进来,把个礼堂照得亮堂堂的。大礼堂的两侧,摆着几张乒乓球台,一下课,许多同学都跑到礼堂去占球台。
我推开沉重大木门,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在推门的那一刻,一个乒乓球滚到门下,门把乒乓球压凹压瘪了。前来拾球的高年级同学一把抓着我,要我赔。我哪有钱买球赔呢(尽管那时一个红双喜的乒乓球只一角二分钱),我急得大哭起来。正在这时,宋老师来上课,她问清情况后,就从士蓝衣的口袋里拿出一角二分钱,对高年级的同学说:“我给他赔吧。”然后,她走到我跟前,用小手绢揩干我的泪。“去玩吧,不要再哭了。”她说。我感激地点了点头,走进了教室。
一个学期过去了,新学期又来了,我们挎着书包走进教室。迎接我们的不是宋老师,讲台上站着一个佩戴“红色教工”符号的新老师。她说,我姓侯,是你们的新班主任;宋老师是地主崽子,是反动军官的姨太太,她没有资格教你们。她还给每人发一张纸,要我们每个同学折出一只纸鸟。
折纸鸟是宋老师最早教给我折的,然后我又教会了同学们。
记得当时每次下课后,同学们或到礼堂去打乒乓球,或玩塑料水枪,或看小人书……。而我没有任何东西可玩,许多时候我孤独地坐在位子上发愣。一天放学后,宋老师约我到她家去。她家就在九总大步桥旁边,一间木板房里,摆着一张小四方桌、两把太师椅和一个茶几。我跪在椅上,可以看到窗外大步桥下的潺潺流水。宋老师一人独住,一张单人小床挨着门右侧摆着,家里收拾得很整洁,木地板擦得看见纹路。
宋老师拿出几张材料纸,说教我折纸鸟。一张纸在她灵巧的手中,一会儿变成了一只小鸟,有头有尾,那翅膀还能扑剌剌地上下拍动。我很快就学会了折纸鸟。
第二天有堂文体课,天下着雨,同学们就在教室里自由活动,我就用张纸折鸟玩。许多同学围拢来,要我教他们折鸟,霎时,我心里的沉郁都消逝了,我和同学们亲近起来。
新来的老师为什么要我们折纸鸟呢?我们只好规规矩矩折好了纸鸟,交给这位“红色教工”。
放学了,我们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校门口围着许多学生,不知在观看什么。我挤进人丛中一看,傻了,宋老师站在那里!她的头发剪去了半边,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大牌子上写着一行大字:“地主崽子、反动军官姨太太、资产阶级的宋黑鬼”,“宋黑鬼”三个字还用红笔打了个大叉。更让人惊讶的是,刚才我们折的五十多只纸鸟,用线串着,挂满了宋老师一身。有的同学(别班的)向她吐痰,还有的向她掷石子。我看着宋老师,泪水猛地在眼眶里转。我知道我折的那只纸鸟,也挂在她的身上。猛然间,我有了一种难言的负疚感。
从那一天以后,学校开过几次批斗会,宋老师总是低着头站在台上。每次批斗会,都是那个戴“红色教工”符号的侯老师主持。她每次都说宋老师的爱人在台湾,是国民党军官,她教学生折鸟,表达的是她要飞向台湾的心愿。后来,宋老师再没教过我们的课了,也再没有在学校里见过她。
过了些日子,我去宋老师住的木板房探访过一次,木板房已换了新的主人,我问宋老师搬到哪里去了,那人茫然不知。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宋老师。
责任编辑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