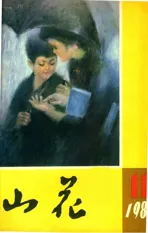他们就这样度过一生(六首)
2003-04-29马永波
马永波
朋友的妻子
朋友的妻子她对我小心翼翼
她知道我不会到他们家里去
一起喝酒三个人
朋友的妻子
开始关心我的个人问题
这是个幸福的日子
他们一起回到了乡下
第二天早上我在路边采了一束倭瓜花
吹着口哨
他们就要走了
那样朋友会幸福
这一天我分明感到过去也变了许多
这是一个幸福的日子
朋友的妻子
走在后面
晨光中我的黑衣服上
沾满花粉
草泥马
你站在雨后的院子里
一部分已经还原
露出黑暗的腹腔
和绣色的稻草
圆圆的眼睛一直望着我们
哥哥又在跑来问我
“用草和泥做一个马叫什么马?”
我不回答
不知道妈妈为什么打他
我哭了,望着你的圆眼睛
你同我一起长大
你的名字被人们重复得丢了
老年你在路边等我
空荡荡的嘴里咬着树叶和谣曲
我们碰碰鼻子,一起去树阴喝水
再没有人提起我们
再没有人被母亲痛打
为一首没有写出的诗辩护
有些东西你不能去碰它,它会粉碎你
你一生都在逃避你所热爱的东西
你的冲动扼止在半空,化成了怪物
没有形式的东西,却没有让
阿佛洛狄忒,脚踩海浪凝成的贝壳
在荷叶、鲜花、清风之中
从存在的幽暗中升起。这首诗写下了
它自己的生长。一个人只有被大风
平地拔起,才有可能让视野
超过他周围的事物,超过玻璃幕墙
增殖和复制的速度,找到最原始的
基因,把它像分裂膨胀的孢子
从发炎的视网膜上拔除。这首诗
写下了一个人的渺小,当万物
将他包围,当远方在他面前
像玻璃幕墙竖起,越来越高
在外省
有些事说着容易,比如依靠常识活着
他的饱嗝使田野更加空旷了
对于生活,他有一颗流星对天空的歉意
有被画花脸的戏子那样的激情
他躺在四面透风的树下
把远方镜子一样举到眼前
阳光开始漫过午后的斜坡
他说,老,是一个嚼不动的词
正如镜子是一个不发光但很亮的词
有时,干懒着也是一道风景
偏僻土路上的马粪还原成了干草
对于这样一个过于寂静的省份
歌唱是多余的。他偶尔抬头
看看庄稼越来越密的田野
感到舌头底下空荡荡的
他继续躺着说:大雪
是从庄稼茬里涌出来的
跑冰排
报上说昨天江上有特大的冰排
有船坞那么大,灰色的,缓慢的运动
报纸总是说昨天和昨天,就像诗歌
记录的都是回忆,即使诗中人
用了许多的现在和此刻
比如说我吧。去年这个时候
陪大春在松花江边蹲着
看冰排,看灰尘撒到水里
(也撒在眼睛里,今年
还没有随泪水排出来)
后来他在诗中把冰排写成一群女囚
镗着哗啦啦响的脚镣
别的我就记不清了。那首诗
好像是两行一节的,和一块块
冰排差不多,只是更为整齐
似乎可以在上面跳跃
提前到下游去。冰排一边出现
一边消失,加宽着江面
流了一天,到傍晚江里只剩下水
和岸边潮湿的黑土。后来
看拍的片子,冰和水都是纯蓝的
风还在吹着,我坐在屋子里
也能感觉到,它旋转着一个塑料袋
让它有静电一样糊在行人的后脑勺上
或者在树梢伪装成风筝
冰排肯定过去了。到现在
和大春约好的《跑冰排》的同题诗
还没有完成。说到底
冰排不是为这首诗存在的
甚至不是为去年的我们
他们就这样度过一生
他们打算就这样度过一生
他们在一个小城安顿下来
阳光很好,邻居的犬吠声很好
夜雨后的星星安宁闪亮
他们要用倒叙把故事讲完
偶尔也会有雨季的霉斑
从屋顶一角剥落下来
落在橘红色的沙发套上
他们就默默地收起来
偶尔有朋友从蚂蚁河与万佛山而来
带来一阵忙乱和过后的空茫
垂钓时或许有诗句
如细小的影子从水底浮上来,盯着他
他们就这样过了,这很好
正如山上的石头
牢牢嵌在自家的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