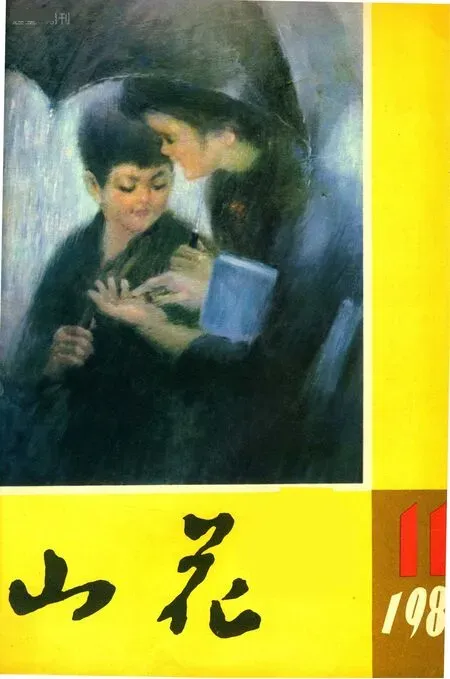海南文化人物二记
2003-04-29李少君
李少君
张志扬抑或墨哲兰
很多人看过“墨哲兰”的文章,但不知道“墨哲兰”就是张志扬,是他的笔名。还有很多人看过张志扬的文章,但不知道张志扬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墨哲兰”。
我很久没有见到张志扬先生了,虽然电话倒还常通。这或许是因为我如今的心态越来越趋近张先生:对纷纭世事不再像以前那样热情,牵肠挂肚地关心,因而深居简出,越来越埋头于自己的事情与专业,冥思苦想,废寝忘食,以至我每次打电话问张先生在干什么,他总是说在读书或赶书稿论文。但说来奇怪,正是这种状况,反倒使我对张先生更惦记一些,更关注一些,比起那些出头露面的风云人物来。
张先生来海南也有近十个年头了,我记得他初来时还有办报、组织讨论会、搞小沙龙的兴趣,后来却渐渐地,他隐居在海南大学那茂密的校园丛林里,坐在书斋中,一天又一天,除了去去他任研究员的海南大学社科中心或在校内及外地讲讲课之外,连门都很少出,朋友都很少会了。他沉迷于他的思考和写作,越来越沉迷。于是,我虽然见他的面少了,却见到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在海南的几年里,他出版了他最重要的那些著作,最早是随笔集《缺席的权利》,这本书的出版被《新民晚报》评为当年文坛的十件大事之一,书也不断再版。1999年,以出版学术书籍著称的上海三联书店一次性推出张志扬的三本理论专著《创作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禁止与引诱——墨哲兰叙事集》、《渎神的节日》,在我有限的视野中,中国出版界还很少如此隆重地推出理论著作。可想而知,这三本书的出版马上成为知识界的一个话题。在网络上更被推崇为当代几大思想家之一。此后,张先生又有《偶在论》、《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等著作接二连三地在境内外问世。
张先生用“墨哲兰”或张志扬时不知有没有什么讲究。我很喜欢“墨哲兰”这个笔名,但不知道他到底在什么情况下用“张志扬”,在什么情况下用“墨哲兰”,两者又有何区别。
生活中的张先生倒是很有两面性。
一面是平常的。对于父母,张先生是典型的孝子,有一段时间,因妻子在外地,他一个人负责照料九十岁上下的父母亲;对于子女,张先生是慈父,在他的教导下,如今他的几个女儿都很有出息;对于妻子,他是称职的丈夫,为照顾妻子,张先生每天早上去买菜,还负责做饭做菜;对于工作,张先生很合格,讲课很投入,算得上勤勉。而其实,张先生的生活之路并不平坦。张先生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独立思考,结果却因此获罪,文革时,在武汉,张先生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监狱达六年之久。在牢里,张先生自学马克思的《资本论》,从此走上哲学之路。文革后,张先生出狱,自学成才,考进了湖北社科院,后又到湖北大学,并逐渐在哲学界声名雀起。早年命运的坎坷,使张先生更珍惜如今难得的一份安静平和,所以对研究工作,他总有一种急迫感。
另一面则是独特的。张先生的哲学论著之特别,以至曾有人质疑其是否学术。张先生的哲学思考,总是从对其个人经验与现实体验的反省与思考开始,强调“个人生存之真实性及其限度”,以求得一点点个人的权利及价值。而这显然来源于他早期的个人遭遇,在那个个人如此渺小以至被藐视甚至可以被忽略不计、个人独特性与差别被彻底消灭的时代,争取个人的权利及价值其实需要何等的勇气与努力。难能可贵的是,而在一个个人主义迅速蔓延的市场经济时代,张先生又强调“限度”,亦即一种“个人自律性”,并认为如果没有个人的自觉与自律,则可能走向虚无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可以说,张先生所说的“个人生存之真实性及其限度”,其实是在摆脱意识形态一体化之后,寻求个人自我道德要求与信仰的一种努力。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因为,市场意识形态同样试图取消差异与独特。由于特别的境遇,张先生的思考是独一无二。著名诗人于坚刚听说张先生来海南时,曾写信给我,让我代他向张先生致敬,并叹息可怜的唯唯喏喏的知识界对张先生工作的意义毫不知晓,至今无法掂量其价值。后来于坚因事与诗人杨炼来海口,在酒桌上,他竟然真的当着一桌子人的面,向坐在对面的张志扬先生公开表示了他的敬意,让我们大跌眼镜。要知道,在当代文坛,于坚是相当桀骜不逊的。
张志扬抑或墨哲兰,这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与他生活中的两面有无某种对称关系?我不知道。我只曾在他的一本书的后记中看到说“墨哲兰”是某种生活的象征。但我还是不太明白。
或许,下次见面时可以再问问他。
耿占春:沉默与絮语
占春不善言词,因此他常常显得很特别。在开会时,在一大群人中间,甚至大街上,占春都显得与众不同、特立独行。当然,占春最常见的姿态还是端坐着的时候:一只手支着下巴,闭着嘴巴,低着头,好像在倾听,又像在沉思,他胡子拉碴,眼睛却很亮,不时闪烁着。他这样的姿态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醒目的存在。
很容易从一大群人中间将占春分辨出来:沉默寡言,听得多说得少,听的时候很认真、细致,是那种真正可以称之为“谛听”的听,说的时候话也不多,但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声音很小,却很有分量,让人印象深刻,不敢轻易忽视。占春说话一般是想了很久似地才说,所以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有一种属于他个人的特别的节奏。
占春是批评家,出过一大堆批评著作,如早期的《隐喻》、《痛苦》、《观察者的幻象》、《话语和回忆之乡》,来海南后才出版的《群岛上的谈话》、《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中魔的镜子》、《炉火和油灯》、《叙事美学》等。一本接一本,一脉相承,颇成气象。占春早期写诗,后来搞评论,如今在海南大学当教授,生活显得平平淡淡,安安静静,却也有滋有味,细水长流。
很容易将占春从一大堆批评家中分别出来:如今的批评家,热衷的是炸作,因为炒作无须下苦功夫,无须细致的分析研究,无须一是一二是二地举例引证,只要简单归纳,喊几句口号,耸人听闻就好,而且还容易一举成名,兼赚红包,名利双收;另外一种捷径则是骂名人,惊世骇俗,无论古人今人,骂倒一切,只要骂得痛快淋漓就好,岂管有无根据道理,一骂成名,一骂成功,既出风头,又很“生效”(如今批评界最红火的一个词,意指产生效果、效益);还有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批评是打着学术的大旗行横行霸道之实的所谓文化批评,顺我者捧,逆我者批,对友军连垃圾之作也大加赞叹,对异己即使佳作也大加讨伐,批评成了拉帮结伙、铲除宿敌的工具,批评只是一种幌子,一块遮羞布,一种名义,这种批评完全违背了批评原本的规范与职责。而占春不同于这样的批评家,占春看重的是作品本身的质量与含量,强调的是细读精读。比起众多不可一世、猖狂张扬的批评家,占春非常地低调,他常常谈的倒是他的困惑,他的疑问,他的自我反省,比如他对批评在当代究竟有何意义、文学在市场化的今天有无价值的思考等等。可以说,占春才是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因为他纯粹,本分,具有一种原始的批评意识。
占春的批评带有很浓厚的个人风格。他也因此常常偏离那种学院化的、循规蹈矩的批评。他更多地将批评本身视为一种创造性的创作。所以他的批评文学也就融入了更多个人化的东西,写得像随笔,又像札记。占春的文风,也没有一般批评文章的那种纯理论的一本正经,更多的倒是金圣叹点评似的随意,本雅明似的深入细腻的叙述,占春的批评是一种带有个人特有节奏的絮语,不急不缓,不慌不忙,如淙淙流水,绵延不绝。
很容易将占春的批评风格与那些急功近利的粗糙的批评文字区别开来:有人说世界上的思想方式有两种,一种建立在希腊论辩术基础上的逻辑实证的方式,一种是中国、印度式的感悟、领悟、直觉的方式。占春无疑更多地是后一种,他也格外看重同类的思考,所以占春格外喜欢韩少功的《暗示》这样的建立在个人性经验经历上的思想随感式的作品。占春既从阅读他人作品中“悟”,也从个人生活经验及感觉感受中“悟”,比如他的被命名为“忆语体”的《炉火与油灯》一书,就是通过个人回忆来思考的,来“悟”的。回忆总是碎片般零散的,所以占春在书中说:“我是时光碎片的收集者”,“我写,我回忆,我聚拢时光的碎片,我汇聚光芒”,“创造光芒,使看不见的事物在其间隐约现形,试着显形”。而《叙事美学》等书及《文学批评的歧途和潜能》等论文中,则更多是在阅读中来“悟”,通过对古今中外名著的阅读,占春“悟”到了文学的真谛,他说:“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一种持久的、不间断的启蒙要素。文学培养我们的敏感性,增加人们对观念的细致的辨析力,对他者经验的感同身受的想象力和同情感,对经验的感受力,和把混沌不清的经验体验为意义的形式的能力,以及话语的说服力。”占春还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希尼的话说,文学的最终意义是学习“做一个敏感的人”。而在《丧失行动的知识人》等论文中,又可窥见占春沉静的外表下似乎还掩盖着某种特别的东西,激烈的、充满锐气的东西,毕竟,占春早年是诗人呢。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占春的思考,越来越与“禅”的精神有相通之处了,虽然他的背景不仅仅是中学,还有西学,但那种安详、沉思、冥想、顿悟,大有深意呢,绝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企盼有所作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