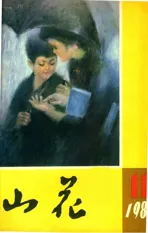挂红
2003-04-29马学文
马学文
一
天快亮的时候,怀贵被尿憋醒了,小肚子隐隐的胀痛,就欠起身去扯搁在枕边的裤头衩子,这时身边躺着的女人突然拖声拽气地哼了一声,怀贵以为是自家的手道拐压着女人头发了,就把撑着身子的手道拐挪了挪。
女人是牛栏江边常见的那种见识很短头发很长的女人,也是地道庄稼人很看中的那种长得很四齐的女人。女人的头发白天用马尾织成的髻套笼在头上一点不显山露水,天黑后上床脱了衣裳解开髻套,黑油油的头发就一下子散开来,一直拖到白生生的屁股上,女人就仰了脸把头猛地一摇,将滑溜溜的头发扬波一抖,众多的发丝就一下子抖抻了,之后女人便把胖嘟嘟的身子莲花般缓缓展开在床上,暄暄软软的黑发就丝绸般柔顺地铺在了女人的身下,怀贵透过昏黄的煤油灯光看着女人就比其它时辰更有了味道。怀贵也就晚晚让女人枕着自己的手臂,自己又枕着女人的长发入眠,那感觉真是好极了。心情愉快的时候,活动起来一点不碍手碍脚,只是有时动作过大会扯痛女人的头发,弄得女人咤呼呼的叫喊,偶尔也会埋怨怀贵几句,但女人并不真生气,似乎倒是很愿意让怀贵在关键时刻扯痛自己的头发。那样,天亮之后,女人就能有心有肠地对着墙上那块状如新月的破镜慢慢精梳细理。
女人又哼了一声,同时扭了扭身子,怀贵就把手从女人的头下抽出来,问:
“我扯着你的头发了?”
女人放在枕头上的脑壳来回滚动了一下。
“不是,是我肚子痛。”
怀贵一下子就没有了尿意,慌忙急火地把头拱进被窝,偏着脸把一只耳朵听诊器似地贴在女人胀鼓鼓的肚子上,又用手指关节轻轻敲了敲女人肚子,传出的音响效果沉闷得如同三伏天熟透的西瓜,怀贵在被子里面嗡声嗡气地问:
“是上边疼,还是下边疼。”
“是下边。”女人长长地哼了一声,“怕是要生了。”
怀贵心里掠过一道喜色之后随即又紧张起来,就掀开被子拍拍女人的脸说:“憋着,再想生都得憋着等我把麻三娘找来再说。”
女人喘着气说:“你得快点啊。”
“一哈哈就来。”怀贵跳下床,边穿衣裳边用脚在地上摸索着趿上鞋子。
怀贵开开门的时候,满天都大亮了,明晃晃的亮光挡都挡不住地挤进门来,怀贵跨出门一反手将亮光关在屋里,随着关门声,门口的粪凼边一下子冒出个人来,冷不防把怀贵吓了一跳,怀贵一看是大嫂才松了口气。
大嫂家和怀贵家住一连房子,分家的时候,家里唯一的茅房分给了怀贵,门口唯一的粪凼就归了大嫂家。分了家的怀贵嫂整天勤劳得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蚂蚁,空手出门从不空手归家,无论是禾是草都得捞一把回来,能沤则沤,能烧则烧,不到一年,往年间一潭臭水的凼里尽沤了山上搂来的木叶杂草,捡来的牛尿马粪,弄得一粪凼山堆海填五颜六色。怀贵哥常年在云南文山帮人挖锌矿,除隔三岔五寄点钱回来,一年难得回家一趟,怀贵嫂带着两个娃儿和一帮猪牲口在家,一时就腾不出手来修茅房,但精明的怀贵嫂从不吃家饭屙野屎,有屎有尿都得往自家的粪凼里流。
怀贵看见大嫂一脸通红的提着还没来及系的裤子,难禁的散尿点点滴滴洒了一裆,心里就笑起来,脸上却装没看见,一本正经地说:“大嫂你忙你的。”
大嫂受了刺激,心里就对怀贵不悦。没好气地说:“怀贵你个砍秋头的,大清早不陪你媳妇睡回笼觉,疯天磕地的起来游百病?”
“我媳妇要生了,我得去请麻三娘来接生。”
怀贵大嫂不屑地噘着嘴说:“你媳妇又不是没下过蛋的雏母鸡,生过娃娃的女人再生娃娃才当屙泡硬头屎!”
话虽如此,怀贵还是很不放心地说:“儿奔生、娘奔死,命隔阎王一张纸,这事还是大意不得。”
说着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怀贵大嫂见怀贵的身子转过房拐拐,又下裤子继续处理未尽之事。
二
麻三娘住在村子东边的龙家老坟山脚,与怀贵家隔着一坝不到一里路的弯子地,弯子里全是一墒墒的包谷洋芋,地埂边全是青枝绿叶的核桃梨子树,去麻三娘家的路就蛇样的缠绕在团团簇簇的绿色里。
这是盛夏的六月,正是长庄稼的黄金季节,老天爷今年似乎格外开恩,总是把天气调和得很让庄稼人可心,整个夏天都是昼悬艳阳,夜垂细雨,且雨脚短、雨丝柔,舒舒缓缓,恰到火候地把地里的泥土溻湿,等来日天晴,日头一照,满山遍野雾气腾腾,高处的尖山梁子,低处的牛栏江畔,眼前的庄稼地,全都泛着迷幻的乳白在山野和包谷林中漫漫地舒卷。这般雨顺风调的气候,咋不养庄稼?往年间长到老死也就齐人高的包谷杆,今年全都一窜就是楼高,怀贵举手也摸不到天花。包谷茎杆的骨力也很好,马刀般锋利条长的叶子,泛着油色的墨绿。这是施足了底肥吸足了水份晒足了阳光才会呈现的颜色。现在,包谷正在扬花授粉,满地都是粉白的天花和粉红的缨须,每棵修长的茎杆上都扒着一个胀鼓鼓的青包谷,空气中到处飘溢着腥甜的乳香,看上去就像穿红着绿的少妇背着熟睡的娃娃。让人心里痒痒的动心。
怀贵投降似地举着双手左右推挡着生有锯形小齿的包谷叶,在地里三弯两拐一路小跑,一会儿就到了麻三娘家。
麻三娘家也是泥巴夯的墙,茅草苫的房,门口用泥巴围了个小院,院墙上全是刺林林的仙人掌,几只早起的小花母鸡和一只衣着艳丽的大红公鸡在院里悠闲信步,鸡们见了怀贵,就都昂着头把脚步走得很小心。倒是圈睡在门口石猪槽旁边的火斑狗仍懒洋洋地躺着不声不响,好像对怀贵这个活物的到来一点也不感兴趣,暗地里却开只眼闭只眼地瞅着怀贵的一举一动。怀贵认得狗是想瞅冷饱偷袭他,就先下手从墙脚抓了把捡粪的钉耙来撵狗,狗就鬼火绿了,后腿一蹬,扑上去咬住钉粑,喉咙里发出叽哩哇啦的吼叫,怀贵握着钉粑的柄不停地捣。
两个打得正热闹,麻三娘家的门开了,里面现出麻三娘的小儿子毛村长来,毛村长揉着干涩的眼窝狠狠地踢了一脚狗屁股:
“狗日的,你咬个球。”
狗惨叫了一声松开咬着的钉耙,夹着尾巴委屈地躲到墙角的院窝里去了。
毛村长走到门口的院坝里,蹶着屁股从前面掏出股黄霜霜的尿对着地上摇来摇去地扫,两眼直楞楞地盯着一地泡沫的尿水问道:“怀贵,大清八早的你有啥事?”样子就像是询问他屙出的尿水。
怀贵见了心里就像有个小虫子爬,别别扭扭的怪不舒服,但又不便做嘴做脸,就把钉耙靠在墙脚说:“我媳妇又要生了,我来找麻三娘去捡生。”
毛村长双手捏着前面用力一抖,将残尿抖尽,顺手把东西塞进裤子:“再生你家就超计划了。”
怀贵苦着脸说:“天不亮就喝嘘呐喊的,出都要出来了,再超计划我也让他回不去了”
毛村长拉上裤子的拉链说:“谁叫你鸡巴闲不住!”
怀贵吱吱唔唔的正不知作何辩解,却听麻三娘隔着门在屋里喊:“是怀贵来了,快进屋来蹲。”
怀贵一看,麻三娘正拖鞋散带地站在堂屋中央一脸笑色,没有扣上纽子的大襟衣裳披披扇扇地耸拉着,样子邋邋的,却处处透出普通农家妇女的慈祥与和蔼,一点不像她当干部的幺儿毛村长,自从一当上干部,说话就哼哼哈哈的,时时打着一副神崩崩的官腔,只有见到县里乡里的官们他才会蔫下来像霜打的秋茄。怀贵就想,人一做了官就他娘的不是东西,从上面往下看他是沉在水底的孙子,从下面往上看他是悬在半空的爷爷。其实在官场上混事,说白了也就是一级给一级当儿子,表面上看起来比做百姓神气,骨子里其实也并不比做百姓快活多少。一个小鸡巴村长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样一想,怀贵刚刚被毛村长日弄在肚里的气就消了许多,肚子消了气,心里也就比先前好过多了,心里好过的怀贵就一脸轻松地对麻三娘笑笑说:
“忙不赢蹲了,三娘。”
“咋会忙不赢蹲了?”
“我媳妇临盆了,麻烦三娘去捡个生。”
一听说生娃娃请接生,麻三娘的兴趣就提起来了,偏着头认真地问:
“疼了没有?”
怀贵说:“天麻麻亮就疼了。”
麻三娘扭着脖子看看天,估摸了一下时辰,自言自语地说:“头胎死喊辣叫,不哭不掉;二胎一疼就破,一破死掉;三胎月份一到,当屙泡尿。你家里都是三胎了吧?”
怀贵说:“正是。”
“那就耽搁不得了”,麻三娘说着,用手拢了拢头发,扣好衣扣,系上围腰,扎紧绑腿带子,头不梳脸不洗就动了身。
临出门,又叮嘱毛村长把猪食锅烧在火上。
毛村长没开腔,和四眼狗一道站在院窝里一脸不悦。怀贵知道毛村长还在为自己超生的事不高兴。
三
怀贵和麻三娘到家时,女人正躺在床上呲牙咧嘴地惨叫,怀贵嫂佝腰驼背地矮着身子,双手扳着女人的两腿帮女人鼓劲。面前放了个小木盆,盆里装了大半盆倒红不黑的污血,以及粘满污血的草纸和破衣烂襟。
怀贵大嫂见怀贵和麻三娘来了,结结巴巴地喊道:“快点……,快点来看,事情麻砸了。”
怀贵过去一看,只见女人下身像夹了个砍了头的羊脖子,脖子里伸出一只血淋淋的小手,小手一扬一扬地抽搐着,像是想抓住什么,又像是在与世外的亲人告别。
怀贵脸就吓白了,身上顷刻沁了一层冷汗,痴呆呆地张着死鱼样的嘴说不出话来。
倒是麻三娘沉得住气,瞅了眼女人的身子,就挽着袖子果断地说:“舀一瓢水来。”
怀贵这才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地从缸里舀了一瓢水递给麻三娘。
麻三娘接过水瓢,埋下头攒劲喝了一大口,含在嘴里,两个瘪狭狭的腮帮一下子胀得像装满了尿的猪尿泡,然后也像猪屙尿一样弯着腰一挤一挤地把水喷到手,两手麻利地交替揉搓着,搓完,拉起胸前的花围腰揩揩,才又直起身吩咐说:“找三份焚钱,三柱馨香。”
怀贵踏着三娘的话音,脚板翻天地跑进厢房寻来。
三娘接过香纸点燃,在怀贵家奉供着天地君亲师位和列祖列宗神位前的香炉里焚了,念过咒,作过揖,回头对怀贵正色道:
“保大人还是保娃娃?”
怀贵两者都割舍不下,含泪乞求说:“大人娃娃都望三娘一起保。”
“那就看你命中的造化了。”
女人先是掏心肝地叫,后来就大口大口地喘气,像一头摁在案板上抽了刀的猪。被泪水汗水和发丝弄得一塌糊涂的脸色阵白阵黑,咬破的嘴唇把满口白牙污得俨如挨刀的石榴籽红红艳艳 。
怀贵不忍心眼睁睁地望着女人受苦,就硬起心肠把头歪朝半边,任由止不住的泪水慢慢地模糊了双眼。
麻三娘却出奇的冷静,不慌不忙地把胎位重新推正了,抬起头大声对女人说:“你现在开始使劲挣,像屙尿一样使劲往下挣。”
女人就翻着白眼使力,咧着的半边嘴裸露出咬得格格直响的牙,闭着的半边嘴则不住地往外吹着血泡。
怀贵拽着女人的肩头往后拖,怀贵大嫂压住女人的腿往外扳,麻三娘拉着娃娃往外引,女人按着麻三娘的号令往下挣,四人通力合作,终于把娃娃完完整整地从母体里揪了出来。
麻三娘倒提起娃娃轻轻拍了拍长满黑色绒毛的背,吐出咔在喉咙里的羊水,娃娃一下子手舞足蹈地哭出了声。
怀贵勾下头睃了一眼娃娃的下身,锁住眉头的皱纹就慢慢展开了,忙附在女人耳边说:“是个屁股上别枪的货。”
女人嘴唇动了动,却没气力吐出声来,便眨了眨迷茫的眼显出少有的亮光。
麻三娘把娃娃放在怀贵的一件破衣裳里裹好放在女人身边,看看娃娃又看看床上的女人说:
“怀贵你祖上的阴功修得好。”
怀贵嫂接过话头道:“要不是三娘这两招,怕是再好的阴功也保不了命哩。”
三娘不以为然:“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不该绝自不绝,凡事都有个定数。”
怀贵嫂从床下抓了把草纸垫到女人屁股下,对怀贵努努嘴:“还不快去找匹红来给三娘挂上感谢人家三娘。”
怀贵应着拔腿就往楼上爬。
麻三娘阻挡着说:“不挂了,不挂了,只要他娘俩个平平安安我就落心了。”
“前人兴下礼,后人照礼行,不挂咋行。”
怀贵嫂转身从水缸里舀了瓢水,笑眯眯地看着麻三娘说:“三娘,我淋水给你把手洗了。”
麻三娘就把一双沾满鲜血的手伸过来。
刚洗完手,怀贵就从楼上找了段红布下来交给大嫂,怀贵嫂接过红布,哈着腰对麻三娘笑道:“请三娘挂红。”
麻三娘假巴意思地推辞说:“团团转转的人,恁个整不好意思沙。”
“这是正理正当的哩。”怀贵嫂说着,又让怀贵抬了条板凳横在大门口的门坎边。
事已至此,麻三娘也就不再客气,扶正头上的大包头,拍打拍打屁股上的灰土,就昂首挺胸地站在怀贵安放好的板凳上。
怀贵嫂清了清嗓子,吐出一口黑糊糊的浓痰,双手托起红布缎子高声颂道:
这匹毛红又长
出在苏州绸锻行
苏州有个巧女子
织出毛红挂三娘
……
怀贵大嫂颂完,将托起红布哈达一样挂在麻三娘的脖子上。
这时,毛村长提了把弯弯镰刀一摇一摆走了来,见他娘那副样子,就忍不住笑起来。
怀贵说:“村长你笑啥。”
毛村长收住笑说:“你们把我娘弄得像明星一样。”
怀贵说:“明星是哪个村的?”
毛村长说:“明星你都不知道?”
怀贵吃惊道:“村长交游好广,连世界明星也认得。”
“认识个吊毛”。毛村长说,“天天看电视,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
麻三娘侧着身子从凳子上下来,问毛村长:“猪食锅烧在火上了?”
“烧在火上了。”毛村长说,“小丫口肖二发争老晏文家的地打伤了老晏文的老婆,我要去断案去,晚上可能回来的晚。”回头又问怀贵,“生的顺不顺?”
怀贵笑着说:“开初不顺,后来让三娘弄顺了。”
毛村长连连道:“顺了就好,顺了就好。”又问,“生男生女?”
怀贵答是生男。
毛村长说:“这回你终于有了‘接班人,计划生育的问题该去了结了吧。”
“怎么个了结?”
“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三胎又扎又罚。”
怀贵苦着脸哀求毛村长:“等满了月后就去扎,罚款的事你就免了吧,人家在外头打工的超生户不扎又不罚。”
“哪个超生户不扎又不罚?”毛村长拿眼睛狠狠逼着怀贵,“你讲出来。”
怀贵说:“前两天听朱二狗说,他家的收音机里有个叫黄宏的在外头打工,参加超生游击队后生了五六个娃娃都不扎不罚。”怀贵说完,怕毛村长不信,又说,“不信你去问朱二狗。”
毛村长也拿不准是真是假,就黑着脸用手指着怀贵的鼻子警告说:“想得通的自己来,想不通的送起来,往外跑的抓回来。这是村里的‘三来规矩。怀贵你要是打错算盘进城去参加‘超生游击队,我就派‘敌后武工队在后方端了你的老窝。外加撵猪吆牛扒房子分田地杀你鸡犬不留。”
怀贵说:“村长你是不想让我一家老小活了?”
毛村长说:“活不活不关我的事,但我们村是全县计划生育先进村,这块牌子不能让你怀贵砸了。”
怀贵说:“村长你是把我往死里整哩。”
“鸡巴二哥整你”,毛村长瞪着怀贵说,“你要不是想生儿子,我整你搓球。”
“我想生儿不仅是为了培养传宗接代的接班人呀村长。”怀贵满腹委屈一脸小心地望着毛村长:“你看我们这山旯旮里头,无水无电无马路,薅刨点种吃喝拉撒,犁田耙地,样样都得肩挑背驮,样样都离不开力气,样样都离不开男人。”
“怀贵!”毛村长见怀贵把话说得离了谱,厉声喝道,“我看你是屁眼屙尿——反了,你这话要告上去,你龟儿子不背大时才怪。”
怀贵嫂见两人说上了火,就过来劝毛村长说:“怀贵是一根肠子通屁眼的笨货,有口无心,毛村长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毛村长却不依,说:“这是原则问题,不收拾他怀贵,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就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
怀贵嫂说:“毛村长你大人大量,你就把他当个屁放掉算了。”
麻三娘见毛村长还不想松口,就过来喊着村长的小名说:“三儿,怀贵他嫂说的在理哩,做官是要讲个原则,但更要通情达理哩……。”
毛村长不耐烦地说:“娘你不懂就少搭点白。”
麻三娘见了儿子当着外人下她的面子,就来了气,正想发火,忽听屋里胎娃娃惊喳喳哭起来,床上女人也弄出异样声响。
怀贵跑进屋里不多时又跑出来,说:“怎么还流血呢?”
怀贵大嫂说:“都生过两回了,不会有什么的,你们男人呀。”
毛村长怕有闪失,建议送王医生家看看。麻三娘和怀贵嫂心里虽有看法,嘴上却不好说什么,不过她们还是帮着把女人弄到板板车上,由两个男人拉走了。
四
来到王医生家,王医生正一个人在家喝酒。看见两人来,并不注意车上拉的是谁,高兴地说:“村长你还欠我一顿酒呢,正好,你快来喝吧!”
毛村长指着板车对王医生说:“怀贵女人生娃娃大流血扎实得很,你先给她止住血再说。”
王医生放下酒杯不屑地冷笑道:“女人生娃娃不流血还生球的娃娃,既然人都拉来了,那就看吧。”
三个男人把女人安顿在耳间屋里。
怀贵望着王医生肥滚滚的后背不放心地试探着问:“会不会有啥闪失?”
“有卵闪失。”王医先十分肯定地否定了怀贵的担忧,从容地从一个小铁盒里夹出一颗针头,接在一根肉色的长皮管上说“吊一瓶液水,撒一泡尿,回家闲一个月你晚上就可以用了。”
怀贵有点不好意思,红着脸说:“王医生你真会讲阴知文。”
五
王医生给女人输上液诟 ,就招呼毛村长和怀贵出来吃饭,两人肚子正饿,也就不讲客气了。
饭桌上摆了几大碗嫩豆花、洋芋丝、红豆酸汤和腊肉墩子。菜不多,不像城里人盘盘碟碟的细做,却很对庄稼人的胃口。牛栏江边的庄稼人在吃食上就讲究个大气和实惠。帮人干活要做大力,请客吃饭要用大碗,弄得不干不净倒在其次,但份量一定要富足,待客一定要热情。舍不舍得请客人吃,诚不诚心请客人吃,关键的一道菜就是肉。肉不能切成片,也不能拉成条,更不能剁成沫,只能解成墩,否则就显得主人太小气太没有诚意。如果是家道清贫,没有肉的人家,有豆花也行,豆花白净不白净虚小,但一定得嫩,嫩才鲜,鲜才香,香才有吃头。
毛村长和怀贵落座后,王医生从碗柜里提出瓶威宁小曲拧开,将每人面前的酒杯倒满,放下酒瓶时,王医生笑盈盈地问怀贵:
“你媳妇给你生了个满山跑的还是锅边转的?”
怀贵就笑笑说:“是满山跑的。”
王医生端起酒杯对怀贵说:“那第一杯酒,就为百年之后有了七月半给你发工资的人干杯。”
“对头对头”毛村长也举杯迎合说,“为怀贵今天喜添贵子,干杯!。
怀贵见王医生和毛村长恁个抬举自己,觉得不好再推诿,就腼腆地端起杯一仰脖子喝了。
王医生一抬手又将酒杯倒满,放下瓶子时对怀贵一笑:“这杯酒该你发个言。”
怀贵也想借此机会说两句感谢毛村长和王医生的心里话,就站起来双手毕恭毕敬地托起酒杯,嘿嘿地笑着说:“多谢毛村长和王医生帮我生了个儿子,我敬你们一杯酒。”
王医生却不喝说:“帮你生儿子的人是毛村长不是我,要敬你得先敬他。”说完两眼开一只闭一只地瞅着毛村长笑。
毛村长张口将酒泼进嘴里,埋着头闷声闷气地说:
“你莫扯卵蛋,爱喝就喝不喝算球。”
怀贵见毛村长喝了,就把酒杯对着王医生请王医生喝。
王医生说人情各有所归,你这杯酒敬的是毛村长,要怀贵单独跟毛村长喝了再和他喝,怀贵只好喝了,又另敬王医生一杯。三杯酒下肚,怀贵感到脸上热烘烘的发烧。但一想到自己终于有了儿子,浑身就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毛村长说:“空肚子喝寡酒胃顶不住,悠着点。”说着夹了坨墩子肉塞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嚼。
王医生也不深劝,说:“随意,随意。”
三人边吃边喝边摆龙门阵,一瓶威宁小曲不知不觉就见了底。
王医生又重新拿了瓶威宁小曲,咧着嘴用牙齿把封口的铁皮盖子咬开。
毛村长忙伸手挡着酒瓶说:“不能再喝了,我还要去小丫口断案。”
“断个啥子案?”王医生似乎不相信毛村长的话。
毛村长说:“肖二发抢占老晏文的地还打伤了老晏文的老婆。”
王医生一下将酒瓶夯在桌上,吓得满桌碗筷都跳起来:“狗日的肖二发,啃不动青杠啃泡木,光欺负老实人。”王医生红着眼咬牙切齿地说,“就凭这事,你毛村长也得喝一杯,喝完老子跟你去把狗日的肖二发依法拿下。”
王医生疾恶如仇的样子让毛村长心里有些感动,就说:“那就只喝一杯,下不为例。”
三人就又为肖二发喝了一杯。毛村长苦着脸吞下酒后,哈着气喊:“扒碗饭,扒碗饭。”
王医生不同意,摇着酒瓶说:“饭肯定要吃,但这瓶酒盖都揭了,不喝完就跑气变成水了。”
毛村长说:“不能喝了,再喝就醉了。”
王医生把脸一拉:“当干部的,哪能喝这点酒就醉,人家干部不光喝酒,还找小姐呢。”
毛村长听了叹着气说:“唉,人家那是说城里当官的,我吊毛一根大的小村长,莫说是找小姐,连寡妇婆娘都找不着。”
毛村长夹了口菜,嚼着嚼着突然问怀贵知不知道王医生的门牙咋会缺了一颗。
怀贵一看,才发现王医生的门牙果然缺了一颗,就摇摇头说:“不晓得。”
毛村长把菜咽下,慢腾腾地把筷子斜搭在菜碗边说:“去年春天,王医生的二弟去兰坪挖锌矿,一去就是一年多没回来。家里女人熬不住了。晚上睡觉就选一只个头大的鸡蛋往下面弄,结果一不小心就把鸡蛋弄进去了。想去乡医院看医生,乡医院的医生都是男的,觉得让外面的男人摸了自家的宝物不划算,还是觉得肥水不落外人田,自家的肉烂在自家锅里好,就厚着脸皮来找王医生解决。王医生含一口冷水来,猛地往里面一口喷进去,二弟媳一个激灵,肌肉一收缩,就将鸡蛋一下子挤飞出来,把王医生的门牙打落了一颗。”
毛村长讲完,不看王医生。也不笑,捋起筷子又继续去桌上拈菜。怀贵却不忍不住了,噗地一声将嘴里嚼得半残不落的酒菜喷了一桌。正好笑出声来,王医生将酒瓶子一下砸在桌上,乌毛乌嘴地瞪着毛村长说:
“毛稳根,你给我少开点黄腔。”
毛村长见王医生生气了,就笑着说:“我是开玩笑的”。怀贵一见这阵式,就不敢再笑出声来,忙把笑意强行咽进肚里,喳得肚子一鼓一鼓的,像偷吃急食的小公鸡被包谷籽卡了喉。
就在这时,怀贵嫂来了。毛村长借着酒意拉她手说:“多一双筷子,坐下来我们一起干!”
怀贵嫂岔开话题问怀贵媳妇的事。
怀贵用手一指王医生家的耳间房,说在里面吊液水。大嫂听了就径直朝耳间房走去,刚走到耳间房门口,突然回头急赤白脸地喊:
“王医生,王医生,液瓶子吊空了!”
听到怀贵嫂的喊声,才想起耳间房里还躺个怀贵女人。怀贵抢在王医生前面挤过去往病床上一看,脑袋瓜“嗡”地下子胀大了,只见女人挂着吊针的手早已从掖好的被子里伸出来悬在床沿边,吊针锁针一样歪歪斜斜地别在手背上,液水从穿空的针头流出来,全部输到了床前的地板上,床上的毡子被子全被女人流出来的血浸透了。怀贵就一下子扑在女人身上绝望地哀嚎道:“唉哟——绝尾巴婆娘唉,我着你做掉了,天宽地阔你不死咋就偏偏死在这里,你叫我咋个整啊!”说着两腿一软,一下子从女人身上滑落下来,“咚”地一声跪倒在王医生面前,把头连三赶四地往地上磕,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着王医生讨饶:“对不住人罗,王医生,今天对不住人罗……”
一直痴呆着的王医生这才回神来,慢慢从地上扶起怀贵说:“短命牲口遇上蚀财人,命中注定我们两个都该倒霉。”
怀贵嫂见王医生把话讲得这般通情达理,很是感动,说:“王医生不愧是久跑四外见过世面的人,把什么事都看得开。”
毛村长说:“怀贵把人弄来死在人家里是犯忌的,按理得请人给王医生家收拾扫送才行。可怀贵也不是故意的,我看就给王医生家挂个红把人拖走算了。”
怀贵大嫂说:“村长讲的在理,我们这就找红来挂。”回头挑起眼角斜瞅着旁边傻呼呼的怀贵训道,“怀贵你个笨得屙牛屎的猪,还不赶快动手把你媳妇抬上车去弄走,嗅哄哄的死人一个又不是大牛大马摆在家头好看。”心里却想,再不赶紧走,等一下王医生反了悔,叫你哭都哭不去好声气来。
怀贵说:“要得,要得,我马上就抱出去。”
怀贵刚把女人抱到外面的板车上收拾完房间;怀贵嫂就从家里抱回一团红布和封火炮回来。
六
毛村长望着空荡荡的来路对王医生说:“明天早上送两千块钱到村委会来。”
王医生不明白毛村长的意思,问:“做啥呢?”
毛村长说:“明天村里要给怀贵发两千块钱的救济款。”
王医生苦着脸说:“我哪有那么多钱。”
毛村长说:“少一分老子都翻脸不认人。”说完也不看王医生一眼,就背着手一摇一摆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