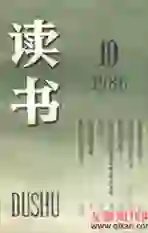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
1986-07-15王圣思
王圣思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十分复杂的作家。人们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前后不同。六十年代以来,陀氏越来越引起评论家的注目,关于他的评论研究文章和学术讨论会不断出现。
二十世纪初,西方读者对陀氏的礼赞并不普遍,只有少数读者作出预言,认为在托尔斯泰的巨大身影背后,陀氏即将崛起。预言变成了现实。一次大战后,西方对陀氏的兴趣日益浓厚起来,以至出现扬陀氏而贬屠格涅夫的时风。为此,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在《屠格涅夫传》一书中愤愤不平地说,指责屠格涅夫没有创作出象陀氏那样的作品,那是在为一棵苹果树没有结出桃子而抱憾。第二次大战后直至今日,现代派作家和相当普遍的读者更是狂热地迷恋起陀氏来。俄国文学的三巨头(屠格涅夫、陀氏、托尔斯泰)中陀氏在西方跃居首位。
陀氏在现代之备受重视,有其复杂的原因。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他同时代的作家大多如此,何以陀氏“一枝独秀”?我们认为,陀氏所以具有现代性,还得从他的作品的其他特色来分析。
陀氏作品中常常孕含有几种人生哲学。当然,优秀的文学大师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常表现几种不同的人生哲学。但作家的主调清晰,常常采用几种方式,或在人物中寻找自己的代言人,或将自己的思想倾向在场面中自然流露,或塑造理想的人物,或直抒胸臆。而陀氏作品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仿佛作家本人隐去,让人物各自表露思想,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又好象作家没有主见,一会儿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上,讲出貌似真理的理由,一会儿又从那个人物的角度,振振有词地予以反驳。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同时表现两种截然相反、互不相容的思想观点。这两种观点,有时并存不悖,有时互相交叉,有时彼此争斗。读者几乎一时难以分清谁对谁错,也一时难以捉摸作家的主观意图。这应当说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显著特色。
此处以《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例,稍作分析。
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平民出身的大学生。他的平民思想是平民环境赋予他的。他真挚、正直,具有人道情感。他憎恨富有者及其不义钱财。他深爱亲人,为无法供养她们而痛心。他常常穷得只剩几个戈比,却还尽力地帮助穷人。他观察到社会上存在着人吃人的现象。但是,他提出一种理论,正好与他的平民思想相抵牾。他认为,人有平凡和不平凡之分。平凡的人成千上万,乐于俯首听命,因为他们没有胆量去夺取金钱和权力,所以一辈子受穷,任人蹂躏。而不平凡的人是极少数,他们有天赋和才华,为达到目标不怕使别人流血,他们能昧着良心跨越人类的道德规范,心安理得地享用一切。他们是刽子手,却被世人尊奉为伟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得出结论,强者为王。他不甘心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想在资本主义激烈的竞争中成为统治别人的人。他自信自己是不平凡的人,但又怀疑自己能跨越人类的良心。他急于对个人意志作一番肯定或否定的检验。在他的理论中,他把他所同情的贫民都视为虱子,但同时即使在他预谋杀人时平民思想仍不断闪现。他选择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作为试验自己属类的对象。是他实施理论的第一步,但也是他平民思想中所含革命因素的流露。这个老太婆是吸血鬼,心狠手辣,她对大家有害而无益。杀死她,用她的钱可以救好多人。选择这个老太婆做牺牲品,说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理由并没有完全离开平民的是非判断。犯罪以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两种思想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对峙,有时轮番占上风。对普通人的鄙视和对“超人”的向往使他不愿轻易认输。而对穷苦人的同情和对有钱人的憎恨又使他保持正直的品质。他直到去自首前,仍没有彻底抛掉自己的理论,同时,他心中的同情心在索尼雅的启迪下,也震荡着回响。在弱肉强食的竞争社会中,有良心的人无法获得成功,他在对自己的愤恨中走向自首。作者在尾声安排他相信了宗教。走向自首是良心的驱使,信仰上帝则是无法调和的调和。
苏联评论家巴赫金曾对陀氏作品的结构冠以“复调小说”之称。他指出,陀氏作品中“许多种独立的和不相混合的声音和意识,各种有价值的声音的真正的复调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似乎很难截然分离,复调既是作品的结构,也是作品的内涵。多元化的思想内涵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的复杂的思想状况。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价值观、道德观等各种观念发生变化,传统观念受到新观念的挑战。不同的观念同时并存,引起城市平民的思想混乱。这类人物是生活中的弱小者,处于劣势,思想随波逐流。当新旧观念从四面八方向拉斯柯尔尼科夫等人同时涌来之时,他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各种不完全思想在他们头脑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各种思想的争论不休也就必不可免了。
应该承认,多种声音并存的现象毕竟是错觉。作家的主调表面上可以隐去,实际上无法真正抹掉。如同埃舍尔的画“画画的双手”,画面上两只手在互画,左手画右手,右手画左手,从平面上看,两只手似乎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其实,互画的双手是由画家埃舍尔的手画出的。如果我们能想到画面以外的那只手,也就能看到画家及其观察角度了。同样,在陀氏那里,作品由他构思,情节由他安排,他的主观意图不能不表现出来。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看到,作家把索尼雅的生活态度奉为理想圭臬。他置索尼雅在一切人之下,她的妓女身分,即使在贫民中也备受歧视。而他赋予她善良、温柔、同情心等美德。她逆来顺受、容忍、宽恕一切。索尼雅是以善抗恶的圣女,是作家为其宗教信仰而塑造的形象。如果陀氏仅仅刻划了这样的人物,那他只能是一个三流作家。不,陀氏的思想从来不象索尼雅那样单纯,他的内心从来没有平静过。尽管他放弃了社会主义信念,但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赞成它,世间的苦难和不公正以及他的贫穷处境更是时时激起他的义愤和怨恨。我们可以想象,在创作激情的支配下,作家本人一定也会在假想中不止一次地举起斧子砍杀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正是在作家的手稿里,我们看到,陀氏在构思中列举出拉斯柯尔尼科夫杀老太婆的理由(杀一人可以救活百人等),作家在书页边上注着:“这是真的,他妈的!”这句活真切地表达了作家内心的真正激动。陀氏的价值就在于他将那些激动他的很象真理的东西表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也将自己分裂的思想体现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这位主人公对社会充满憎恨,处在神经质的理论臆想之中,进而采用极端的手段反抗恶劣的处境。他藐视上帝,是以恶抗恶的典型。索尼雅只不过是作家理性思考的结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才是作家激情狂想的产儿。在这个人物身上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和痛苦,也就特别具有艺术魅力。产生这种写作形式的外在原因是当时俄国社会的多结构性和矛盾性,它们为陀氏提供了结构小说的模式。我们认为这种模式更易于为现当代读者所理解。因为现当代社会的结构性和矛盾性比陀氏的时代更为庞杂和繁复。传播媒介迅速而大量地传递信息,全球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着种种重大事件。人们不再满足于认识狭隘意义上与己相关的事物,而把世界看成互有联系,互为因果的巨型网络结构。人们要应付千变万化的现实,还要时时面临众多的选择。多元化和多样性成为现当代明显的时代特征。现当代的人们看陀氏作品会产生一种共鸣。也许,对其表现的内涵会各有取舍,但对其内涵复杂纷乱的状况及其表现形式则会发生强烈的共鸣。陀氏在上世纪后半期就以文学的样式提供了他对社会观察的角度,与现代人对世界的领悟正好相符。
多元化的哲学思想引起人物的思想混乱,必然导致思想分裂乃至心理分裂。而复调的结构也正适合于表现这样双重分裂。陀氏着重描写了人物的心理分裂,他从人物的变态心理刻划入手,揭示出人性的深度。如果将陀氏对市民心态的表现看作是群体现实心理的反映的话,那么他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心理剖析则可以视为个体深层心理的坦露。陀氏将主人公置于特定的事件中,造成主人公心理分裂的极端化表现。他刻划了主人公犯罪前后、尤其在杀人之后的畸形心理扭曲。主人公在“超人”思想的折磨下蓄谋杀人,他的自我意识已出现分裂。在作案之时,主人公心理极度混乱,行为失控,精神上的反常举动也已暴露无遗。杀人之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精神濒临崩溃的境地,意识的综合力失去作用,彼此分裂的意识同步活动,而分裂的意识又与无意识、潜意识、下意识搅和在一起,或交替出现,或同时并流。人物内心的骚乱不安超越了神经中枢控制的极限。拉斯柯尔尼科夫时而处在亢奋的清醒之中,藏匿赃物,消灭罪证;时而陷入热病的狂癫状态,出现女房东挨打的幻觉,产生恶梦和惊吓;时而故作镇静,试探警方虚实;时而丧失理智,表现出无意识、下意识的冲动……。总之,在他内心非理性与理性并存,无意识与意识相交。
任何人的心理都不免带有变态成分,但变态的反应往往一闪而过,甚至本人一时都无法意识到,而有时这种变态的成分在常态心理的对照下恰恰表现了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陀氏将笔触深入内里,抓住人物内心在瞬息间闪过的下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的反应,集中地加以动态描写,将人性最隐秘、最不易捕捉的心理状态用文字表达出来,一下子公布于众。这就是陀氏艺术具有震撼人心的深刻之所在。陀氏不承认自己是心理学家,他认为自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确实,他将人作为自己一生研究的对象,他说:“人是一个谜,我要探索这个谜……”。他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对人深层心理的剖析,除了他对他人进行精细地观察之外,还不能排除他个人生理、病理上的体验。他父亲的性情暴躁易怒、阴郁、神经质。遗传因子对作家本人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影响。苦役生活的后遗症——癫痫病(羊癫疯)更使作家亲身经历了病态心理体验。因此,陀氏能用文字形象开掘人类认识自身心理的新领域——变态心理、无意识领域,寻求人们内心异常骚动不安的潜在心理根源,帮助人们重新发现自己,进一步深刻地认识自己。这正是陀氏对文学所作的最大贡献。就揭示人类深层心理从而展现人性的深度、灵魂的奥秘这点来说,陀氏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超越了俄国的时空。
法国作家纪德在他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九二二)中谈到二十世纪初西方读者对陀氏的非理性表示反感,指责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的不是人生,而是恶梦。曾几何时,西方读者的看法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恶梦般的两次大战在亿万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人们在自己亲身的经历中认识到,恶梦是人生的一部分。同时,现代哲学进一步发展,尤其现代心理学诞生,将变态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从中挖掘了无意识领域,并且打通常态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的界限。这一切促使人们用理性去认识非理性,用理性去研究无意识。借助于科学的探索和哲学的眼光,人们对陀氏的先见之明也就赞叹不已。在经历过一场场人间灾难之后,人们自会较为清醒地认识世界,反省自身。当然,人们可以从文学教诲的作用出发,对陀氏及现代派作家的非理性和病态描写持保留态度。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不合理的根源。如果真正理解“心病还须心药医”的道理,即使仅仅为了了解病情,也有必要读一读陀氏。
人物由于内心呈持续的分裂状态,其孤独感也就必生无疑。陀氏挖掘了主人公的孤独感,它正蛰居于分裂内心的裂痕深处。拉斯柯尔尼科夫善于思索,一向自视甚高,也就离群索居。贫困的生活使他回避熟人,尤其因为付不起房租,更常常躲避女房东。他是陀氏笔下有思想的主人公,分裂的思想、分裂的心理使他充满矛盾和痛苦,他更多地注视自己内心的冲突,而与世人保持一段距离。在他杀人以后,良心的谴责使他感到一种彻底的孤独,他承认杀了人,也就杀了自己,剪断了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他怕露出蛛丝马迹,就把朋友赶走;他自从有罪,而伸不出手去拥抱亲人;对卢仁之流,他又誓不两立。因此陪伴他的只有强烈的孤独感。人多的时候,他渴望独处;独自一人时,他又希望找人倾诉。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他终于在索尼雅那儿找到同情,即使在脱卸心灵重负的情况下,孤独感仍然缠绕着他,他对己对人都憎爱并存,对索尼雅也不例外,在爱中闪过恨,在恨中寓有爱。他与别人无法在思想上真正沟通,无论是妹妹还是索尼雅都没有真正理解他。而他对自己也无能为力,无法将分裂的思想、分裂的内心统一起来,他的孤独感也就难以消除。
在常态情况下人与人是可以交流,可以沟通的,但因为人性的复杂,因为人内心的变态因素,因为有某些难以表露的隐秘情感,使人与人在深层意义上的沟通碰到了障碍。天才的人物在他的时代不被理解,往往也会产生孤独感。当一个人处在变态心境下,他与处在常态心境的他人更难对话,孤独感也就有增无减。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要存在着人,就存在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就会产生理解与不被理解的问题,协调与不协调的问题。在某个局部范围内,一旦个人不被他人所理解,个体与群体不甚协调的话,孤独感就可能油然而生。青年在青春期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更关注于内心,也可能被孤独感所困扰。每个个体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环境,人生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都能诱使孤独的心境出现。因此,孤独感并不尽是俄国和西方社会的特有产物。而当今社会生活因物质环境迅速变化造成了种种矛盾纠葛,往往更令人感到困惑,也就益发加深了现当代人所共有的一种内在孤独感。当人们的目光从地球本体转向宇宙系统之际,宇宙间地球人的根本孤独感是人最深层的心理意识。也许,正是为了摆脱孤独感,人们才在科幻世界里寻找外星人,人们才主张社会生活中的互相关注和支持,人们才顽强地进行科学文化创造,以便尽可能地、自觉地进行交流和沟通。
陀氏的时代是一个动荡而转折的时期,是新旧交替的时期,是方生和未死的时期。在社会现实中,旧时代的、过渡时代的、新时代的多种社会现象混杂地存在。陀氏反映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城市生活是当时俄国现实的一部分,这部分恰好代表了新时代的社会现象,代表了当时的现代因素。他把自己对当时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融入他的作品中,以期获得同时代人的共鸣。可是同时代人对旧时代还记忆犹新,而对新时代的社会现象还没来得及全部领悟,因此,陀氏作品中的美学特质不易被人发觉,或者被歪曲理解。加上革命民主主义者们出于社会斗争的需要,较多地着眼于社会学的角度评价陀氏,也就不能不失之偏颇,从而忽略了他应有的美学价值。在遭到同时代人的误解和否定的情况下,陀氏进而宣称:“虽然我不为现在的俄国人民所理解,但我将为将来的俄国人民所理解。”确实,当他的作品作为一种遗产被纳入以后的时代,经过时间的检验和社会发展的验证,原先未被发现的某些美学特质此时正被发现,原先未予肯定的美学价值在重新获得肯定。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七月第一版,1.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