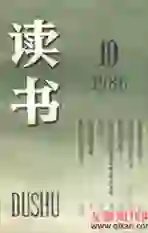文明与愚昧的倒错
1986-07-15叶芳
叶 芳
莫应丰的长篇新作《桃源梦》叙述了一个人性嬗变的故事。它的悲剧性结局从一个十分直接的角度证明了这样一种看法:“当‘文明的道德占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个人生活的健康与活力可能受损,而这种牺牲个人、伤害个人以激进文明的制度,如果升达某一个高度,无疑将反转过来,有害于原来的目的。”(弗洛依德《爱情心理学》)
这部小说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紧张、忐忑不安和带有恐惧感的阅读效果,这一效果所带来的明确结论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或曰宗教的)背景下,对人性的过度羁勒会产生远比放纵更难预计的可怕结果。
一
小说以保存物种的内容为线索,讲的是逃避土匪迫害的五户人家如何在一个荒无人迹的悬崖绝壁上重新生活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的故事。很自然,物种的保存和延续是被逼入绝境的人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正是保存、延续物种的这条独特的途径把这个与世无争的小社会引向了彻底覆灭的深渊。要弄清这一毁灭的发酵剂和原生力是什么,还得认真分析小说中描写的那个环境和那个环境中的文化、宗教和心理因素。
居住在三省交界的这个小盆地里的居民具有一种天生的、混杂的文化心理。他们既长期受益于风调雨顺、物产丰富的自然环境,同时又受到来自传统道德和交界地区强悍、诡谲的民风这两方面因素的夹击,因而在气质上掺杂着温仁、善良与自私、狭窄、狂暴等多种互相矛盾的基因。这些因素必然是日后产生不安定局面的潜在的火种,并且不断导致他们从道德固置的边缘走向道德倾覆的悬崖,周而复始,危险重重。同时也使他们对自身和外界的变化采取了极其敏感和猜疑的态度。
或许还与小盆地居民身上那种多民族的血统有关,盆地居民对玄想的兴趣大大影响了他们洞察世事后所下的判断。这种玄想的辉煌果实是盆地居民视若神明的龙居正的出生。龙居正的母亲和她的邻里一样耽于幻想和释梦。龙居正母亲怀孕时做的怪梦因其邻里的阐释而具象化,因而龙居正一出生即成了一个神奇的、仙风清骨式的人物。很有迹象表明这个后来成为天外天居民心中的偶像的圣人原是个先天不足者,因此见血即晕,又不吃肉,还常常受幻觉的蛊惑,他的思维中充满了星相说般的迷魂的预测性。爱好玄想的当地人则把龙居正的种种怪癖的举止都推想为一个新的救世主产生的征兆。从这一点看,盆地居民的文化背景中极少反映出儒家正统观念的掣肘作用。相反,他们倒更偏信某种机遇、巧合和自然现象中所包孕和潜伏着的神秘的力量。因而他们既信鬼神,又公然设想会有一个新皇帝的降临。
然而,耽于幻想并不表明小盆地居民是一群纯洁无邪的宗教信徒,他们从未摒弃过财富,他们所渴望的安宁生活是和荣华富贵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本是一群俗而又俗、充满欲望的凡人,却被玄想的气质罩上了一道眩眼的光圈。
于是悲剧的宿因早就潜伏于逃上山的居民的未来生活中。
土匪牛步天逼迫以龙居正为首的盆地居民逃离山下世界,似乎也只是这场悲剧中最为外在的一个契机,人们本以为这可能是个幸福(而不是悲惨)的开端。
对龙居正来说,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清苦生活是轻而易举的,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封闭、清心寡欲的人物。他的魅力在于面对恶势力时随时可以阐发的、即兴的、稀奇古怪的联想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所带来的信念上的平静会给予诚信他的人以宗教的力量和自信。
然而,他带上山的却是一群充满私欲、尚且惊魂不定的人群。对他们的净化是要以昂贵的代价为前提的。一开始,生活环境还是轻易地成全了他们,他们上山不久就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道德和社会秩序方面的防范制度。这个制度旨在克服私欲、净化道德、循规蹈矩。这也使得天外天居民顺利地避开了因自卫而误伤亲人时产生的自责悔恨情绪的刺激,从此相信有一种来自上天的神灵的力量在假龙居正之身传达它的旨意,维护天外天居民的生活秩序。
二
道德禁忌几乎是每个封闭性民族或国家把守生活秩序的一道人生栅栏。《桃源梦》中所描绘的正是这种力量与人性中最难驾驭的那部分自由天性的冲突。
在混杂着儒家三从四德和迷信、占卜内容的宗教背景下,龙居正作为善的化身领导着天外天五户居民的精神生活。他的道德宗旨是以善来对抗一切反动势力,这个“善”的实质是超世的精神。在各种世俗的矛盾冲突中它以消极、退让、忍隐为主要手段。
要建立天外天生活的道德秩序首先必须克服精神和情绪上的障碍。这种障碍的实质是对财富的渴望。龙居正以丧失一条胳膊的代价制服了天外天头一个野心人物张果树,平息了一场争夺土地的纠纷。尔后,在宗教情绪的推动下,龙居正那条断胳膊被作为祭礼供奉起来。因深受良心谴责而坐卧不安的张果树终因摆脱不了梦魇的折磨,啃起那条神圣的断胳膊来。这个可怖的行为却被当作善化的实际效果,张果树既然明白自己冒犯了神的旨意,他就必死无疑。于是天外天道德秩序就由这块沉重、恐怖却也强有力的基石奠定下来。重要的是,这样的情节进展表明那种至善的力量和信仰一开始就建立在带有残酷意味的自我鞭挞、虐待的基础上。至善的伦理至此已毋须考虑个人的利益,而以群体的伦理保障代替了它。这种情况的出现本源于经济生活缺乏充裕感的环境中。正如萨特曾分析的那样,“在匮乏的经济状况下,伦理学发展成为一道毁灭令,要求消灭‘作对的人,即具有威胁性的人,因为他是恶人。暴力就这样产生了,不过它始终自命为反暴力,也就是对‘别人的暴力的报复”。
当然,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天外天独特的宗教道德伦理似乎一直在起着一种防止伤风败俗、利欲熏心行为的作用,而且也确实显得颇有成效。它使天外天的居民有了一统的人生观。人们认为这种道德的纯洁性是神意的,凛然不可侵犯的。可悲的是,“偏颇不全的道德终必招致种种深可叹息的反动”,因而也就“足以败坏道德”。(《分析的时代》〔美〕M.怀特著)天外天的宗教并不见得比任何一种宗教来得更系统、宽泛和合理,它本身的缺陷因为狂热的阐释、幻想而缺乏足够的现实依据,一开始就如同一条被生硬地撕裂的缝隙朝毁灭的深渊伸展。
三
在这部小说中性爱时常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性内容来加以分析和描写。侏儒狗贱丑陋不堪,愚钝无知,却被人人平等和泛人道主义的社会法则赋予了极不相称的自尊心和傲慢性。他娶了漂亮的早啼姑娘为妻,充分享受了这个特殊社会的种种优惠和恩泽。然而早啼在性爱上的觉醒却完全背逆了传统的美德,她与木匠阿通的私情成为对通行的道德原则的第一次反叛。可以说早啼姑娘的追求是人性的一次自由舒展和享受。与此同时,另一个年青的男人麻秆自动与畜牲打交道,被天外天那种爱每一种生物如己一般的感情熏陶着成长,既然
可是,不管怎么说,牛人麻秆是在宽容的态度下被天外天居民所承认、首肯的。而浪子瓜青则是外强中干的天外天道德法则力挫的对手。早啼和麻秆都没有浪子瓜青那么聪明、机灵的头脑,因此不足以嘲弄那些神的旨意。浪子瓜青却天生一个犯忌者的形象。他公然不把大善童子像和善人们放在眼里,在他聪明的恶作剧中,神像、神话如同一层极脆薄的玻璃外罩一碰即碎,显露在人们眼前的仅是一堆泥巴和几团虚弱的肉身。这次可真正惊醒了天外天居民安详的、向神乞灵已久的迷魂,所有积聚已久、改头换面地以绝对平等控制个人意识的狂暴力量一下子复苏过来,在浪子瓜青身上找到了最好的发泄对象。此时所谓善化的观念已完全超越了一切,成为集法、权于一身的绝对观念。人们巧妙地也异常刻薄地让浪子瓜青在一间冷冰冰的、与外界,毫无联系的石屋里绝望而死。
至此,天外天这艘孤独的、凝滞在道德僵流中的船只已因为不堪人生负重而缓缓欲沉。这时导致这艘船只沉没的另一件更有影响力的事情发生了。
天外天青年三喊偶然地掉下了悬崖,看见了山下另一个世界的面貌,并带回了一个名叫珍珠的姑娘为妻。珍珠姑娘的衣着打扮、饮食起居的习惯都激起了封闭已久的天外天居民内心深处嫉恨的情绪。表面上天外天大多数人都以一种大度、慷慨的姿态对待那位既想吃荤腥、又有私有观念的外来者,实际上他们已无法再让自己禁锢在这道清心少欲的破旧篱笆后面,仅仅充当一名卫道士或旁观者了。于是,积聚已久、如沸腾的岩浆般难以控制的七情六欲以种种极端的方式喷发出来。宗教道德成为反道德、反秩序的原生力,它的自我分裂的结果使天外天得以支撑的精神大厦成了无数片再也无法纠集起来的残枝碎片。
陷入道德混乱中的天外天居民一下子撞开了毁灭的大门。野心勃勃、智力低下,却一直被允许与牛交媾的麻秆疯了,那条牛也成了杀人的刽子手。卫道士们无法正视这场牛杀人的惨剧,因为许多年来他们将人格赋予了畜牲,他们不能杀生,不能自卫,只有虚幻的信念和固执不变的道德教条。而现在这种信念也已风化,严守禁欲原则的人分化了。一些尝开了禁果的人首先觉醒过来,决心不再作无谓的牺牲以保全自己。然而,已经为时太晚,那些个以牺牲野心、情欲和私有制为代价,获取另一种虚无飘渺却也是绝对崇高的地位的人已深切感到精神上的彻底毁灭的到来。在野心和荣誉的双重损失下,他们牵引着整个部落的生命走下自我毁灭的极端。原是为了保存自己、对付外来侵犯者的滚石雷成了这个最终仍拒绝外来世界影响的小社会的葬身之地。
四
在莫应丰的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对狭窄的群体意识的表现和批判。这种群体意识的顶端是善化的观念,而整个过程则表现为对善的循序渐进历程的统一、驯服的内容。使人对那个环境感到窒息的不是某个人物,而正是那种超越了个性、情欲的规范化了的群体意识。这个群体意识起先是作为一道自卫、自强、自立的防线设立起来的,尔后当外患消除,这道防线渐化为一道套在每个健康的生命的脖颈上的死绳。并且,天外天的每个人都系结在这条致命的绳索上而无一遗漏。这个危险的整体中只要有人试图挣脱它的缠绕、获得个性的解放都将无异于将这一绳索往死亡的路上拽引。结局是必然的,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就这一点而言莫应丰是成功的。他用文字导演了一场现实悲剧,并且象魔术家一般用仅有的一条情节绳索打了个似乎极有希望的活结,然后让人们沿着他的手法行进,在终场时让读者兴犹未尽,只是结局已很明朗,无需再续。
但是,既然作者把一个近乎编年史般的开端展示在读者面前,读者便有理由希望自己在作品中有更多层次、更丰富联想的发现。确实,小说绝不乏精彩的细节、情节和人物。比如那个部族公子狗贱便是个极出色的人物形象,有多种文学因素包容其间。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人类许多种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比如那个恋牛的麻秆和浪子瓜青,也是文学作品中十分独特的人物,让人卒读全文后还回味不已。可是,或许正因为作者充分地强调了那种以善为核心的集体宗教意识的作用,结果把小说思想的运转跑道规定的过分清晰、明确了。读者们绝不会逾雷池一步,因为作者老不忘记把读者拉回既定的目标上来。因此,阅读中虽也够惊心动魄,读者的思绪却也循规蹈矩,始终不脱离作者指引的航线。
当然,我这么说并非要求小说的思想意义模糊不清或模棱两可。我的意思是当一部小说具备了坚强的核心内涵之后,必须具有更为强大的外渗力和放射性。莫应丰十分容易地做到了第一步,他将他的小说故事设置在一个极特殊而富有实验意义的氛围里,并且选择了一个很有民族性、地区性内容的题材,他的内核是充实、丰满的。可是他在整个故事进展中一味强调了这个内涵的包孕作用、聚缩作用,使作品充满了对善的种种正反两面的推敲、论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却也忽视了更为广泛的(或许也是更不确定的)外延渗透作用。
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人一定不会忘记那种既荒诞又写实的情节和艺术手法,也不会忘记初读之后既深有感触又带有一丝茫然和痛苦的阅读经验。我们很难以一种确切的词语去阐述其中无数个精妙的细节的含义,更难确定它的意义所及范围和疆界。因为它可能写实、可能象征、可能荒唐,但是绝非无意义。我们在更高的人生境界上、在哲学的批判眼光中是可以领悟到一种类似登巅峰而茫茫然的惊讶、叹息之情的。换言之,小说的观念必须超越它自身情节的确定范畴,必须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走向涵盖的境界。在这些方面,或许莫应丰的小说尚有单薄之嫌。我想,读者是有理由要求超越善的观念之外的更多的思想内容和人生经验的。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于杭州
(《桃源梦》,莫应丰著,载于《当代长篇小说增刊》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