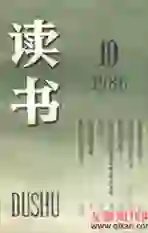科学的独立品格
1986-07-15纪树立
纪树立
红州学友来信说,他“面壁十年”方拈出了“科学能力”四个字。没有经历过这种思想历程的人不大容易体会到个中甘苦。所谓“科学能力”,无非是说,科学是一种社会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社会的科学力量”。这样一连串的平淡而又有点拗口的论断,可能挑不起读者的兴趣。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同我一起仔细玩味一番,我敢说,你将从这些论断中品尝出作者的匠心所在以及它们的尖锐的现实意义。
这里所说的“社会的科学力量”是一个二律背反。科学是“社会的”,必然受社会的制约并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决不是某种为了增加安全感的饰词。任何一种严肃的考察都不能不承认科学的这种社会品格。但是也不能不承认,更重要的是科学作为科学的自主力量,它“相对独立地推动科学自身的发展与变化”的力量,它的独立品格。不错,这种独立是相对的,不能超越于社会范围之外;但又毕竟是独立的:不仅独立于社会政治结构(并不直接从属于政治需要),而且独立于社会生产结构(并不一定直接完成生产任务)。在最近十年中,同步于历史的前进运动,大体上也是科学日益显示它的这种品格的过程。红洲的这本《引论》,就是从这个过程中结晶出来的。
科学的独立品格,按照我的理解,首先在于它通过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所形成的知识结构,其次是这种结构所导致的独立的社会结构,而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沉淀为社会心理结构中的独立人格。我不敢奢望以此来概括《引论》的全貌,我只是阐发我自己的体会。因此,我无权要求本书作者对这里所叙述的任何一个论点负责。
科学的知识结构
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力。科学不生产钢铁和粮食,它生产概念、定律和理论系统。因此,科学不仅是人类试图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并驾驭自然力这种总的努力的一部分,而且是人类试图从认识上摆脱束缚、从精神上驾驭自然的一种努力。如果说,人类的生产劳动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是一种本质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那么,科学便是整个社会生产中最自由、最自觉的部分,是人类自觉性的集中表现。
科学要发挥这种自觉的作用,就必须从一般物质生产活动中提炼出来,形成自己独立的结构,获得自己独立的存在。在一些古代文明中,也包括在中国文明中,已经有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其中已包括丰富的科学因素。但它们溶解于生产之中,最多只能是一些潜在形态的科学。只有在古希腊文明中,科学通过对绝对知识的追求,通过逻辑演绎结构的建造而超越于直接生产过程,从而最初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品格。中世纪教会的统治曾经使科学沦为神学的俘虏,它又一次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直到文艺复兴,通过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问世,“自然科学宣布了它的独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它再一次从浑沌的生产经验中离析出其中的形式要素来,凝结成为假说-演绎的逻辑结构。科学只有付出“脱离生产”的代价,才有可能从更高层面上对社会生产发挥整体的而不是零打碎敲的作用。科学同生产的分化,到处都是人类进化历史中的重大步骤。
科学这种独立的知识结构,使人类进一步从一般动物界提升起来:他不再赤手空拳地站在冷漠无情而又满怀敌意的自然界面前。他创造了一个横亘在他同自然界之间的中介物,一个横亘在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之间的独特的中介世界。这是精神同物质交会的结果:它包含图书情报、实验装备等物质要素,但这只不过是精神的物化形态;它也包含概念、定律、理论等精神要素,但这也是物质的精神表现。二者“性别”不同,却都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产儿。科学不是精神之父的纯粹创造,这种先验唯心论观点取消了科学的客观性。科学也不是自然之母的单性生殖,这种机械反映论倾向则否定了科学的某种主观性。二者从不同的两极出发,最后都抹煞了科学的独立品格。按照《引论》作者的巧妙构思,这都可以用“二极管模型”来描述:不管是把科学认识过程看作阳极(精神)主动而板极(物质)受动,还是反过来板极发射而阳极接受,都把这个过程简单化了。“三极管模型”可以部分弥补这个缺陷。它表明,在精神到物质的行程中还有一个居间的“栅极”,人们通过这个中间机构来调控自己的活动,过滤来自对极的信息,并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放大或缩小的加工。显然,这道栅栏尽管必须适应物质世界中的风云变幻,必须根据来自那边的反馈而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但又毕竟是一种精神建构物。在这个包括全部人类文明的广袤的中介国土上,它是“阳性”的,更接近于精神世界。
从这一方面看,“栅极”的类比就不那么完美了。这道栅栏决不是用僵硬的铜丝编成的。作者说得好,这是一种“柔性结构”,一个“思维势场”。“场”的类比是富于想象力的,这意味着某种波-粒子的二象互补结构。它可以凝聚为粒子态的“知识细胞”(概念)或“知识纤维”,也可以硬化为更大范围的“知识幔层”(理论系统),但它的基态仍然是一个弥散的、躁动的、振荡的、变动不居的波场,一个波涛翻滚的“智力海洋”。正是思维的这种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易变性,才意味着最大的创造潜力,最广泛的发展可能。这是科学真正的生命之源。科学总是在探索着,寻觅着,追求着,总是不安于现状,不满于既成。任何硬化的实体形态都是暂时的,易逝的,随时都会回归到弥散状态,集结新的势能而重新塑造自己,重新探求方向。
不错,就算它是一个汪洋大海吧,也仍然是整个地球的一部分,不能超越于地球重力和磁场的作用范围。科学同样不能超越于它所属的母系统,不能脱离人类适应环境、求得生存这个总目标。在这一方面,科学作为人同自然之间的一种中介,也是人类驾驭自然、争得自由、实现这个总目标的一种手段。当我们说科学是一种社会生产力或者一种文化系统时,就是就它的这一总目标而言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系统总是包含不同的层级。对于更大的母系统来说,子系统固然只是一种手段,而对于这个子系统本身来说,它又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又有母目标以下的子目标。在这里,手段变成了目的。每个子系统为了充分发挥自己这部分的作用,总是力求把手段上升为目的。这种转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但是当人类的各种求生手段逐步转化为独立目标而构成一个广袤的中介世界即文化世界时,却准确地标记了人类与一般动物界分离的程度,标记了人类进化的高度。
科学的独立目标就是建构和维护自己的这种知识结构。这决定了它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定向:它追求纯粹知识——这是科学自从古希腊以来一脉相承的传统。诚然,后世对这种“纯粹知识”的理解一直在变化。今天我们已放弃了古代那种绝对知识的奢望,我们也修改了近代单纯从经验世界中获致可靠知识的理想。现代人更倾向于把科学看作一定的思维框架同经验材料的综合结构。但是不管怎样,贯穿这整个过程的主线始终是对某种可靠的纯粹知识的追求,原则上不顾政治的干预或生产的吁求。一旦形成了结构,它首先服从于从自己的深层所释放出来的“结合能”,从思维势场中所迸发出来的对知识的渴望。它锲而不舍地走自己的路,划出自己的运动轨迹,不管外界的干扰曾使这条轨迹出现过多少曲折和停顿。它从一个采掘场地转移到另一个场地,从一个世界中心迁徒到另一个中心,无一不是科学沿着自己的价值定向、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而选择的。
科学的这种知识品格,是它的全部独立品格的内在根据。
科学的社会结构
如果说,古代科学由于它的知识结构本身的依赖性,它的社会结构的轮廓还不是很清晰,那么,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情况就不同了:出现了“科学家”(英国的scientists和法国的savant)的专门称号,并结成了相对独立的科学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与世隔绝的小社会,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尚习俗,自己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它不是政治社群或集团。当然,二者也有联系:不仅许多科学家都关心政治的风云变幻,还要发表政治见解,而且,在这两个社群之间也有一些居间的联结机构,例如政府的科学智囊团之类。但是,科学社群作为独立的社会集团,却不以取得和加强政治权力为自己的活动目的。它别有自己的追求。它一旦放弃了这种追求,也就丧失了自己的本质。混淆这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曾经是许多历史悲剧的根源。
科学社群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形式来保证自己的目标。红州用了充分的篇幅来回顾这段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这首先是学会组织。十七世纪最早出现了英国皇家学会。其前身其实只是一个并无定形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其成员完全出于共同的兴趣而定期集会于学院、酒馆或者家庭之中。后来皇家学会把这种兴趣用章程固定下来,规定自己的任务是“增进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和一切有用的技艺……以了解自然界或技艺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并记录对于原因的理智解释”(《学会章程草案》)。它要求科学自由,要求不参与政治的独立性。据一位研究皇家学会史的权威说:“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希望呼吸较为自由的空气,并且互相安静地交谈,而不参与那个沉闷时代的各种情绪激动的狂热。”(托马斯·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十九世纪英国另一个影响巨大的“科学促进协会”还由它的第一任书记出面声明:它的目的是“使国民更加重视科学的目标,并排除一切阻碍科学进步的绊脚石”。
学会组织的出现,增强了科学社群的粘稠度。其成员之间的交往强化了它所特有的价值准则和精神气质。它有自己特有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科学家不应为了任何科学以外的动机而篡改和伪造实验数据或历史事实,不应在任何情况下违心地改变自己的学术见解。科学家必须听从自己的科学良心的呼唤,否则将受到科学道德的谴责。显然,这同政治伦理价值是不完全一样的。此外,科学为了保证自己的目标的实现,还鼓励自由探索和自由讨论,鼓励对传统或权威的批判,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培植了对不同观点的宽容态度。这同一个政治集团往往更需要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更倾向于排除妨碍这种行动的异端见解,也是很不一样的。这两个社群之间的这种社会性格上的差异,可能在任何已知历史条件下都是存在的,尽管表现的形式大相径庭。
当然,学会并不是科学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各种“硬度”不同的组织,包括那种现代科学中所谓“大科学”的高度硬性的组织。不能忽视从这种结构中所爆发出来的集团力。它也同军事组织或生产组织一样,服从于整体大于各部分总和的规律。“大科学”的出现,说明这也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在一个时期内集中优势力量解决已经成熟并迫切需要的课题。谁敢低估例如电子计算机的制成、原子弹的研制(撇开伦理方面的问题)以及回旋加速器建成等等的科学贡献呢?
但我还是要强调,科学的社会结构同它的知识结构相对应,也是柔性的。科学社群可以硬化为学会,或者更硬的学院或学派,但它的基态仍然是各个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他们的自我追求,他们寻觅自己目标的随机的探索活动。它的更为经常的组织形式是学者之间的对话和通信,是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是在报刊上的交流和批判性讨论,是短期合作和交换讲学,如此等等。只有保持科学社群足够的柔韧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大的激发科学家的创造性,更多地索取它的组织结构的特殊馈赠。把政治集团或军事组织的某些曾经行之有效的原则机械地搬用于科学的社会结构之中,必然会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把集体力量仅仅看成是那种类军事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力量,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甚至在谈到工业生产中的这种力量时也强调:“单纯的社会接触,也会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引起竞争心,成为生活精神的适当刺激,并由此增进各人的劳动效能。”(《资本论》第一卷)如果在一种高度组织的现代工业生产中还需要这种竞争的刺激,那么在科学的精神生产中就更不待言了。科学社群的内部竞争,与商品经济的市场竞争之间具有某种共同性。我国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者往往忽略或者回避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近代科学是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同兴起的,二者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某种同构性。在商品交换市场上,双方都以独立人格参加随机的供求,他们力求以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生产,并人人平等地服从于谁也无法预知的变化莫测的市场价格。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经济运动形式。它并非先天注定的罪恶渊薮,尽管其中确实发生过许多罪恶。近代科学大体上也是按照这种活动模式发展起来的。当科学从经院哲学中独立出来,科学家也以独立生产者的身份出现于商品市场上。他的产品必须为这个市场所接受并获得一定的评价,以证明它含有凝结着这位卖主的聪明睿智的内在价值。也同一切商品生产一样,他必须在竞争的压力下缩短自己用于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而且——不管你会多么吃惊——他还类似于一切投机商人,冒的风险愈大,收获就愈多。这个市场上竞争的严酷性,丝毫不下于物质商品市场。如果你对这一点仍有怀疑,以为这简直是亵渎神圣,我建议你读读遗传基因结构的发现者之一沃森(J.DWar-son)所著《双螺旋》一书,它以惊人的坦率揭露了科学家在这种竞争中曾经采用一些什么样的令人咋舌的手段。也许随着社会的进化,这些手段将受到更高的道德准则的约束。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是:竞争压力一直是一种不可取代的创造性的启动器,它能够把隐匿在心灵深处的才智与狡诈统统调动起来,投入这个市场,使这种随机的混乱运动涌现出最大的组织性来。
这里我想提醒读者小心区分“组织性”这个字的不同用法。现代系统论中所说的组织性(organization)是判然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用法的。科学社群所要求的组织性,显然在于它的充满活力的自由竞争之中,也即随机探索和冒险活动中的有序性,混沌之中的信息量。
现代社会趋向于打破单向垂直的社会结构模式,不断地横向分化出一些相对独立的中间组织、中间机构来。科学社群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这种多维的独立发展,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新的活力。
科学的心理结构
红州引用了贝尔纳的一段话:“维持和发展科学的主要责任,必然要落到科学家自身,因为只有他们才懂得这种工作的性质和前进的方法。”用爱因斯坦式的谐谑来说:只有穿鞋子的人才知道鞋子在哪里夹脚。对于科学的命运,科学家责无旁贷。科学能否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归根到底在于科学家是否具有一种独立心态和独立人格。
这不是太苛求于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文弱书生了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难道不是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吗?一五五三年当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时候,教会烧死了他。一六○○年当布鲁诺正在发展日心悦并论证宇宙无限论的时候,异端裁判所也燃起了这把罪恶之火。根据《引论》所引用的材料,西班牙有位名叫托尔奎马达的裁判所所长竟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就烧死了四千人。上帝保佑,他烧毁了多少秀木,烧死了多少塞尔维特和布鲁诺啊!难道我们不应当首先要这些刽子手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制度负责吗?难道我们不应当用诅咒的毒火让那些托尔奎马达们永远龟缩在阴暗的炼狱里受煎熬吗?
是的,即使我们搜遍所有的辞典,也未必找得出合适的辞句来拯救这位克尽厥职的所长的邪恶的灵魂,以及他形形色色的遗孽们。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说,这并不足以减轻科学家自己的责任,他们的神圣的历史责任。应当说,塞尔维特和布鲁诺是完成了这种责任的。他们尽管把发现血液循环和论证日心学说的责任交给了几十年以后的哈维和伽利略,但是他们却用他们的躯体燃起了思想自由和科学独立的火光,照亮了以后几个世纪科学发展的道路。何况,我们还不能不承认,历史毕竟前进了:托尔奎马达死了,火刑场不见了。随着科学自由的扩大,科学家的历史的以及道义的责任也加重了。他不能总是诿过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不能只停留于谴责托尔奎马达的阴魂。他也需要反躬自省:我自己有无足够的道德勇气来承担历史赋予我的责任?没有科学上觉醒的独立人格,科学的独立品格也就落空了。
每一种历史的使命都要求一批献身者。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出现过“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对于他们,生命的意义就是增殖资本,扩大再生产。发展科学的历史使命也召唤一批“人格化的科学”或“科学人”。他们体现着科学自我扩张的冲动。爱因斯坦曾经描述,他们投身科学的动机有二,消极的“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积极的动机则“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描画出一幅简化的易于理解的世界图象,试图用他的这个宇宙来代替并征服经验世界”,以获致在喧嚣拥挤的尘寰中所享受不到的纯净空气和宁静景色(《探索的动机》)。简单地说吧,他逃避现实,追求自我,寄情于自己建构的宇宙之中。也正因此,他阅世不深,天真未泯,独立不羁,乖僻孤介,对于人间荣华看得比较淡泊。上苍似乎专门派遣这样一批人降临世间发展科学的。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但在科学社群中确实也不乏接近的典型。爱因斯坦就是一个。他深信“科学是为科学而存在”(《论科学》)。他把自己看作“孤独的旅客”,“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自己的国家、家庭、朋友甚至情人”(《我的世界观》)。他终生追求科学的自由,不仅社会所容许的“外在的自由”,更重要的还有那种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束缚的“内心的自由”(《自由和科学》)。他深信,科学的极乐在于求索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感到并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很牢靠,也不能肯定自己的道路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七十岁生日时的心情》)。当科学本身侵犯了人的独立性,他甚至宁愿当小贩而不当科学家。他在一个广阔的扇面上展现了一位科学家的独立人格的许多侧面。
这不是说,科学社群都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科学的庙堂”中,如爱因斯坦所说,这种人总是少数。其中多数人或者追求才智上的满足,或者谋求现实的功利。他们进入这个庙堂全属机遇。当环境变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弃学而当官、经商或者作电影演员。科学不是他们的目的,只是达到另外的、可能也同样值得尊重的目的的手段。他们中间并不乏才智超群而且人格高尚之士,对科学也有不可缺少的卓越贡献。甚至正由于他们的功利的追求,才填满了从理论科学到实用技术之间的连续光谱。没有他们,科学的庙堂就要坍塌。但尽管如此,这所庙堂的顶梁柱仍然是第一种人:他们支撑了科学的独立存在,规定了科学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以为从事科学就是一种最高尚的职业,这种理想化的科学人格也未必就是我们所向往的最高的理想人格。人完全被“科学化”了,成为单纯实现科学目标的“科学机器”,成了人所创造的科学的零件,这也是一种异化。现代科学的过分专业化所造就的所谓“无知的专家”、“有学问的白痴”,已引起了一些思想家的严重不安。而且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一位科学家真的达到了对自己所处时代、所属民族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作为一个人,他是否还能保持那种献身科学的激情呢?就说爱因斯坦吧,正是他,以最大的社会责任感投入为和平、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时代潮流。他并没有超越于他的时代。我们最高的理想人格应当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是摆脱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束缚的自由的人。“科学人”的理想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但这又是迈向这种理想人格的一个中间步骤。当人从狭小的本我欲求中、从名缰利索中解脱出来而投身于纯粹科学的追求时,他就获致了一种精神上的升华;当他通过科学而摆脱了政治依附甚至人身依附的地位,不再是“物美价廉”的工具或者政治赌赛的筹码,他也获得了某种独立的社会价值。他付出了依附于科学的代价,却摆脱了更大的依附。他借助于科学的独立而获取了人作为人的部分独立性。这不是完全的独立。但是,离开这种切实的中间步骤,最高的理想人格就只能是虚无飘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炷爝火,甚至干脆就是欺骗世人的鬼火。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没有分化出独立的科学结构来,天文历算、百工技艺不是直接属于“官学”,也是首先为宫廷官府服务。从业者也相应地充当太史令、太医令、尚方令等官职,难以形成知识分子的中间社群及其独立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士-大夫”之间没有明确界限,个人修身养性、十年寒窗都是为了“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标。范仲淹所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进退都不忘政治的庙堂。这表现了知识分子为社会责任所驱使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但也带来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君王的庙堂原则上不容许另外一个科学的庙堂与之并列,因而也不可能出现爱因斯坦那种类型的独立人格。鲁迅曾说到中国不乏忠君死节的烈士,却很少为自己的学说献身的勇士,可能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一种表现。
因此,建立科学所必需的心理结构,培植这种独立的科学人格,可能是我们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前提。
西方近代科学从颁布自己的独立宣言开始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科学在自己的生长发育期中,也象生物进化中一种新的物种的形成一样,需要一个同环境隔离的时期。这导致一种从科学的内部因素寻求科学能力源泉的“内部论”(internalism)。十九世纪以来日臻成熟的近代科学开始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联系,这又为另一种“外部论”(externalism)科学观提供了依据,并使“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最初结胎。更加晚近的倾向则试图把这两个对立的方面统一起来,视科学为一种在一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独立发展的力量——红洲的“社会的科学力量”这个短语,正是覆盖了这一段丰富的历史过程。由此出发,人们更倾向于把上述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看作两种互补的研究方法,即“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internal and externalapproaches)。红洲所构想的“科学能力”,显然也是这种总的潮流中的一种尝试。
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去追随某些西方作者的思路。我们的科学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同西方恰恰相反。我们的传统本来就没有为“内部论”提供土壤。二十年前开始的那场灾难又推出了某种漫画形式的“外部论”。它强迫科学去直接提高工业产量,直接推行某种政策,把那种本来不无合理性的“外部论”丑化为一种后来所谓“代替论”或“取消论”。因此,当噩梦消逝的时候,首先必须把科学从那种淹没一切的政治魔法中解放出来,从而也把科学劳动者作为生产劳动者从贱民地位中解放出来。今天,历史又迅速推到一个新的层面上,要求把科学进一步从一般物质生产中独立出来,以深入挖掘它内在的自我运动的源泉,并同时提出科学劳动者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劳动者所负有的特殊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同西方走过的路径相反,这是一个从“外部论”转向“内部论”的过程,这就要补“内部方法”之课,要强调被我们的传统所一直忽略了的科学的独立品格。这就是为什么本书作者在广泛考虑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联系的同时,却又着重研究了科学的内在结构和内在动力的原因所在。
(《科学能力学引论》,赵红州著,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版,3.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