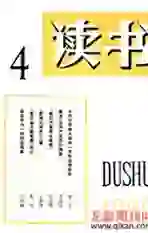直译、硬译与意译
1980-07-15洪素野
洪素野
读了1979年《读书》第三期上一篇《论翻译书》后面罗新璋同志的“附记”,觉得他提倡的译法,将使他自己走上歧途,也影响青年读者走错路。骨鲠在喉,不能不吐。这里把个人的意见说出来,以就正于读者。
我认为“直译”是翻译的康庄大道,过去多少先行者,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努力,已经走出路来了。简单点说:象戴望舒、梁宗岱、李健吾等人译的法国诗文、戏剧,高植、曹靖华、巴金、汝龙等人译的俄国(及苏联)作品,卞之琳、曹禺、方重、范存忠等人译的莎氏戏剧及英国其他佳作,罗念生、周作人、杨宪益译的希腊诗、剧等等,都是直译很好的范作,都受到了读者的赞赏和学习。
“硬译”本来是极个别的现象,过去有人诬蔑鲁迅先生的译品是“硬译”,但先生译的诗文,除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的《论艺术》那三本比较难译的书以外,其它全部长短篇译文,都可以说是标准的译法,是近数十年译作中的精品,值得后人揣摩学习(尤其是《毁灭》、《死魂灵》、《十月》、《表》等等)。过去我看到的巴尔扎克小说的中译本中,有不少是语言学者高名凯教授译的,读起来是比较吃力的,有的一个句子竟长达五十多字,这是想走直译的路子而掌握得太呆板了一点,难免给人“硬译”的印象(但他译的《巴尔扎克传》却又是流畅好读的。所以他译的小说,毛病出在哪里,还没有摸清楚)。有的译品叫人读不下去,多半是由于译者外文未到家,或中文太差,不能错认为是由于直译之故。
“意译”的毛病,象林纾、伍光建那样的译品,是一看就清楚的,他们可以增添原文所没有的字句或意思,也可以任意略去原文本来有的字句或意思,看不出民族国家有什么区别,也看不到作者特有的风格,尽管译的是不同作者的作品,却只能看到译者个人的笔调。作为过渡时期的一种译法,当时起过一定作用,今天再走这条老路,实在毫无必要。另一种也是意译,毛病实际是一样的,他们任意变更原文的句式和句法,改用中国的句式和句法,使“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他们的最高理想是“重神似不重形似”,因此也可以随便增减字句(《读书》1979年第二期上程代熙同志文章说到傅雷先生译巴尔扎克《幻灭》中的一句话说:“原文并无‘专讲二字,译者无意中加上这两个字,倒反而把事情弄得复杂了”)。正如《读书》1979年第三期上一篇《许崇信教授论直译与意译》中说得好:“意译的消极的一面,在于它的保守性,因为它容易排斥新的表达形式,总是把新的表达形式改造成自己的面貌。”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毛病也就在这里(他译的罗曼罗兰和服尔德的书尚未读到,故未论及)。
现在罗新璋同志却认为傅先生的译笔是最理想的一种译法,准备亦步亦趋地学习这种译法,甚至“把傅译……计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字,一字不漏地抄在原著上,以便随时翻检查阅”,认为“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而傅译就是他的“规矩”,并认为“我们不妨把傅译作为一种译派(他寄傅雷函则称之为“宗派”),……同时提倡各种翻译风格竞进争雄。”我的意见认为翻译外国文艺作品,只有“正确的”与“不正确的”两类,凡能够正确无误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保全原作的神韵和风格的,就是好的译文,否则就是较差或很差的。如再加上许崇信教授的话,即“更能反映异国的风光与情调,更能吸收我们心里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新的表达手段”的,就是好译法。决不能说这里边还可分出许多“宗派”来,也不能说“不妨……提倡各种翻译风格竞进争雄”,因为只有各不相同的作者才有各自不同的风格,译者只能跟着作者走,自己有了固定的风格就糟了。有人说,读傅氏的译品,往往使人闻到一种油腔滑调的气味,读起来不费劲,但象读的本国小说,总觉得这里面短了一些东西,原因就在于他“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化的结果,原作者不见了,读者看到的是貌似合而神离的译者在说话,所以失望了。论傅氏的用力之勤,所下的功夫之深,都是令人敬佩的,可惜走错了路子,使他的译作好多需要重译(象泰纳的《艺术哲学》或许不必重译吧,此书未见),为了以后的译者不至于重陷这个覆辙,特写了以上几句。《读书》编者把许教授论翻译的文字与罗文同时刊出,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好使读者知道那一种译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