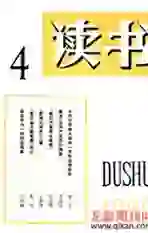关于书的杂感
1980-07-15秦似
秦 似
近年以来,我在教书,编书,当然也看书和买书,但买书是有条件的,我辈能买得到而又买得起的书很有限。比方一部二十四史,虽基本出齐了,我的书架上只有几分之一,也买不全。其它的图书更不用说了。
我常常觉得,现代中国人要想多读点书,比古人来要艰苦得多。古人说“学富五车”,那是马车拉的竹简,大概“五经”加个《左传》就有了。到了汉以后,就得多读一些,李白二十岁前把书都读好了,除古人那五车之外,当然还多了一些史、子、集和《文选》之类。那个范围到底也还有限的。夏衍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闭幕词上现身说法,讲到读书的重要,说他青年时代泡到十九世纪外国文学的染缸去了,中国古籍读得少,是解放后因工作需要才逐渐补课的。这对我们和再后一辈都应很有启发。其实,相反的人恐更不在少数,即《论》、《孟》史传,《诗经》、《老》、《庄》之类读了一些,而外国文学知之甚少。这同样是很大的缺陷。
书的范围既然很广,中外古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专深与普及,成人与儿童,无所不包,那么,象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全面计划书的编印和出版,就不能不是一件大事情。这样的计划,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部门作整个的考虑与安排,如何实行两条腿走路,既有国家的计划,又借助于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得书的出版和供应大体与需求一致,克服出版的无政府状态和闹书荒的现象。从过去看来,这一工作似乎并不比人口控制简单些,紊乱现象是颇为惊人的。比方说,四人帮大破坏的十年,有些出版社的牌子索性收起,只挂“毛著出版办公室”的牌子了,因为纸张、机器、印刷物资都控制在那个地方,就算想印点别的书,也得从那里头想办法。毛主席著作当然要印,但别的东西一律让路,那还有什么科学知识的发展?还有什么文艺的繁荣?反正四人帮并不要这些。这不是比例失调,而是没有比例。
连年以来,我们都听说,纸张生产不足,影响到出书。但是,另一方面,大量书刊报废,浪费纸张的事比比皆是。四人帮要批所谓“三株大毒草”,下令全国大批印原文,有些地方则不待下令,闻风而动(我们是一个对风特别有兴趣的国家),几百万份在几天之内就印齐了。光这一项所报废掉的纸,大概就够印几千种科学或文学书籍。事情是否仅止于此呢?那并不见得,因为某些人的长官意志也大可以造成其它的书灾。
说到具体的部署,那问题也不少。以影印或重排古籍而论,计划在哪里?不知道。因为周总理讲了话,二十四史标点本总算出书了。《诸子集成》这类书就不见重印。甚至象《诗经》这样的书,也没有把《诗集传》或别的本子选一种印出来。早几年在北京中国书店还有几部四川严氏刻印的《音学丛书》,那是把明清人对音韵学的研究成果汇刻在一起的,现已卖光,不知要到哪一年才能复印。好些重要的诗人,也没有印集子。这种状况,对大学里的科研和教学不能没有影响。外国文学方面,全部停止印行了有十多年之久,现在才开始印了一点。象《一千零一夜》、《基度山伯爵》,都要抢购,事实说明读者很需要读外国文学书,有些人需要得甚至比我们当代的小说还迫切。至于对于文化交流,文艺工作者的借鉴,大学的教学来说,今天出版的外国文学书更远远不能适应要求。外国文学的课程出现停工待料的情况。对于别人的现状是情况不明,对于古希腊罗马或文艺复兴时期的东西,只能翻旧书堆去寻觅若干残存的材料。这种情形不早日改变,科学文化就很难提高。
读者要读什么书,作为个人,他完全是可以有偏好的。但作为全面出版计划,就得统筹兼顾,不能凭一时的趋尚或主观的设想,丰于彼而俭于此。比方说工具书,对于科研教学或自学都很有必要,这几年来抓了《辞海》、《辞源》,陆续出了书,补上了一个很大的空缺。但我以为新的《辞海》出了,旧的《辞海》仍可同时印行,理由是光就价钱而论,新的比旧的就贵得多。况且旧的并非就没有一定的用途。我们有的作家出了专集,还可出选集,为什么《辞海》不可以同时发行两种呢?(《辞源》情况稍不同,这里不论。)
我国既有各种专业性的出版社,各省区大市又各有出版社。出版机构不可谓少。但如何合理发挥其作用,避免重复与浪费,却不是不存在问题。举个例说,现在又有一个风,各省区出个文艺刊物之外,还由出版社出一个大型的文艺季刊(或双月刊)。这种步调为什么那样一致,颇堪思议。当然,要求繁荣文艺创作的愿望是好的,但做法并不一定要千篇一律。我很疑心,千篇一律的做法,是不是好办法。近来农村形势有了一些起色,就是因地制宜,搞得比较活了之故。现在已有的一大堆文艺刊物是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和特色来的。又比方说,近来有的短篇小说较受读者欢迎了,就连报纸副刊也不考虑其篇幅的特点,宁可全版刊一个短篇小说,独沽一味,甚至连载两三期,而每周又只有一期!这对于读者和报纸是不是那样合适,可以不管,因为重要的是看风。其实,并非短篇小说才可以干预生活,漫画、杂文、短论、随笔,不是也行吗?物极必反,这样的事情已不止一次了,但似乎独立思考,因事制宜,到底还很不容易做到。这就使得我们的出版机构虽多,却仍然不能通过分工协作,对全面的出版要求作出更大贡献。
其次谈谈编书。一些老朋友在一起,常常谈到在过去一两个人就编一个杂志,或编一套丛书,而现在则非几十人不办。当然,现在的分工细了,集体研究加强了,比起过去是大不相同的。但有没有“内耗”或“内积”的现象,带来层次堆叠,公文往返,议而不决,拖延时日,甚至编辑部在某种程度上衙门化的问题呢?我看也是值得思议的。一二人干不好,人太多,人海战术,未必就干得好。真正把责任制建立起来,很有必要。一份杂志应有个性格,一本书须有一个人自始至终负责到底,审阅、修改、与作者反复研究商量,才能保证质量。
书印出来,要经过发行部门,才能到达读者手上。我听到一位书店同志说:“你以为现在的发行工作,还象过去一些进步书店那样做法吗?”他指的是,解放前的进步书店要自负盈亏,千方百计多发行一点,现在则不同,发行越多,工作越累,八小时做多少,就是多少了。这当然得从合理的规章制度包括奖金制度去解决,否则也会增加读者买书的困难。
以上所谈,都是些浅近之见,且由于见闻寡陋,失当之处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