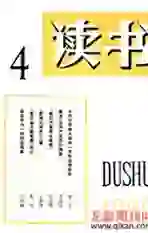是非颠倒的沉痛教训读孙冶方书有感
1980-07-15卢之超
卢之超
读孙冶方书有感
一
听说《读书》杂志的选题计划里有一个题目叫《中国禁书考》。如果有作者肯花一番功夫,对中国禁书史作一点考证,写出这样一篇文章来,我想是很有价值的。
我的历史知识很贫乏,但是我想,古时候的当权者对他们不满意的书,恐怕不外乎是阻止这书和读者见面,“严禁”而已。当然,对作者甚至对读者可以抓起来,或者杀头,抄家。但是,发动许多人甚至整个读书界,甚至各行各业,去“批判”、围剿一本书的情况,大概是没有的,那时也是不可能的。林彪、“四人帮”时期,这种“事业”是大大发展和前进了。不仅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除少数几种以外的一切书,还能把一本书印成几千万册,发到全国各地,强令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去“批判”;不仅已经写成的书要“批判”,明明还没有写成的书,明明是处于写作过程中的初稿、修改稿、内部讨论稿,也给印出来“批判”,例如“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就是这样做的。这在禁书史上要算是个发明创造。建议写《禁书考》的同志,不要忽略了他们的这个“新发明”。
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是不久前才出版的。实际上,它所遭的厄运比“三株大毒草”更惨重,时间也更长。此书收集的文章,大部分是作者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四年间写的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稿,包括内部报告、工作建议、发言提纲。在收集成书之前,早就被当作“反面教材”,遭到十多年的内部的和公开的“批判”。作者也因此坐了七、八年的牢。孙冶方同志的观点,以及受“批判”的事,过去听说过一点,文章没有系统地看过。现在书出版了,内容是按时间编排的,系统地读起来,不仅从里面那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中受到教育和启发,而且象读历史一样,从十几、二十年来的是非颠倒中,深深地感到沉痛的教训。
当然,我不是说,书中所有的观点都完全正确。作者自己也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有不少问题还要继续讨论。有些观点,如否定企业利润留成和奖金制等,受了当时“左”的影响,是错误的。但是可以说,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正好切中二十年来我国经济状况的时弊,其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对我们今天的经济调整和改革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即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就陆续地提出这些问题,并且明确表示了自己关于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孙冶方同志及其文章的命运,不是一个人及其观点遭受磨难与挫折的问题,它反映一个国家受到的磨难与挫折;这不是一些文章的是非颠倒的问题,它反映了一个时期里许多的是非颠倒。
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党的八大分析了新的形势,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如果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不是越来越厉害地批判孙冶方同志的或其他与之类似的观点,而是在当年就按照这样的观点和建议去做,即按客观经济规律去搞经济建设,注意改革经济体制,注意在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条件下扩大建设规模,并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完善我们的制度,那样的话,我们现在将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看虽然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至少大大接近了现代化。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瞎想。在这二十多年里,许多比较落后的或遭到破坏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一些基础同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接近实现现代化。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何况,在这二十多年里,我国人民为建设国家付出的辛勤劳动、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牺牲,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可歌可泣的。可惜,由于把许多正确的东西当做错误去批,而把某些错误的东西当做正确的去做,人民的许多劳动是白白地浪费了。
这里要顺便说到同样遭受多年“批判”的马寅初先生。如果二十多年前不“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所谓“马尔萨斯”观点,而是按照他的和许多同他类似的建议去做,注意计划生育,二十年不懈地抓下来,我国现在可能只有七八亿人口或者还不到。可惜,由于把正确的东西当做错误的去批,而把错误的东西当做正确的去做,现在人口增长到近十亿。物质生产的增长有限,十亿人一平均,生活的提高就更少了。
我绝不是说二十年来的挫折、失误,仅仅是因为没有接受孙冶方同志和马寅初先生的建议。我不想把问题如此简单化,也不想如此夸大他们两位的作用。这里只是想说,对他们两位的“批判”,这个具体问题上的是非颠倒,反映了一个颠倒是非的时期。因为把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反动的”、“修正主义的”大肆“批判”,恰恰证明自己主张和实行的不正确。不是吗?这类“批判”在当时看来轰轰烈烈,但是轰轰烈烈的政治尘雾消散之后,呈现出来的轮廓是什么呢?经济上越来越糟糕,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切还得费力得多地从头做起。历史给我们的惩罚是不轻的。
二
还是回过头来说孙冶方同志的书。我们应当从这里面吸取点什么教训呢?
首先是大批判问题。对孙冶方同志文章观点的批判,开始是在陈伯达的指使下,以内部讨论的方式进行的。当时,如孙冶方同志本人所说,虽然“帽子公司”、“钢铁公司”已经快要开张,但还允许被批判者答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背上“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的罪名,受到“大批判”了。这种“大批判”只能低头认罪,是不容答辩的。何况后来作者已经坐了牢,接受“武器的批判”去了,更无从答辩。
如果记得不错的话,批判二字之前加上“大”字——“大批判”,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明和兴起的。为了美化,前面还加了“革命”两个字。文痞姚文元把持舆论工具时,还写过“抓紧革命大批判”之类的文章,把它吹得无以复加。今天看来很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有其特定的含义,距“批判”的原意相当远,同马克思主义科学意义上的批判,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它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采取批判的态度。《资本论》的副题,就叫“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也常常采取批判的态度。毫无疑问,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永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绝不应当同任何反动的、错误的东西妥协。对人对己都应当这样。但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批判精神或批判态度,首先应当是如马克思所说:“不崇拜任何东西”。对待任何事物或观点绝不迷信、绝不盲从,绝不简单地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分析、判断、吸收、否定、继承和扬弃。这种批判的出发点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这种批判,首先要有科学的态度,同时要有民主的精神,承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容许被批判者进行申辩,进行反批判。无论对于什么人,什么问题,都只服从事实,只服从真理。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榜样。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许多所谓“大批判”,恰恰与此相反。这种“批判”的出发点不是事实,而是某种已定的结论;不是拿批判的对象同客观现实及其规律相对照,而是拿它同现代迷信的教条或“理论权威”头脑里的观念相对照。批判的方法不是分析、说理,以理服人,而是断章取义,断句取义,一哄而上,棍帽齐下,不许反驳,不许申辩,并且伴随着的往往是逮捕、监禁……。简言之,这不是科学的批判,简直象某种新式的宗教裁判。对孙冶方同志就是这样做的。“比修正主义还修正主义”,“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陈伯达和那个“理论权威”早在批判以前就做出了这个结论。往后的全部“大批判”过程,不过是到作者的文章里去寻章摘句以“证明”这个结论,以至许多“大批判”的参加者都没弄清孙冶方同志文章里究竟说了些什么,他的价值概念和利润概念到底是什么涵义。
孙冶方同志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他后来曾半开玩笑地说过,他倒不在乎有没有“三不主义”,反正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事经受得够多的了。他的最大要求是给被批判者以答辩权。在你批判了一通之后,允许人家申辩和反批判。这是作者在十多年的不幸遭遇和七八年的铁窗生活之后,带着切肤之痛和悲愤之情说出的“戏言”。但愿它今后能成为现实。
有的同志会说:难道所有的“大批判”所批判过的东西,都是好的么?就没有错误的或反动的么?我说,即使有,即使被批判的确实是坏东西,那种“大批判”也无损于它一根毫毛。因为那种不讲道理的做法,并不能真正克服错误的或反动的东西。文化大革命中大搞破“四旧”,除了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以外,确也触及一些真的“四旧”。但结果“四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泛滥起来了。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毛主席曾经说过:“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这是在我们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前说的。当时一些人的毛病还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夺取政权以后,有人以为有权有势,不仅可以用装腔作势吓人,而且可以直接用权势压人了。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权威”,更把权的作用夸大到完全可以主宰真理的程度,真是“呜呼哀哉”了。
三
读了这本书,给予我们的另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理论原则,坚持科学态度。此书忠实地记录了作者的这种态度。书里收集的文章,最早的写于一九五六年,最晚的写于“四人帮”垮台之后,前后二十多年。无论这二十多年中屡遭风浪,几经反复,作者的基本观点是首尾一贯的。当文化大革命前夕作者遭到围攻的时候,他表示:“如果大家把我驳倒了,我坚决地、彻底地检讨,该戴什么帽子我自己来戴”(第292页)。但是如果理论上驳不倒,驳得没有道理,光凭政治帽子、政治压力,他的态度是:“越是有人反对我,我越是肯定”;“尽管人家在那儿给我敲警钟,提警告,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第290—291页)。后来他坐在牢里,仍旧是这种态度。尽管在某些聪明人看来有点不识时务,但确实是可贵的科学态度。特别在那个理论观点随着政治风向迅速转换成为时髦的年代,这种态度更加难能可贵。
历史证明,科学的态度是不可战胜的,因为科学是打不倒的。那怕你搞一万次“大批判”,最后还得承认它是科学,还得照它去办事。孙冶方同志这本书里的那些文章,多年来都以为已经“批倒批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不仅没有倒,没有臭,许多事还得照它的道理去做。类似的情形很多。文化大革命中开动了多少宣传机器,浪费了多少纸张和精力,竭力企图“批倒批臭”的那些东西,除了一些本来就错误、就应该倒的和本身已经臭了的以外,没有什么是被“批”倒和被“批”臭的。凡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都批不倒,也臭不了。它们不是已经恢复了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名誉,就是将要恢复。这个历史,应当增强我们坚持原则、坚持科学的信心。
是什么给科学以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实践。这就是大家热烈讨论过的题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即使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也需要科学的理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大批判”的文章里,也常常举出实践中的若干事例,以证明“批判”之正确和必要。比方说,为了证明以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的综合指标是“修正主义的利润挂帅”,可以举出事实说,某些企业这么做了,结果出现了追逐利润、不顾品种质量的现象;为了证明有了政治挂帅就可以不算经济账,也可以举出事实说,某些企业在一定的政治鼓动之下超额完成了任务。如此等等。越到后来,这种文章做得越“神”。例如某地区某企业的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几,如果正值批“利润挂帅”,就说是由于批“利润挂帅”激发了群众的劳动热情,如何如何;如果正值“批林批孔”,又可说由于批了孔老二,如何如何。其他依此类推。反正按这种办法,“实践”可以永远证明当时的“大批判”是正确的。
但是这已经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而是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了。我们应当同这种实用主义明确地划清界限。我们所说的实践,是社会的实践,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而且实践是一个过程。孤立的个别的事例什么也证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必须把某一观点或理论放在社会实践里具体地历史地去考察。一种观点或理论需要多大范围和多长时间的实践才能证明,要视这种观点和理论的普遍性大小而定。一个具体的科学假设正确与否,若干次甚至一次成功的科学实验就可以证明;一个具体的计划或政策正确与否,在它的实施过程中就可以证明。要证明普遍性较大的科学概括,则需要更为广泛和长期的社会实践。如果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根本理论的对错,要什么样的实践才能证明?可以说,需要许多国家的人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的实践。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社会主义的历史,则不过是这个历史时期的开端。从这个观点出发,孙冶方同志这本书里的观点,也只是部分地被实践所证明。主要是其中对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主张,以及提出改革的大致方向等等。更多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有待今后更多的实践去证明。孙冶方同志在本书的“前言”中说,他把这些旧文章发表出来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财政、经济实际工作者和经济学研究工作者,能够对这些文章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展开讨论。他将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同大家一起继续钻研这些问题。我认为,这种态度也是科学的。
所以,对于理论问题,特别是对于具有较大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应当允许不同观点在较长的时间里同时存在,相互讨论和相互竞争。我们要肯定的,只是那种经过实践检验被充分证明了的东西;我们要否定的,只是那种经过实践检验被充分驳倒了的东西。对于大多数的新问题,只能在继续实践中不断去探索正确的答案。这种认识事物的实际状况,是“百家争鸣”方针的客观依据。科学的态度应当包含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因为科学不可能是封闭的系统,它永远向着未来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