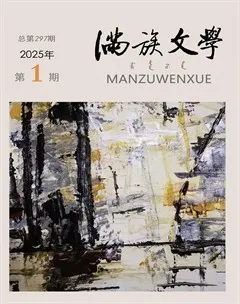千古河床
2025-01-01张继会
一
这里怎么会曾经是一条河呢?一条几乎与地面齐平的凹槽逶迤在裸露的戈壁滩上,如果不近距离地观察,很难发现这是一条千古河床。
这里确实曾经是一条河,哺育敦煌绿洲的党河。河床上间或出现的巨大石块说明这是祁连山雪水融化形成山洪的杰作。荒原戈壁,原本是人类生命的禁区,却因这条不起眼的季节性河流,低调地嫁接起一座文化桥梁,把几大古老文明融汇在这片戈壁上,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敦煌文化。季羡林曾经说过,在人类发展历史上,能沿袭下来没有间断的只有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国的儒家文化,而这四大文化融汇地只有两处,一是位于亚洲腹地的新疆,另一处就是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
河西走廊呈西北——东南走向,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像一头长颈鹿的脖颈,狭长且直,又形如两条山脉之间的走廊,因地处黄河之西,被称为“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道,也是古代中国汉地同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河西走廊有幸依偎在祁连山脚下,山上的万年积雪融化时汇流成河流,滋润着河西走廊的绿洲,给了这块土地生命的气息。在汉代以前一直是西北游牧民族的生活区域,几乎与中原地区处于隔绝状态。
二
最先意识到河西走廊重要性的就是那位虽略输文采的汉武帝。
与崇尚酷法治国的秦始皇不同,新生的刘汉政权深受道家影响,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几十年。到汉武帝时期,国力日渐强大,初步具备了同崛起于漠北的匈奴帝国一较高低的实力,对匈奴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
彼时的河西走廊一直被匈奴牢牢控制着,在秦汉交替之际,北方的草原上也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君主冒顿单于。秦二世元年,也就是秦始皇去世的翌年,冒顿杀父而自立,在统一了北方草原后又灭东胡,征服西域,建立一个地域辽阔国力强盛的匈奴帝国,对新兴的西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英雄所见略同,这是对眼光敏锐见解独到之人的一种褒扬。当冒顿单于和汉武帝这两位伟大的君主先后把目光聚焦在河西走廊时,才让后人领略到什么是战略家的眼光。一个要据有河西走廊,切断中原王朝同西域的联系,形成合围之势。一个要打破这种封锁,联合西域诸国形成反包围。如果不能撕开这种犬牙交错的死结,历史也许会一直这样纠缠下去。历史离不开战略家的运筹帷幄,更需要探险家的勇往直前。当同样伟大的张骞掀开脸上的面纱,走向前台的时候,人类历史注定要书写新的一页。
三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西域的地理概念很宽泛,狭义的西域在今新疆地域内,广义可扩充到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地区。张骞的第一次出使不算很成功,没有完成汉武帝赋予的联络西域诸国夹击匈奴的使命,中间还做了十多年匈奴人的俘虏。后来总算凭着一股探险家的执着劲,不但逃离了虎口,还真到达了出使的目的地。不过他还是失望了,失望的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要拉拢的主要对象大月氏已经远离故土,重建家园。这也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特性,逐草而居,好了伤疤也就忘了仇恨,乐不思蜀。再一点就是和匈奴亦战亦和的近邻,首鼠两端患得患失。比如曾经生活在敦煌地区的乌孙国。总之,现实没有给这位天朝来使一个满意的答复。按理说这位汉使应该是失望满满的,可是倔强的张骞偏偏说不,执着地在西域游说奔走。谁知这一凿死卯精神却带来了意外的收获,成就了一个旅行家的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当一份内容丰富翔实的旅行调研报告呈现到汉武帝的眼前时,这位汉武大帝眼前一亮,他的战略格局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狭窄的河西走廊,而是西域更为广阔的天地。实际上,在张骞出使未归、生死未卜之际,汉武大帝已经对匈奴帝国发起了全面的反击。战争的结果是把河西走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也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做了铺垫。
同第一次怀着忐忑不安的出使心情相比,这次张骞明显高调得多,一个由三百多人组建的使团承载着中原大国的外交使命出发了。
自此以后,无论是严冬酷暑,还是大漠斜阳,东来西往的驼铃声穿过河西走廊飘荡在天山南北、大漠东西,一条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就这样诞生了。丝绸之路让河西走廊焕发了无限生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四座在绿洲上新兴起的城镇犹如四颗明珠把河西走廊串联起来。
河西四郡是汉武帝经营河西走廊的战略布局,除了在四郡驻军屯田外,还从中原迁移来大批人口,中原文化也逐渐在河西走廊开花结果。处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郡就依托党河而建,党河从此不再寂寞。
四
阳关和玉门关是当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四郡外又建立的两关,处在今天的敦煌城西南和西北方向八十公里左右的位置上,是大汉王朝的国门和边界口岸。各国商人就是在这里变换通关文牒后里出外进的。今天的阳关早已不见过去的踪影,玉门关留给后人的也仅是一座四方城遗迹。贯穿河西走廊的疏勒河就在不远处流过,党河是疏勒河的支流,在党河水库没有建成之前,祁连山的雪水会沿着党河浅浅的河床源源不断地注入疏勒河之中,然后缓缓地向西流去。
我们无法想象当年两关的繁忙景象,只能透过王维的《渭城曲》感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慨叹,抑或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惆怅。当然,商业的繁荣是以武力或王朝实力做支撑的。徘徊在党河岸边的,不仅仅是穿梭于大漠之间风尘仆仆的驼队,也有旌旗映衬下的铁马金戈。当陈汤那句响彻寰宇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还在西域上空经久飘荡的时候,班超正以古稀之年向朝廷上书:“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五
敦煌自建城之日起,就处在中原王朝连接西部世界的桥头堡位置,也是河西人才荟萃之地。魏晋之后中原战乱不止,在“永嘉南渡”的同时,也有大批中原文人纷纷携家带口迁移到河西地区。相对于中原的乱世纷争,这里倒是安静得很。“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敦煌绿洲俨然成为一片世外桃源。西域商旅、中原墨客、天竺的苦行僧渐次而至,错综交融。不知不觉间,诞生于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悄悄地在党河河畔生根发芽。
敦煌莫高窟坐落在敦煌市西南的戈壁滩上,党河故道就从旁边穿流而过。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僔的和尚从中原云游到敦煌。至于他为什么来到敦煌,无从考察。或许是对漫漫黄沙大漠夕阳的向往,也可能是中原战乱让他无地立足。直到有一天,他沿着党河漫步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不远处的三危山在夕阳映衬下霞光万道,顿时头清目明。在一干信众的帮扶下,他开凿了三危山上第一洞石窟。也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从开工破土的那一刻起,一座积淀千年的文化宝藏渐渐露出了真容,世界知道了敦煌。
敦煌莫高窟从开凿第一个石窟开始,一直延续到蒙元时期,历经一千余年,至今还保留着十个朝代四百九十二个洞窟。
敦煌莫高窟留给世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完整的壁画艺术。用壁画这种艺术形式进行传道是佛教东传的主要形式,更有助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民众理解佛家教义。在敦煌,那些古代不知名的画工们,在描绘佛教经典故事的同时,也把丝路上的文化交流和繁荣的生活场景融入画中,不经意间完成佛教与本土文化形式上的融合。现在看,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历史文化价值远远大于宗教本身的意义。
实际上自魏晋以后,中原王朝就逐渐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河西走廊也处在北面的东突厥势力和祁连山以南的吐谷浑汗国的威胁之下。大隋统一全国后,隋炀帝杨广在位时虽然一度打通了通往西域的要道,但是随着大隋政权的灭亡,整个西域又被西突厥汗国控制了。唐朝初定之时,李世民为了巩固内政,下令关闭敦煌口岸,不许国人出境。人们可能对《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回味不已。事实上,受当时大环境影响,玄奘法师在多次请求远赴天竺无果后,最后是在敦煌的玉门关口岸偷渡出境的。
归国后的玄奘法师一边在长安讲经弘法,一边把这些年西行的所见所闻记录备案。一部涵盖整个西域中亚山河地理风俗人情的《大唐西域记》就这样问世了。有意思的是,玄奘法师历经艰难带回来的几百部佛经,由于义理深奥,很难被普通信众理解而被束之高阁,而一部回忆性的游记却成为改变历史的关键。
唐太宗在征服漠北的东突厥后,就把战略眼光放到了西域这个广袤的空间上。正苦于缺乏对西域的了解,不敢贸然出兵的时候,一部《大唐西域记》无异于雪中送炭,唐太宗怎么会错过这个机会呢?
悠悠丝路,辉煌再现。
六
汉唐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引以为豪的时代,也是中原王朝对西域及中亚最具影响力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每天都会穿梭在敦煌城的戈壁滩上,沿着党河河道取水补充给养。当干瘪的皮囊被清澈的河水灌满的时候,那些精明的商人还不忘对着河水整理一下布满灰尘的衣衫,然后微微一笑,带着驼队走向大漠深处。
如果没有亲临沙漠或是戈壁滩,你很难切身感受到水对于有生世界的意义,尤其是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人。茫茫戈壁滩上,除了疏落的骆驼草外,再很难见到生命的迹象。党河水默默地滋润着敦煌绿洲,为这个地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天然保障。敦煌作为中原王朝的国门,也是王朝势力所能触摸的极限,它的兴衰伴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力。
在中国历史上,抛开短暂辉煌的蒙元帝国,对西域这块土地产生影响力的只有三个王朝,强盛时期的汉唐无需笔墨。纵使如此,其影响力也是随着国力盛衰时断时续,更多是军事上的征服,儒家文化并没有在广袤的西域扎根。反倒是随着蒙元上层贵族对伊斯兰教的膜拜,清真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这片空间遍地开花。
随着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曾经辉煌一时的河西走廊再也没有了往昔的繁华。虽然羌笛悠悠声依在,但是玉门关外的杨柳却很难沐浴中原文化的春风了,只剩下大漠深处的胡杨依旧傲然矗立。
朱明王朝时期,敦煌这座辉煌一时的边境桥头堡,被彻底遗弃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再次成为牧民游乐场。曾经繁华一时的边塞小城沦为废墟,在牧民的歌声中无声地哭泣。只有党河水还在那一直默默地陪伴,不离不弃。
七
再次把这块土地揽入怀抱的是另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清王朝。清王朝西征后,把天山南北和青藏高原统统纳入自己的版图。敦煌这个弃儿再一次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但此时的它,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人们只能追忆它曾经的辉煌。
清疆域的拓展,为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提供了纵深空间,但同时也影响了新兴的清王朝国策,延缓了这个文明古国由农业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过渡,海洋文明更趋于现代的节奏。
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角度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不可逆转,从大河文化向海洋文化过渡也是大势所趋。就像党河改造一样,修建党河水库,改造党河河道,这是用一种更合理更科学的方式去润养这块土地。敦煌这座新兴的历史名城,也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五洲四海的游客,只是轰鸣的汽笛代替了往昔的大漠驼铃。
这段逐渐被世人遗忘在戈壁滩上的党河河床,更像一个饱经沧桑又濒临迟暮之年的老人,在大漠斜阳中欲言又止,只能让后人隔着历史时空凭吊千年往事。
千古河床,千秋史话。
【责任编辑】涉 祺
张继会,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延河》《吉林日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