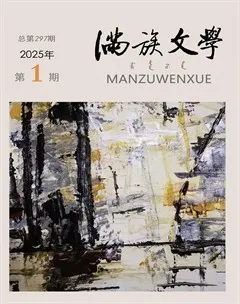错位
2025-01-01朱以撒
一
这个深秋,进到了三峡中的一段。窥一斑而试图见全豹,也只能如此了——有许多行程我都没有从头至尾地完成——看一部电影,片尾曲还未响起,我就要拔腿走了。买的书只看了几篇,都是中间部分,结局如何全然不知。就连我买的车也如此,两厢,不能算全须全尾。即便这样,片段中也含有了整体的信息。就如出外的这几日,餐桌上都会出现一条新鲜的鮰鱼,肉质细腻且刺少,甚是喜欢,但我也只品尝了其中的几节。许多喜爱都是如此,片断而已。
片断有片断之美。我通常是用对照的方法来进行的。一条江,两岸崖壁。山是静的,水是动的。崖壁如此坚硬,流水更显出了轻柔。崖壁的棺木如此远久,里边的人早已枯骨。下边的人正丰满地走着,血肉生机。草木或荣或枯,枯者焦黄,荣者深绿,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延续。长居于此的人早已见惯,此时摊子摆开,放上土特产,期待行者解囊。远来的行者只想着多走动,并不想照顾她们的生意。
人的想法、做法,就是以差异出现的。
有人问哪个时间段会看到更多的对比,我说秋季中的深秋。
车开了很远,来到乡村一个大湖边,看正在下坠的残荷。风很大,撩起人的衣角,如同荷叶乱舞。荷伸出湖面,正在走向它的终结。夏日不是这样的,荷盘圆润均匀,露珠其上,粒粒晶莹。此时再也难以挑出一张完整的叶片了。湖水日复一日地冷去,凌厉的风每日都在吹走叶片上的水分,让上边的绿色,逐渐成为枯焦,再过些时候,枯焦的叶片就会被风吹碎,只余下如同黑铁古铜的荷干直愣愣地戳着,使湖面平添了许多瘦硬和坚劲。我庆幸自己来得正是时候,一湖的残荷在此时到达它最耐人寻味的节点上。夏日里人们摩肩接踵来看荷花,看到它的好看——许多人都是奔着好看前往的。只有好看才让行者不枉钱财,内心满意。奔不好看而往的人终究是不多的,就如此行,在寒风瑟瑟的湖边,也就我们一行四人而已。如今的确说不上好看了,被风日复一日摧残的容颜,没有光泽、华滋,满眼可见疏瘦、憔悴。当一个人过了追逐好看的年龄,他对那些残缺的、散乱的、荒寒的形态,会更有一些倾心。直白地说,就是对这种自然而然进入丑的历程的景致,咀嚼、品咂出了不同的韵味。这些为数不多的人有探赜索隐的能力,是与大多数人感觉错开的,陶然其中,以为甚好。
古人笔下的残荷也是我乐意把玩的。张守中、陈淳、吕纪笔下,都有残荷的题材。此时荷是畸荷,人也是畸人。这样的题材在笔下,无论画技高下,趋奇溢怪,却都不会落俗格。而我看到的更多的荷画,攫取荷历程中最圆满的形态、色泽,好看是好看,脂粉气上来了,入艳俗境了。人与人的看法差异太大了,就如同看荷,没有谁会守在湖边看荷的整个历程。正因为这样,人们选择出行的时间段就见出不同。白居易有“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的看法,说的就是错位的道理——大家都在一窝蜂涌动的时候,我不妨闲适地待着,不必成为其中的一员。正是个人的识见差异太大了,由此丰富多彩,就像一出戏,有人喜欢看它的圆满喜庆,有的则看离散之悲,都循自己内心的走向便可。当然,如我这般观赏回来,是无从与人说道的。残荷之散乱、萧条、破败,是不必与人分享的。分享在时下越来越时兴了。我觉得私享更好,自己回味,贮存起来。
一条江,穿过两边崖壁一直向前。每一段都被人为地规划着,使自然景致嵌入了许多工匠的气味,使原先之无成为时下之有。在有与无之间,我还是喜欢选择无,选择早先空空荡荡的状态。回溯逝去的许多时间,这里是以无的面目出现的,只是江水与崖壁的映衬。现在,设置一艘仿旧木船固定好,一位显然是被粉饰了的村姑于船头坐定,正在以假动作绣着什么。接下来是古旧的石桥,又一位巧笑的村姑撑着花色伞,站在拱起的桥中,不时挥手。再往下走是几位服饰鲜亮的村姑正在浣洗,织品一半在手,一半在水,正在不断地拂动,使涟漪散开。这些设置太直接了,如果是无,则会有更多的隐喻和暗示——高崖、秋水、空旷、静寂,人于其中,理所当然浮想无端、横纵无碍,可能是与此景相投合的,或乖悖的;也可能离题万里毫不搭界的感受,纷至沓来,总不至于只是此时的这般约束。塞萨尔·艾拉早说过:大自然被人类的社会性包裹起来了。但凡有些审美价值,无非都记录了这样的情景。艾拉所说与我所想一致,尽管艾拉远在阿根廷,却也遇到了同样的场景。自然景致中,天趣是蕴含其中的。天趣循天道而强弱、浅深、藏露,总是难以言说,使人玄思,时而妙悟。这么一来,行程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声响。声响奔着明说而来,就像有人期望引导者多说一些,倚仗于此,说的和听者,得到的也大抵是皮相。内涵说不出来,隐喻藏于静谧处,超越了口说这种普通大众的需求。有人行一路,一言不发。旁人以为他装深沉,实则不是。
回头的时候,天色暗了下来,人工的装饰也准备撤离。浣女已经从水边消失了,石桥上不见了撑伞的影子,船头的绣女已经躲入舱中。
此时,有点像本来的样子了。
二
三弟发个信息来,问我有没有读过残雪的作品——他对文学是没什么兴趣的。开个画廊,字画买进卖出。兼作书画培训。画廊里有个茶桌,每日都有一些闲下来的江湖弟兄在这里喝茶,他们是不可能买字买画,只是闲聊中透露各种疑真疑幻的信息,使日子一天天过去。估计是里边的某个人提到残雪了,让三弟记住这个名字。
我说没读过。没读过就是没读过,不必装曾经读过,更不必自诩读懂了。我想起旧日文人刘文典的一些趣闻。他治《庄子》,认为天下只有两个半的人能懂《庄子》,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他刘文典,而所有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只能算半个。现在也有人说天下只有一个半的人能读懂残雪的作品,一个是残雪本人,半个是她兄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如何无遮拦地表达都可以。既然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人了,我还是不想去买这个人的书来读。我有自己要忙的事,没有闲工夫另开辙轨。电影《水芹菜》中,主角斯蒂文这么说:“我试图表达的永远是孤立的感觉。”孤立就是不趋附,虽形单影只,但内在充实丰富,自己看的是另一个方向的文字——有的文字和我能建立起关系,有的则不能。我本快意,其中的缘由,就是离有的文字近了,有的又远了。
我看的一些书都不是时兴的,有不少是小人物写的,说出来很多人不知——小人物、小事件,不会让人注意。很多人是忽略小的。清人袁枚认为“游山者必登岱,观水者必观海”,其实未必,小山川也有自己的许多特色。山不在高,贵在层次,水不在深,妙在曲折,就看每个人的趣好。这也使不少人聚在一起分享某一当红文本时,我浑然无知。无知就无知,不必装有知,这是我一贯基本的认知。有时也想把这本热门的书买回来看看,但很快这个念头就消失了——我与我周旋久,还是专注自己的眼下。
三十多岁时有不少如我这般喜欢下笔写一些文字的人。那时正是写什么都热门的时节,有时在一些场面上就相遇了,更多的是在报刊上相遇,他们读到我的文字,我也读到他们的文字。有时相互赞同,有时也商榷,弄得不欢而散。尽管如此还是各自不停地写。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年,我以为这会成为一种常态,一直持续下去。忽然有几年,我发现好几个人从纸面上消失了,他们都约好了似的,像有的城市的景观灯,到晚间十点半就各唰唰地不再闪烁了。世间有许多事要比写文来得有意义,或者说有意思。这时我正好读到约恩·福瑟的一本书,他在里面谈到了时间这个问题。通常认为,对一个人来说,有过去、时下、后来三个时段,但他认为时间不是像闹钟那般以线性为表现的。人宛如在梦境里,时间囫囵一团可伸可缩。人不是一以贯之的,块面般地忽此忽彼,非流动,而是跃动。约恩·福瑟强调人的意识,如幽梦、幻觉——没有哪一个梦是一气做到底的。人生如梦,不是说稍纵即逝,而是在于它的变数。很多年后我遇到了搁笔中的一位,他很惊异我此时还在乐此不疲地书写。他的问题是,像我们笔下写的是否还有人看。我说我之所以写还是给自己看的,他人看多看少也不是我关心的。记得简文帝曾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会心处,专注于这个会心处,一个人还是做得到的。过去、时下都如此了,至于以后,随年齿渐老大,更不会想改弦易辙,还是会继续倚仗于写——不写,我就更是无用之人了。
手稿渐渐地多了起来,它是铅字的前身,但比刊物上的铅字要生动和率意得多。手稿上面都是改动的痕迹,涂抹的划痕,要到定稿的那一份才算清晰起来。可是如此多看几眼,又会在上边再改动起来——文字是经不起看的,看了就会发现差错,就要下手,往往是这样,又花了不少时间。此时我就会歆羡数学的推导,答案正确了,一切也就可以停止下来。文字没有这样的答案,它永远都可以被修理,可能修理得更合己意,却不一定更好。手稿只能留着自己看,给别人看徒费精神,也不礼貌。在我看来,手稿是最不装饰的。一个人情性、态度甚至连动作、习惯都在里边,只是旁人未知罢了。从一些资料来看,不少作家都内向得不得了,他们在对外的文字上下功夫,写了许多文本,在对内方面则写了许多日记、信函,比如伍尔夫、卡夫卡、艾略特。卡夫卡给菲利斯写了超过五百封信,艾略特给艾米莉写过的信可以超过一千封。而伍尔夫,二十六年来写下的日记,是多么大的一个数量。这些写给对方一个人看、写给自己一个人看的文字,裸着心灵、情性,无一丝遮掩,简直是赤裸裸的表达。尤其是日记,记每日的欢悦、哀怨,还有一些锋锐之见,只适宜藏匿于纸张深处。住集体宿舍时,我晚间要写日记,就开锁打开木箱,写毕又锁于箱内。在我看来日记也有如定时炸弹——如果一个人在日记里作假,写些美颂谀辞,那干脆不要写了。真实表达是日记的灵魂,心灵史的一部分就是由日记来承载的,它的危险性也因此具备甚至越来越危险。伍尔夫去世十二年后,她的先生伦那德才选编了伍尔夫的日记,这就是著名的《一个作家的日记》。为什么要等到十二年,肯定是有原因的,应该是世道人事发生了变化,这枚炸弹可以安然地展示在众人的面前。
后来我也不写日记了,写信也稀少,我当然知道其中原因。我现在手写的文字,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在进行散文创作,或理论研究。乱糟糟的手稿有时让自己不知身处何处、今夕何夕,混沌不堪。大家都在迅疾地赶路,满街快递小哥疾驰的身影就是这个城市的节奏。但具体到某一个人,他可以选择慢,选择相反。
到书法馆去看展览,明显觉得写草书的人多起来了。写二王这一路的,衍生开来,便占了很大部分。学张旭、怀素、黄庭坚、王铎的,如挟大海之风涛,显然以气胜之。慢慢看就看出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宜写草书,就如舞禅杖唯鲁智深得宜,林冲还得使枪上手。只不过人生于这个迅捷之世,下笔莫名其妙地快起来。我于草书没太多兴致,它需要急速,我跟不上,如果进到狂草,人还得有狂放之气,纵横之力。草书是热门,很多人奔草书而去,适宜的人,不适宜的人。潮流的涌动就是由许多细小的水珠聚合在一起的,风来,就鼓荡起来。在时兴面前我还是惯常自守,先锋的事让别人做去,总是要有人来开拓新境。相比于写草书的激情,我是守于常道的,找些楷书来,慢慢写去。楷书的端人佩玉之相,使写的人心安,使看的人也心安,常道遵守了再说,至于日后是否通变,难说。有时楷书也会有一些奇异笔调出现,我都视为偶然。心机徐缓、心事平平,笔下没有激情襄助,真的很难出彩。和我谈草书的人多,很推崇怀素“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的醉后状态。这里不免有夸张手法,但笔下这样速度的人,天下是无多的。更重要的是如此疾如星火的速度还能毫厘不爽,这样的速度无疑具有了绝高的审美价值。具备速度的文士自古以来都受到赞美。刘穆之一日百函,何涓一夜赋潇湘,王璘日试万言,颜延之受诏便成,秦少游对客挥毫,皆为快手。如我这般人死活快不起来,那真是没什么好自责的,只能自安,不乱。
现在的很多想法与过去相差太多了。留校任教之初,精力剩余太多,也就经常去听一些与自己专业相远或者不相干的课,觉得为学之道如此。后来才知道不须如此多情,自己的专业还有那么多的疑难未解,为何不用功去。大学对教师的要求并非通才,而是专才,广大度是次要的。使自己渐渐臻于熟练,如果能循旧辙而开新境,那就再好不过。我适宜这种规范,说得世俗一点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别人的专业与我何干,就如我的专业,也与其他教师无干——出差公干好几天,没人替我上课,只能回来再补。这样,我就越来越熟悉自己这一摊的功能、任务,还有方法、方式,同时与其他越来越远。守之以一,而不是游移不定——我几十年前的大学生活大抵如此,让人习惯于单干,不耐烦与人合作。这和我讲授的书法艺术如合符契。书法语言的表达就是以不与人合作为前提的。始终一个人写、写、写,即使有人好心来为我牵纸,我也是谢绝。雅克·里维埃说:“我们遇到的那种语言是特意为我们挑选的。如此令人激动,而从前并不知晓。那种语言不仅安抚我们的感觉,也向我们揭示我们自身。它触及我们灵魂中的未知区域,拨动我们的心弦。”其实,这段话也是我要说的,只不过我会把这段话里的“我们”,全都改成“我”。
接下来就是下课了,我到教工食堂吃午饭。每个教师排着队,端着盘子,挑选菜肴。每个人盘子里盛的都不相同,过了秤,算了钱,选一个位子,坐下来慢慢品尝。食堂里很静,吃饭者在讲台上已经开讲半天了,有的讲魏晋文学史,有的讲热力学、植物地理学,还有的讲结构化学、复变函数、生物信息学,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课程。现在懒得说话了,只是吃菜、喝汤。白米饭质量甚好,菜肴也是自己挑选的,甚合口味,不可辜负。想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自己守住这个专业,下了许多功夫,已经痴迷于单干了,不禁有了明月入怀的畅快。
【责任编辑】王雪茜
朱以撒,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出版有《俯仰之间》等五部散文集及多部书法著作。在《十月》《散文》《散文·海外版》《美文》《散文选刊》等刊物发表散文三百多万字。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最美散文》《中国散文精选》《中国年度最佳散文》等一百多部选集。曾获首届冰心散文奖,全国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