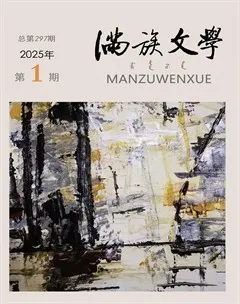那件事情,先锋小说
2025-01-01陈鹏于晓威
于晓威:陈鹏兄好,很久就想跟您聊聊了,惜乎多年您居云南,我居东北,相隔太远。上次云南开会,也是匆匆一见,我们似乎都太忙了。好在多年,我觉得我们彼此还算是心气相通。这次读到您的中篇新作《下午,翠湖》,我很兴奋,您对自己的文字和小说要求很严,写得也不多,这部小说让我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它仿佛集合了罗伯-格里耶、略萨、米兰·昆德拉以及元小说和反小说的很多后现代主义叙述特点,用您文中反复嵌入的句子来说,“那件事情”,套用一下,我觉得这是一次事件,是关于当下小说的一次美妙的事件。作为先锋派小说家之一,您觉得自己这么干的心得是什么?您是否在意别人能否读懂这部小说?
陈 鹏:谢谢晓威兄对这个小说的肯定。其实我对自己每一部小说都有要求——尽量,尽量不太一样。既和诸多同行小说不太一样,和自己上一部小说也不太一样,虽然,很难,也多有线性的“讲故事”的小说,但基本上,我每一个中短篇都尽可能体现“元叙述”特色,即关于小说的小说,袒露写作者的小说。这个观念在我小说中根深蒂固,我想,这既是马原对我的影响(我从不避讳他对我的影响。了不起的马原),更与我十余年记者经历有关。新闻是对事实的再现,但这行干久了,你会越来越困惑于你面对的现实——到底何为现实?你选择的就是现实?还是,你没写下来的才是现实?这就很让人沮丧了。也就是说,它逐步构建了我的世界观:怎么看待世界。我认为现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所谓真相,永远不可触及。这构成我诸多小说的底色,法国“自我虚构”一派也给了我重大启发。是啊,就应该这么写小说,把自己也写进小说,让你虚实难辨,真假难分,这不就是叙事的快乐之一?至于格里耶,他的《为了一种新小说》是革命性的,我最近创办发行的刊物就叫《新小说手册》,就为了一种“不太一样的”小说。略萨的结构主义对我影响不大,米兰·昆德拉的哲理或复调小说更是另一个路子了……我的确不太在意读者能否“读懂”,实际上,小说家最在乎的还是自我完成,不会考虑读者,这么说绝非夜郎自大。试想,自己都不满意不尽兴,写作还有意义吗?其实因为二十年记者经历,我的小说向来是“好看”的。
于晓威: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您觉得先锋文学的使命完成了吗?它当下是否还有意义,有的话,是什么?
陈 鹏: 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以莫言获奖为标志。但骨子里,从更深远的文学史意义上看,又远没有完成。当年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们的写作抵达过世界级高峰,足以与最优秀的文学等量齐观。我这么说不是瞎吹,自信有海量的阅读撑着。我相信马原的“叙事圈套”、苏童的“人性之恶”、余华的“死亡叙事”……都好,都是了不起的突围,让中国的小说突然挣脱桎梏呈现出应有的精湛的叙事面目,而非仅仅只有“革命现实主义”一脉。惜乎后来没走下去,没能走得更远(马原小说例外),个中原因太复杂,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学自身的……先锋之后,“新写实”崛起,一种向世俗立即投怀送抱的小说运动开始了。先锋小说最大局限或许在于,小说的“技”被当成了小说的全部。但技术是不可穷尽的。小说,说白了关乎人类最本质的存在,因此如何以“技”言“道”,尤其讲述人类共通的存在之道,更考验作家的雄心与能力。这的确是一项长跑赛事,不容马虎,也不容游移、取巧,要的就应该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在这一点上,我不太喜欢的乔伊斯反倒是个正面典型——死磕到底,语不惊人死不休,必须撂出震世骇俗的文本,充满想象力和原创性。不得不说,当年我们的先锋作家短时间内博得大名之后,过于轻巧、急切地退回了世俗叙事一路,这与美国的唐·德里罗、约翰·巴思、巴塞尔姆们一辈子孜孜以求比起来,就太让人遗憾了……固然,作家自己没有所谓“先锋的义务”,但先锋运动不该过早凋谢,先锋小说和先锋技法早该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应该有更多“好事者”跟上来。可惜啊,我们好像轻轻松松就为先锋派们留下的遗产投了反对票,虽然嘴巴上常说,那些玩意儿早就是常识了,还有什么稀奇?问题是,一旦很多有先锋气息的小说出来,大多会遭到主流期刊的拒绝。先锋遗产,逐渐成为被埋葬被凭吊的残骸,仅供观瞻而已。实际上,好小说大多基于反叛,否则原创性就无从谈起。这方面我多次聊过,法国小说就是很好的榜样,一直在反叛,在前进,如去年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小说,多么新鲜生猛,多么深刻而本质。相比之下,我们太偷懒了。原因很多,如国情、观念,等等。莫言说我们都是讲故事的人也误导了很多人。实际上他正话反说,一位一流的小说家又怎么可能仅仅满足于讲故事呢?当下,我们还是需要往前走,继续探索,继续反叛。好,问题来了,眼下到底该反叛什么呢?——对一种庸俗的故事性写作发起挑战,算不算?向埃尔诺这样的写作致敬,算不算?答案是肯定的。它们将逐渐改变我们的文学生态。
于晓威:从您这部小说散漫而精致的叙述中,我读到了每一个人物生命的某种无力感以及尖锐的疼痛(包括叙述者),包括况味,它是一个复调的东西,折射许多“能指”与“所指”,结构或解构。吕克·赫尔曼和巴特·维瓦克在其所著的《叙事分析手册》里,提到过“叙述代理人”的问题,这部小说的视点、人称都有很多变化,您觉得在小说创作中,叙述者以及叙述重要吗?假设一下,它在一篇现代小说创作中占有多大比重?为什么?
陈 鹏:这个问题太具体了,我持保留意见。哈哈。简单说吧,叙述者的声音有时退居幕后完全让位于小说叙述,比如加缪的小说。也有叙述者的声音远大于小说叙述的,比如我推崇备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种极致的个性强调小说人物、故事的独一无二,它必然构成一部伟大的独具个性的艺术品。注意,小说是最难最复杂的艺术,绝不仅仅是故事。它是它自身,不会是某种功能性使用手册或人间生活指南,因此,个性,艺术性,丰富,内省,终将构成一部小说杰作的全部。
于晓威: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对当下文坛的小说写作满意吗?为什么?
陈 鹏:不太满意。这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写作,我们不能随便就把自己摘出去。我上面大概说了原因,我们的文学确有单一之嫌,太重视线性的现实主义法则,可是,别忘了,卡夫卡也是现实主义之一种啊,我们应该把诸多现代派后现代派的丰富遗产都“拿来”,不是拒绝,不是仅仅保留某一种“故事现实主义”,那会成为“故事会”的升级版甚至不如“故事会”。
于晓威:您什么时候想当作家的?您自己写小说时的初衷是什么?
陈 鹏:大概十四五岁就在做作家梦啦。我从小踢球,大概就是从初二初三开始吧,训练之余我埋头写小说,胡编各种好玩的故事,古代的现代的。队友争相传阅,这种写和读的互动对我都是刺激。写小说的初衷简单至极,就是迷恋文学创造的那个无与伦比的世界,它和现实截然不同,太独特了。我记得高二高三我不是忙于高考(那时候一边训练一边备考),而是拼命看小说,《小说月报》每期都买,同时也读经典,沉醉不已。一边读一边继续写,十七岁在《滇池》发处女作,激动坏了。一个中学生能在《滇池》上发小说,算是大事件了,我从此“入坑”,哈哈。
于晓威:您曾做过著名的《大家》文学杂志主编,文坛经常奇怪这么一本瑰丽而迷幻的、具有文本实验性写作特点的刊物,怎么会产生于云南,它的偶然性或必然性是什么?
陈 鹏:云南偏居中国西南一隅,有点山高皇帝远的意思,所以云南人行事难免天马行空;再就是,云南是高原,缺氧,就更容易让人胡思乱想了。其三,这地方生活着二十五个少数民族,所谓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自然而然有碰撞有沟通有交融,文学肯定是不一样的。其四,兼容并包的西南联大精神对昆明影响甚巨,迄今不绝,所以云南、昆明一直就自带某种先天的魔幻先锋气质,诞生一两部先锋杂志再正常不过。当年《大家》创刊就得益于之前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美文学书系的铺垫。那套书系,影响太大了。
于晓威:您喜欢跟人打交道吗?
陈 鹏:不喜欢。从小就在集体长大,对人群烦不胜烦。少年时期的记忆也多苦涩,严重影响了我成年后的性格,人际交往一直有缺陷。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读,写。当然,身边也有二三最好的哥们,能偶尔小聚,足够了。人其实是不需要朋友的,人生而孤独,是常态也是本质。为了应对孤独,写作是其一,择一二友人,算是其二。
于晓威:您对颜色敏感吗?您最喜欢什么颜色?它会给你带来特别的记忆吗?
陈 鹏:还算敏感吧。最喜欢的还是球场的绿色。从小水泥地上、黄土地上摸爬滚打,一旦上了真草球场,那叫一个幸福!堪比现在突然发一个长篇。哈哈。所以每周还是要踢球,要拥抱九百平方米的浓绿,呼吸昆明真草球场浓烈刺鼻的香气,会让我觉得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于晓威:遇见作者写得不令您满意的小说时,您经常会跟他们说什么?
陈 鹏:是我在编辑《新小说手册》的境况吧?会遇到,会让他们改一改,朝某个方向,再试试看……如果是朋友的小说,偶尔读到,不满意,说不说,两可。有的老友是能说的,我就直接告诉他哪哪很棒,哪哪还不太好。当然,这纯属业务交流了。
于晓威:您对写作场所要求很高吗?比如,不得不出差或旅行的时候,您能写作吗?
陈 鹏:不高。我通常在家写作,书房,大多站着写——效仿海明威。我随时可以进入,这是当记者时训练出来的,任何时候都能写。出差、旅行也如此,房间里写,毫无问题。
于晓威:您二十岁之前读到的印象最深的文学作品是什么?还记得吗?
陈 鹏:十七岁,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从此爱上老海。爱了一辈子。后来发现《老人与海》还不是他最好的小说,他最好的还是那些短篇,精妙无比。再就是《永别了武器》《太阳照常升起》。当时,我记得当时第一次读海明威整个儿蒙了,太强大了,多简单的故事啊,基本上没什么故事,就一个老头,一条大鱼,居然写得如此惊心动魄,没一处败笔,没一句废话,这不是最棒的小说是什么?我还记得我读完之后久久伫立在阳台上,那地方也是我睡觉的地盘,遥望昆明天空,鸽群起起落落,遥想那个叫圣地亚哥的老人独自驾着小船在大海里飘荡……
于晓威:据我所知,您还是国家二级足球运动员,可以同时讲讲您的相关履历?
陈 鹏:我很小就踢球,差不多十岁进了准专业队,也叫体校校外班,一拨伙伴从小一起生活,训练,比赛。我们那一拨孩子是昆明最好的,1988年曾缔造昆明校园足球历史,一举在幼苗杯西南赛区比赛中出线,跻身全国四强。后来1989年、1990年也都跻身全国四强。但是我们整队都没有选择进专业队(职业队),我高二高三之后太厌倦足球了,又忙于高考,顺利考上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管理专业,也在院队踢过,但基本上,大学之后,算是正式向专业化足球道别了。大学期间拼命写小说读小说,大批经典就是那时候读的,如饥似渴。武汉体院图书馆的名著挺多,我徜徉其间乐此不疲。周末就写小说,在《青春》《萌芽》发了几个。1995年去《大家》实习,对我影响太大,你突然进入文学现场了。从未离开足球,一辈子的挚爱啊,其哲学与老海的精神多么相似,你可以毁灭我,不可以打败我。
于晓威:您的小说写完或发表后,家人们每次都读吗?他们(她们)如何评价?
陈 鹏:一概不读。他们热衷电视剧。哈哈。
于晓威:您看电视吗?所有的电视节目中,您最喜欢看什么节目?为什么?
陈 鹏:偶尔。主要看足球比赛。间或也看《十三邀》《圆桌派》和陈丹青《局部》之类,其余,我最爱的是关于美术的纪录片。我热爱名画。对古典派、印象派、后印象派、现代派、后现代派情感颇深。每次去巴黎都要泡在卢浮宫、奥赛、蓬皮杜。尤其热爱英国的弗朗西斯科·培根,这家伙画出了人类邪恶又天真的潜意识,太棒了。戈雅后期也多棒啊!2019年我去蓬皮杜刚好撞上培根个展,极震撼。当然,梵高也是我的挚爱。哎,谁又不爱梵高呢?
于晓威:我记得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里,论述过“爱欲”或“性”与“思维机器”之间存在的悖论。文学作品从不应该回避写“性”,这是一个常识了,然而,我还是想饶舌一下,您觉得真正的文学作品中写性,究竟是为了什么?
陈 鹏: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性要写好太难了,所以不如点到即止。劳伦斯是正面写还能写那么好的典范,但中国语境大不同,凡性描写,都不免有博眼球之嫌。优秀的文学经典中的性描写,应该与最具体的人和人的处境水乳交融,比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它与劳伦斯以自然抵御工业的想法高度契合。否则,不如不写。
于晓威:如果可能的话,您最想跟国外的哪一位作家成为同时代的好朋友?为什么?
陈 鹏:海明威。他知行合一,他充满力量,他如此慷慨……
于晓威:您觉得什么情境或标准之下,您自己的写作才是成功的?
陈 鹏:我想,首先还是要能写出堪与经典较量的文本吧。我说的经典一定是19世纪以来的经典。大经典。要能写出《罪与罚》《太阳照常升起》《堂吉诃德》《白鲸》这样的东西,你还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是现在衡量标准不一,好的往往被说成不好的,不好的又被奉为新的经典……但文学是有标准的,有绝对标准。这种绝对标准基于经典之上,也就是说,你的反叛,你的原创性,是踩在巨人肩膀上的,你不能跳离那只肩膀,不能怪力乱神自说自话。继承然后创新,这就是文学最难的地方啊。
于晓威:您的业余爱好还有什么?
陈 鹏:坚持踢球。再就是游泳,看画册,练习书法,听摇滚乐。对,我热爱摇滚乐。
于晓威:您会一直写下去吗?
陈 鹏:会,这是最大的人生乐趣与意义所在,干吗放弃?
于晓威:好,最后一个问题,您最想跟写小说的同道们说些什么?
陈 鹏:好好活着,认真写。对,认真,请务必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