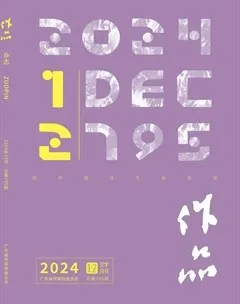此岸(散文)
2024-12-31忽兰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布尔津县城里有两排最老的大树,它们是普通的杨树,不是那种笔直的穿天杨,就是散漫模样的粗大杨树,叶片比巴掌大,盛夏时节绿到几乎黑亮,生长在哈萨克小学校园的正中间,简直就是长长的苍绿蓊郁的拱廊,从正北的大门一直到正南的后门,一列有二三十棵,总共五十棵,一个怀抱那么粗。
还有一棵很老的大树,在南大桥进到县城的那截坡底下,守住了一个路口。这是一个大拐弯,旁边是哈萨克小学的土坯围墙转角,是父母去上班我们去上学的必经之路,自行车使劲一拐,擦过大柳树。如果是走路,我们就过去抱一下,摸一摸沧桑的树皮,我们把耳朵贴上去,试图听见树心脏的跳动。
柳树枝丫像我们的头发一样蓬乱,被布尔津一年四季的大风随便吹。我们三姐妹蓬乱的自来卷长发,真像土坯城堡里的野生公主,每当我们手牵手走过两排最老的大树建构起来的绿色拱廊,我们就是额尔齐斯河谷森林里真正的公主,拥有淡漠的脸。
那些年我们仨一字排开走在布尔津的柏油马路上,嘴里永远在吃东西,冰棒,口香糖,杏干,葡萄干,月饼,馕,奶疙瘩,苹果,果丹皮,俄罗斯小面包,穿着喇叭裤健美鞋,头上围着七彩纱巾或者红格子绿格子围巾。会不会有老布尔津人至今记得我们斯文淡定其实野蛮的样子,我们的侏罗纪世代,身体里是游鱼,眼睛是可可托海的宝石,呼吸是北河森林里的白蔷薇?而今我们仨在祖国的大地上最北最中最南如是分布,偶尔回忆起布尔津的大树和大风,我们的蓬勃卷曲长发飞舞在空中,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好交织苦涩的滋味。
苦涩是因为那两排古老大树在上世纪初期栽下,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暑假,我放假从乌鲁木齐回来,蓦然发现家门前大坡下哈萨克小学校园里两排最老的大树,我们的伙伴,它们只剩下了两排和地齐平的树桩子,它们死了!它们被世界杀死了!我们心惊地蹲下来摸着树桩的木头。母亲安慰我们,让我们抬头看校园西南角,那里像苗圃一样种起密密的树苗。母亲说,要不了几十年这里就会是一片小森林了。我们不相信。我们难过得几乎要流泪,那天起我对命数充满无奈。
而那棵巨大的柳树拥有奇异的命运,它没有死,它目睹了两大排老杨树的被无辜处死,也曾心凉过吧。但它负有使命,它知道我们仨,和它长着一样乱发的我们,放假回到布尔津就要来注视它抚摸它,它便暗施魔力,改变人族的决定,让自己活下去。人们开来挖土机将它挪到南大桥下布尔津的南大门处,像是招财猫或者发财树。我们打听到它的踪迹快步前去又一次摸到了它,它已历劫完毕,叶片抖擞,树身敦实,树冠温柔,我们亦是历劫的人,在社会上历练,面包渣子掉了一地。
如果大街上没有人,我想抱住柳树哭一场,它见过襁褓中的我,我的蹒跚学步,我背上书包开始上小学,我学会了骑车,飞驰向中学,我考上了学,告别布尔津,与它倾心作别。青年的我回到布尔津,埋头亲吻了它,它会永远在,不,它也许会突然死掉,人世是有很坏的,这样的深刻思考已在我们的潜知觉里,所以我们常常含有悲情。多希望这悲情始终坚固,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庸俗,而庸俗是致命的灵魂毁灭。当我因庸俗而大笑,一个声音对我说:当心,无知无畏的地球人!
曾经老杨树们的叶子在四月生出,五月招展,六月七月深绿肥大,八月九月红冠燃烧。我家红柳枝篱笆的大门对着坡下的哈萨克小学校园,树叶集体舞动,在与万物说话,形成天籁,也来到我们的耳畔,我们在睡梦中听得格外清晰,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如果基因里刻写了多些的善良和温暖,那就是布尔津的它们在早年交付于我们的。它们已消逝得干干净净,中年的我在回忆的瞬间确然嗅见了那亿万万墨绿叶片的浓郁香味。
多年后我的阿勒泰文友李文强告诉我:你说的这个应该是额河杨,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是阿勒泰这里特有的银白杨和黑杨的天然杂交树种!
2
我们的父亲是木匠,我们的母亲是裁缝,我们三姐妹是小学生,在布尔津及至全新疆没有一个亲人,像是活得孤绝的一家五口。小县城里别的家族活得风生水起根系相连一荣俱荣简直可以写一部《红楼梦》。但是我们不会在意这些,我们一家五口热爱早饭午饭晚饭,热爱去河边洗衣裳和散步,有时我们骑上自行车在红霞漫天的傍晚往电影院去,我们吃苹果看电影,在黑漆漆的夜里沿着河堤往家赶,白炽灯红黄的光一亮,我们热爱夜里煮汤圆或者饺子,煎馒头片或者烤土豆,用巨大的搪瓷缸泡深绿的大叶茶,我们心满意足睡去,土坯屋子冬暖夏凉,五口人静静地呼吸,我们的猫儿狗儿也在温暖的屋子里。似乎这些记忆是上苍对我的惩罚,不然为何我泪水涟涟心如刀割;似乎这些记忆是上苍对我的奖励,中年的我起身望向天空,活着毕竟是好的,因为我曾拥有过。
我家坡下是哈萨克小学。也就是说我家住在一个缓缓的坡上,地势略高那么一些,向东连着的是布尔津的东戈壁,后窗对着的就是额尔齐斯河,我们只要走出后院的小门,几十步就能站在高高的河堤上,面向元史里记载的伟大的河流。我们是河谷的孩子,也是戈壁的孩子,是森林的孩子,是草原的孩子,是大山的孩子,我们是一个山东人和一个四川人的孩子。
我们那里说,山川半的孩子最聪明,因为相隔甚远所以产生的新的基因会很优秀。我们三个立刻信了,姐姐觉得自己很智慧,我觉得自己很勤劳,妹妹觉得自己很优雅。我们三个推着勒勒车往坡下走,一条很小的土和鹅卵石的原始路,我们走过娜扎提家的黄色大门,走过小学的后门,索性穿过小学,从正门出去,就到了县城大街上,那里热闹非凡,人来人往,压挂面的铺子就开在那里。我们的勒勒车上是半袋面粉,母亲交代我们午后带上面粉去压成面条。我们迈着矜持的步子推着勒勒车,妹妹坐上了勒勒车,神情更加优雅,姐姐机灵地掌舵,我扶住一侧车把手,遇见坡坎则奉献全部的力量。
就是这样的一家人,晚餐是羊肉西红柿土豆下的汤面条,搭配四川泡菜——长豇豆和长芹菜,绿辣椒和包包菜,推了一天刨子的父亲面容黧黑额角有青筋满身刨花味,裁剪布料站了一天的母亲卷发蓬乱眼角下垂满身线头。就是这样的一家人,有谁会用温暖的目光多注视我们一下呢?竟然是有的。娜扎提他们家。
娜扎提是我们童年的伙伴,我们年龄相仿,她的眉毛和眼睛极其黑,那眉毛和眼睫毛简直是电影里的印度女子。她家的门是黄色的,很大,推开门走进去是一个很大的院子,种着两三棵年轻的榆树,屋子更高大,蓝色的门和窗子,白色的窗帘。走进正屋,地毯和壁毯,长条的大餐桌上是水晶器皿盛着的干果和点心。我们上到一个铺着花毡的大炕,娜扎提从墙上取下冬不拉我们弹拨着玩,说点儿小话。我们喝着娜扎提熬的茯砖茶,小瓷碗里半碗浓茶,搭配山上牧民做的奶疙瘩和她的母亲烤的牛奶鸡蛋饼干。到了傍晚我们就回家了,因为我们要做晚饭了,中午和的面已发开,我们姐妹仨安静地揉面,生火,馒头起锅的时候大桥上是返回的牛的列队,娜扎提家的也在其中,她会带上一根树枝在桥头接上她的牛儿。她的母亲在牛圈里蹲着挤奶,一个白色的小铁桶。
娜扎提的父亲是我们布尔津县的县长,大家都叫他哈县长。他是一个个子不高,肤色很白,神情和气的男子,眼睛细眯着,会漾开微笑,常穿灰色的中山装,我们遇见了就会喊一声叔叔好,因为他是娜扎提的父亲,而娜扎提是我们的小伙伴。我们的父母亲则喊他哈县长好啊,佳克斯嘛!
我总是相信这人世间会有上天安排好的一个好人就在那里,当他看见你受苦就轻轻走了过来,搀住你虚弱的胳膊,扶你离开泥泞的小道,他与你非亲非故而你并没有能力回赠他什么,但是他就那么坚定地向你走来。
哈县长就是那个无偿自愿地帮助我们的父母的人。我们童年的时候国家鼓励个人挖金子,挖到的金子必须全部卖给国家的银行。我们的父母亲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赶着驴车奔向了更深的山谷和河谷,这将是我们五口之家这个清贫的小小家族的第一桶金。哈县长担心我们的父母挖金子被当地的牧民阻拦——牧民们都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哈县长为父母亲写了一张纸条,那上面用哈萨克语写着:牧民同志你好,这是我的邻居,也是我们一家人的好朋友,他们响应国家的政策到你们这里挖金子,希望你们不要驱赶他们,并能够给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比如空置的木屋,可以借给他们住。
我至今记得那间木屋,我和妹妹暑假随着父母亲来到森林里。森林里的树木笔直高大,小小的我们第一次仰起头向森林的天空看去,那树就嗖地几乎插到天上去了。白天他们在河边淘洗金子,我们在木屋的蚊帐里大睁着眼睛倾听暴雨,等待他们回来。有牧民的马从木屋边走过,但是我们知道有娜扎提父亲写的纸条,他们会友好地待我们。纸条在父亲的藏蓝色中山装大大的口袋里,掏出来展开,折叠好装回去。到了秋天他们赶着驴车从森林里返回家的时候,那张纸条已经敝旧不堪了。
七十岁的母亲是布尔津各路消息的接收者之一,而我们却疏离太久了。有一年春节全家团圆,母亲说,夏天回布尔津去政府大楼办事,遇见了娜扎提。我和妹妹都没有接话,陷入悄悄的沉默里,我们怕问多一句话都会惊扰到那玻璃人儿一样的温柔沉静的娜扎提,她微笑地注视着我们,那墙上的冬不拉,十岁小姑娘亲手熬制的砖茶。
3
房子是安全的,房间是飘摇的。传说里的公主生活在城堡里,城堡的一个阳台独属于她。我们三姐妹在额尔齐斯河边父母亲建造的那所房子里昏睡。土地局的人来测量,前后院五百平米,夜里父亲笑眯眯的,他说,这五百平米从此就是我们自己的了。我们安全地昏睡,夏日有凉爽的风从窗外的水井和黑枣树那里吹进来,绿色纱窗让世界更绿。冬天母亲把白菜从菜窖挪进来,几十棵白菜挤挤挨挨几乎占据我们房间的一小半,这些白菜立春之后开始腐烂,就剥去外面的帮子,继续腐烂继续剥。春天终于来到北国的时候,它们小小的,父亲用虾皮凉拌白菜心,用小刀剜去土豆的绿芽,冬天终于结束了。
有一天我们去一位老乡家里做客,山东人,我们的父亲有三个女儿,但是这个山东叔叔家里只生了一个女儿,叫作婶婶的女人,大约身体不太好,所以不能继续生养了,否则一个山东人的家里必定是要生出儿子来才罢休。我们大为惊异的是这个女儿拥有属于她自己的一个房间,白布门帘上绣着一簇红梅,她的名字叫丽梅。她掀开门帘走出来,她掀开门帘走进去,我们姐妹三个大大睁着眼睛,她的房间里有独属于她的木床、木桌、木椅、木头衣柜、窗帘、木桌上一摞杂志,《少年文艺》和《奥秘》。她与我们差不多大,但是她从不与一层层腐烂下去的白菜同住一屋,她是一个真正的森林公主。
在我家,父母亲拥有一个屋子,一个放着电视和餐桌的房间叫作客厅,一间三姐妹同睡一张大床的房子,一进门是厨房,通向后院的小房间其实就是一条稍宽的走道,放着一个巨大的水缸和洗衣机。我们逡巡一圈终于明白我们谁也不可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一个房间,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无法以公主的曼妙身姿掀开绣花白布门帘进入闲人莫进的自己的空间,那里面,一个叫丽梅的少女以幽香和秩序,沉静长大。
房子是安全的,房间是飘摇的,这是父母亲的家,它是我们的,但也可以不是我们的,因为我无法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既无心爱之物,也无存放心爱之物的房间,我打扫干净每一个房间,来到院子里站定,就像这里是我生命中一个较为长久的驿站,我时时在停留中与它作别。我仰望蓝天中心的老鹰、排排大雁,就觉心中有诀别的悲怆,我已知自己原来是一无所有的,而未来有什么我不得而知,更觉心中困顿寂寥。
母亲对渐已长大的我们叮嘱:啥都要靠自己挣,就算是丈夫还隔着一道手。
母亲的话更加重了我的忧虑,如果一个女人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方式——嫁人——其实也改变不了命运,我果然就得靠自己去挣,而我又能挣得什么呢?
叫丽梅的女孩和姐姐同龄,但我们并不在一起玩。如果在学校或者大街上偶然见到,我们也只轻微一笑,略略点头,各走东西。丽梅的父亲是县文化馆馆长,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电影海报贴在电影院门口,那上面酣畅浓墨的四个大字——木棉袈裟,就出自他之手。丽梅的母亲在教育局工作,早年毕业于师专。她喜欢自己给丽梅做棉袄,做裙子,她带着布料到母亲的裁缝店,母亲裁剪停当,她就伏在店里的缝纫机上,踩机子,她是一个说话声音很柔很慢的女人。
丽梅的樱花条绒马甲裙、碎花灯笼袖连衣裙、蓝白小格子薄棉袄,令我们艳羡。但我们并没有央求母亲也做一样的,我们觉得只有丽梅那样洁白皮肤瓜子脸两根长辫子的女孩才配穿这样好看的衣裙,只有那种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一个房间的女孩子——她掀开门帘走出来,她的样子这么好看才对。
很小的我们就很老成地在心里断定了:我们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我们的命运注定是完全的不同。她含着金钥匙出生,这一下就是一个制高点,这个高点决定了她未来的嫁人,她所嫁的人将是另一个制高点。
但我们并没有气馁,气馁意味着全盘否定自己的父母亲和那五百平米漂亮的院子。那个宽敞的院子何其漂亮啊,有雪白的芫荽花像浮在空气中的云朵,有深紫色的蝴蝶花,有健壮的玉米林,有一定年年结果子的苹果树。有红砖慢道,有抬头就望见的漫天星斗,我们三个沉沉睡去的时候,父亲轻轻走进来打开炉盖捅一捅炉灰再添几块煤。东边戈壁上的金光洒进来,我们蓬乱着长长的头发匆匆爬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我和丽梅在博客上相遇。我看见她访问了我。她的笔名是另一个名字,我知道这个名字,大家是同行,她也写作多年了。我们彼此问候。她说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因为癌症。我也想说一说我那死去的父亲,但我什么也没有说。
丽梅嫁的人是我姐姐的同学,这个男同学出生在县委大院里,青年时代托人到丽梅的家说这门亲事,丽梅的温婉远近闻名,是童话书上画着的真正的森林公主的模样。多年后这个男子已是某县的书记。我们很早就预见到了,丽梅会是县长夫人这样的女子,这是森林里的公主该有的命运。果然是这样的。
4
我去过大连,那是一座洁净的城市,像是给公主王子布置的宫殿,但是我几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那一年是二〇〇四年秋天,后来我从大连去了丹东,那里的人家喜欢在门前屋檐下烧烤鱼和肉。我白天在鸭绿江边走了走,似乎买了邮票和蛤蜊干,可以远远望见朝鲜吧,这个我也不记得了。
人生动荡的时候记不住什么,大约是低头谋生占据了我更多的脑海,还有无助和焦虑。所以二〇〇四年的我过得并不好。如果当时我过得好,我会仔仔细细到大连海湾的岬角上看看,那里一定有大码头和大轮船,我们的父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穿越大海,站在大连的码头上。
他们闯关东的人都是走水路吗?陆路是过山海关。父亲是烟台人,丘处机就是登州栖霞(今属烟台)人。父亲是烟台牟平养马岛人,他是大海的儿子。他坐上大船在大海上乘风破浪往大连去,也或者是丹东码头,他着陆于东北陆地,继续向北前行,沈阳,他最小的姐姐在这里工作,那么父亲这也算是闯关东吧,虽然闯关东是他的父辈爷辈的事情和说法,他的小姐姐就是伯父带上一起闯关东的。父亲是最小的孩子,与上面的哥哥姐姐年龄相差很多,到了他,祖国已经解放,而闯关东是民国上溯至清的讲法。
今天的我只能面对地图以手指摩挲,大东北,二十三岁的父亲穿黑色对襟棉袄,围白色羊毛围巾,脚穿黄色大头靴,微觑着眼,面对照相机,留下他青年俊秀自尊的样子。如果他就此在沈阳留下,在印染厂做着一名工人,下班后拉二胡看电影做美食,在小姐姐和大哥哥的庇护下,他快乐的微笑我至今瞬间就能想起,做一个永远的无忧无虑的人,那多好。但是他被遣返了。母亲说,东北出台的遣返盲流政策,定了一个年份,这个年份后进入的都得返回原籍。
父亲从山海关返回牟平养马岛,不甘心地停留了一年后他又选择新疆,开拔了。新疆没有遣返盲流,但是有盲流收容所,在这里他们乌泱泱的盲流们等待着分配到广袤的新疆各地去,做农民或者工人,下农村或者进县城。父亲从乌鲁木齐分配去了布尔津,那里有一个大集体企业,手工业联合社,他的职业从此定格,一名木匠。这位木匠娶了一个从成都飘摇跌宕而来的失去双亲的女子,然后有了我们三姐妹。
5
家中最小的女儿渐渐地就长大了,头上扎粉色蝴蝶结,几乎盖住小小圆圆的脑袋,棕黑色的头发贴着头皮梳得紧紧的,那是坐在小马扎上母亲的膝前梳的。土巷子那头欢欢推开门走了出来,土巷子这头我们的妹妹推开门走了出来,她们背着绿色布面的画夹往县城中心电影院旁边的文化馆去了。
如果能够穿越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光阴里,我就在南桥下税务局门前的古老榆树那里等待这两个女孩子走过来吧,她们走着经久不变的路线,下坡后过娜扎提家的黄色木头大门,进哈萨克小学后门,穿过长长的古老额河杨的拱廊,出前门,这就走到了税务局门前的古老大榆树下,每当春天淡黄绿色的榆钱像花朵一样密密匝匝,多少孩子大人停下来捋一手掌吃。这古老大榆树在今天也不在了,所以我要穿越到它面前来,手抚着它,等待那两个亲爱的小孩。
绿色画夹子里夹着一页页铅笔素描画,是小小姑娘们认认真真一笔笔描绘出来的。在一个又一个长长的暑假里,她们在文化馆完成着作为一个森林公主该有的蜕变,森林公主既是原始的拥有充沛生命力的,也是智慧的矜持的威严的。一个人一旦掌握了一门普通人无法企及的技艺,她就有理由脖颈更加端正坚挺,眼神坚毅,甚至睥睨众生。
我骑车带着妹妹,雷雷骑车带着欢欢,我们四个先进入农贸市场买两份加了更多的油辣椒醋和香菜的凉皮、两个热烫的馕,然后我们就向城北的大河森林进发了。从桥头上下去,就到了河边,森林与大河紧紧手拉手,它们是一体,虽然已经是盛夏,洁白淡粉淡黄的蔷薇花还在刺丫缝隙里稀稀落落地开着,它们的盛大时节是在五六月。在这里,杨树桦树榆树柳树松树混合生长,偶尔会有牧民人家蓝墙的房子在林间闪出,炙烈的阳光下,白亮的北河里有男孩子们在从此岸渡向彼岸。我们的妹妹们已经在河边的平缓大石块上坐下来了,她们微觑着眼睛,手中的铅笔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她们白皙的面庞,她们巨大的粉色蝴蝶结,她们洁白的有细微花边的衬衫,她们粉色的塑料凉鞋,她们纤美的手指。我和雷雷殷勤小心地铺开一块旧布,凉皮和馕摆开,自家菜地里摘的西红柿在河水里洗一下摆上,我们抱着膝盖静静地等待,只等两个小小森林公主突然放下手中的笔,端严地把画夹从膝盖上挪下来,我们立刻就欢欣雀跃地吃了起来。绿色行军壶里倒出来清香的茯茶,这壶已经有几处凹坑,陪伴母亲打土坯和淘金,我们用盖子传着喝,静静地看大河里、河岸上、树林里的风景。它们是我们坚固的江山,灵魂的骨骼,热烈的生之命题,也是未来不变的殇歌,多年后,欢欢说,谁敢回忆这些?
我的妹妹嫁给了大学里的同学,多年后,我去南方之端看望她,她所嫁入的古老家族,那是一个温和的大家庭。我走进妹妹的书房,里面立着一个画架,她家窗外是东莞的东江,她说她更想画的依然是布尔津的南河和北河,南河的晚霞半边天都铺满了,北河的森林自成我们的宫殿,我们骑车向它而去,自行车上的我们穿城而过,布尔津黑色的柏油马路上洒落着我们的清脆大笑,就像深夜满天河的星星纷纷掉落,掉落在我们发间。
多年后,又是多年后,我在杭州和欢欢相见。她的孩子有绘画的天赋,我给他送了一个画架,他拥有欢欢童年时的眼睛,明亮乌黑逼人。我对欢欢说,他们这一代的基因里会刻写有布尔津北河的质地,所以那叶片和叶片的喃喃私语,一阵风来,森林里的清香,草根和花朵里涌出的浓香,不会被岁月轻易湮灭的。
6
我们的邻居小女孩儿欢欢如果没有考取西南大学,她会去读本系统的职工委培大专或者大学。就像我姐姐的一个同学,也是她的懵懂初恋,他落榜后去了长春读一所金融大学,多年后,他是某银行行长,显然姐姐命中注定不是行长夫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姐姐考取了新疆大学,从此在乌鲁木齐不回来了,多年后,她成为一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文化学者。
欢欢若是读了本系统的委培,毕业后,她会进到我们县城的她的父亲或者母亲的单位,也就是说她会和家人成为同事。这很正常。比如我的一个女同学的母亲是县医院药房的药剂师,抓中药,取西药,在那间有推拉小窗户的屋子里忙得团团转,我的这个女同学初中毕业去了地区卫校委培,回来后进了镇卫生所的药房工作。我见过她穿白大褂的样子,她的眼睛黑黑的亮亮的大大的,乌黑的头发齐耳,笑起来就是“莞尔”二字。她的样子看着很慢,而我行色匆匆,即使也读了书也进了满意的单位,但是我心中腾起的焦灼始终盘桓不定,是原生家庭的不配得感在作祟。
所以呢,如果姐姐没有考上大学反而可以做气定神闲的行长夫人,她的眼神里始终有一股子淡淡悲情混杂的急行军气质,这也是我们一家五口的本色。我们的祖上不这样,我们的下一代不这样,只有我们三姐妹随着父母是这样的。父亲是遗腹子,母亲是孤儿,双亲在动乱时代中早亡,于是我们这个小小家族须用半个世纪平息一场血液里的孤绝风沙。
如果我没有考上省城的中专,我会挤进母亲的裁缝店。那是一间铁皮屋子,冬冷夏热,幸好布尔津夏天树荫下的风任何时候都是清凉的,幸好布尔津的煤十分充足,铁皮炉子在漫长的冬天毫不吝啬地一直在燃烧。我将挤进去,午饭时间才能坐到铁皮炉子边的椅子上进入短暂的小憩。我不想重复母亲的命运,那是被山一样的布料绑架的命运,她的下肢静脉曲张得非常严重,作为一个裁剪师傅,她每天站立达十个小时以上。因为深知命运非彼即此,录取通知书一到,我的心就已经飞走了,生怕稍有闪失就得挤进那间铁皮裁缝店。虽然门前的两棵穿天杨是我爱的,虽然我知道这一走,不仅仅是布尔津,连带着布尔津周边的所有森林都将从我的人生里急遽退去,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但我又似乎更擅长的是思念森林,在我的思念里它们更加清晰生动。
我的一个初中女同学,她和隔壁班的一个尖子生早恋了,这个尖子生的班主任好高骛远,给他填报了省城最一流的中专学校。没有想到竟然落榜了。我的初中女同学和尖子生放弃了直升高中,选择了私奔,奔向了男方内地父母的家,在那里生下一个孩子。在我们都还在校园里读书的时候,他们又折返回布尔津,住进了蔬菜大队女方父母的家,以卖菜和水果为生。多年后,我们在布尔津农贸市场遇见,当时我蹲下来选了一箱葡萄、一兜西红柿辣椒,我一抬头和他们夫妻俩眼睛明亮地互相注视,我们当然都认出了彼此,我们能说的就是,都好吧。分别后我心里想,如果他们不早恋,如果他的班主任不给他不理性地填写志愿,以他们的分数,女方读一个地区师范或者卫校是没有问题的,男方读一个省城普通中专是没有问题的。命运陡然滑入底部,原来少年时代就不能有任何差池出现,一步错步步错。当然,也许他们是结结实实地在活着,整个布尔津和四围的森林大河,都结结实实被他们拥有。
布尔津的女孩子的出路千万条,虽然条条大路不一定都通向世俗眼中最对的繁华罗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布尔津有享誉全疆甚至全国的毛纺厂,生产的羊毛布匹毛呢和羊毛毯至今也和上海的质量不相上下。那时候进毛纺厂就是进国企,多少考不上学但家里有关系的女孩子托人买毛纺厂的指标,两千块一个,是一个工人两年不吃不喝存下的钱,是一个农民家庭一个秋季收下的所有麦子土豆豌豆花豆的钱,是一个牧民家庭在秋天赶上几十只羊进布尔津县东戈壁上的屠宰场卖得的钱。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背负着对亲人的无限的歉疚,系着白围裙,站在了永恒的织机面前,这是新时代的崭新的女工,她们进厂的年龄不会超过十八岁。当她们领到了第一个月工资,会只给自己留下五分之一的零用钱,其余的全部交给娘老子,这让她感到很快乐。直到有一天她恋爱了,出嫁了,似乎对娘家的所欠渐渐平息了。这个女工同所有的新娘子一样,婚礼那天穿一身红色羊毛布料套裙,也许正是我们的母亲所裁剪缝制的,也许是去遥远的乌鲁木齐大十字商业街买来的成品。她的小家会有一排三间平房和一个大院子,有自行车缝纫机洗衣机冰箱,她会很快怀里抱着一个婴孩走在布尔津黄昏的马路上。然后她们就失业了,毛纺厂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倒闭。布匹和毛毯的质量全国拔尖,浪漫的雪花呢甚至获得过全国金奖,为什么会倒闭?原因不详,或许是商品流通环节出了问题,布尔津毛纺厂产品的广告只有限地出现在本地和阿勒泰地区的电视频道上。失业了的布尔津的女子们开始自谋出路,三十岁左右的她们到农贸市场租摊位,卖从乌鲁木齐大西门批发来的鞋子衣裙。有的开起了早餐店、凉皮店、咖啡酸奶吧,有的考取了驾照开起了五元起步价的出租车,有的则充满勇气向喀纳斯和禾木进发,在那里做起了旅客的生意,比如承包饭店和宾馆。
通向罗马的道路千万条,布尔津的森林公主、青年女子、中年女性的命运千万种。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母亲的裁缝店关门了,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人们都去买货美价廉的批发来的衣裙,如果是订制也将选择高级订制。江浙来的服装大师出现在县城中心的商业街,留着小胡子像是归国的洋博士,说是祖上是在上海滩服装店做过学徒和师傅的。
7
婴儿时代浮在命运里,儿童时代活在已有里,少年时代睡在未知里,青年时代行在颠荡中,中年的我坐在这里敲击着键盘,就像西伯利亚的北风对着踏雪前行的我们一气呵十几个耳光(欢欢语),这耳光火辣辣但清爽之气令肺腑愉悦,所以当我们跑进院子掀开门毡推开木门,骤然迎接屋子里炭火的温暖,冻红的苹果脸总是笑嘻嘻的。
我在十二岁时遇见了这一生我觉得美好的人家,母亲白皙娟秀,大大的黑眼睛,黑头发披肩,写得一手好字,热爱文学,拥有一个装满书的书架。生下的两个同样灵巧娟秀的女儿,尤其小的女儿欢欢娇气极了,弹琴画画,自信的眼睛里目光逼人,但谁都爱她。至今我觉得欢欢的母亲是日本电影海报上走下来的女子,她若说她来自北海道或者冲绳我就信了。她嫁的是一位一米八高的英俊极了的男子。欢欢的父亲常常去乌鲁木齐出差,带回来美丽的衣裳,欢欢穿上就来找我们玩儿,我们看着眼前这个和布娃娃一样美丽精致的女孩子,心中升起爱惜之情。
多年后,欢欢说,我一直记得你们对我的好,后来我自己的孩子出门玩被小伙伴冷落回家哭,我就想起了你们,像你们这样的其实并不多,现在我才知道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友爱。
欢欢的母亲青年时代是我们那里煤矿的出纳,因为一手好字,优美的文笔,进了一家事业单位,转干,读书,从此就是真正的国家的人了。手艺人工人的女儿其实过的是兵荒马乱的生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母亲做了个体户,父亲成为一个小小的包工头。而欢欢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女儿。但是我们只要和雷雷欢欢聚首就不会思虑这些事,我们活在大笑奔跑和尖叫里,我们永恒的土巷子,夜幕降临,我们才各自回家。
欢欢说,你们出去读书工作,只有我和三三(我的妹妹)有时候在一起玩儿。有一个暑假,我接到三三的电话。那时候我家搬进了楼房,我们已经离开河边小巷子了。三三说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我们就约好一起去南大桥上散步。大桥上没有人,只有汽车轰隆隆开过去,那时候这座老桥还在用,现在不用了,只能过人,当作纪念物。我和三三伏在大桥栏杆上,三三一直在讲《狮子王》,把一部电影讲完了,我听得如痴如醉。多少年后我看《狮子王》,竟然是在八岁的儿子身边坐下看的。
其实在漫长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里,我们多少次会死于额尔齐斯河。初秋我和妹妹、雷雷欢欢,我们四个在丘陵上找到粗硬的红柳枝,它们看起来挺长,助力我们过到河对岸去。秋天一到河水就消瘦了许多,河心渐渐多出四五个六七个圆圆的小小的岛,其实就是河床的小小的隆起地,三四个人站上去就站满了。在五道湾甚至出现了一条细细的过河之路,我们几乎就能够渡到南岸去了。我们四个手拉手越走水流越湍急,但是不用怕,我们紧握红柳枝探路,鹅卵石的河底是结实的,水位并没有没过红柳枝,于是我们坚定地向前走,直到站在了一个小小圆圆的岛上。现在我们四个已然是位于伟大的也儿的石河的中心了,想着是一个骑着高大的马儿的骑士也如此这般过,所以我们感到骄傲极了。
我们曾经畅想亲手制作一条木船,用院子里废弃的木板,我们四个将泛舟而下,往西边去,那里河谷的深处是古老的森林,无数猫头鹰乖巧伶俐,冷眼看着我们闯入。我们身穿粉纱的长裙,长发披散到腰间,额上戴着紫色蝴蝶编的花环。我们跳下船采摘野果,有一种红红的绵甜的小小果子,有酸甜的蔷薇果,有满山的野草莓和野酸梅果,甚至还有板栗树。我们的小船上堆满了果子,我们挥桨逆流而上返回家。
真是幸运,我们竟然没有死于额尔齐斯河湍急的河流,布尔津有多少人家的孩子死于河中游泳。而我们在水温热的时节里每一天都走进河水,我们在河边洗衣裳,洗好的衣物铺开晒在鹅卵石滩上,我们弯下腰洗头发,用蜂花洗发水,我们擦洗手臂和腿,用力士香皂,我们趴下晒太阳,后背热热的。我们眺望南山,山那边的世界竟然在将来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在当年被布尔津紧紧拥抱住,几乎窒息,几乎麻木,但那样的纯真和平静,后面却不再拥有了。
到了冬季,大河冰封,又被厚雪覆盖,每天刮大风,扫去一些雪,露出蓝雪下面冰层的碧绿,我们四个又手执粗硬的红柳枝来了,我们手牵手向河心走去。如果红柳枝没有捅破冰面我们就坚定地走下去,一直走到河对岸高高的丘陵下,我们爬上去,再飞速地滑下来。直到一轮单薄而艳红的太阳出现在大桥的西边,我们终于开始感到寒冷,棉鞋和棉裤都已经润湿冰凉,我们原路返回。在无数个冬天,我们没有死于冰面塌陷的冰窟窿中。
多年后欢欢问我,你还记得我们在河边堤坝下挖出的雪房子吗?我们叫它宫殿,我们自己的宫殿。那是隆冬时节的硬雪,在一个背风的坡下,雪越积越多,越来越硬,我们带着铁锨去,挖出隧道,挖出更大的小房间,我们四个团团坐在里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后来我们决定烤肉吃。初冬父亲用苹果木熏的牛肉块,我们去小仓房选出来一块半肥半瘦的,切成小块,我们带上火柴刨花往我们的宫殿来了。我们去东戈壁的丘陵上捡拾红柳枝,火燃烧起来,熏肉穿在柳枝上,油脂滴滴答答滴到火上,火更加旺盛,橘红色的,宛若斜阳。我们爬回到宫殿里,盘腿坐下,认真吃手中的烤肉,我们遗忘了世界和我们的前世今生未来,世界也遗忘了我们。如果我们四个不断地寻找我们的宫殿,不断地上演森林里的公主的各种该有的壮举和存在样式,那么我们就是生长在纯真时代里的小鸟儿。
我们布尔津的女孩子不可能一直做着森林里的公主——与夏天的额尔齐斯河是伙伴,一次次地扑入,以北河森林的蔷薇林杨树林为天然的我们的宫殿,常常走进去徘徊,到了冬天我们则登上高高的丘陵进入小小的白雪的宫殿。而分离很快就会来到,是猝不及防的,我们和布尔津之间的骨肉分离之拉扯的疼痛,当时不甚清晰,这份疼痛要到多年后才如此明了。
姐姐第一个离开,一卷擀毡一张褥子一张棉被一个红色皮箱一个白瓷脸盆。她考上了新疆大学,毕业后留校。第二个离开的是欢欢的姐姐雷雷,她用滑冰刀的本领和高挑的个子考取了阿勒泰地区体育学校,说是立刻就有了干部指标,与考上中专或者大学是一样的待遇。第三个离开的是我,以应届生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省城的交通学校,青年时代的末期登陆武汉。第四个离开的是妹妹,她考取了江西财经大学,那年夏天庐山上她穿着母亲为她裁剪制作的粉色真丝大衬衫配淡蓝牛仔裤,白净的面庞一双麻花辫,似乎已注定会远嫁南方古老家族。第五个离开的是欢欢,她考取了西南大学,毕业后去了杭州,嫁给一位祖上是赤峰满人的小伙子。当年我们都不懂得怎样告别,于是单个的人在某个清晨就出发了,坐上长途汽车过南大桥往南去。只有三三和欢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伏在桥上讲《狮子王》的电影,那是一次郑重的真正的告别。
唯有雷雷折转命运回来了,她从阿勒泰体育学校毕业后进了布尔津县体委,参加过多次自治区和全国的比赛,获得过银奖和铜奖,退役后进入文体局,后来文化旅游局成立,她成为这个单位的领导。有一天她在额尔齐斯河畔康剑先生创办的金山书屋读到我的长篇小说《布尔津光谱》《禾木》,眼睛里闪烁着泪花。
我们分散在布尔津以外的许多个点上,回望布尔津时,不约而同看向我们的土巷子里曾经的小伙伴雷雷,如今她作为文旅局局长是布尔津的代言人,出现在视频里,她延续着我们对布尔津的爱。她在童年时代就无师自通地深懂穿着冰刀鞋飞驰、水上探险漂流、丘陵上滑雪、雪屋烧烤等一切未来的旅游项目,她代替我们一年四季深深凝望南河北河的森林——曾经我们是这里的森林公主。
8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距今多少年了?四十年!二〇〇四年,我们姐妹仨开始寻找一幅画,那是一幅油画,画上是三姐妹,圆脸,挂在我们老家土屋最大的正屋里,刷了石灰的泥墙干净简朴,透出一种今日大家说的侘寂风的美。它的名字叫画张纸,小县城的新华书店里买的,在最里面最头上的那节玻璃柜台上,它们平展展地铺开,厚厚的一摞,我们往墙上看,那上面悬挂着所有样品,我们喜欢哪一个就请售货员从画堆里给我们找出来。很小心地卷起来,不能破边儿,回到家挂在白墙上。十二岁的姐姐,十岁的我,七岁的妹妹,我们一齐望向这张画。画上的三姐妹多么美,外国女孩儿,卷发,有飘带有蕾丝的纱裙,主调是金色。她们每个人的怀里抱着一个属于自己的爱,究竟抱着的是什么,当然忘记了,但是我们突然有一天计划着找到这幅画。
怎么说呢,就像画张纸要小心不能破边,人生也一样,但是人生在所难免地很容易就破边,防不胜防,有时是主动破边。一张破边的画张纸挂在墙上就不美了,必须是崭新的挺括的,姐姐站在椅子上,我和妹妹指挥高低左右,四个银亮的图钉摁过纸面,榔头轻轻锤下去。三个女孩儿也许一生都不会真正拥有法式的浪漫成长,但是这幅画一挂上,就像挂在了我们心灵之树最高的枝丫上,于是我们启程了。少年时代的末期渐渐分开,走上一条条交叉小径,两条路中的一条,一次次选择,一次次出发,那是独自的一个身影,晨曦昏雾,披星戴月,也曾茫然四顾,也曾面海微笑,也曾在泥潭虚假温暖里坍塌般地跪下,破边的我,再也不能崭新挺括如一张最美的画张纸被人仰面凝视,纯真洁白,精神互为呼应。
这幅画的作者名叫埃米尔,法国人。我的妹妹用她的智慧以及天意赠送给我们的路径竟然找到了,那幅挂在少年时代的白墙上的我们的喜爱和希冀,属于我们的少女时代,甚至作为女人的一生,它越发朦胧,几乎只能如此描述,那是三姐妹,她们的脸很圆,当然是世界名画,不然不会拥有平静却惊心动魄的美。又是一个夏天,我收到一个包裹,它是装画的圆筒,我拆着,瞥见物品内容埃米尔,大脑神奇连线那幅画,如果我的妹妹怀着满溢却暗含着的喜悦请我收一个神秘礼物,那么一定是它。打开卷着的画,四十年的光阴轻轻浸透纸张,这就是最普通的印刷纸,它们曾经同一批生产出来,运往全国大大小小各个城市的新华书店。我们的那一张早已随风飘逝,这一张也是陈年旧物了,但是它完全没有破边,干净利落地再次进入我们三姐妹的人生,轻巧地滑入,最小的女孩手中握着一个红苹果,残月的残被弥合了,灵魂的破边也因此缝补齐整了。
责编:胡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