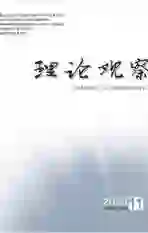论马克思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思想
2024-12-31叶浪明阮玉春
摘 要:马克思的“绝对贫困”思想包含着三个层面的意蕴,一是人的必要需要匮乏到危及人的基本生存;二是人的劳动能力与劳动资料相分离;三是人的感性需要被异化。马克思的“相对贫困”思想包括社会分工引起的相对贫困,以及需要与消费不平等引起的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根源不在劳动个体和自由市场,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正是以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作为前提。真正反贫困的根本在于雇佣劳动体制的变革,重建个人所有制,建立真正的共同体。
关键词:绝对贫困;相对贫困;需要;社会分工;生产方式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11 — 0053 — 04
在2021年成功消灭绝对贫困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的贫困问题迎来了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从以“治贫”为核心转向以“防贫”重点,从消灭绝对贫困为主转向防范相对贫困为主。回顾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重新考察马克思对“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理解,从而为中国新阶段反贫困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和启示。
一、马克思“绝对贫困”思想的三层意蕴
(一)两极分化下人的必要需要的匮乏
马克思在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考察中,揭示了人的绝对贫困、必要需要的极度匮乏,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的。一方是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另一方是人的绝对贫困。这种绝对贫困表现在至少四个方面。1.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穷,包括由资本竞争、失业导致的“饿死或行乞”。2.身体残疾或重病,例如在恶劣劳动环境下工人患上各种职业病。3.过劳死。资本为获得剩余价值的增殖而在最大程度上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以至于工人的饮食、睡眠等等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1]1214.遭受流行病、瘟疫的侵袭而危及生命。一边是生产创造的舒适环境,另一边是劳动者拥挤在狭窄的地下室以及工作在狭小空间的厂房中,呼吸系统流行病大量增加,工人罹患传染病而死亡的人数大量增加。“多么好的新鲜的空气,那是英国地下室住所充满瘟疫菌的空气!”[2]380这一点在全球新冠疫情中,依然可以得到验证。
(二)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孕育了绝对贫困
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下,工人劳动能力和劳动资料、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存资料,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分离对工人造成了制度性的、悖论性的绝对贫困。“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3]39因为“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3]40马克思称之为工人陷入了自由地一无所有的境地。因为雇佣劳动者是双重自由,“他们摆脱了奴役,因而是自由的;同时,他们自由地一无所有,没有财产甚至没有土地权。”[4]34-35一旦生产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分离,劳动者便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与资本进行交换,在这种交换过程中,工人的劳动本身被设定为非对象化劳动,非价值。一方面,这种非对象化劳动,是同劳动的客体性、现实性相分离的,因而“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5]253因此,这种劳动表现为“绝对的贫穷”,而资本则作为财富的现实性而存在,两者形成对立和对抗的关系。
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丧失一切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有可能因成为“相对过剩人口”而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如马克思所言:“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5]607正如,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模式下,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是由资本设定的,当资本追求的生产力发展、相对剩余价值的提高的时候,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也必然提高,或者说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所对应的必要劳动的数量下降了。假定工人总的劳动能力是一个定量,那么随着资本生产中必要劳动的比例不断减少,另一部分劳动能力将变成过剩,也就是产生了过剩人口。当工人不再能够通过必要劳动养活自己,即不再能够通过与资本的交换来养活自己的时候,他们便成为了乞丐和赤贫。
(三)人的感性需要的异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感性需要的异化理解为绝对贫困。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生成,人要成为完整的人,必须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人自身对世界的关系,对世界的感官感觉、思维、情感、直观、爱等等,他自身的一切器官,在形式上直接就是社会的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1]189但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下,人的对象性活动和感性需要的关系却变成了这样:人本来通过对象性关系对对象的感性的占有,变成了单纯的直接的占有、拥有和片面的享受。需要成了利己主义的性质,自然界失去了人的效用而成为了纯粹有用性的、功用性的效用。“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在丰富性。”[1]190因此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189正如阿格妮丝·赫勒所说,人们普遍把马克思的需要概念作为经济需要范畴在使用,而事实上,当人们把需要概念归结为经济范畴的时候,已经表明了需要的异化。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追求资本的增殖。异化的需要表现为质与量的分离,需要的发展及其丰富性,仅仅表现为物质需要的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增长;对物的数量化的占有取代了对物的质的享有。
二、马克思的“相对贫困”思想的两个方面
马克思对相对贫困的理解不是与绝对贫困截然分离的,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本身,也就是相对贫困。工人生活水平与资本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虽然工人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6]67
(一)社会分工引起的相对贫困
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工是“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565的阶段,这种社会分工产生了三个层面的相对贫困。
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和技术的发展导致相对过剩人口及其相对贫困。马克思曾指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7]508首先,生产技术的提高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资料的节约,使得相对剩余价值增加而工人的活劳动力——可变资本的投入下降,也即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导致更多相对过剩人口和贫困人口的产生。“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这种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对抗性的和杀人的一面。”[8]507其次,机器的发展加剧了工人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为工人的“慢性贫困”埋下伏笔。“在机器逐渐地占领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过度迅速进行的地方,机器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和急性的。”[7]496再者,机器还可以被资本利用成为“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8]476-477于是机器成为了与雇佣工人相敌对的力量。这样,技术进步本身便在“资本主义应用”下成为工人阶级落入相对过剩人口、落入资本主义贫困的陷阱。
二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工还带来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及其相对贫困。在机器大工业中,人的劳动被束缚于机器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渐分离,划分为适应机器运作的不同操作,劳动者沦为机器的奴隶,劳动变得片面,精神变得单一,文盲大量产生,工人的创造性和反思性被压抑,陷入“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8]402。劳动者“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159社会分工产生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但同时却“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159
三是城乡的分离、对立产生的相对贫困。以机器为主的大工业生产、资本对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剥夺,使得生产工具集中于城市,交通的拓展也促进了城市生产力集中,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进入不同的生产部门。一边是城市经济、人口的日甚一日的发展,资源的越来越集中,另一方面是农村的相对贫困。资本和工业支配了地产和农业,使得“农村从属于城市”。
(二)需要与消费不平等产生的相对贫困
除了在生产、社会分工领域的相对贫困,还有在需要和消费领域的相对贫困。社会需要的生产使得人与人的需要不是为他人的存在,而是经由货币中介陷入对立。这种对立集中地表现在需要的粗陋化与需要的精致化的对立,“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上的自身。”[1]225于是在工人那里,甚至连新鲜的空气都不再是需要,人甚至还不如退回到穴居中,因为连空气也被污染,他的居所成为每一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只要他交不起房租,便每天都可能被赶走。
在马克思的视角中,粗陋需要与精致需要之间的对立,实质上反映了两种不同需求生产方式,一种是工业对需要的讲究进行的生产,另一种是工业对需要的粗陋进行的生产。需要的生产体系总是迎合人们的各种需要,以至于激起人们病态的欲望。“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1]224-225就是说,工业不仅利用需要的讲究进行投机,也利用需要的粗陋进行投机,并且人为地造成需要的粗陋进行投机。这种粗陋的需要,是自我麻醉,是对需要的表面满足,这种享受包容在需要的粗陋中的文明之中。于是,生产的产品和满足需要范围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各种非人的欲望,因为这种生产和需要的扩大总是精打细算地从属于非人的、非自然的、精致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
这两种需要的生产同时也引起人们的消费性的心理贫困,而消费社会正是以这种相对贫困作为商品生产消费的“密码”。正如马克思所举的例子,一座小房子只要能满足居住的需求,而且他周围的房子都差不多,那么房子的主人的心理是平衡的。但是当小房子周围建起一座宫殿的时候,即使小房子的尺寸和内部装饰都随着社会发展得到一些改进,房子的主人依然会越来越不舒服,不平衡。这种心理落差带来的挫折感、贫困感,有时表现为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的“绝对贫困”所带来的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有时表现为单纯羡慕、嫉妒、攀比带来的心理性贫困。而这种需要生产体系下的消费社会通过广告、媒体等方式往往“恰到好处”地渲染这种落差带来的苦恼,“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背后,是“更高级的社会享受”,因为这代表着“更高级的社会地位”。这种需要的层级化生产,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通过符号编码操纵理论,被进一步表达为更为具体的需要的差异化的工业化生产。对商品符号与差异的同质化生产,直接导致的是消费等级及其不平等,丰盛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生产结构性的匮乏和贫困。“不平等的功能就是增长本身。”[9]33这种不平衡、相对贫困不在贫民窟中,而在这种生产结构中。消费者永远都不会满意,因为他的消费永远都是差异性的消费,在这个富有差异结构的消费领域,似乎永远无法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人在其中消费,会感到总是不够的。在这种消费意识形态下,与丰盛、匮乏、贫困、不足相伴的,还有浪费。浪费,不再是“非理性的残渣”,而是作为生产性的消费,为消费体系起到重要作用:商品必须尽可能迅速地被消灭、破坏,以产生新的需要和生产。
三、马克思“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思想的当代启示
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从自由主义市场本身解决贫困问题,即诉诸市民社会自身的特殊性,减少国家对贫困问题的干预,以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方法。斯密认为自由市场的充分发展必然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10]67李嘉图甚至将国家之于贫困的救济也视为影响市场和国家财富增长的阻碍。[11]50虽然这种自由主义反贫困理论在市民社会无数个别的事实、纷乱的个人任性、混沌的局面中找到了具有普遍性的必然性的联系,即个人在市民社会这个需要体系中在满足自身需要同时也满足了他人需要。[12]210但是这种反贫困方案没有解决财富分配受制于资本而产生不平等、相对贫困的问题,也无法解释为何人们在市场中的普遍联系与社会财富的普遍增长的同时,劳动者对异化劳动的依赖性和匮乏性也在增长。
马克思不是将贫困问题诉诸劳动个体,也不是诉诸市场本身,而是诉诸市场经济背后的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对马克思来说,“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6]10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1]368马克思批判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尽可能贫困的生活、生存需要当成普遍的标准,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把这种标准适用到大多数人,他们不明白“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是如何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1]226
马克思关心的显然不是单纯的日工资、贫困线标准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悖论性贫困背后的经济大厦、生产方式、制度。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1]614这种悖论性的贫困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压迫性的力量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如何通过消灭这种社会对抗来解决贫困问题,这是马克思思考“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的出发点。而马克思探究的问题的答案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正是以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为前提的。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根本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的变革,“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用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3]993建立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相统一的真正共同体,扬弃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使人的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不再仅仅是人谋生的需要。
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消灭绝对贫困之后,中国的反贫困重心转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防范相对贫困两个方面。马克思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思想为新阶段反贫困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一是新时代解决贫困问题,不能重走自由主义反贫困的老路,而必须切实深入到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国家力量扬弃私有制的弊病。二是防范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核心在于劳动保障和新产业就业。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原则,培育精神文明建设。资本要素的发展使得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生产仍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以需要层级的差异化为生产原则和导向。当人性中的攀比、嫉妒、虚荣等等被嵌入到以交换价值为主导的商品生产的消费社会中时,心理性贫困等消费心理困境也将被结构性地“生产”出来。在这种状况下,一方面要考虑到消费对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资本为追逐利益而制造的差异化商品消费产生的价值观扭曲、心理性贫困等问题。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大同世界[M]. 王行坤,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0]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11]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责任编辑:侯庆海,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