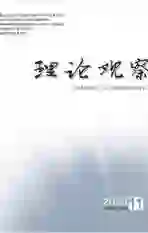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激进解读
2024-12-31王旗孙倩倩
摘 要:为了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开拓理论“空间”,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国家理论做了激进化解读。这一解读是通过拓扑学以及斯宾诺莎的理论“迂回”完成的。通过拓扑学,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关于社会—国家结构的“大厦”转变为拓扑学的平面。它遵循斯宾诺莎的内在性线索,以创构性的力量为根基,是多元力量建构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阿尔都塞的国家观就是一种力量政治学。通过“掏空”国家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认识论内容,阿尔都塞凸显了其国家观的激进性以及“当代性”。说到底,阿尔都塞的国家观实际上是一种反国家观,本质上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激进政治模式。
关键词:阿尔都塞;国家;拓扑学;斯宾诺莎;力量
中图分类号:B565;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11 — 0048 — 05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国家理论的重释源于自己哲学观的改变。早在《保卫马克思》的著作中,阿尔都塞就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然而,1968年的五月风暴动摇了阿尔都塞的观念。在经历了总罢工之后,阿尔都塞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随着自我反思的展开,他逐渐明确了一个观点,即“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1]由此,他对哲学的认识从认识论(理论实践)领域转向了政治实践领域。哲学不再是理论实践的理论,而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2]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都塞将目光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前沿阵地,意图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理论和实践的“介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打开一个新的“空间”。
一、“大厦”的空间隐喻和国家的拓扑学平面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在《论再生产》中,阿尔都塞认为,这里马克思提出了描绘社会—国家的“一个空间的隐喻,一个地形学的隐喻。”[4]马克思将社会结构隐喻为一座“大厦”,这座“大厦”由“基础”(“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两部分构成。一方面,“基础”(“下层建筑”)对“上层建筑”具有归根到底决定作用,是整个“大厦”结构中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另方面,“上层建筑”虽然不能脱离“基础”而独自“漂浮”在空中,但“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出来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基础”具有(决定性)反作用。
阿尔都塞承认,“这个隐喻有一个优势,它使我们直观地看到社会结构各层的作用指数的大小”。[5]由于“基础”归根到底决定着“上层建筑”,所以在“大厦”的整体中,“基础”的作用指数更大。不仅如此,这个关于社会整体(结构)的隐喻,还将马克思的整体和黑格尔的总体区别开来。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总体是一种表现性的总体。他的历史世界中具体生活的所有因素,都根源于“绝对精神”的外化,因而都能够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内在本原。然而,马克思的总体是一种结构性的总体,复杂性是其社会组织的核心。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社会(国家)整体的统一性是“复杂性构成的、被构成的整体的统一性,因而包含着人们所说的不同的和‘相对独立’的层次。”[6]
尽管阿尔都塞肯定马克思这一“大厦”空间隐喻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但更多强调的是其“描述性的”[7]的性质。所谓“描述性”的,指“大厦”的隐喻未能在理论上说明“上层建筑”的存在和性质的问题,也就是未能在理论上对“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问题以及“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问题做出说明。不仅如此,在阿尔都塞看来,“大厦空间”的隐喻表征了一种“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垂直的作用关系,这种关系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国家表述为一个封闭的堡垒。在堡垒的逻辑中,“基础”通过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产生足够的、有效支撑上层建筑的可以累加的“量”,而“上层建筑”则在“基础”的规定下和限度内服务(反作用)于“基础”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形成了一个“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加强“基础”的无法爆破的结构。为了突破这种局面,进而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创造理论“空间”,阿尔都塞运用拓扑学对其进行了“改造”。
20世纪40、50年代,许多数学的方法被引入到人文科学领域,这其中就包括拓扑学。“拓扑学”(Topology)是几何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它只考虑物体间的位置关系而不考虑它们的形状、长短、大小、面积、体积等度量性质和数量性质,因此,也称位置几何学。在《来日方长》中,阿尔都塞表明,早在获得巴黎高师教师学衔之前,他就间接得知拉康在搞莫比乌斯圈(拓扑学),以用它来表明精神分析对二元对立观念的质疑和“穿越幻想”的可能性,并承认拉康对他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影响。基于此,可以推测,阿尔都塞之所以用拓扑学“改造”马克思的地形学空间与拉康的启发是密不可分的。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原则呈现出一种‘拓扑学’(topography)的形式,即在拓扑空间中图形的位置变换,这个空间定义了图形的拓扑位置以及关系,以使相对外部性、决定等成为‘可见’关系,从而使‘实体’之间的效能成为‘可见’关系,所谓‘实体’即基础(生产/剥削,因此是经济的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的要素(法律、国家、意识形态)。”[8]
在阿尔都塞那里,通过拓扑学的引入,尽管“基础”与“上层建筑”并不具有同样的认识论内容,不具有同样的“质”和“量”,但在拓扑学中它们都能够被“等价变换”为国家这一平面上的具体的点或图形。或者说,不管“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否具有同样的层次、位置以及力量,它们都可以经“拓扑变换”(“压扁”)被“投影”到国家这一平面,成为“异素同构”[9]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事实上,为了突破“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堡垒结构,阿尔都塞就是要“抽空”它们的认识论内容,让它们成为形式化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当把它们“抽空”以后,剩下的就是非认识论的、非本质的平面。这个平面就是拓扑学的平面(空间)。如此,“大厦”的空间成为一个纯粹的形式化的平面。在这个形式化的平面上,各种因素(力量)不断地错位、移置、凝缩,甚至爆炸。也就是不断地进行着拓扑变换(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经过“拓扑变换”的国家平面,没有了“作用”(决定)和“反作用”的概念和关系,只有具有各自作用力指数[10]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影响、相互重构。至于它们各自作用力指数的大小,不取决于它们的数量,也就是不取决于它们各自在拓扑变换中获得位置(力量)的累积之和,而是取决于它们在拓扑变换中所获得位置(力量)的几何总和。在作用指数的意义上讲,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意识形态都是同等重要的,都对国家这一平面的统一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通过拓扑学,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的“大厦”(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压扁”(拓扑变换),构造了一个社会—国家的拓扑学平面,从而取消了“基础”和“上层建筑”垂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将它们转化为在拓扑平面内水平的、异质的因素“相互重构、相互决定” [11]的关系。如此一来,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一个坚固的堡垒,而是一个特殊的经由拓扑变换而不断再生产的平面。通过拓扑变换,“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成为了“异素同构”[12]的元素。它们在矛盾统一体(国家的拓扑学平面)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生产条件“再生产”的过程。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进行“再生产”(拓扑变换),即通过不断地使“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中的各个要素、结构相互作用、相互重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矛盾的统一体才能够得以维持而不至于破裂。这就是阿尔都塞发现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维持的“再生产”(拓扑变换)的秘密。
二、国家的建构和多元力量的斗争
在《论再生产》中,阿尔都塞之所以对国家中的各要素做拓扑变换,在于他将国家看作是不断进行再生产的力量的拓扑学平面,一个力量的动态结构,亦即能量转化的装置。如果需要以力量的统一性名义“想象”国家的存在,就必须做大量的“歪曲”(拓扑变换),以便把各个要素都熔进这个统一性的模型中。在这个力量的“统一”装置,即国家这台“机器”中,阶级斗争的力量或者暴力,转化为国家权力,即转化为国家法律和法权的力量。[13]在将国家看作是一个力量的转化装置这方面,斯宾诺莎可谓是阿尔都塞获得灵感的源泉。关于阿尔都塞和斯宾诺莎的关系,用学者赵文的话讲就是“旁边站着斯宾诺莎的阿尔都塞。”[14]
实体(substantia),也就是神、自然,是斯宾诺莎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在斯宾诺莎那里,实体拥有无限多的属性,属性(attributus)是“构成实体本质的东西。”[15]每个属性都以特定的方式体现着实体的本质。样式是“实体的分殊(affectiones)”。[16]所谓分殊,也就是实体的具体化、特殊化的变相,即实体的现实效果。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整个世界除了效果,别无他物。世界的物性身体就是各种具体的、个别的样式(事实)“结合”的结果,即“它是诸事物相遇的过程和结果,它本身在它内部进行着‘势激理易’的‘情动分殊’。”[17]
在阿尔都塞那里,通过斯宾诺莎的理论“迂回”,不仅世界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国家这部“机器”,作为一种“多元决定”的装置,就各种存在的事实(如经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都是它的效果而言,国家的建构与存在正是各种在它之内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家“这个统一体是‘复杂的’,那么它也是‘被结构’的。”[18]如果说,思维、广延以及意识形态一般、生产方式一般、阶级斗争一般等都是世界的属性,反映世界的本质,那么各种国家机器、具体的生产方式、具体的阶级斗争等等就是世界的种种属性单独分殊的样态或是相互“结合”分殊的样态。这些具体的样态在世界之内“情动分殊”,它们“结合”(“偶然相遇”)而成的结构就是国家的整体本身。
由于某种属性的“情动分殊”并不是必然的,因此任何一种样式的存在也不是必然的。这就意味着,国家作为各种样式“结合”的结构同样不是必然的。具有必然性的只有神,因为只有神是绝对无限力量的存在。存在即力量、能力或者权力,反之亦然。力量或权力是神和万物赖以存在的东西。“不能够存在就是无力,反之,能够存在就是有力”[19]除了神以外,诸多样态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因此它们都是非必然的存在。所以为了能够自我保存,它们就必须进行自我保存的努力。这种自我保存的努力是一切样态的现实本质,是万物的“自然权利”。国家作为一种力量的动态结构,同样承袭着这样的“自然权利”,所以不断将暴力转化为人民一致同意的权力以维系自身的存在。
总的来说,在阿尔都塞那里,国家这一整体表现为具有内在性张力以及创构性的拓扑平面。它是一种被多元力量建构的平面,所以也是一种不稳定的平面,无时无刻不处在多元要素的相互作用即不平衡的力量的变化之中。阶级镇压是一种力量,阶级的意识形态化也是一种力量。[20]除了作为国家效果的各种力量,国家的平面上什么也没有。以至于国家这个平面就像流沙一样,是一个不断自我凹陷的“陷阱”。“陷阱”里面究竟是什么是无法知道的。如此,国家的平面是否存在?根据阿尔都塞,国家的平面是一种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在阿尔都塞那里,这种归根到底决定作用自始至终都是作为一种隐含的神秘的作用在起作用,或者作为一种最终的作用而起作用。它总要作为一种最终的、最有力量的统治力量占据一个绝对优势的位置。说到底,实际上作为隐含的、最终起作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经常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力量占据这个位置。所以,实际存在的总是力量和力量之间的斗争,也只有这种斗争。换言之,存在的仅仅是多元力量强度的不断转移和凝缩。
显然,力量在阿尔都塞的国家思想中占据重要的理论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阿尔都塞的政治哲学就是一种力量政治学。阿尔都塞总是在强调力量的作用。例如: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在资产阶级国家的AIE中“得到承认,是由于力量。”[21]在亚、非、拉国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被完全禁止,也是由于力量。[22]总之,“理性也好,狡计也罢;无能也好,灵活也罢;事实就摆在这里。……事情可能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这最终取决于一场历史性的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对比。”[23]
三、结 语
总的来看,按照阿尔都塞的逻辑,永恒的胜者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无穷的力量的斗争。结果是,国家是否存在的问题已经不重要。国家的存在需要建构,需要不同的力量建构。这种力量是一种存在的力量,是一种实体表现的力量。它不是归根到底统治意义上的力量,也就是法权意义上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并不是被一种超越的力量所决定。这种超越的力量作为另外一种本体的力量通过合法化的暴力转化为权力。换言之,国家不是被权力所建构、决定的。相反,国家是一种力量的综合体,世界本身也是一种力量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总是在不断地进行多元力量的斗争,不断地交换“位置”进行拓扑学的(力量的)变换,也就是不断地进行再生产。这就是事实,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归根到底的决定(国家)不复存在以后,阿尔都塞下一步的理论逻辑就是:不存在“决定”,存在的只有“非决定”;不存在“国家”,存在的只有“非国家”。“非决定”恰恰是“当代性”的难题性。奈格里正是强调“非决定”,拒绝用“决定”同资本主义国家调情。“非决定”、“反决定”给“诸众”创造了“联合”的空间,从而让“诸众”拥有一种野蛮的创制的力量。“诸众”联合形成力量并通过力量建构国家,就是“诸众”的实践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然而,按照这种逻辑推演,群众则成为了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激进化解读。由此可见,阿尔都塞的国家观实际上是一种反国家观。阿尔都塞通过反国家的方式凸显了他国家思想的激进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激进政治模式。
为了反对目的论的国家观,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开拓理论“空间”,阿尔都塞力图要突破“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本质性的差别。当“基础”被掏空以后,“上层建筑”的内容实际上也随之被掏空了。当“一切”都失去了的时候,就只能通过再生产维持国家这个不可被还原的结构。不可被还原到什么样的结构?不可被还原到具有归根到底决定作用的结构。因为,一旦被还原到这样的结构中,就成为黑格尔的具有同一性的(实际上也就是归根到底决定的)表现性的总体。一些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经济决定论,显然遵循的就是黑格尔的同一性的逻辑。然而,这恰恰是阿尔都塞所反对的。在阿尔都塞那里,拓扑变换后的国家的拓扑学平面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同质的经济的平面空间。在后者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机械的因果关系(直线性的因果关系)。而在前者中,不存在谁先于谁存在的可“追溯”的还原主义问题,更多强调的是共时性的各因素,即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阿尔都塞坚称从来没有一种社会实体是由一个或一组其他的社会实体所决定。相反,社会中的每一个乃至所有的实体总是由所有其他实体的效果同时决定的。换言之,每一个实体都是所有其他实体间相互影响的产物。其由所有这些其他实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个或某组实体单独决定。”[24]因此,“基础”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中法—政治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甚至“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在同一平面共同贡献作用指数的意义上,不再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前理论的问题。在国家的拓扑平面中,存在的只有力量以及力量之间的斗争。也正是由于力量的斗争,国家才得以建构。这种力量的斗争归根到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斗争。
可见,通过对斯宾诺莎的理论“迂回”,阿尔都塞的国家观具有了“当代性”。用阿尔都塞“当代性”的问题式来解读马克思,恰恰就产生了奈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阿尔都塞晚期和奈格里一样,都走上了“诀别”马克思的道路。可以说,阿尔都塞的思想中一直存在激进的成分。这也正是阿尔都塞合乎逻辑地走向了“当代”的理论根本。阿尔都塞也因此成为当代斯宾诺莎复兴,包括用斯宾诺莎解读马克思的理论先驱。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德勒兹、马舍雷、奈格里和巴里巴尔等人。正是在此理论意义上,阿尔都塞不是一个纯粹的结构主义者,他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的先驱,即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是当代法国激进左翼话语的先驱。
〔参 考 文 献〕
[1][法]阿尔都塞.哲学是革命的武器[C]//莫徒,译.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05):160.
[2] [法]阿图塞.答刘易斯(自我批评)[C]//杜章智,沈起予,译.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8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
[4] [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M].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134.
[5]吴子枫.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05):112.
[6] [法]阿尔都塞,[法]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07-108.
[7] [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M].吴子枫,译.陕西: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135.
[8]Althusser. Marx in his Limits[A]. Francois Matheron, Oliver Corpet.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1978-87[C]. London & New York:Verso,2006:47.
[9]姚云帆.重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地形学构造:《论再生产》读后[J].东方学刊,2020(01):115.
[10] [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M].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134.
[11]姚云帆.重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地形学构造:《论再生产》读后[J].东方学刊,2020(01):115.
[12]姚云帆.重绘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地形学构造:《论再生产》读后[J].东方学刊,2020(01):115.
[13]Althusser. Marx in his Limits[A]. Francois Matheron, Oliver Corpet.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1978-87[C]. London & New York:Verso,2006:108.
[14]赵文.力量政治学与群众的自我启蒙: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及其难题性[J].东方学刊,2021(01):94.
[15]斯宾诺莎文集:第4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
[16]斯宾诺莎文集:第4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
[17]赵文.力量政治学与群众的自我启蒙: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及其难题性[J].东方学刊,2021(01):99.
[18][美]沃伦·蒙塔格.结构与表现难题:阿尔都塞早期的“相遇的唯物主义”[J].赵文,兰丽英,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01):151.
[19]斯宾诺莎文集:第4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
[20] [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M].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299.
[21][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M].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208.
[22][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M].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212.
[23][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M].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219-220.
[24][美]斯蒂芬·A·雷斯尼克,[美]理查德·D·沃尔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M].王虎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88.
〔责任编辑:侯庆海,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