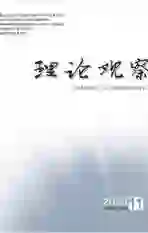延安时期党对民主集中制的探索与发展
2024-12-31刘晓润
摘 要: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制度保障和重要法宝。延安时期党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不懈探索,具体表现为:党既重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又注重坚持党的集中统一;科学认识与把握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促进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制度化具体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民主集中制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11 — 0033 — 04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所坚持的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①。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虽未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在党的会议、文件和工作中已蕴含着鲜明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延安时期是百年党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民主集中制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历史时期。因此,深刻把握延安时期党对民主集中制的探索和发展,对于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完善发展和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以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民主集中制的“名与实”
民主集中制这一概念是由列宁首次明确提出的,作为列宁的重要党建理论之一,民主集中制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先后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主要包括:集中制、民主制、民主的集中制和民主集中制等概念演变。中国共产党接受民主集中制后,其概念和内涵也处在不断变化和丰富发展中。延安时期,党章中关于民主集中制名称的表述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从“民主集中制”修改为“民主的集中制”,这一字之差的变化有着特定的内涵和意义。关于“民主的集中制”这个提法是从俄语中直接翻译过来的,单从语法上来看,许多人认为“民主的集中制”是一个复合词,“民主的”作为形容词是修饰“集中制”的限定语,起修饰辅助的作用,而“集中制”是主语和重心。早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译法也是这种结构,直到党的五大在党章中才明确表述为“民主集中制”。因此,长期以来就容易把民主集中制的侧重点和落脚点放在“集中制”上,这就涉及到民主集中制的“名与实”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民主集中制时强调:“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②实际上,党的七大在党章中把“民主集中制”表述为“民主的集中制”并没有导致党过分侧重集中而弱化和忽视民主,而是依然注重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民主的”作为“集中制”的修饰语,不仅是为了限定“集中制”,防止其发展为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更是作为一种根本政治原则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民主和集中作为一对矛盾共同体,并不是相互排斥,彼此对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延安时期党始终重视并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既把党的纪律和集中统一领导置于重要地位,又重视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首先,在党内民主方面。1945年新修订和通过的七大党章明确规定和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基本条件,前两条强调的是民主,后两条强调的是集中。其中,前两条基本原则为“(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①这两条原则集中反映了党的领导机关的产生和运行都遵循民主原则。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是党的组织生活的主体。此外,七大党章在第一章“党员”中,首次明确规定了广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切实保障了党员民主权利的有效行使与发挥,充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广大党员参与革命战争和党的工作的积极性得以提高。针对党内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党中央曾作出重要指示,此外,突出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党员群众作为主体放在重要位置以调动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创造性发展。延安时期,民主集中制与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二者无论在概念的表述上还是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都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对民主集中制作出深刻阐释,认为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是党内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和深刻反映,是集中于广大党员群众,又贯彻于党员群众中的重要制度,真正实现了广大党员群众与党的领导骨干的深刻结合。②这一重要论述科学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及与群众路线的创造性结合,是党在这一时期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把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和实践提升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
其次,在集中和纪律方面。鉴于延安时期王明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在组织上闹独立性等问题以及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大搞宗派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篡夺党的领导权,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纪律,给党和红军造成极大危害。1938年中共中央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完整地提出“四个服从”的基本原则。四个服从”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原则。1945年,党的七大在党章中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第三条基本条款载入其中,并且第四条基本原则明确指出要“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③。关于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七大党章也作出明确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广大党员应坚决恪守党的纪律,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参与国内革命运动,拥护并贯彻党组织的决议与政策,始终不渝地同党内外损害党的利益和事业的现象与行为作坚决斗争。④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在发扬和践行党内民主原则的同时,坚持对党的集中统一的重视和运用,并且高度注重党的纪律建设。此外,延安时期有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涌入延安,党的队伍迅速扩大,但部分人不能正确地理解民主,党组织内也随之出现了思想不纯的现象,加之中国共产党长期面临的是分散的、独立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导致了党内存在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等错误倾向。对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并予以系统地分析和批判,在其论著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对自由主义的来源、表现形式以及危害等进行了科学分析与论述,对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党的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具有重要意义。总之,注重党的纪律建设,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是延安时期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凝聚和团结党的组织,集中力量推动党的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和关键所在。
二、科学认识和把握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党要正确理解与把握民主集中制,必须科学认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对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进行明确阐述,但却以鲜明的辩证思维对党的民主与集中原则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们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既要高度重视发扬民主原则,又要注重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和保持党的纪律,二者不可偏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与集中关系的正确认识,为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正式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第一次对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和具体内涵作出明确规定,并把民主集中制作为俄共必须遵循的组织原则写入党章。但列宁对于民主制与集中制大多是分开论述的,在实践中侧重于对某一方面的应用,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的认识和论述相对较少,这主要是由当时俄国面临的具体情况和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还不成熟等原因决定的。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解还很不充分,大多时候把民主和集中分开来看待,不能充分认清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党内民主与集中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家长制”“一堂言”和极端民主化等两极分化的错误倾向。
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延安时期党更多地从二者之间的结合和辩证关系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刘少奇在1936年第一次提出:“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集中”①,阐明了民主与集中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应把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毛泽东曾于1938年10月发表文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着重强调,党内民主生活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要使党员深刻理解民主生活的内涵,深刻把握民主制与集中制的关系,了解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路径。如此方可实现,既扩大党内民主生活,同时又能坚持党的集中和纪律,避免极端民主化和放任自由主义的错误。②这一论述明确强调要科学把握民主制与集中制之间的关系,不可使二者走到两极分化的地步,并且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把握和有效落实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作用和意义。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谈到民主集中制问题时指出,理解和把握民主制和集中制要注意“度”的问题,强调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应是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此外,毛泽东还基于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视角出发,对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加以深刻阐述,他强调,无论是民主还是集中,都是要达到很高程度的,尽管两者间存在一定矛盾,但这矛盾是能够统一的,民主集中制能够切实将两者统一起来。③这标志着党对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认识上升到新高度。1945年5月,刘少奇在《论党》一文中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进行了深刻阐释,并对何为党内集中制和民主制这两个基本问题作出了具体的回答和阐释,指出党的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而非完全脱离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同时,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而非无领导的极端民主化和党内无政府状态。④刘少奇对民主集中制内涵的科学论述深刻阐明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并且他提出党内秩序的建立要遵循“四个服从”的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
科学把握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并非强调民主与集中二者之间的绝对平分和对等,二者是随着革命实际的变化以达到动态平衡的辩证关系。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两者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所谓动态平衡,就是指民主与集中不是两个固定不变的等量要素,而是应根据党和国家面临的具体实际和中心任务,有时民主多一些,有时集中多一些,像天平一样随着砝码的轻重变化来回波动,以此达到二者之间的相对平衡状态。民主与集中之间离开任何一方就会造成极端错误的倾向,离开了集中只讲民主就会变成极端民主化;离开了民主只讲集中就会变成集权和专制,因此绝对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根据这一时期革命环境的具体情况强调,要壮大党的力量,调动起全党参与革命斗争和党的事业的积极性,就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反动和内战期间,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⑤。在这一重要论述中,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民主制”与“集中制”的概念,还强调了要把握民主制与集中制之间的动态平衡。民主与集中不是一半对一半的关系,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加以变化和调整的。
三、推动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制度化具体化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制度需要靠一系列具体制度来体现和贯彻执行。延安时期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的具体制度建设取得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完善了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健全了党代会制度和党委会制度,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和“三三制”等。这些具体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各个方面和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延伸,推动了这一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具体化发展。
首先,延安时期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制度化。延安时期以前,民主集中制大多是作为党的一项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而存在的,党对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建设探索成果较少且在实践中存在着过度侧重民主或过度侧重集中的倾向。实际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一项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需要靠一系列具体制度来贯彻执行并加以规范和保障。延安时期党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运用民主集中制,并注重开展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具体制度建设,为民主集中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推动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制度化。在党内制度层面,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文件,对民主集中制及相关内容作出具体规定和安排,促进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化发展。这一时期,党还建立和完善了包括请示报告制度、党代会制度和党委会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具体制度,这些具体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在实际的运行和落实过程中,既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原则,促进了民主集中制在各个方面的有效贯彻落实,推动了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消除党和军队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和无纪律状态,克服党内存在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党进一步健全了党委会制度并正式建立了党的请示报告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在政权建设层面,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团结起最广大人民的力量夺取抗战胜利,1940年春,党提出了“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即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政权人员分配的三分之一。作为党在特殊的革命战争环境中的重要制度创新,“三三制”原则不仅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一时期的具体制度表现,同时也实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政权建设层面的创造性运用。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的“三三制”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又团结起社会各阶级抗日民主力量,很好地平衡了抗日与民主的关系,是民主集中制在政权建设方面的成功尝试和制度创新。
其次,延安时期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具体化。制度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要使延安时期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具体制度得以有效贯彻落实,就要使这些制度进一步具体化。在党内选举制方面,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一文中,对党章内容作出深刻阐释,他指出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时,必须保证大会主席团、各代表团以及所有代表,都具有提出候选人的权利,同时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个候选人的权利。必须在经过充分讨论并确定候选人名单后,根据名单开展无记名投票或表决。①党员代表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党内民主选举得以有效开展的前提和基础。七大党章第一次以条文的形式明确了党员享有的基本权利,其中第二条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把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关于党内选举需要遵循的原则,刘少奇强调,在任何能够组织大会并开展选举的地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以及党员大会,都必须以党章规定为根本依据,通过大会进行各级领导机关的选举工作。②这表明党的会议的召开和党内选举都要遵循党章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内选举制度的集中原则。在组织制度方面,党代会作为党的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执行的重要组织载体。延安时期,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把党代会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推向了高潮。七大党章对党的组织机构、组织系统等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三章“党的中央组织”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集、职权以及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等作出详细规定,既体现民主原则又贯彻集中原则,是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生动体现。在领导制度方面,延安时期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党委会制度。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克服党内存在的个人专断、个人包办和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延安时期党十分注重健全和完善党委会制度。这一时期党围绕党委会的具体工作和制度建设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对如何健全党委制作出具体要求,强调既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保证党的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又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发挥好党委书记这个“班长”的重要作用,提高党的决策和工作效率。党委会制度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表现,充分贯彻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利于克服党内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两种错误倾向。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