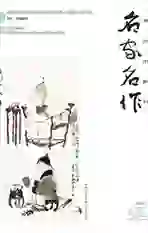论《福》中属下星期五的困境、代表与反抗
2024-12-19李响
[摘 要] 库切的小说《福》展现了星期五作为属下的困境和反抗,他通过拒绝和模拟达到对殖民霸权的抵制消解。对小说《福》的后殖民分析有助于读者发现殖民霸权的存在、被控制被代表的困境,并对霸权做出可能的抵抗。
[关 键 词] 《福》;星期五;殖民霸权;库切
库切于1986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福》,这本小说是对《鲁宾逊漂流记》的解构书写,讲述了苏珊·巴顿在流落荒岛被救助后将星期五从非洲带到英国,并意图不断控制星期五,但在英国时她的生活和写作都受到了福先生管控的故事。本文以殖民霸权的受害者星期五为切入点,探讨了苏珊对星期五住行的控制,和为合法她的主人身份对星期五丢失舌头的归罪;以及福先生作为星期五的虚伪代表,意图打压苏珊和精神控制星期五;星期五作为无言的属下通过跳舞和音乐拒绝苏珊的控制,通过写字、画画来模拟殖民语言等一系列事件,也体现了星期五对殖民霸权所做出的反抗和消解。
一、属下星期五的困境——苏珊对其住行的控制和舌头的归罪
在《福》中,苏珊自诩为星期五的主人,不断地控制他的住、行,这使得星期五陷入了困境。而她对星期五所谓的负责,其实是对星期五的压迫和占有。此外,苏珊将割掉星期五舌头的罪恶行为怪罪到鲁宾逊身上,是她在合法化自己的主人身份。
苏珊对于星期五的控制展现在住行两个方面,尤其是多次决定星期五的行路去向。而对星期五去向的绝对控制,是苏珊对自己主人权威的试探与确定。苏珊决定了三次星期五的行路和去向:去英国、回非洲和不回非洲。在苏珊等到离开孤岛的商船时,她认为“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不能将他一个人丢在那里”[1]34,于是她哀求船长把星期五抓回来一起带回英国。苏珊自认为这是对星期五的责任,其实是她合理控制星期五的遮羞布。于是她不顾星期五的意愿便决定了他的命运和去向,即使观察到星期五看见商船后逃跑和被抓到后的不情愿——“耷拉着肩”[1]36。对于殖民者来说,被殖民者的拒绝会被无视,这正是他们的困境所在。并且殖民者苏珊冠冕堂皇地认为,星期五在英国会“获得自由……,在英国的生活比岛上的生活要好得多”[1]36。事实上,星期五在英国的生活并不好,他被囚禁在地下室,还要承担洗衣和修建花园的杂务。之后,苏珊察觉星期五的拒绝和反抗后,再次决定了他的去向——送他回非洲,但又中途反悔,这是因为她将星期五当作了她的奴隶和所有物,而非一个与她平等的人。其次,苏珊还决定了星期五的住宿情况且比船上所有人都差,“至于星期五,我要求不要让他与其他水手待在一起”[1]36,苏珊让他躺在地板上而非床上睡觉,这是她对自己主人的身份和星期五奴隶身份的确定,也是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等级不同的强调。的确,苏珊支配了星期五,这位女性征服者让星期五成了她的奴隶[2]350。在吃住上,苏珊与星期五的不同也展现出二者地位的不平等,即苏珊作为主人和殖民者比星期五高一等,“我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星期五睡在地下室的床上,我帮他送饭过去”[1]41。纵观星期五在英国的住宿不是地下室就是壁橱,而这所处空间的狭窄和闭塞展现了苏珊对星期五的压迫,这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压迫。
在决定星期五的英国之行时,苏珊就已经成了星期五不合法的主人,而她对星期五的合法化占有,是通过怪罪鲁宾逊割掉星期五的舌头而达成。将星期五丢失的舌头与鲁宾逊相连,苏珊意图把鲁宾逊塑造为残暴的主人,旨在夺取星期五的所属权。在苏珊带星期五来到英国后,为了合法化她不正当的主人身份,她意图让星期五指认是他的主人鲁宾逊割掉了他的舌头:“星期五,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吗?鲁宾逊主人割掉了你的舌头吗?”[1]60星期五在情绪上没有任何的波动,这是对鲁宾逊罪名的否定,是对苏珊合法化主人身份的反抗,这使得苏珊首次争夺奴隶的计划失败。但苏珊没有放弃,继续将星期五的麻木与空洞归罪于鲁宾逊,意图指控鲁宾逊为不合格的主人,“只是星期五跟着鲁宾逊过了多年的麻木日子,早已变得冷漠,没有好奇心”[1]62。与鲁宾逊主人的不称职相反的是苏珊对星期五的友好对待,她将福先生给她的钱“大部分都用于为星期五添置衣服”[1]56。但这仍不能改变鲁宾逊才是星期五的主人这一事实,因此,苏珊再次回到了星期五丢失舌头的话题上:“是不是你的主人割掉了你的舌头,然后怪罪到奴隶贩子身上?”[1]74并且苏珊还自诩为“克鲁索夫人”[1]41,这样就能合法继承“死去丈夫”的遗产——奴隶星期五。在不断怪罪鲁宾逊,树立自己是鲁宾逊夫人身份的同时,苏珊说服自己、福先生和星期五,她才应该是星期五的主人,而不是伤害星期五的鲁宾逊。事实上,苏珊并非真正在意星期五失去舌头的前因,她只在意星期五归属于她的结果。其实,在将星期五视为奴隶的过程中,鲁宾逊和苏珊都消除了星期五的声音[3]134,意图将他的无声默认为自愿服从。无论是成为鲁宾逊还是苏珊的奴隶,星期五都是不能讲话的属下,奴隶和主人的交流注定失败,因为奴隶只需要听从,不需要发声,这就是星期五作为属下的境况,“不能说话”[4]128。
二、属下星期五的代表——福先生的假意发声和精神控制
福先生作为星期五的代表,批评了苏珊对星期五的管控,但真实意图旨在打压苏珊。星期五作为被殖民者和属下不能讲话,只能接受殖民者霸权的统治。如斯皮瓦克所说,属下正因为没有发言权,因此需要有代言人[5]60。对于星期五来说,他没有代言人,而福先生只是他的虚伪代表。
福先生批判苏珊把星期五留在英国的行为,但只为打压苏珊对他的质疑和否定。在苏珊质疑福先生对于杰克的不管控,并自满于她对星期五的负责时,福先生感到权威受到了挑战才为星期五发声,即星期五更愿意被带到有同类的地方而不是和苏珊待在一起。福先生作为星期五的代表只为反击苏珊的质疑,而非真正替星期五发声。并且福先生对于星期五的代言也是表面的,他认为星期五更喜欢和“伦敦的黑人”[1]116在一起成为英国的奴隶,而非回到非洲。正如斯皮瓦克所说,“那些企图为从属阶层代言的人,都是试图把处于从属阶层的人带离他们所属的那个空间”[5]60,而福先生所暗示的是抹杀了星期五真正所属的空间——非洲,将星期五归纳到伦敦黑人这一从属阶层。至此,在福先生对星期五的首次代表中,福先生把星期五当作了用于压制苏珊的利器,并抹杀了星期五的所属空间。
福先生第二次作为星期五的代表是因为苏珊对他让星期五学习英语命令的反抗,并且福先生要求星期五学习英语的目的在于通过语言殖民而达到精神殖民。在福先生不允许苏珊停止对星期五的英语教学时,苏珊再一次感受到了男性对她的控制,如同过往的鲁宾逊,因此她将自己与星期五划为一类,即都是需要自由的人。福先生反驳道,“自由”这种字眼对于星期五没有学习的必要,并且让星期五学习“自由”的字眼简直可笑。因为星期五并不自由,并不是如苏珊所说的那样,“自从克鲁索过世之后,他就是自己的主人了”[1]139。福先生揭露了苏珊的谎言,“星期五还是跟随你,而不是你跟随着他”[1]139,即苏珊成为星期五新的主人不断地管控他,消除了他的自由。这一次福先生作为星期五的代表真切地说出了星期五的困境,但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星期五的困境,而是意欲打压挑战他权威的苏珊。福先生逼迫星期五学习英语的行为,表面是为了让星期五讲出自己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事实上是为了实现对星期五精神上的殖民和控制,将星期五永远锁在“伦敦黑人”这一从属空间,而非自由的非洲人。在福先生对星期五的两次短暂代表中,他的目的不是改变星期五的处境,只是借星期五作为跳板来压制来自苏珊的反抗,并且他绝对不会暂停让星期五学习英语,以此实现精神上的殖民。
三、属下星期五的反抗——舞蹈、音乐的拒绝和对殖民语言的模拟
星期五虽然作为沉默的属下不能说话,但是他对于苏珊的控制以及福先生的假意做出了反抗。星期五通过舞蹈、音乐来拒绝苏珊,又模拟殖民霸权的语言来挑战和消解殖民者的权威。
星期五对苏珊做出的反抗是逐渐强烈的,从拒绝对视到拒绝屈服,主要表现在星期五的舞蹈和音乐上。星期五对苏珊做出的最早的反抗在他的英国之行之前,他拒绝与苏珊对视和离开非洲,“星期五被带上船后,并不看我的眼睛”[1]36。殖民者无视星期五拒绝的行为,将他带到英国,之后星期五的反抗行为愈加剧烈。在找到了福先生的长袍和假发并沉浸在自己的舞蹈中时,星期五离他记忆中的非洲更进了一步,这给了他更多的力量来进行肢体反抗,“他听不见我叫他的名字,我伸出手拽他会被他推到一边”[1]82。在舞蹈转圈中,星期五才是中心,他拒绝苏珊的控制并努力地追求自由。而后星期五在吹笛子中继续他的反抗,无视并拒绝与苏珊合奏。在苏珊努力练习吹出与星期五类似的调子时,二者的权力关系得到了短暂的反转,是苏珊在努力与星期五同频,而非控制星期五。苏珊也发现了这一事实,所以她“无法克制自己不在曲调上做些变化”[1]87,想要重新获得对曲调以及星期五的掌控权。但星期五决心已定,“依旧保持他的老曲调”[1]87,保持他的民族性与非洲的精神,绝不屈服。在舞蹈与音乐中,星期五完成了反抗的升级,坚定地忽视与拒绝苏珊的控制。
星期五的反抗还包括他对殖民语言的模拟,他在模拟的过程中对殖民权威进行了挑战和消解。殖民模拟(mimicry)的概念来自霍米·巴巴的《文化的定位》,是被殖民者对于殖民者的模仿,会“产生几乎相同而又不太一样”[6]86的效果,而这种似是而非的模拟与讽刺相差无几[6]88。并且,模拟后与殖民者的差异对“规范化了的知识和规约性权力都构成了内在的威胁”[6]86,以及分解扰乱了殖民话语的权威[6]88。星期五在学习殖民语言的过程中就进行了反抗,他的模拟与殖民语言产生了差异,完成了对殖民语言话语权威的消解。在苏珊教星期五学习“船”这个单词时,苏珊要求星期五模仿她所书写的h-o-u-s,但星期五写下的h-o-u-s只能是“勉强称得上是字母的东西”[8]134,这就与苏珊所使用的殖民语言产生了差异。在之后苏珊对于星期五的测试中,星期五表现出更大的差异。他所书写的字母与苏珊所教的殖民语言关联甚少,排列也几乎完全不同,这是他对殖民权威故意做出的挑衅,而殖民者苏珊和福先生也拿他毫无办法。事实上,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模拟过程中,星期五的这种差异就是对殖民者强硬“自恋的”[6]88要求的打断与干预。星期五在福先生和苏珊的殖民权威下自由而又有创造力地写和画,“一排排的眼睛下面都长着脚,成了会走路的眼睛”[1]136,并且这种会走路的眼睛所形成的动态画面超越了殖民话语的字母,这严重消解了殖民话语和殖民霸权的权威。尽管殖民者还想继续控制星期五,即苏珊想要拿掉石板,但星期五直接违抗苏珊的命令,并“将三根手指放在嘴里蘸些口水,将石板擦得一干二净”[1]136。星期五这种始料不及的反抗打乱了殖民霸权的原有计划,完全挑战了殖民霸权。星期五一系列反抗的行为是对殖民霸权的嘲弄,也是他通过模拟作为被殖民者和属下对殖民霸权的抵抗和消解。
四、结束语
星期五作为属下和被殖民者,受到了殖民者苏珊和福先生的压迫和精神殖民。苏珊对星期五住行的管控和对其舌头的好奇都表现出她作为主人对星期五的占有和压迫,其中她将星期五被割舌头的行为怪罪于鲁宾逊,只为合法自己的主人地位。而福先生作为星期五的两次代表发言,只是以星期五为跳板打压意图挑战他权威的苏珊。星期五作为属下丧失话语权,但他通过跳舞、音乐、画画以及对殖民语言的模拟做出了反抗。通过对库切《福》中星期五的困境与反抗进行分析,了解到殖民霸权对被殖民者造成的压迫和精神殖民,其中对殖民语言的模拟达到了嘲讽和消解殖民霸权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南非]J.M.库切.福[M],王敬慧,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2]Foxcroft,Nigel H. The Power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J. M. Coetzee’s Foe[J]. ECAH2013 IAFOR:Offic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2013.
[3]Dagar,Seema. Exploring Objectification of Colonial Subjects in J. M. Coetzee’s Foe[J]. Philosophy study,2017.
[4][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6]Bhabha,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
作者单位: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