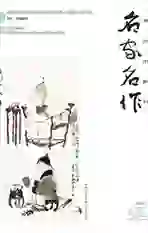浅谈龟兹文化之源及其影响
2024-12-19魏玉娟王兵兵
[摘 要] 龟兹文化有其独有的特色和风格,既具有本土特征,又融合了外来文化(佛教文化),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龟兹文化曾在中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经过东传后对当时的中原文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关 键 词] 龟兹文化;龟兹石窟;中华文化;佛教文化;犍陀罗
一、龟兹文化概述
龟兹文化是在龟兹古国形成的具有其鲜明特色的一种复合型文化,其核心内容是佛教文化。班固的《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酐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①由此可知,龟兹在当时西域三十六国中属于“大国”之列,人口众多,行政组织较为完善,经济发展较好。龟兹在历代汉文史籍中还被称为丘慈、丘兹、屈支、屈茨等,皆源于对龟兹语kutsi的不同译法。
薛宗正、霍旭初在《龟兹历史与佛教文化》一书中指出:“龟兹初本臣属匈奴,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在位的龟兹王降宾率先降汉,遂成为最早降汉的西域诸国之一。”②公元前2世纪之际,龟兹便与中原王朝有了正式交往。龟兹古国地处现今新疆阿克苏地区包括库车、新和、沙雅、拜城、温宿、乌什、柯坪、阿瓦提和阿克苏七县二市,其东境还跨有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所属的轮台县。
作为一种复合型文化,龟兹文化是我国古代汉唐文化、西域文化与国外古印度文化、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融会贯通,并结合龟兹的人文特点而孕育的一种有着鲜明民族特征与地域特色的文化综合体。其形成也与古佛教文化、佛教石窟壁画、石窟题记、乐舞、戏曲、文物、诗词等兼容并包、兼收并蓄,是中华文明在形成和积淀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
二、龟兹文化之“源”
龟兹文化有着复杂多样的历史源流。龟兹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中亚地区间商业运转的中间站。龟兹文化中蕴含着犍陀罗③艺术元素、印度艺术元素、波斯艺术元素、北方草原艺术元素、中原艺术元素,最终在龟兹这片土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龟兹文化。
第一,犍陀罗艺术元素的融入。龟兹石窟作为龟兹文化的重要承载者,石窟中的佛传图、本生图、交脚像、焰肩像、禅定像、化佛像等都包含着典型的犍陀罗艺术元素,无论是人物动态、画面组织还是表现手法,皆体现出犍陀罗艺术风格。关于犍陀罗的中原史籍记载,较早的如《三辅黄图》中讲述了汉武帝赐董偃千涂国所献玉晶的故事,其中千涂即为犍陀罗。④这说明汉朝时便与犍陀罗有了交往。除此以外,从文字来看,犍陀罗语与龟兹语非常接近。刘锡淦、陈良伟在《龟兹古国史》中指出:“龟兹居民的文字是借助印度西北地区的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构词法。”①这说明犍陀罗与龟兹之间往来早、交往程度深。从佛教经典看,犍陀罗与龟兹也有着密切的联系。龟兹流行的佛教经典为“说一切有部”②,而犍陀罗是“说一切有部”早期传化的重要地区。目前,从考古发现和现存龟兹石窟壁画中发现了很多与犍陀罗相似的佛教文物,如携带式龛像、石雕龛像、佛传浮雕等。这些龛像很可能就是龟兹石窟画师最早的摹本,并且龟兹石窟壁画所用青金石颜料的产地是古代阿富汗的巴达赫尚,这些都能够说明犍陀罗与龟兹往来密切。文字、佛经及考古发现等都能够证明龟兹文化中蕴含着犍陀罗艺术。
第二,印度艺术元素的融入。在龟兹文化中,核心内容即为佛教文化,印度艺术文化是基于印度本土信仰及传统造像产生的艺术元素,区别于犍陀罗艺术。印度在中国古籍中最早出现在《史记·大宛列传》中,将印度称为“身毒”:“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由此可知,西汉时便与印度有往来,包含经济贸易。《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其中,天竺相较于身毒而言,蕴含着对西天佛国的敬意和向往之情。后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言:“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由此,印度之称沿用至今。龟兹与印度的往来,始终是非常密切的。根据史料记载,其往来通道主要是经西北印度地区成行。在龟兹石窟壁画中,存在大量的类似印度艺术创作风格的图案,主要表现为对人体描绘时展现出的肉感,其中裸体女性形象以其丰满的肉体、诱人的姿态区别于国内其他石窟壁画。龟兹石窟中人物形象描绘的特征与印度本土艺术元素类似,而非龟兹民族本土固有的文化习俗。
第三,波斯艺术元素的融入。龟兹文化中的波斯艺术元素主要是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融入的。龟兹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大量的商人带着波斯的织锦、货币和器皿在龟兹汇聚,展现出繁华的商业活动。而这些在龟兹石窟壁画中皆有描绘,再现了丝路贸易的繁荣和波斯奢华的物质生活,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工艺器皿及装饰纹样,都蕴含着波斯艺术元素。龟兹石窟中世俗供养人(信徒)的形象,在体型和服饰上都体现出波斯的特征:颀长笔挺的长袍,大翻领在胸前翻开,腰间系有金属腰带,服饰上的装饰品都是仿波斯的装饰风格。军服也是波斯样式,克孜尔壁画中手持长矛的人物,头戴圆锥形头盔,身穿铠甲,手持长矛或者砍、刺两用的长剑,还保持着波斯人的优雅气质。③除此以外,更为明显的便是壁画人物独特的站立姿势:脚跟向内,脚尖向外,以芭蕾舞的姿势脚尖点地叉开站立,且其脚部与人物体型不成比例,又尖又小。这种脚部特征和站立姿势在波斯金银币及波斯银盘图案中皆存在,这足以说明龟兹文化中波斯艺术文化的融入。
第四,北方草原艺术元素的融入。由于龟兹古国独特的地理位置,故而与北方草原民族自始至终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佛教传入龟兹之前,当地主要体现为游牧文明的特征;佛教传入之后,北方草原文化融入龟兹石窟中,这也使得龟兹石窟壁画中充分体现着北方草原文化的信仰与习俗、游牧服饰以及特征鲜明的动物造型。如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角类动物形象,将原本印度文化中短小的鹿角呈现为与身体等长的大角,同时壁画中的鹿做曲肢姿势,这些都是北方草原艺术中常有的动物姿态。从信仰和习俗的角度来看,在龟兹壁画中出现了壁画人物拔发、划脸划胸的哀悼姿势,无论是印度还是犍陀罗地区,都没有这种哀悼姿势的源头。《隋书·突厥传》中记载:“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从现存最早的汉文史料记载中可知,继匈奴之后,氐羌、契胡、突厥、车师、粟特、铁勒等游牧民族皆有此习俗。除此以外,从龟兹石窟中人物服饰特色来看,存在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左衽及窄袖袍、窄腿宽裤裆、尖头长靴、腰系蹀躞带的着装,体现出游牧服饰的特征。
第五,中原艺术元素的融入。公元65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入龟兹,统辖龟兹镇、焉耆镇、疏勒镇、于阗镇,史称安西四镇。由此,龟兹石窟呈现出典型的汉地风格,转变为中原艺术样式,出现了完全体现中原佛教艺术样式的石窟。汉地风貌石窟的出现反映了唐王朝对龟兹有力的统治和汉文化的强大融合力。郑炳林在其著作中强调中原艺术最主要是由敦煌传入龟兹的。他认为敦煌是古代中国经营西域的基地,汉唐以来中央政府经营西域,都以敦煌为军屯要塞,而且很多行军路线也都是以敦煌为起点,同时中央政府派遣敦煌地区的官员带军出征西域地区。①敦煌与西域之间的密切往来使得两地文化间的交融成为可能。按照佛教传播的路径,早期敦煌壁画受印度和西域影响较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地区便是龟兹。随着时代的变迁,唐代敦煌壁画发展到鼎盛时期,逐渐反向影响龟兹壁画风格,由此,龟兹石窟壁画中呈现出盛唐气象。安西都护府迁入龟兹,为汉地文化在龟兹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基础。中原艺术元素融入的一个突出表现在于:龟兹佛教经印度传入的主要为小乘佛教,随着中原佛教艺术的传入以及僧众之间的往来,大乘佛法及汉地石窟风格也传入龟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库木土拉石窟和阿艾石窟,是典型的“汉风窟”。
三、龟兹文化的影响
龟兹古国在西汉初期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一个大国,亦是一个著名的佛国,境内佛教文化异常繁盛。龟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开放的环境,使得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汇集。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龟兹文化曾经在中亚地区辉煌了一千多年的时间,不仅影响了该地区各国的历史进程,还为古代中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曙光。伴随西域佛教的东传,龟兹文化逐步对中原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一,龟兹文化开创了中原地区石窟文化的先河,中原地区的石窟寺大多发源于龟兹石窟,并以西北地区的石窟寺为代表。同时,仿照龟兹石窟式样,在汉地出现了大像窟和大型立佛。敦煌石窟在早期呈现出浓厚的西域佛教艺术特色,无论是色彩还是渲染方式,都带有龟兹石窟风格。可以说,龟兹对于中华文化中佛教石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龟兹文化影响了古代中原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其中,出生于龟兹的鸠摩罗什便是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之一。鸠摩罗什的父亲是天竺人,母亲是龟兹王妹。鸠摩罗什七岁随母亲出家,跟随龟兹的著名僧人学习佛教经典,其最大的成就在于译经。鸠摩罗什与弟子在弘始三年至十一年期间(401—409),译出《大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论。这些译著的问世,对汉地佛教的兴盛提供了重要支撑。
第三,龟兹文化丰富了古代中原文化的内容,从建筑形式到绘画艺术再到乐舞方面,在一定范围内都呈现出龟兹文化的印记。从建筑形式上看,龟兹石窟建筑中的中心方柱形支提窟被称为“龟兹窟”,这种石窟风格是在印度支提窟的基础上结合龟兹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特点形成的本土化风格。在敦煌也发现了这种风格的石窟,如莫高窟19号窟中的中心方柱形。同样,在龟兹库木土拉石窟中发现的“五连洞”形石窟建筑风格,天水麦积山石窟004号窟也是同类修建。从绘画艺术的角度看,中原地区石窟壁画的绘画内容和风格与龟兹石窟壁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呈现出继承关系。从龟兹乐舞方面看,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高度概括了龟兹乐舞的繁盛,彰显了龟兹乐舞闻名于世。宋人沈辽在诗歌中记载:“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揭示了龟兹舞自汉朝便已传入中原,而且被收录于乐府中,由此便可窥见其历史地位。龟兹乐舞的东传扩散,在更大范围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文明宝库。
第四,龟兹文化不仅在艺术和宗教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在语言文字方面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龟兹古国曾使用一种名为“龟兹文”的文字,这种文字源自印度的婆罗米文,后经过演变形成了独特的书写体系。龟兹文在龟兹地区广泛使用,甚至影响到了周边地区,如焉耆、高昌等地。龟兹文的使用,不仅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也为后世学者研究古代中亚语言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五,在医学领域,龟兹文化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龟兹地区曾是东西方医学交流的重要枢纽,当地人民在吸收印度、波斯等地医学知识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医学体系。龟兹医学在治疗内外科疾病、药物配制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龟兹医学中关于草药的使用和配伍,对中原地区的药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在政治制度方面,龟兹古国也展现出了其独特的智慧。龟兹实行的是一种以国王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国王之下设有各级官吏,负责管理国家的各个方面。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同时,龟兹还与周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关系,通过联姻、贸易等方式,增强了自身的影响力。龟兹的政治制度和外交策略,对后来的西域诸国乃至中原王朝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龟兹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不仅在艺术、宗教、语言文字、医学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为古代中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曙光。龟兹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丰富内涵,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新疆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