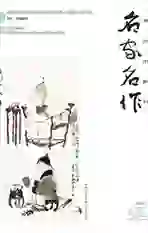开端与二重性
2024-12-19孙静宜
[摘 要] 作为希腊哲学中宇宙论之重要文本,《蒂迈欧篇》实现了宇宙起源与运作逻辑的“近似论述”。探讨作为影像之言语的危机对于起源与“发生”问题中时间之内在悖论的揭示;追踪蒂迈欧宇宙论中可见世界之显现进程,揭示“第三种类型”如何构成不同于传统二元论框架的“二重性”逻辑;通过“二重性”之逻辑揭示感性与理知之间保留的“能动性”,探讨《蒂迈欧篇》关于身体的论述开启的独特认识论视角。“发生”的非时间性、存在与生成之“二重性”、理知与感性世界的不可分离性,即《蒂迈欧篇》之“哲学—影像”。
[关 键 词] 柏拉图;宇宙论;时间;二重性;《蒂迈欧篇》
作为希腊哲学中宇宙论之重要文本,《蒂迈欧篇》涉及了宇宙起源与运作逻辑——既铺展了一幅渺远而神秘的起源构架与创世图景,又融贯了数学、音乐、天文乃至医学等诸多领域,以精湛的技艺(techne)将其编织成秩序井然的迭复系统。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说:“它尚未被修辞格或解释性翻译所耗尽。”①通过“影像”(image)的言语抵临“起源”的疑难与时间的悖论,通过世界与身体的“影像化”机制追踪宇宙的生产秩序,将为《蒂迈欧篇》打开全新的解读空间。
一、开端的危险:“近似论述”与时间—影像
在古希腊语中,“宇宙”(Kosmos)一词含有“世界”和“设置秩序”双重含义,对宇宙起源的追溯总是关乎从无序到有序的“发生”。然而,对“发生”的追问总是关涉如下疑难:如果我们将“起源”视为被给定的时间之点,则其必定服从于先在的时间秩序而取消了自身的优先性。反之,先于时间而存在、俯瞰并推动时间发生的“起源”又是如何可能的?无论何种猜想,都将问题引向一种更复杂的情形:作为一种时间性的表述的“起源”(Arche),如何能够作为时间超出自身的部分而标记时间的“发生”?
这一疑难正是《蒂迈欧篇》全部的神秘与晦涩所在,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的:“它尚未被这些类型的修辞格或解释性翻译所耗尽。”虽然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圣造物主(Demiurge)被引入了宇宙论的起源论述,但我们不应将“起源”(Arche)或“起源性本源”(Geneseōs Arche)还原为神创论框架。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论述的开端,蒂迈欧便提到了一种“危险”,这一危险实际上涉及言语自身的危机。在柏拉图的文本中,我们屡次被警告影像(image)或生成物所具有的欺骗性质,但蒂迈欧坦承,关于存在的论说本身难以与这种“欺骗”本身拉开距离。实际上,论述的危机始源于时间自身的悖论:时间并不能还原为时刻相继的连续性,而是在构成自身的断裂之点处不断地自我启动、自我触发。在每一个断裂之点处,“立刻”的迅疾总是太迟,当人们声称捕获了可锚定的开端或时间之点,实际上捕获的仅仅是一重动态影像。并且,依循线性序列的论述本身便是一重影像,模仿永恒者却无法还原为永恒者的自我同一性。因此,蒂迈欧所称的“危险”,正是在不断自我差异、自我偏离的时间—影像之中,严格依循影像之“技艺”的完美来抵临(而非超逾)存在本身。蒂迈欧希望我们接受这一危险的尝试,并在最后总结时,称之为“近似故事”(eikos mythos)、“近似论述”(eikos logos),而恰恰是近似的、与真实保持一定严格偏离的“影像言语”能最真切地实现关于存在的论说,或者说,含混正是对存在之不可锚定性之精确还原,因此蒂迈欧作出如下声明:“较之其他解释,这论说的近似性不会更弱,而是更强。”(48D)
在论述的开端,蒂迈欧向苏格拉底指出讨论宇宙本性的关键——起源与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讨论宇宙本性问题,考察它的起源,或者要是没有起源的话,它是如何存在的。”(28B-C)起源的论说首先关乎可见的宇宙的“发生”,它似乎处于两种存在的交接点上:其一是不变的永恒者,不可见且自身同一的存在;其二是可见的生成物,作为“保持同一的永恒的动态影像”(37D)而永恒变化。在蒂迈欧的论说中,造物者(Demiurge)总是不偏不倚、无私而公正的,希望万事万物尽可能无缺陷。由此,起源的故事总是关乎某一“不可分”的完满者的影像化,可见世界也依循某一包含一切、没有任何部分流失在外的“完整的生命体”(31B)而产生,这身体呈球状,并“在原处作同一运动,在自身中不断地自我旋转”(34A)。由于没有任何事物外在于这一身体,造物者把它的外表造得绝对平滑:它不需要用手来抓东西或保护自己,也不需要用脚或其他肢体来支撑自己。它无需双眼,因为外面没有东西可看;他无需听觉与呼吸,因为外面没有声音与空气。器官的缺乏并非意味着宇宙身体相对于人类处于进化的低级形式,恰恰相反,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器官,与宇宙的完满自足相比仅仅是某种附属物或赘余。
随后,蒂迈欧谈及造物者制造灵魂的方式与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因此而断定蒂迈欧的宇宙论述中身体相较于灵魂处于优先地位,这将是一种误解。在身体与灵魂的起源论述中,时序的偶尔中断与颠倒或许也构成了开端之“危险”本身,虽然安置灵魂的行动在建造身体之后,但蒂迈欧强调,灵魂“更老练”(35C),较之身体具有更大的“潜能”,宇宙身体的运动秩序内含于灵魂的理性与和谐。由此,蒂迈欧坚持,被注入灵魂的宇宙同时是“活生生”且可以“理知”的。随着造物主将灵魂注入身体,可见世界、天体、昼夜作为“生产时间所需的联合体被赋予适当的运动”(38E),与时间一同诞生并进入共同的秩序,并且“是因为共同产生才使它们有可能共同消失(如果它们还会消失的话)”(38C)。造物者注入灵魂的行动涉及时间与空间的共同生成,而生成之“起源”即存在的划分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因此,接下来在对灵魂与身体的结合(42E-44C)这一理知(intellect)的作品进行描述后,蒂迈欧又不得不“重新再开一次头”(48E)。在这里,蒂迈欧引入了第三种划分,此为《蒂迈欧》篇中最难解的部分:
首先,存在着理型,不生不灭,既不容纳他物于自身,也不会进入其他事物中,不可见不可感觉,只能为思想所把握。其次,我们有与理型同名并相似的东西,可以感知,被产生,总在运动,来去匆匆,我们通过知觉和信念来把握它们。第三者是空间,不朽而永恒,并作为一切生成物运动变化的场所;感觉无法认识它,而只能靠一种不纯粹的理性推理来认识它,它也很难是信念的对象。(52A)①
抵及开端的困难揭示了蒂迈欧对时间之诸点不连续且不可捕获的洞见,开篇对“不变”与“变”之二分仍旧无法揭示“变”如何在“不变”中确切地发生。倘若人们将生成物自存在的“发生”简单归于目的因与动力因的协同,仍旧难免沦为囿于传统线性时间序列的解释性意象。因此,此处被重新引入的、即将被命名为“χρα”的第三种空间,如德里达所说,是“非时间的”(anachronique)。第三种类型是“存在中的非时间性”,更确切地说,存在之非时间性,它使存在非时间化。
二、生成之“二重性”与世界—影像
关于灵魂如何“合成”,蒂迈欧在论述“理知(nous)的创造”时进行了概括说明:(造物主)用不可分的、永恒同一的存在者与有关形体的可分的、生成的存在者,混合成第三种存在者,令它兼具同和异的性质;他就这样把它从不可分的一方与形体领域可分的一方中间合成出来。然后将这三者再混合为一体,强使同和异的性质相结合。(35B)我们已经看到,对应于柏拉图哲学体系的二分,第一种类型是自身同一的“理式”,彻头彻尾是其自身,不可见、不可为感官所把握,却不生不灭、永恒存在,只能为“理知”所洞察。第二种类型是这“理式”的可见“摹本”,就像裹卷在海上的海浪,生成并消亡,可以通过感觉为意见所把握。在这里,全部的问题在于如何从“一、二”数到“三”,然而,计数的悖论在于被计数者必然在某一类型中可彼此区分和识别。但是,如果要计数的恰恰是类型本身,我们是否能够采取一个范围更广的视点,使被计数者可以被视为另一更高类型的子类型?可是,这样的做法也必定取消了第一种类型的自我同一性。在Khra一书中,德里达提到了在二元项之间谈论“第三种类型”(troisième genre)的双重危险:“我们甚至不能说它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或者它既是这个又是那个。”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将第三种类型归诸“非存在”并宣告同与异的绝对分离,而是如同德里达所指出的,应当思考一种超越类型的类型(un genre au-delà du genre)的可能,即“双重排除(ni / ni)和双重参与(à la fois... et,ceci et cela)”的可能。
在对“理知(nous)的创造”进行论述后,蒂迈欧又“重新再开一次头”,开始讨论必然性(Ananche)的作用(48A)。应当注意到,造物主并非从“非存在”中创造宇宙,而是通过“劝说”(persuade)一种预先存在的混沌环境,“引导它们从无序走向有序”(30a)。在造物主将理型引入这个世界的事物之前,已经预先形成了火、水、气、土之元素,这些预先存在的元素带有一些作为其固有性质的“痕迹”,但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法国研究者Luca Pitteloud将元素与痕迹的混乱状态概括为“前宇宙”(pré-cosmique)的混沌运动,并准确指出:“这种前宇宙运动的出现必须具有准实体(quasi-entités)的特征”①。前宇宙的运动非宇宙历史中的一个时期,而是作为第三种类型,作为蒂迈欧“思想实验”中的一个时刻。蒂迈欧通过理式在某一载体上进行“压印”的机制实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近似论述,并将这一过程的载体命名为“χρα”(52a),即第三种类型:“容器”(hypodoche,英译:receptacle),作为一种接受者与承受一切运动形式的铸造材料:“当它承受万物时,它完全不丧失它的本性;也不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时候占据任何一种形式。”(51b)“无形式”的载体受到既不相似也不平衡的力量的影响,参与生成之物的“部分”而显现自身:“火是它的一部分,即不断扬起的火焰……水则是它浸润的部分。”并且,载体总是与生成者共属一场生成运动:“四种成分就是以这种方式被载体震荡不止;而它自己则像簸箕一样也在震荡中。”(53a)因而,载体同时既是场所又是推动者,既是材料又是过程,载体自身的容纳与震荡,构成生成运动自身的必然性,并且使生成者可见的同时,保留了有待生成的时间化与世界化。因此,第三种类型昭示着变者与不变者、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不可分离,可见者之显现过程也正是场所自身的差异化的动态“影像”,正如德里达所说:“这种对第三种类型的称谓成为走向超越类型的类型的一种迂回(détour)。”而恰恰是这种超越类型的类型“χρα”能够作为生成与存在两种类型之“最好的结合”——“最好的结合就是使自身和被结合的事物尽可能成为一体的事物”(32C)。
法国学者吕卡·皮特洛(Luca Pitteloud)指出,没有理知参与的世界“并不等同于非存在(non-être),而是等同于存在与生成中的不可还原的混沌维度”。德里达也以法语中的“有”(ilya)了第三种类型的实在性:“Khra并非既不可感也不可理知。有 Khra,我们甚至可以审问它的本性和动力”。生成与存在作为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区分,意指的恰恰是:存在作为生成之物的原因,其显现正是自身的隐藏,这一隐藏经由“第三种类型”保存为有待生成的时间化与世界化,因而严格构成了生成者之生产过程本身,此即生成与存在之“二重性”。《蒂迈欧篇》中这一显现与隐藏之“二重性”明显有别于传统柏拉图学说中生成与存在、可见性与不可见性、摹本与原型的二元论。有且仅有一个作为必然性的世界,一切生成之物的场所(medium),世界本身即“χρα”——非“地方”(place)的绝对“场域”(field)。蒂迈欧表示:“它是实实在在的,只是我们无法唤醒我们自己而对它给出真实的说明。”(52c)这第三种类型虽是实在的,但并不是可见之现实的,虽是可认识的,但只能为一种“不纯的推理”(spurious reason)所认识,作为非现实性并对现实之物构成性作用的“实在性”,这就是“χρα”之“必然性”所意谓的事情。
三、身心平行论与身体—影像
如上文所述,“χρα”作为可见性与不可见性、显现(生成者)与显现条件(存在)的深层折叠,意谓着“存在”之不可见性并非令诸造物服从于可见世界的机械因果性,而是将“χρα”的载体作为人们“参与”可见者显现的方式②,通过“必然性”本身在感性与理知之间保留了某种“能动性”。因此,在宇宙的起源论述之外,《蒂迈欧篇》无疑开启了近代认识论中接受的感性与能动的知性的漫长哲学主题,将宇宙论的论述推向了“将世界作为影像”的全新认识论视角。正如学者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re Nevsky)在其著作《将世界视作影像》(Voir le monde comme une image)中指出的:“将世界作为影像,认识到它的幻象(phantasma)性质并不是指纯粹和简单的虚无,而是表明它的内在联系……具有真实的实在(réalité veritable)。影像不是纯粹的幻象,它是通向不可见事物的可见之门。”①
正如蒂迈欧以影像言语来建立可见宇宙之“发生”的“近似论述”(eikos logos),宇宙的诸造物皆能够通过一种影像化的“不纯的推理”(spurious reason)(52B)来推知宇宙的构成力量。作为纯粹理知(nous)的一重影像,人类的头脑与思维毕竟无法与理知对“存在”之观照(theoria)相提并论,而是与一种思想与身体交互的实践、制作性的技艺(techne)密不可分。因此,在《蒂迈欧篇》中,身体与头脑似乎处于平行地位,身体的各个部分应该按照同样的原则、遵循宇宙的秩序来加以关照。蒂迈欧指出,我们的身体并非封闭的体系,而是一种具有“多孔机理”(porous texture)的结构,“在内部通过进入它的物质而加热和冷却,在外部环境中被干燥和浸润,并且受到这两个过程中的干扰”(88D)。因此,身体必然朝向宇宙开放,与宇宙同样遵从同一种生产秩序,并以相同的秩序生产和表现自身。而这并不意味着身体在宇宙中保持被动性或“惰性”(inert),蒂迈欧格外强调身体的能动性,他指出,一切运动中最优越的是“我们在自身之中生产自身的运动”(89A),因为它最接近于思想的运动和宇宙的运动。那么,相对于思想,身体作为被动的接受者,如何另一方面使得自身的能动性得以保留呢?在对肝脏的结构与功能的细致描述中,蒂迈欧再度以影像的方式维系起灵魂与身体:肝脏并非头脑,即理性和智慧的生产者,却充当了理性和感觉之潜能的载体和媒介,将“从我们理智中流出的思想力量”之影像投射在自身细密而光洁的表层上,从而控制了隔膜以下的器官带来的难以驾驭的激情(如“被诸神系在胃部食槽旁的饕餮”),而这种控制并非指向后世基督教学说中基于个体原罪与有限性的禁欲行为,而是通过多孔结构的动态互渗,与宇宙本身的秩序实现一种“均衡”,因此,肝脏得以作为诸神的“预言器官”安眠度夜,执行它的预兆,人们的身体在夜间通过肝脏实现与诸神的沟通。
因此,在蒂迈欧的构造中,身体即影像,同时思想也是影像本身,或许这正是近代身心平行论的滥觞。我们通过影像感知,并能够在身体与思想中不断参与影像的再生产,并且宇宙自身便是一重影像,它充分地自足,如果这里存在着运动,那么它正是必然性成就其自身的运动。宇宙因其必然性之自足而并不具有任何爱欲或野心,不需要在与他物的镜像遭遇中找到其完整性,因此,既没有可欲的外部,也没有外在对象能构成其可毁灭性。由此,在蒂迈欧的论述中,关于灵魂与身体之疾病的“治疗”,并非苏格拉底所追求的,通过德性的探求和对自我认识的辩证追问,朝向不可见世界的上升欲望。治疗毋宁意味着并不沉溺于非理性的快感,而是按照宇宙的严格必然性,对宇宙之不可僭逾的公正进行充分的肯定,通过实践、制作性的行动,达到人类灵魂与宇宙秩序的后发和谐:“不做无视身体的灵魂运动,也不做无视灵魂的体力活动。这样就可以使两者各得其所,和谐健康……人体的许多部位都应循此原则来调养以模仿宇宙的构造。”(88B)
四、结束语
将世界视为影像,通过χρα这“第三种类型”,身体与灵魂、可感性与可理知性实现了“非协调的协调”,这几乎是悖论性的,宇宙也因此获得了独异的特征:“一种可理知的影像,一个可感的神(92C)。”《蒂迈欧篇》最后一句正是宇宙神的颂歌的终曲:“它是可见的神,最伟大、最好、最美、最完满——是独一无二的天(92C)。”宇宙之所以完满,因其是影像自身的协奏曲。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