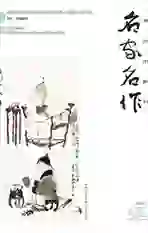李贺诗词色彩描写中的自卑、自恋意蕴
2024-12-19杜汇川
[摘 要] 李贺诗词的色彩描写反映了他的自卑与自恋。冷色折射出其自卑心理,主要表现在他对自身体貌方面的过分介怀,如“巨鼻宜山褐”“秋姿白发生”“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艳色表征出其自恋情结,主要集中在他对才华品格、身世抱负的陶然自醉,如“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等。多舛的命运与功业豪情的猛烈碰撞,使其诗在色彩运用上有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关 键 词] 李贺诗词;色彩描写;自卑;自恋;冷色调
中唐有“诗鬼”之誉的诗人李贺出身没落世家,有抱负欠机运,身羸弱却欲雄万军,履田园写平淡而无陶潜放达,故笔端屡屡在无意中流露出不平之气。这样的心路历程、格局,造就了李贺独具色彩的诗词歌赋,不仅在诗句中直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的鬼魅幽森,而且在诗词色彩书写中塑造了瑰丽冷崛的视觉意象。钱锺书称“长吉穿幽入仄,惨淡经营,都在修辞设色,举凡谋篇命意,均落第二义”①,断非虚语。身弱与心雄反差,使他不得不寄托于穿幽入仄、修辞设色,诗卷画意中凛凛不平气的底层则是诗人的自卑、自恋。
自卑、自恋是西方文艺理论概念。然而,它们作为人类独特的精神现象,早已存在于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之中,体现在古代文人面对自我与环境剧烈冲突时所做出的种种反应中。李贺诗词的所谓“设色”,涉及索绪尔语言学的纵聚合这一同义语言成分的替换方式,体现出诗人强烈的主观性、个人风格及其审美内涵。因此,研究李贺诗词的“设色”问题可以更好地挖掘其内在情感和价值取向。
一、无奈而遁世——冷色中的自卑
李贺诗对冷色调词汇的使用频率较高,“灰蝶生阴松”(《感讽》其五),灰色呼应“阴”,愈显抑郁;“一方黑照三方紫”(《北中寒》),紫本吉祥色,被黑所穿凿而令活跃深幽的气息荡然无存;更有“三十六宫土花碧”(《金铜仙人辞汉歌》),碧色生机葳蕤遇“土”而价值归尘。李贺习惯将以上颜色采取“冷处理”的方式,表现人生寥落、情志卑沉。其一,诗中“青”“冷”相随,如《苏小小墓》的“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再有《伤心行》的“灯青兰膏歇,落照飞蛾舞”。其中,绿草、青松非指生机勃勃,却如青灯相对,如泣如诉,冷艳之景,哀人之思,字里行间皆不能不承受其中的人生卑沉。其二,将贵重之色、生机之色加一定前缀,否定贵重、泯灭生机,卑如尘芥,怜比蝼蚁。如“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梦天》),“黄尘”“清水”并锦连用,代指沧海桑田,抒叹人生短暂与世事无常。其三,红色也被李贺作冷色处理,专门用来写衰败之景、吐愁苦之情。如“吴兴才人怨春风,桃花满陌千里红”(《送沈亚之歌·并序》)、“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琉璃钟》)等。
李贺诗词修辞设色,自陈卑志,转而将眼光投向道家的遁世隐逸。以其描绘农村风光的《南山田中行》为例:“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其色调一如上述而显得幽冷阴凉。蛰萤昏黄点动,如漆鬼灯阴暗冷寒,与蛰萤动态类似,若明若暗,浅深显灭。以此搭配“凿穿”“冷红泣露娇啼色”,恰在揭示“云根苔藓山上石”中“石为云根”的道家超逸旨趣。与儒家入世、建功立业的社会取向不同,道家具有超世、寄情山水的自然取向。《南山田中行》首联“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秋野自然,秋风素白,塘水旷远,虫声唧唧,一派田园风貌,非关道家而何!首联声景光貌,紧扣后三联而结之连襟于“云根苔藓山上石”。诗句因平仄需要而倒装,应为“苔藓山上石云根”,李贺的《南山田中行》中冷色调的遣用、艳色的冷处理,皆关乎“石为云根”的道家旨趣。
“石为云根”的理论总结①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总结而来。北方雨后的山间云雾弥漫,或华夏南方的山整年云雾缭绕,人们观察中常见到山上的云雾被树枝、陡峭山崖、山石所羁绊,给人的错觉往往是云从石头底部或石间生出,云的轻盈向上与飞鸟相似,给予善于想象的人们以契机,以此成为驾云上天与仙人绸缪的凭借。道家青鸟探看的典故,羽化登仙、驾鹤成仙的传说,皆自观察飞鸟而来。炼丹长生、驾云上天的道家仪式,则自“石为云根”的想象和践行而来。换言之,人们把石头看作云之根只是初步的活动,认为通过一定的神秘操作,让石头生云的道理在人体内产生相似的灵化反应,才是深入的操作和目的。中医“吃啥补啥”就蕴含着这个道理。同理,华夏古人想象把自然界有灵气的石头汇聚在炼丹炉内,利用加热、物质配比等手段,人类同样能在仙丹里获得自然灵气,服用仙丹后定能轻则飞檐走壁、缩骨延臂,高则羽化登仙、长生不老。对于李贺来说,如果不能建功立业、燕然勒石,那么延年益寿、驾云往还天地之间也是很好的选择。换言之,建功立业不成,雄心难竞,留意自然求仙问道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选择罢了,内在真实的心声则仍不离深深的自卑。
李贺自卑心寓道家旨趣,诗词亦随之。道家崇白,白色在李贺诗中出现次数最多,大多与孤冷的情绪或感受相关,显示其在命运、功业上的无力感。《南山田中行》“秋风白”,又如“月午树无影,一山唯白晓”(《感讽》其三),“白”字写整个山野间,只悬月一色,愈托山岗的孤寂清冷和诡异。又如“塞长连白空,遥见汉旗红”(《平城下》),“白”与“红”相衬,边塞战士孤单寥落。李贺以“白”字描写田野衰败,如“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自昌谷到洛后门》),一“白”字出,田野茫茫景象而全诗悲伤,就此奠定基调。
钱锺书常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舆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如明珠错落。”②大抵可以将之理解为李贺总对近景进行十分细致的描摹,而对远景则模糊处理,视线始终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空间。换言之,他更多地关心与自己相关的事物,偏重主观感受,而缺乏远、深、阔的视野。究其原因,是自卑心理在作祟。
二、没落贵族心态——艳色中的自恋
说李贺是没落贵族,符合事实。李唐皇家远裔,贵极血统的流淌使李贺生来就自高一等,因而对建功立业、直斩楼兰,直以霍去病自诩。但憧憬过多,失败越大,自信就走向自卑或自恋的结局。自卑则移心别向,自恋则自我封闭,眷恋于一方艺术天地,遣词造句、设色自娱,此时的设色为艳色,心理则为自恋。艺术书写的自恋体现着李贺的没落贵族心态。
李贺诗绚丽多彩,意境脱俗,艳色描写自成一格。“飞香走红满天春,花龙盘盘上紫云。三千彩女列金屋,五十弦瑟海上闻。天河碎碎银沙路,嬴女机中断烟素。断烟素,缝舞衣,八月一日君前舞。”(《上云乐》)其中,艳色如红、紫、彩、金、银等,绚丽多姿、辞藻富繁,依稀四方来贺的盛唐王朝气象。《李凭箜篌引》谓:“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在此,李贺的绚丽色彩组合,艺术感染力极强,充满奇崛的浪漫色彩。“炫才逞能”的创作,是其在才华上自恋、沾沾自喜、无暇他顾的表现。
李贺肆意挥洒笔墨,大量渲染饱满色彩,倾于将大块油彩直接铺陈于画布,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写历史、写战争,李贺浓墨重彩,意境雄浑壮丽、慷慨悲壮。《雁门太守行》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起笔,黑与金对,压抑逼仄和贵重昂扬复调铺排。继以“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声觉、视觉交叉轰炸感官、通感错置,秋色打底,暗黑为衬,敷加燕脂之深红,黑红相衬相裂,张力再起,声色捭阖,又燕脂凝夜紫,黑红张力上再加黑紫,层层叠嶂,色色相遇,试问:“汉武有闲暇为之?寄情山水的李白可为之?‘早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可为之?”答案是明确的,建功业、求仙道、忧黎元之心一旦充斥内里,断然不会达到李贺的色彩境界,何故?自恋为本也。至于“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句句着色,色彩艳丽斑斓,大红大紫中不仅显示出李贺对建立功勋的渴望,更可以看出他对自身才华的自恋。然而,这种宏大的战争场面描写,却又混合着李贺深度的自卑。皇室血脉里的轻狂与不屈使他不甘心沉于下僚,诗中那些极富层次的壮丽艳色背后,是他自卑过度以后饱含自信的白日幻想。纵观李贺生平,自卑的体貌条件及其不愿屈就现实的孤傲人格,导致他常遭碰壁而又屡次不满,其诗就表现为自卑与自信孪出的个人特征。事功缺失、诗心自恋,使他唯有逃避在色彩斑斓的诗性世界中才能以白日梦的方式获得精神上的短暂满足。
换言之,艺术书写的自恋同时体现为李贺的没落贵族心态。与同为没落世家出身的张爱玲相比,二人均擅长明艳色彩的描写,在描写中透露出浮华落尽前的未尽余温。《第一炉香》写天色已暗月华初上月色“黄黄的,像玉色缎子上,刺绣时弹落了一点香灰,烧糊了一小片”。黄黄的玉色缎子,华丽高雅,不意落了燃烧未尽的烟灰,烧糊了,糊黑的点极为煞风景地破坏了华丽高贵氛围,如鸟粪落在精心烹制的汤里,滋味尽毁。《留情》说了两个生命,“第一个生命是青绿色的,第二个是暗红的”,如木炭的经历,初起是树木,后来死了,但身子里仍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可最终虽然活着却快成灰了。如果说青绿代表迫人的生机,那么暗红则代表垂死的生命,流血殆尽徒留外表了。暗红未尽而非灰黑,一方面是说生机将尽未尽,生命力是顽强的,另一方面是说脱离人间以前眷恋如日中天的曾经繁华。就后者而言,则是自恋无疑。对张爱玲《第一炉香》是窗帘和床单猩红的土灰色,是家具样式的古旧和曾引领一时风骚。对李贺则是骨子里的皇家血统的傲娇在现实里处处碰壁后的自恋眷依,只能在诗句里营造意象的高贵繁华和色彩五彩斑斓;仅是五彩斑斓的艳丽意象,也只留给后人西山残照、落日余晖了。
三、李贺的色彩描写与其自卑、自恋心态
李贺诗中的冷色描写是他自卑心理的体现,艳色描写是其自恋情结的表征。唐人张碧说:“读李长吉集,谓春拆红翠,霹开蛰户,其奇峭不可攻也。”纵观李贺之诗,不难看出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味。“巨鼻宜山褐,秋姿白发生。”素以风流飘逸自命的李贺,却以“巨、褐、白”这些阴暗灰冷的词语描述自己的外貌。两条浓黑粗大的眉毛连在一起,过于肥大的鼻子,比例失衡的五官,以上种种纽结在一起。这样一副瘦弱而近乎可怖的面目,始终是李贺的心病。加之因年岁增长和疾病的催迫,他的情志、抱负也愈加黯淡。在他笔下,就形成了极具凄冷的色调。然而,这正是他孑然独立而又卑微渺小的生命所投出的自卑的叹息。
身为皇族之后,七岁就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师,始终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在其诗中亦见沛然。“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如此开阔明丽的意境,是他对实现人生理想的自信。 然而,丑陋、病弱的体貌和现实的打击,使李贺再也无法做到淡定从容地正视自己的苦难。他目睹了诸多王公贵族奢华糜烂的生活,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于是创作了大量诗歌加以讥讽。“袅袅沉水烟,乌啼夜阑景。曲沼芙蓉波,腰围白玉冷。”(《贵公子夜阑曲》)这是写贵族公子彻夜饮宴作乐的诗,虽然它未直接描述贵族公子沉湎于寻欢作乐、彻夜宴饮的场景,但通过“袅袅沉水烟”“腰围白玉玲”,却让人想象出宴饮场面之盛与宴乐之长。李贺看到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寥寥数语就表达出他寂寞惆怅、灰心失望的孤苦心境。他的《荣华乐》《贵主征行乐》通过大量的篇幅和华丽的辞藻,描述了贵族纵情享乐的奢侈生活,与其他讽喻同情民生疾苦的主旨不同,李贺的内心还怀有对于富贵生活的羡慕和向往,但他既徘徊又流连于讽刺和向往这两种立场。作为一个自卑与自恋的矛盾者,李贺很难达到某种平衡。皇族血统与才华满腹让他意气风发,可身体缺陷和坎坷仕途却又使他壮志难酬。因而,在李贺痛苦不平的情绪无从宣泄时,便只能转头在诗歌中流淌出这种奇特瑰丽的诗篇了。
自恋者的高度自我关注显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李贺而言,他始终有一种异于常人的优越感,然而他又始终不能与外部现实作出切割,因此他只能表现为对权力、功名等长此往复的孤苦幻想。就其自恋的形式而言,有着显性和隐性之分。除上述显性自恋以外,其隐性自恋体现在他内心潜在的自卑情结所导致的对他人评价的极度敏感、过分焦虑与不安。纵观李贺的诗词,无论是天国的快乐、仙境的美妙,或是充当豪侠壮士的豪言壮语和屠宰烛龙、锤碎白日的谎言,还是皇族贵胄天才少年的自恋和走桃花运的幻想,实则都是回避现实挫折和伤害。在此意义上,李贺在诗中寻求对有缺陷的人生和苦闷的精神的安慰,实际上是其自卑与自恋的潜意识的外化,是追求他人尊重和渴望被爱以及自我实现的心理补偿。
参考文献:
[1]陈友冰.论李贺的皇族意识:对《李长吉歌诗》的另类解读[J].江淮论坛,2003(5):133-140.
[2]孟修祥.李贺的变态心理与诗歌创作[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73-78,84.
[3]李至柔.桃花乱落如红雨:以色彩看李贺的生命意识[J].汉字文化,2018(1):45-47.
[4]赵静,张海钟.自恋研究进展[J].精神医学杂志,2007(1):52-57.
[5]陶文鹏.论李贺诗歌的色彩表现艺术[J].文学评论,1997(6):98-105.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