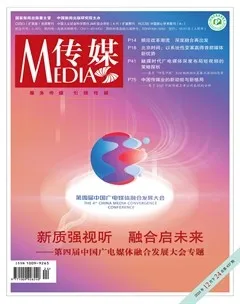《新青年》中“科学”的概念与编辑宗旨变迁
2024-12-10娄煜东
摘要:刊物的时代背景、编辑宗旨与阅读意义生成之间的关系,是传媒史和阅读史研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引入概念史研究方法,通过对《新青年》中“科学”概念内涵从本体、方法和价值三方面的分析,旨在揭示文本核心概念与杂志编辑宗旨之间的关联。《新青年》涉及的领域从开辟多元主题向专注政治理论的转型;编辑理念由以学术争论引领舆论风潮转向以政治信仰开展革命动员;秉持的意识形态由崇尚自由主义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些都见于作者笔下“科学”概念的工具属性切换。
关键词:《新青年》 科学 编辑宗旨 陈独秀
一本刊物的编辑宗旨,总是会约束着编辑对信息的收集、筛选和编排。而编辑工作的社会价值也正在这种信息的加工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在读者群体中得以实现。因此,刊物文章作者释放出的信息,就成为编辑宗旨和刊物价值之间的媒介。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既可以窥见编辑宗旨,也有助于评估刊物在受众之中的影响。笔者引入概念史研究方法,着眼于《新青年》这一中国近代极具时代特征的典型刊物,对其中高频涉及的“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展开个案分析,以期管窥刊物的时代背景、编辑宗旨和社会影响之间的关联性。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以下统称《新青年》),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6年7月25日为最后一刊,短短的十年多时间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和性质变迁重要的见证。关于其编辑出版史的研究不胜枚举,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早期的《新青年》主要以针对青年群体的思想启蒙为主,而后则转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共机关刊物。其中“科学”一词作为刊物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出现在每一阶段不同作者的笔下,其内涵有着时代所赋予的共同特征,也存在个体差异。据统计,“科学”一词在《新青年》中一共出现了1658次。鉴于出现频率高,及科学概念内涵的复杂性与相近、相反概念的多元性,故将“科学”一词在《新青年》中的用法,结合前后文语境,分为本体论角度、方法论角度和价值论角度三类进行分析。
一、“科学”概念的本体论角度分析
“科学”概念的本体论角度即从“科学”所涉及的知识范畴来看。结合“科学”的概念史可知,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无论是“格致”还是“科学”,已出现过所指代的知识范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专指自然科学。在各个阶段的《新青年》作者中均可看到该种理解。任鸿隽在《何为科学家》一文中将“学”与“术”剥离,认为科学是形而上的理论,而非形而下的应用:“我们要晓得科学是学问,不是一种艺术……学是根本,术是学的应用。”另有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并称的用法,如马君武所言:“……不惟自然科学之理论上进步而已。凡技术工艺交通诸问题皆然,以造成今世界之文明生活。然其他精神方面及社会关系则不惟毫无进步,反有退步焉。”其不仅将理论与实践区别开,也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社会关系等领域分割理解。
2.指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总和。此种认知与前者的差异关键在于是否认同科学方法可以移植于人文社会领域研究,抑或对已有人文社会领域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是否持肯定态度。刘叔雅在反思一战之教训时,强调国家之兴衰存亡在乎科学,而“举凡政治、军事、工业、商业、经济、教育、交通、及国家社会之凡百事业,无不唯科学是赖”。将个体人文社会研究领域认同为科学的案例还有“实验教育学者,欧美最新之科学”“(孔道西)想把历史作成一科学”“(马克思)郑重的归咎于经济科学的本身”等。1920年,陈独秀在对“新文化运动”的阐释中将狭义的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而广义的科学则包括了社会科学,可谓这种观点最具代表性的陈述。
3.指代自然科学和基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知识。这一种观点混淆了理论性的科学规律探索和实践性的技术应用。例如,“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德用闷杀瓦斯以攻敌。法则用铝质之嘴套以御之。科学愈明。攻战愈巧。”“人种改良学乃对于将来人类研究改良其体格及精神上之种族的性质,而增进其安宁幸福之科学也。”
二、“科学”概念的方法论角度分析
“科学”概念的方法论角度即《新青年》作者关于“科学”研究方法的认知。近代西方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包括归纳和演绎逻辑的运用、以数学语言为表达工具、通过实验验证假说等,通常总结为“数理实验科学”。在《新青年》中一些哲学文章和关于科学的综合性议论文中,都涉及作者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解。
1.归纳和演绎逻辑。近代科学所赖以发端的哲学基础之一,即培根与笛卡尔等哲人关于归纳和演绎逻辑的深入探索。高擎“科学”大旗的《新青年》同人们,回归科学的认识论基础,试图从学理层面为其辩护。高一涵最早在《新青年》中指出这二者的区别:“夫求科学之道,不外于万殊物理之中,归籍其统一会通之则。执此统一会通之则。以逆万殊之事。以断未然之机也。前者谓之归纳。后者谓之演绎。”更进一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作者们还讨论了理性感性二者与科学的关系,明确了理性主义的立场,却难免有一定极端理性倾向:“欲得真实之自然界知识及解释世界疑迷,惟赖良知(现译理性)……所谓兴会者,乃脑髓之一种复杂作用,由哀乐感触,好恶悬想,及拒求倾向等,联合所成……而认识真理,全不需此。”
2.通过数学语言描述规律。例如,“德人处事,随在皆有科学精神。如浴盆,至琐事也,因调浴汤之冷暖,普通以摄氏三十八度为宜”。李亦民所谓德国人的“科学精神”,即对数学的运用。王星拱则指出了科学精确性的关键在于数学:“各科学都以算学为基础,算学是最真实的……科学的精神,指算学确切的精神。”
3.对于证据、实验和客观性的阐述。《新青年》同人热衷于西方科学哲学的引介。对于实验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等思想均展开详细辨析。如陈独秀于《敬告青年》中写道:“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刘叔雅也云:“……循科学之通例,据经验之事实。”此二人都道出了科学研究基于事实这一特性。马君武更是揭示出“事实”的根基在于感官收集之信息:“吾侪解释世界大疑谜之方法,不外纯粹的科学知识,由经验以得结论,科学之结验,由吾侪用感觉机关及大脑之感觉府,积多种观察及实验得之。”胡适更是进一步指出科学规律之实用主义进路,对真理的符合论发起挑战,可见《新青年》早期同人思想的多元性和论战性。
三、“科学”概念的价值论角度分析
“科学”概念的价值论角度即“科学”作为形容词的含义。科学除了是一种知识范畴之外,早在工业革命之初的西方社会,自然科学正是借助同技术的整合,发挥出了其在生产力领域中的潜质,成为凌驾于其他知识形式之上,甚至用于衡量一切知识形式的尺度。在坚船利炮之下深陷民族危机的近代中国,将科学视作挽救危亡的武器。这一时期学人整体呈现“全盘西化”特征的背景下,科学难免被推上教条化的神坛。
1.表示合理的、好的、正确的。例如,陈独秀所言:“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蒋光赤的语言习惯则直接反映了“科学”在他的认知中之价值准绳地位:“现代科学指示我们……科学指示我们……”身为科学家的王星拱则强调了科学在道德领域中的价值:“真实的就是善的……有了真是非(就是真实和错误),我们的行为,才有标准。所以科学的道德观,要能辨别是非(就是善恶)。”这种用科学上的“是非”取代“善恶”的理解,显然是科学绝对化倾向的表现。

2.表示非宗教的、非迷信的。作者们试图以科学为工具驱散迷信,宣扬理性精神,在《新青年》早期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宗旨下尤其明显。《敬告青年》中有:“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马君武则指出科学与宗教之差异在于信仰与理性的先后关系:“所谓道德学者,乃不出耶稣经典之范围。以信仰为先,知识为后……”这一理解成为同人们几乎毫无争议的共同立场:“迷信和非理是人类的大敌,科学和理性是人类的挚友。”
3.表示革命的、符合马列主义的。《新青年》后期意识形态转向马列主义后,“科学”一词往往与“社会主义”构成词组,指代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路线。例如,李大钊早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区分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两个阶段:“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高一涵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重点理解为其革命性和实践性:“科学的社会主义家不是专门描写将来的理想的社会,只注意在实际上的社会改革。”自唯物史观进入青年红色理论家们的视野后,科学性又通过唯物史观得以彰显:“马克思关于(一)为实现那个当作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怎样的‘物质的基础’,和(二)那个必要的‘物质的基础’如何才能完成——这两个问题,曾经做了科学的研究;所以在这一点上,他的社会主义可以称做科学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科学性”,已经成为宣传唯物史观的工具概念。李达曾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五个方面:“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
四、“科学”的概念史与编辑宗旨变迁的关联
从历时性变迁的角度审查,不难发现,《新青年》作者在使用“科学”这一概念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思想启蒙为主要导向。通过塑造旧中国与新西方之间的对立,在道德、思想、艺术、政治,甚至文字等广泛的上层建筑空间内,用西学全面取代传统。早期文章中的“科学”更多以自然科学为所指,通过将自然科学研究之方法、精神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基石,创建新的上层建筑。这一阶段的高峰主要在第一卷到第三卷。第二阶段进入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并存的时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和民族危亡的现实压力,使得作者们继续思想启蒙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科学”对于救亡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强调科学的应用可以增强国力,另一方面,借助宣扬进化论思想,强调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应积极谋求民族的独立自强。这一阶段的高峰大致从第五卷到第七卷。第三阶段以宣传马列主义为主要导向。这一阶段的“科学”,大部分都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用于塑造马列主义在思想界中的权威地位。社会进化论的地位被唯物史观所取代,这一阶段的“科学”,几乎成了政治主张宣传和革命动员的工具。
“科学”概念的嬗变与刊物编辑宗旨的变迁有着非常显著的关联性。从陈独秀独自担任主编,到第四卷以后北京大学的同人轮流主编,再到第七卷后由中共党内理论家主导,其编辑宗旨伴随着主编群体的变化和社会时局的影响而几经转型。最初,刊物关注的重点在于针对青年群体的思想启蒙,文章主题多涉及思想界、科学界和文艺界,企图“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后进入同人共同创作阶段后,更是发扬这一传统。作者如胡适等人更是明确提出“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在第四卷到第六卷主编轮替期间,每一期刊物的文章主题中都可以看到轮值主编清晰的个人烙印。正是在这一时期,政治理论开始在刊物中初露头角,但整体上仍旧保持了主题多元化的风格。1920年5月,第七卷第六号专门开设“劳动节纪念专号”,围绕劳工和劳动问题展开,特别是本期最后《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翻译了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放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内地所设的工厂,与夫俄国官员,或牧师,或委员等,所有不受中国法庭的审判等的特权”,赢得了国内各界极高的评价。这些都推动《新青年》和国内思想界向“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革命”等关键词看齐。随后,由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大量加入编辑队伍,刊物主导意识形态开始迅速向马列主义转向。伴随着第八卷中常设的“俄罗斯研究”专栏,马列主义宣传成为刊物明确的宗旨,直到1923年完全转型成为中共机关刊物。
(作者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中外历史书写中的‘现代’话语研究”(项目编号:22JJD770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J].新青年,1919,6(05).
[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新青年,1920,7(05).
[4]高语罕.青年之敌[J].青年杂志,1916,1(06).
[5]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J].青年杂志,1915,1(03).
[6]马君武.赫克尔之一元哲学(续)[J].新青年,1916,2(03).
[7]王星拱.科学的起源和效果[J].新青年,1919,7(01).
[8]刘叔雅.叔本华自我意志说[J].青年杂志,1915,1(04).
[9]胡适.实验主义[J].新青年,1919,6(04).
[10]蒋光赤.经济形式与社会关系之变迁[J].新青年,1923(02).
[11]李达.马克思还原[J].新青年,1921,8(05).
[12]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J].历史研究,2009(03).
[13]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M]//陈东晓.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局,1933.
【编辑:陈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