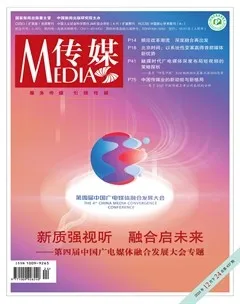人文地理纪录片《文脉春秋》“地方感”建构策略研究
2024-12-10许鑫
随着媒介地理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人文地理类纪实影像不断受到学界关注。在媒体融合日益推进的当下,人文地理类纪实影像借助数字技术不断打造具有互动性、融合性、具身性的媒介产品,借助融合思维不断向用户下沉,让地理信息与观众之间形成共生体验。
《文脉春秋》作为融合思维下的人文地理纪录片典范,于2023年末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推出,对中华五千年历史地理展开变迁叙事,将地方与历史、地方与人文相互交织,通过多个历史名城的案例勾连起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脉络,对“何以中国”“中华民族何以伟大”“中华文明何以不朽”作出回答,用名城的千年发展史建构起地方感。“地方感”由地方性、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共同构成,三者间为路径助推关系,即个体在场接触地方的相关信息之后对地方产生依恋与认同,因而纪录片对地方感的建构即为对祖国大地、家乡故土、共有精神家园的高度依恋与认同的影像呈现。
一、历史对话中的具身书写
人文地理纪录片作为纪实影像的重要分支,在对历史与当下的梳理中发挥时空见证功能。它们通过数字技术搭建的虚拟场景,让历史的“在场”表达得以再现,形成跨越荧屏的具身观感,从而通过强烈的历史召唤能力增强观众的观影体验。
1.互动性空间的搭建。互动性是媒体深度融合下媒介影像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强调影像经由媒介传播与观众产生互动关联与情感共鸣。《文脉春秋》依靠互动叙事搭建起互动性空间,巧妙借助城市地理地形、人文景观、历史名人之间的互动关联展现中华数千年的文脉图景。
《文脉春秋》与以往人文地理纪录片分隔式展现城市空间场景相比,增加了时间关联与空间互动,让叙事风格呈现别具一格。在时间维度上,《文脉春秋》通过介绍历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让城市历史地理影像的演变过程跃上荧屏,梳理清晰历史间的城市与城市、人物与人物、故事与故事之间的对话脉络,营造出“肉身”在场的沉浸式体验。第1集《文脉春秋·绍兴》从大禹治水的历史典故引出绍兴的城市诞生渊源,大禹与当地古越人的关联,并经由讲解绍兴古名“会稽”“越州”的变迁及内涵,从而衍生出王羲之、王阳明、鲁迅等绍兴历史名人故事。该片打通了历史名人间的时间壁垒,使其经由同一地方——绍兴而产生互动对话,让观众得以在30分钟的影像中极大程度地了解千年时间的绍兴故事。而影片中出现的人物故事皆为观众耳熟能详的中华历史名人,借助其名人效应,在人物的讲解中进一步激发个体与时间维度中中华文脉的深度联结。
在空间维度上,《文脉春秋》采用地图位移分点讲解的方式展开互动叙事,让城市间的各处地形、景点、街巷从物理空间关联的基础上产生人文的互动关联。该片囊括的地图形式多样,其中包括数字动画地图、古代城舆图、航拍地图。镜头景别从远至近,按“城市—街区—建筑”的层次展开空间脉络,逐步讲解城市内部单一地理坐标的名称典故、实际意义与表征功能的同时,还串联起坐标间互动交织的人文故事。
2.身体的在场感知。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数字技术产物带来影像媒介新一轮的身体性转向,进而赋予主体能动的、多模态的、沉浸式的通感知觉。在法国身体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看来,身体、知觉、世界三者是完整统合的共同体,人通过身体接触世界从而产生知觉,也可以通过知觉再次感悟世界。《文脉春秋》将AR技术引入纪录片场景,应用于地图变迁的视频转场,将现实场景叠加在数字动画地图、古代城舆图之上,形成由古观今、拨云见日的历史在场感,进一步拉近历史与当下的距离,让观众感知脚下的道路仍是历史长河中古人走过的路。在《文脉春秋·歙县》一期中采用如今歙县的航拍地图,通过AR技术,将虚拟金黄色分界线应用于当下城市场景,清晰讲解唐代之后由于徽州府治与歙县县治同在一座城池,而在乌聊山下形成的“城套城”的独特格局,自然而然地将观众的身体带入故事的具体场景。在具身性实践中,由于身体具有物质性,必然与空间或地方紧密关联才能完成身体的流动与生产,因而空间或地方赋予身体广阔的施展舞台。《文脉春秋》通过历史名城当地居民的切身体验,诸如影像中身体在场的古城街巷里的猪肉摊老板、菜市场摊贩、油粮店售货员,促成了身体融入空间的影像传递。此时,古城居民在影像中扮演着“漫游者”(Flaneur)的角色,借由其凝视、触摸、漫步、攀谈的身体行为与历史名城、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等空间媒介物形成互动,共同构成纪录片影像中流动的身体感知。人是城市建设的关键,生活在旧街区老建筑里的人们亲身体验了历史与岁月的痕迹。
3.历史脉络的叙事。历史是空间见证下的时间遗存,伴随着物质载体与精神载体的持续保存而被反复吟唱。它不仅是人自我存在的证明与主体性的表征,还是人与世界的交互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平遥古城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而回到历史现场,对历史脉络展开梳理是让观众清晰感知历史的必要途径。《文脉春秋》每集均采用时间顺序叙事,用历史的自然时间流逝还原与回溯中华大地的变与不变。在《文脉春秋·剑川》一期中通过数字动画地图的位置移动,展现自唐代建立罗鲁城后长达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中,剑川城址在金华山与剑湖间的空间变迁。但在《文脉春秋·泉州》一期中,泉州的地标性街道西街和中山路组成的十字形格局从五代时期至今未曾改变,前后延续1000多年,变幻的光影记录让观众在时间的流逝中感悟城市的沧海桑田。
同时,在叙事维度上,该片对每座城市的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均附文标注该处承载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在《文脉春秋·绍兴》一期中展示了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于2019年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脉春秋·抚州》一期中展示了抚州下辖的竹桥村于2010年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该片不仅将历史脉络的宝贵遗存进行突出展示,还充分利用历史元素,经由历史典籍、古诗、绘画还原历史故事,用历史来讲历史,进一步增强了纪录片的材料真实感和历史在场感。苏州篇便引用白居易所写《武丘寺路》诗中尾联“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来形容苏州山塘街的悠长历史。
二、中华大地上的情感联结
人文地理纪录片是对现实空间图景的影像生产,但与自然地理纪录片相比,其因人文情感联结而更具有温度和社会意义。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土地与“家”“国”概念绑定,“国—家”意识是个体对地方萌发情感的主要助推作用,而这种观念构成了“家庭”“家乡”“国家”的三重物理空间形态,除此之外还诞生了一种独特的空间划分——“家园”。“家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乡,独立于物理空间而存在于个体对家国自然的意识想象。《文脉春秋》便在物质与精神双重维度上建构起观众内心的地理情感寄托。
1.“国家爱恋”:中华大地的文脉传承。“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青铜铭文:“宅兹中国”,意指周王在中心地区建立王室,统治天下百姓,将黄河中原地区居住地称为“中国”。在历史的演变中,“中国”逐渐从地理称谓转变为地理与国家概念的统一体。《文脉春秋》将中国的历史溯源,对历朝历代至今城市的居住演变、文化习俗、建筑风格等进行系统性再现,用遗留痕迹回答了“何以中国”。在《文脉春秋·绍兴》一期中开篇介绍夏朝开国君王大禹与绍兴的历史故事,并用“大禹陵”进行影像佐证,让观众了解这位历史人物与绍兴的既有往事,感悟文脉的根源,找寻“我们从何处来”的家国情怀。
《文脉春秋》巧妙邀请历史名城的居民作为纪录片内容的主要参与者,不仅达到真实还原与再现城市生活和烟火气息的效果,还向外沉浸式刻画与传播居民的生活与习俗信息。与宏大叙事的纪录片有所区别,该片经常取景于早市、菜市场、饭店、校园等富有人文气息的场景,并不施加独特修饰与服化道的扮演,仅通过真实居民的日常生活来反映其对中华大地的爱恋。
《文脉春秋》不仅通过繁忙热闹的街道反映出影像中城市居民积极阳光的生活态度,还通过影像空间展现城市居民对中华文脉的传承与创新。例如,在《文脉春秋·阆中》一期中,国学馆女教师鲜明带领儿童前往阆中古城边的锦屏山观星楼,一同吟诵古诗,欣赏古迹,实现了中华文脉的教育传递。在该期中,创作者向观众介绍阆中西汉时期天文学家落下闳,普及其创作《太初历》纳入历法体系的历史知识的同时,还加入了如今小学校园学生吟诵二十四节气歌的影像片段,呈现出中华儿女对中华文脉的薪火相传。
2.“家乡追恋”:多民族的交流共生。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国家,在岁月长河中自然演化形成中华民族的族群意识。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了不同分支,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各具特色的地区方言、民俗风格和风土人情。《文脉春秋》在叙事时将各地域的方言融入纪录片的制作中,四川话、闽南语、吴语、徽语等地域方言活化了影像的地理场景。该片充分借助电视视听媒介的优势,采用方言来表达居民对家乡更为细腻的情感。方言作为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多民族聚集的遗存,是巴蜀人、吴人、越人、滇人等先民族的精神保留。尽管在后续的演变中,地理方位由于王朝更替、行政规划、自然灾害等原因发生变动,但方言的保留能瞬间唤醒民众对家乡的追恋与记忆。
同时,《文脉春秋》还原了古民族在不同地域的生存发展脉络,为找寻中华民族历史根源提供影像依托。在《文脉春秋·绍兴》一期中详细介绍越人在绍兴的繁衍与发展,考据《国语》记载的越国生育奖励典章制度“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并进一步讲解其中“二壶酒”奖励的便是当今浙江绍兴一带的特产——黄酒。影像用酒文化的保留这一细节具体展现绍兴居民“恋地情结”,用日常生活品的传承见证古越人在这里的繁衍生息。
3.“家园依恋”:集体居所的自然向往。“家园”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不仅仅是指家乡、故乡,更是代表一种“情感愿景”,一种精神的归属、慰藉和寄托。而这种对家园的“情感愿景”往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万物与人归于一体的理想状态。《文脉春秋》结合历史名城的城市规划将古人与今人对集体居所的情感依恋和自然追求进行信息解读与内涵诠释。在《文脉春秋·苏州》一期中介绍苏州古城河道时提到纵向河道的流向并非与古城南北垂直朝向,而是南偏东约7度。该片揭晓这一精妙设计是有意为之,由于河道与城池偏向东南可以避开西南太湖方向洪水的正面冲击,防止洪水灌入城中引发洪涝,还让河道成为通风走廊,发挥调节古城局部气候的功效,让古城生态更加宜居。
在《文脉春秋·泉州》一期中讲述了闽南传统建筑修缮工匠曾国伟的故事。他在对泉州中山路进行修缮时,将旧有现代感极强的铝合金门窗换成带有花鸟木雕刻的木窗。作为泉州本地人,曾国伟怀揣着对故土的期待,在对家园的想象上统一了中山路的建筑风格,使其在别具一格的基础上更显自然天成。该片将古今国人心中“天—地—人”三者相互交织、自然和合的家园理念加以传播,全方位展现了居民对城市的满腔热情与智慧。
三、集体记忆下的地方认同呈现
集体记忆承载着地方的经验、智慧与精神。作为精神纽带,集体记忆打破了不同地域、乡族之间的社会屏障,使之形成统一的共同体。在中华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血脉深厚、文明悠久、遗产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通过地方认同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动力。人文地理纪录片作为地方集体记忆的媒介载体,具有凝聚地方认同的实践功能。
《文脉春秋》主要借助集体记忆下的文化展演来激发观众的文化认同,通过文化认同呈现地方认同。在《文脉春秋·绍兴》一期中,影片介绍耳熟能详的绍兴历史文化名人——鲁迅,在影像中展示了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寿镜吾先生雕像,将存在于小学课本中的课文原型搬上荧幕,让观众了解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还原场景。在《文脉春秋·安阳》一期中,影片通过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文物对古老文字甲骨文进行详细讲解,用当地出土的考古文物真实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文化魅力。该片勾勒出文化记忆的历史样貌与现实场景,让观众的知识与现实相互印证,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除了每集必有的关于地域特产美食文化的介绍外,《文脉春秋》还将戏剧作为最为重要的地域文化展示的组成部分。戏剧作为独特的艺术形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结合地方方言、地方故事、地方习俗形成各具特色的表演种类。无论是浙江绍兴篇的越剧、河南安阳篇的淮调、江苏苏州篇的评弹,还是江西抚州篇的采茶戏、广东佛山篇的粤剧,《文脉春秋》不仅介绍了戏剧的起名、发源与演变,还展示了戏剧的后台准备过程等不为人知的幕后环节,并通过戏班班主、演出人员的直接讲述揭示出真切的地方文化,传递出戏剧演员热爱与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风貌。在唤醒观众文化记忆和地方感知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凝聚起观众对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地方认同既来源于地方依恋,同时也会受到文化自豪感的影响。《文脉春秋》通过文脉知识的科学普及,用科学性视角阐述历史上中国古人的营城智慧和集体居住理念,诠释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在对文脉根基的深层次解读下增进观众对地方的情感共鸣与记忆联动。该片从江南河道的规划设计到山西民居的院落安排,逐步剖析古人在房屋建筑、城市布局、装修设计中蕴藏着的科学原理和实际功用,激发起观众内心的文化自豪感,进而增进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
四、结语
《文脉春秋》回首中华民族的文脉渊源,展望文化记忆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作为人文地理纪录片的典型之作,它结合历史与当下、古老与现代,描绘出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的文化长卷,通过营造在场感、展示情感联结、强化共同体意识呈现出地方性、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从而建构起观众的地方感。《文脉春秋》在采用虚拟数字技术与动态地图的基础上再现历史文脉,增进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用生动、真实的城市样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陈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