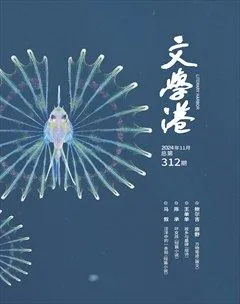岁岁
2024-12-04酸枣小孩
重阳节与庙会
今年的重阳节山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跑过去看。山会规模比往年小了许多。人也少了许多。在山上买了一根登山杖,和店主聊天,说之所以规模小是仓促之故——最初是取消了,临时又决定重新开放。还是喜欢往年山会人潮涌动的样子,虽然到处是人挤人,那才是常态的人间生活。人总是如此,失去了才知道珍贵。
沿着环山的健步道走,这次走得比上次远,一直走到临近南门的望岱亭处。望岱亭太高了,上了几个台阶,又退下来。留着以后再上吧。以后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不用去想它的时候。
午饭是在山上吃的。山会上有许多小吃摊,买两笼灌汤包,买一杯冰糖雪梨汤,买几只橘子,买几个芝麻烧饼。还买了一只特大个的烟台苹果,两个人吃不了,带了下山。
坐在树林中的长椅上吃午饭。午后的阳光温暖中隐含着渐趋的冷淡。树底下落满了五颜六色的树叶。没有风,落叶都很安静。
相较于“夏花之绚烂”,我更喜欢此时的“秋叶之静美”。
赏菊与饮茶
趵突泉公园里的菊展刚刚开始。和往年一样的绚烂夺目,无非也是新颜色替换了旧颜色,新花王取代了老花王。可是年年都有人来观看拍照,乐此不疲。于我来说,每年的逛山会看菊展,更多的是完成一种仪式。看了无非如此,不看又心生遗憾。不是有人说过,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
去年看菊展还是三个人一起,看完菊花,坐在茶社里喝茶,隔了窗看桥上如织的游人。今年此时,小哈正在学校里为了他的人生梦想努力。半个月才有的短暂相聚,也是埋首于夜以继日的课业中……想想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日渐剥离过程中完成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他将离你越来越远。
有一首歌中唱道:时间都去哪儿了?它带给你人生中诸多的欢乐,又将这些欢乐从你人生中逐一带走。
暮秋初冬
有人去红叶谷,站在万木凋零的空山里,手里擎着一枚捡来的红叶拍照。我行走于八条沟的山沟里,眼前所见与红叶谷景象相差无几。城市里还是晚秋,山中的冬季早已来临。连游客也是寥寥。只有几辆车停靠在山坳里,山里唯一的农家乐还在营业,只是老板也懒得招揽客人了,中午只接待了几个经常来此徒步登山的熟客。
沿着山沟往深处走,原来熟悉的风景有些变化。土路变成了水泥路,有新建的几座蓄水池。这是三年前那场山火之后的新变化。山火的痕迹早已经没有了。大自然是最擅长自我疗伤的。
山路旁边的涧里隐约有流水声,扒开乱石杂草,一丝细流蜿蜒而下。溯溪流而上,峰回路转,渐至幽境。走过一片树林中的石阶小路,便到了尽头。一座山崖挡住了去路。山崖的那边是什么?有好奇,却没有勇气爬上去。在山崖的下方,是溪流的源头,一处自然生发的山泉。
坐在树林中的石头上,听着耳畔哗哗的流水声。没有风,没有鸟鸣,仿佛置身一处空境。仿佛那细微的流水声也在千里之外。
中午时分,两个人坐在藕池水库边举办简易的冷餐会。一边吃,一边看水。水波不兴,有点像一面镜子。真的像一面镜子么?看着看着,又似乎不像。在水的远处,还可以看到山,山影淡淡的,罩着一圈隐隐约约的山岚。
坐在水边。就这么安静地坐在水边。也不需要太久。
立冬与失眠症
立冬以后,下了一场雨。雨不大,淅淅沥沥的,一夜也就过去了。
晚间出去散步,梧桐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地急急坠下,如大厦倾,地面上覆了厚厚一层。想起李易安的那句传世名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早起时看窗外,往常所见的梧桐树变了样子,使人陡然想起“岁月流转”这样的词来——时间是一个让人不敢细思的事物。
最近又犯了失眠症,听外面的雨声,听手机里的雨声,汇集成模模糊糊的意象,在半梦半醒之间穿梭交错。仿佛身处无数个平行宇宙。仿佛度过了许多个漫长世纪。
小雪
朋友圈到处下雪的小雪节,济南城里正下着一场雨。据说济南也下雪了,薄薄的一层,落在了城外的南山。
到了明天,晨起的人们裹紧了棉衣,许多个脚步踩在湿漉漉的落叶上,惶惶然地向着冬的深处走去了。
城市里的鸟鸣
在城市里看不到亲切的事物,除了麻雀。可是麻雀不会跳到你的窗台上来。它离你最近的时候是停落在窗外的电线上。像一枚琴谱上的休止符。一动不动。突然间它就消失了。
城市里也有其他鸟类。常见的除了麻雀,还有灰喜鹊。白肚皮,蓝灰色翅膀。公园里多,生活区也能偶尔看到。因为有树。有树的地方就能吸引鸟儿停驻。一天下午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中校园里几株大树上结着三四个硕大的鸟巢。冬天的树木光秃秃的,叶子掉光了,分不清是杨树还是柳树。线条分明的树枝衬托得这几个鸟巢非常惹人瞩目。有鸟鸣声,一两只灰喜鹊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
山上的鸟儿也多。有一次去爬华不注山,暮晚时分,倦鸟归林,天空中的灰喜鹊鸣叫着三三两两地飞过头顶。灰喜鹊的巢结在高高的树梢上。麻雀们则聚集在一座寺庙的山墙上,叽叽喳喳个不停。
城市里的麻雀比灰喜鹊数量多。大明湖公园的草地上,有几十只麻雀聚集一处在开会,它们蹦蹦跳跳,叽叽喳喳。热闹得很,让人想起“雀跃”“翔集”这样美好灵动的词语。
乡村里的麻雀数量也在慢慢恢复。偶尔回去,在村庄里、田野里,都能看到它们活跃的身影。然而,像小时候所见的空麦场上轰然而起,遮天蔽日一样的大规模麻雀群现象,再也见不到了。
诗和“远方”
有一天下午出去得早,三四点钟,站在东环桥上,眺望桥下的流水。冬日的太阳落山早,余辉斜照河面,波光粼粼,让人想起“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诗句。
绕河散步至桥下,看到桥洞里住着两个流浪汉。一坐一卧,神情淡然。河两岸有数孔桥洞,从春至冬,总是会成为流浪汉的首选之地。也有流浪汉会选择马路边和街心广场作为临时的住所。大多数的流浪汉会呆坐入定或席地而卧,偶尔也会看到喝啤酒看手机的流浪汉。
许多年前住在柳行头,经常会穿行海晏门市场,在那条街边常年住着一个上了年纪的流浪汉,他的住所固定在街边,搭着一个小小的简易窝棚。白天他坐在窝棚外面,晚上钻进去睡觉。很是逍遥自在。记得每次路过他的“家”时都要羡慕一番。
那天下午散步回来时,途经一处老式小区,在进入小区的路口,有一个老妇人趴在地上,用一条旧被子蒙头大恸。旁边四五个人在围观,有两个年轻的女人在低头抚慰那痛哭的老妇人。问旁边一家花店的女老板,说这老妇人的儿子得了重病,躺在医院里没钱治,她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大地上的事情
早起有新发现。先是看到地面是湿漉漉的,尔后看到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细细碎碎的小雪粒。没多久,小雪粒就变成了小雨滴,正契合了天气预报。
一只灰喜鹊从一幢高楼飞向一个树梢,稍作停留之后,又从树梢飞向另一幢高楼。小区里的行道树最近被伐去了许多,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可供它们憩息玩耍的地方少了。
大寒已过,立春将近。寒冷的日子正逐渐消减,城里只下过一次像样的小雪。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远离“雪”的意境了。像“小雪”“大雪”这样的节气,也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经历过“寒冬腊月”“漫天飞雪”这种“古代”气候的人们,常常会不由自主陷入绵长的回忆。
最近在读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他谈到一些自然中事物的消失,心有戚戚。在一定的前提下,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要面对共同的结局。逝者不必再担忧了,活着的已然觉醒的人们却忧心忡忡。
在我小的时候,一到了冬天,看见雪还是极容易的事情。小麻雀在雪地上走来走去,留下小小的爪印。野生的小兔子在雪地里时隐时现,像一只灰色的精灵。像这样美好的事物,即使是在乡村,现在也很难看到了。
冬日黄河
有一日去看黄河。天气是晴而冷的。黄河边依然有零散的游人。从大坝下去,就到了河边。有几个人围坐一起打牌玩,有几个人是渔夫装束,站在河里撒网捕鱼,也有执着一根兜网在河里走来走去网鱼的,另外一个人提着鱼桶跟着。他们在河水里越走越远,走了半天也没看见捕上鱼来。
撒网的人依然站在原地。河边有几只鱼桶。每只桶里都有鱼,大鱼,小鱼,它们被困于狭小的桶里,无奈地甩动着尾巴。
在捕鱼者的旁边,有一艘长年搁浅的大船,我们从坝上下来的时候,看到大船外侧悬挂着的木牌上写着:此处可放生。不知道鱼桶里的那几条鱼是从哪里游来的。
沿着黄河走,看着河水向前缓缓流淌,河道里小有落差的地方,水流会发出哗哗的响声。冬日的黄河水冷静,没有了往日的动感。一只白色水鸟孤独地飞过河面,向着大桥方向远去了。隔河遥望,能看见北岸鹊山的轮廓。
北有鹊山,南有华山,中间一条黄河滔滔不绝,千年万年,永无休止。想来这世上,除时间之外,最长久的莫过去山川河流了。小小的人类生存其间,是何等渺小而微不足道,却又是何等的傲慢无知。
老街
去大明湖散步,由东门入,出西南门,转到一条小巷子口。巷子是老巷子,抬头看见墙上的名牌:寿佛楼街。这片街区属于济南老城,却是第一次认真看到。
老城区还保留着一种浓郁的原始生活气息。狭长的胡同、窄小的木式街门、高挑的老式瓦脊,以及瓦脊上长着的几茎衰草。从敞开着的门洞望过去,便可窥见一幅杂乱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
沿寿佛楼街走一段,右转,入寿康楼街。街上除了有一座旧式的两层开放式居民楼外,还存有几处古迹:题壁堂、吕祖庙、寿康楼。题壁堂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原为道观,后为祠堂,又做戏楼。是山东省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戏院,被称为“江北第一楼”。只可惜现在已不闻梨园之声,空留一座孤寂衰朽的遗址。我们出大门的时候,有几个外地人进来,嘴里在议论着这是不是吕祖庙。
吕祖庙就在题壁堂西邻,几步之遥。也是一把铁锁谢了访客。再往西走,走到街尾,便是寿康楼遗址了。这座建于清代的中西合璧式建筑群,曾经是清末《山东官报》的社址,孙中山先生曾经在此拍照留影。
看了寿康楼,转身往回走的时候,从一座瓦房顶上走过来一条大型的长毛狗,它慢慢地走在房檐上,并不在意我们仰视的目光。它停驻在房山头,微微转了头,注视着远处,仿佛它是一个王。
在那样的高处,它确实是一个王者。俯视众生的王者。
那一天下午,我们在这一片老街区里转到了天黑。认识了许多街名:慈林院街、西公界街、将军庙街、水胡同、鞭指巷……然后这些过目的街名霎时又迷失于那一条条错综交叉的老街巷里。
海棠春睡
这是一处新小区。物业在路的两边都种了树,一边是桃树,一边是海棠树。
春天时散步从这里路过,桃树开着粉色的花朵,海棠树开着红色的花朵。夏天时散步从这里路过,桃树结着青色的小果,海棠树结着青色的小果。到了秋天,桃树结的果实早已不知去向,海棠树的果实变成了红彤彤的,有点山楂的样子。红彤彤的海棠果挂在树上,并没有人采摘。据说海棠果是可以吃的,生津解渴健脾胃。可以制成海棠果脯。
冬天到了,无人采摘的海棠果变成了褐色的干果。在一场又一场的朔风之后,这些风干的果实也消失不见了。
在海棠还开着红色花朵的时节,夜色里从它身边经过,脑海里总会跳出苏轼写给她的那首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年年春天,海棠树都会一身红妆,而我们的岁月呢,却是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杏花与油菜花
昨日下了一天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淋湿了不打雨伞不穿雨衣的豪放派。今日下了半天雪。纷纷扬扬,纷纷扬扬。路边早开的几株粉杏花,不幸被打落了许多在地上。
北方的杏花开得早,江南的油菜花开得早。一大片金黄灿烂开放在朋友圈。有人说因为去年闰月,所以今年的花期提前了。不知真假。
去公园里散步,大大小小的柳树上都挂满了嫩绿鹅黄的“绿丝绦”,在乍寒的春风里飘飘摇摇。
今年花胜去年红
春天总是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激动和希望。这个“莫名其妙”是用得恰当的。因为激动其实也真的只是生理上荷尔蒙的萌动;而希望,也只是人们口是心非的虚妄之词。
想想也是荒诞,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天里,有人忙着发动战争,有人忙着追名逐利,有人忙着勾心斗角,有人忙着谈情说爱,有人忙着八卦绯闻……而有的人,却拼命想尽一切办法,好让自己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更长久一些,为此他们愿意忍受任何痛苦。
有时候走在大街上,喜欢观望行色匆匆的路人,凭着他们的表情和外貌暗自揣测他们会有怎样的人生遭迹。
文章中说,生命是如此顽强。文章中又说,生命是如此脆弱。文章中还说,生命如草芥,如鲜花。草生草灭,花开花落。一切自有定规。
又是一年春好处。似乎是看不尽的花开花落。昨日游走于春雨中,有人做诗:雨打樱花落。
欧阳修说:今年花胜去年红。
至于明年花开得是不是更好,要等到明年才知道。
有人讨厌春天,大约是因为有隐疾,或者是“伤春”故。我是常常凸生“虚妄”之感,借了伤春故,可能更盛一些。生性冷淡的人,是不是都会产生逃离之心?觉得这市井之声太过喧嚣,身外的一切都显得杂乱不堪,令人不堪重负。正如“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人的出生地对心灵的影响根深蒂固,无论如何,都觉得小时候的家园是最好的。不敢称“极乐”(那是上西天了),乐土是不虚的。
今天看到一个词:耕读第。不由心生向往。自给自足,自得其乐,自由自在。人生若能得此境界,也是圆满了。可是,谁能允许时光倒退。
昨夜看《疯狂动物城》,今日看《爱丽丝漫游奇境》。我还是喜欢童话般的奇幻世界,虽然并不是真的“一切皆有可能”。疯帽子说:谁又分得清梦想和现实呢?
镜子永远只照得见自己的内心。
我愿意永远生活在“梦想”之中,虽然它到头来或许会(真的)支离破碎。又有什么关系呢。
逝者如斯
仲春的尾声。最近几日常在下午五时左右在清河边散步。空气里有特殊的紫丁香花的香气。海棠花差不多要开败了。有一天拍到一段微风吹拂的视频,白色海棠花轻轻摇曳,那是一种动人心魄的微妙。
有一段岸边坡地上种着几株矮小的樱花,开着粉色花。但见樱花开,令人思往事。今年不能去五龙潭看樱花了。想象着那几株高大的樱花树下纷纷扬扬花瓣飘落的情景。
到处能见到紫荆花,光秃秃的树干上密密麻麻开满了深紫色的小花朵,连根部也不放过。是我不喜欢的风格。柳叶的颜色已经由浅入深,很快就会变得不那么稚嫩可爱了,柳絮早已长老,挂在枝条上。
站在岸边看水,一层一层的波纹缓缓向前推进,夕阳的余光打在波峰上,一轮一轮的光圈晃晃荡荡,断断续续,看得久了,你会觉得置身船上,一种轻微的晕眩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河边呆久了,你会和几千年前的老夫子产生同样的感慨。
自然里的水真是个奇妙的事物,它构成了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可以滋养生命,也可以毁灭生命。它是单纯的,又是复杂的。它是短暂的,又是恒久的。它从亿万万年流淌而来,又流向亿万万年而去。可是被它呵护滋养的生命呢?又能在世上生活多久?几年,几十年,几百年,终究都会被它带走。
小楼一夜听春雨
小楼一夜听春雨。
梦里听了一夜雨声,清晨醒来脑海里便跳出这句诗。
不是小楼,是旧楼。春雨声势也颇大,借了风势,叮叮咚咚、砰砰噔噔敲打着窗棂。
昨日下午有约至芙蓉街。天色灰蒙蒙的压抑,有“山雨欲来”的况味。行至途中,果然噼里啪啦的急雨倾泻而下。
有会做生意的中年妇人,抱了一堆透明的简易白雨伞,守了公交车车门,一把把地卖将出去。
挂了雨幕的街上便多了许多透明的白雨伞了。
芙蓉街是老街道,下水道系统也是老旧的,青石板路面上污水横流,一股股的臭气熏人。使得略有洁癖的小哈起了厌憎之心,从前他是很喜欢芙蓉街的。
雨后夜游。穿过曲水亭街,至百花洲,又至大明湖。
大明湖上夜灯璀璨,湖面上垂柳摇荡,夜风鼓动着湖水发出轻微的哗哗声。
大明湖没有夜航船。这是颇为遗憾的。
廊亭下三三两两的游人散淡坐着。我也想坐下去,清清静静的,坐到更深夜静时分。
前日刚刚过了“谷雨”,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小时候学农谚,会背“谷雨前后,种瓜种豆”。乡下种地的人家也该“种瓜种豆”了。从前在我们家,这些都是父亲的工作,如今父亲老了,诸事都不放在心上了。
想起来前几日在阳台种下的一些荆芥种子,今日早起去看,蓦然发现泥土里拱出来零零落落的绿色芽苞。婆婆前些时打来电话说她的荆芥早发芽了,南方温度高,适宜种子萌芽。荆芥种子是她从老家带到常州的,我春节时去,她又转赠我一些带回济南。无论如何,今年夏天吃黄瓜丝凉面时终于可以有荆芥来辅助提味了。
去年曾经跑到张夏看杏花。满山的杏花开,只是缺了细雨。如今有细雨打窗,却又看不到杏花。
杏花也落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