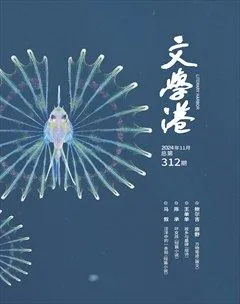红
2024-12-04虞燕
雨下得突然,试探着落下几滴,紧接着密集砸下,雨点连在一起,如一张大网挂于天地间。街上的人急慌慌奔进路边的莹莹家,到檐下便安定了,哗哗雨声中,躲雨者拉起了家常,你一句我一句,恣意谈笑。她就出现在这个时候,趿着拖鞋,深一脚浅一脚,怕踩到蚂蚁似的,慢得让人着急,终于笨拙地挪至檐下,却悄悄退到墙边。湿透的红裙子皱巴巴的,紧贴她矮胖的身子,像一块烂布头裹着圆桶,她的头发和裙子不住往下滴水,不一会,地上就多了一摊水,从我这个方向看去,仿佛,她陷在一个很深的阴影里。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她。
之后,隔三岔五听到人们议论她,说白长了那么大的脑袋,里头全是浆糊,身体也不正常,估计一直没发育,某个那日躲雨的人力证,对对,以前没注意,被雨浇透就明显了,胸部还是平的。不知谁给她取了个外号——大头梅童,是海里常见的一种鱼,憨乎乎的,恰似大头娃娃。闲着也是闲着,大家的舌头随意一伸一翻,每一粒喷溅的唾沫星子都为她出了力。不过,那些闲话似乎对她毫无影响,或者说,她的世界自动屏蔽了其他信息,自始至终,她都慢慢悠悠过着自己的日子,走路如踩棉花,缓而软,爱轻晃大脑袋,旁人看着吃力,她才不管,左一晃,右一晃,大模大样地晃。眼神却定定的,她的眼睛大且略凸,眼珠子呈褐色,上面总像蒙了一层东西,看什么都是淡的散的,以为在看你,也可能在看他,又好像谁都没看。两片厚嘴唇安安分分地叠着,大多不主动搭腔,若有人问她话,回答也短促,从唇间挤出来的每个字都又沉又干脆,如一块块石头落下,绝不拖泥带水。
有那么一回,几个女人碰一起,一人随口提及了她,这下好了,个个成了热心人,愁她的长相,愁她的智力,愁她以后嫁不出去,大概过于投入,竟没发现她已出现在旁,悄无声息地。而她神色如常,忽略掉那些僵住的脸和舌头,眼神越过眼前的一切,不知飘向了哪里。女人们自然聊不下去了,抬起屁股赧赧散去。
她名字里带个“红”,莹莹、大芬她们叫她阿红。阿红爱穿红色,她觉得红色是世上最好看的颜色,红裙子、红衬衫、红毛衣、红外套,连袖套和袜子都选红色,家里人透露,非红色的她好说歹说都不穿,要闹脾气,把衣服扔一边。有段时间,穿红衣裳的阿红经常从教导队那条路出来,远远地,一抹红色磨磨蹭蹭晃过来,我们便知道是她。她已习惯了往这个方向,习惯到莹莹家及附近,也习惯了跟所有聚于莹莹家玩闹的人相处,包括我。那次,她挺高兴,厚嘴唇难得持续开开合合,一次性迸出了一连串字词,虽然有些语无伦次。大意为,她以前一直在王家道地,不晓得这边好玩,不然早就认识我们了,话毕,累着了似的喘口气,而后,脑袋大幅度一摆,后脑勺翘起的一簇短发随之跃动,像只振翅欲飞的燕子。
阿红比我大几岁,与她同龄的其他女孩,我都称姐姐,唯独对着她,我实在叫不出来。我跟着莹莹她们叫她阿红,或者,以“哎”“喂”代替,她都认真应着。我刚认识阿红那会,她已上完了初中,大家心知肚明,一个笨笨的人,上学不过是混混日子,成绩可想而知,但阿红爱上学,她说学校里人多,热闹,比家里好。
曾听父母亲聊起她的家人,哥哥长得帅气,母亲年轻时算得上村里数一数二的美人,怎么到她这竟成这样了?长得一言难尽也罢了,还木头木脑,未来堪忧啊。人们怀疑阿红母亲对女儿不上心,理由是,阿红永远留“游泳头”(接近于男式短发),头发浓密、粗硬,乱蓬蓬的,一看就没好好打理,显得头更大;还有,衣服质量不咋地,要么起球要么有皱痕要么不大合身。倒是其母亲,打扮得时髦又体面。对此,莹莹妈不以为然,说阿红这样的,再精心拾掇又能如何?这些背地里的闲话,不过如屋外吹过的轻风,除了其时拂动过几片叶子,过后了无痕迹,说话者没有放在心上,更不会对阿红的境遇有丝毫改变。
幸好,阿红不懂这些,思维简单让活着也变得简单,简单可能更容易获得快乐。阿红只要有红衣裳穿,有零食吃,有人陪,她便晃起大脑袋,迈着粗短的腿,把自个儿挪过来挪过去,表情一贯略为僵呆,却是松弛的,无邪的,阳光洒下来,照得她的脸红红的,亮亮的。她若喜欢谁,会一点一点靠近人家,厚嘴唇轻抿,嘴角微翘,冷不防把零食塞到对方手里,劲还挺大。我也收到过阿红的糖果,惊讶到不知该怎么办,拿着,抑或还给她?之前母亲提醒过,阿红终归跟我们不大一样,与她在一起要注意,切忌和她争,尤其吃食,让着她点儿,她主动给的也不能要,随时会反悔,她还是个小孩子。曾有人好事,逗阿红,拿走其吃了一半的大饼,此举彻底惹恼了阿红,她瞬间涨红了脸,嘴唇哆嗦着,上身前倾,不停地狠狠地跺脚,似要把石板给跺碎了,怎么也哄不好……想及此,捏着糖果的我有点发怵,偷偷观察阿红,她稍稍扬起下巴,褐色的眸子正郑重朝向我,同时,摊开手掌,示意我看其手上那颗糖果,跟我的一模一样。我剥开糖纸,硬糖入口,是荔枝味的,很甜。隐隐的笑意从阿红嘴角漾开,随即,她缓缓转过身,给我一个矮墩墩的背影,她大约想表现得轻快点,无奈短腿和圆润的身子不配合,走起路来一颠一颠,有点儿滑稽。
好些时候,我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阿红。她喜欢扎进人堆,但不闹腾,甚至不大出声,我们做什么,她便做什么,像一个乖巧的小孩努力跟紧大人。我们玩折纸,折元宝、灯笼、船等,她也拿着纸煞有介事地折来折去,大多成了四不像,最后,我们的成品放在一起评比,她的被晾在一旁,可仿佛并不影响她的兴致,下一次,她照样热情地折出各种怪形状;我们抛沙包抓麻将牌,一个一个轮着来,起初,也让阿红参与,只是,她那肉乎乎的手实在不争气,沙包抛不高牌抓不牢不说,往往沙包已掉在桌上,她的短手指还未碰到牌,于是,只能站边上看我们玩,她颇有耐心,总是从头看到尾;去一号码头看露天电影,拎竹椅,提马扎,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发,阿红在队伍里有些显眼,身体随着大脑袋左右摆动,两腿像被什么粘住了,迈得挺吃力。到达目的地,看电影的人黑压压一大片,大家忙着抢好位置,顾不上阿红,她倒淡定,干脆往最前面的地上一坐,抬起大脑袋,看得有滋有味。电影散场时,天已黑如锅底,我们意犹未尽,边兴奋地聊电影边往家赶,走了近一半的路,才想起了阿红,遂回头找。即便是夜里,我也一眼认出了那个缓慢移动的身影,见着我们,她激动地发出“啊呀啊呀”,声音沙沙的钝钝的,手臂慌忙前伸,身体随之勉力靠过来,差点摔了跟头。我们有些内疚,半天没吭声,阿红自顾自连说了几次“电影真好看”,仅此一句,她想不出更漂亮更复杂的来表达。
阿红是真的爱看电影电视,这是我之后发现的。看电影机会少,看电视容易实现,场地一般选莹莹家或者我家,阿红家也有电视,但她总是巴巴地过来和我们挤一起。有一年暑假,播放一部武侠剧,每天时间一到,我们就围在电视机前,阿红更是积极,每次都像模像样地坐在小杌子上,左手托住脸,入定了一般。其他人觉得其样子可笑,时不时唤她,甚至轻轻推她,她从不回头,只扭动下身子做个回应,然后,继续保持原来的姿势。两集播完,我们埋怨这么快就完了,关了电视,很快散去,唯阿红还在原地,大脑袋耷一边,眼睛仍瞅着电视,叫她出来,她不动,喃喃自语,明天还有吧明天还有吧?
那日,我们几个聊女孩间的事儿,阿红插不上嘴,倚在桌边,似听非听,一会剥剥指甲,一会挖挖鼻孔。突然,我的耳朵捕捉到了一个声音,低低的,闷闷的,不大连贯,但听得出来是一段旋律,且感觉熟悉,我立马想起,不就那部武侠剧的主题曲嘛。这是阿红无意间哼出来的,她正勾着头,眼皮微垂,一缕头发黏在大脑门上。莫名有点可爱。
阿红知道,假期结束,我们就要上学了,便神情恹恹,厚嘴唇紧闭,闷头绕着桌子走,而一听每周都有礼拜天,还可以一起玩,她顿时咧开了嘴,露出宽宽的门牙。果真,每到礼拜天,阿红就会过来。莹莹妈说阿红,平日看着呆笨,我看记性一点都不差,蛮可怜的,跟她差不多大的,人家嫌她,只能勉强跟你们这帮小东西混一起。
我已经习惯每周见到阿红,那个红色的身影总会悠悠然拐进小道,奔我们而来。其实她来与不来,对我们的计划不会有任何影响,我们学习,她不会扰乱,我们玩耍,她未能增光添彩,亦不至于拖后腿,她从不提要求,只默默跟随。这样的阿红挺省心的,这样的日子像屋旁静静流淌的小河,舒缓、简淡,让人安心。
那个礼拜天发生的事,如同有人往小河里扔了块大石头,“噗通”,水花飞溅,打破了一向的平静。那户人家在莹莹家前一进,一口咬定阿红偷了钱,从她家写字台抽屉里。我和莹莹当场懵怔,阿红确实跟在我们后头进过里间,那家女儿带的路,可阿红哪是这么眼疾手快的人啊,我不相信。她家如此肯定的依据是,阿红靠过写字台。女孩的母亲在院子里逼问阿红,阿红晃动着大脑袋,厚嘴唇嗫嚅着,终于吐出“没有偷”三个字,她一脸茫然,眼神不知该落在何处。那个女人不依不饶,声音尖利,说还敢抵赖,你个傻子怎么怎么,边一把拽过阿红,搜她的身。阿红吓得浑身颤抖,拼命跺脚,嘴里发出含糊的嘶吼,像某种动物惊恐的叫声。嘈杂声惊动了周边,阿红的母亲也得到了消息,跑来与那个女人对骂了一通。
阿红几乎是被她母亲拖着走的,鞋底与路面的摩擦声刺耳得令人心惊,她的脖子缩起,像圆卜隆冬的身子上直接安了个大脑袋,风吹起她红衣一角,顷刻,消失在拐角处。
此后,阿红过来得少了,直至,再未露面,不知是家人阻拦,还是她自己不想。阿红是否知晓自己的冤枉已经洗清?抽屉里的钱实为女人的儿子所偷。我没有找到机会问她。
我的身体内恍若有什么窜动着,东鼓一下,西抻一下,长大简直是一瞬间的事。我的世界越来越大了,要装下太多太多的东西,再无暇关注阿红,甚而,逐渐淡忘了她。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了阿红,她好像更矮了,穿着旧旧的红衣裳,短发依然乱蓬蓬的,犹如一个被丢弃的布娃娃。我朝她挥手,她歪着大脑袋看向我,眼神定定的,迟疑地迈出一小步,停顿了几秒,又默默收了回去。我唤她名字,她依然木楞楞,脸上涂抹了胶水般,五官紧绷,看不出神色变化。我有些失落,阿红多半不记得我了。
母亲安慰道,阿红挺长时间没见我,而我又长得快,变化大,估计一时没认出来。是啊,我和莹莹她们都长大了,跟阿红同龄的那批姐姐更是如花盛放,一个个亭亭玉立,鲜亮如霞,享受着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她们聪慧、自由、博识,被宠爱被倾慕被呵护,只有阿红,老天不知对她施了什么魔法,被禁锢在时间的牢笼里,成为人们眼中例外的怪异的那一个。我突然很难过,为阿红,我找了个借口来稀释这种难过,阿红的心智和肉身已然被封存,或许,她不会老吧,起码比其他人不易老,也挺好。
我在成人世界里摸爬滚打,屡屡受伤的时候,偶尔会想起阿红,想起她那个只有吃和玩的世界,想起她所拥有的简单的快乐。我当然不能说那是一种幸运,只是有一刹那的异想天开,如果可以,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能不能借阿红的世界躲一下。
被无视了多年的阿红,再次引起集体关注全民热议,缘于一次信口而出的说亲。我们村有个男的,父亲早逝,母亲聋哑,可谓家徒四壁,一直娶不上老婆,无论长相丑陋的,还是略有残疾的,均不愿嫁入他家。家族里的一位老人想到了阿红,试图去她家说亲,却被男的一口回绝。这事不知怎的,被迅速传了开去,有人说男的一根筋,阿红好歹家境还不错,而更多的人,把关注点落在了阿红身上,说,看看,连他都不要她,一秒都没考虑,这是有多看不上眼!也是,万一阿红生个孩子也跟她一样,不就惨了,哦,她可能连孩子都生不来,她爹妈也是命苦,摊上这么个女儿,没人要,只能做养老囡喽,她家以后的日子只怕是难了……如此种种,甚嚣尘上。
阿红的名字及父母的名字被人们的舌头搅拌,在空气里翻滚,反反复复,同情者有之,忧虑者有之,看好戏者亦有之,但阿红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据说,阿红“最红”的那几天,她都在海滩上捡鹅卵石。
后来,阿红全家搬离了小岛,住进了市里的房子,没过多久,我也在另一个城市安家落户。
时间挟裹着庸碌忙乱的日常滚滚而去,若干记忆碎片从它的缝隙间渐渐漏落,我的生活重心几度转移、置换,日复一日,兜兜转转,精力终究都付于经营人生与家庭了。当母亲在电话那头提起阿红,我有些懵憕,这个名字带着某种奇异的气息,从遥远的时光深处飘来,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母亲并非特意来告知,她把阿红的事放在讲完正事之后——阿红被车撞了,情况不大好,马上接下去说,市里跟岛上可不一样,车辆那么多,她这么个木木的慢慢腾腾的人,在街上乱晃,难免出事。我半晌说不出话,心里沉沉的,挂电话前,念叨了数遍,她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
那晚,我梦见了一个穿红衣裳的女孩,晃着大脑袋,以蜗牛般的奇慢速度行进,她始终背对着我,一点一点向前挪动。那条路窄而长,以为她要走很久,一眨眼,路上却没了人,半空中,一抹红影掠过,如芳红飘飞,倏忽不见。我猛然惊醒,月光正从窗帘一角潲进来,凉如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