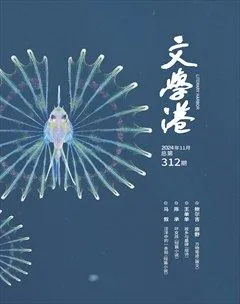访谈:真正的诗人是一种宿命
2024-12-04
朱夏楠:王老师好。你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和诗歌结缘的?
王单单:应该是二十年前了,青春期的心灵密语促使我孤独地爬上诗歌的天梯,我在那里徘徊许久,最终被无形之手拖进诗歌的大殿,接受一个个语词的拣选与认领。我总是近乎偏执地认为,真正的诗人是一种宿命,从他呱呱坠地开始,生命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在为“诗”作准备,而“写下”,只是诗在语言中现形。
朱夏楠:很多人都遭遇了青春期的迷茫与挣扎,不断地找寻着出路。虽然是无形之手使然,但想必也是个人的主动选择吧?你是如何做出这个选择的呢?
王单单:毕业之后,我飘荡了一年,一无所获。迫不得已,只能回老家参加特岗教师招聘考编。那是2006年秋天,我只身来到镇雄西部一所偏僻颓败的乡村中学教书,在那里我举目无亲,第一次陷入沉重的孤独与失落,加之乡村生活的单调,这一切将我逼向漫无边际的阅读中。还是诗歌,它让我的阅读逐渐有了朝向,像离岸久远的孤岛,成为迷雾漫漫的大海上最先向我伸过来的半截归途。相较于学生时代的浅尝辄止,在这个乡村,我开始痴迷于诗歌的阅读与写作,甚至到了无药可救的程度,似乎在里面触摸到了另一个我,他埋得很深,但已经被我死死攥住,我要将他从无尽的深渊中拽出来,我要和他滴血认亲,使其归位于我的心灵。
朱夏楠: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王单单:算了一下,我大约写了九年才正式在刊物上发表诗歌,虽然长期默默无闻,但一直乐在其中,我尤其珍视这段时光,阅读与写作带来的愉悦是如此纯粹。我第一次正式发表诗歌,是在2012年《诗刊》第5期下半月“诗歌新元素”栏目,天才少年诗人王芗远是本期头条诗人,无比遗憾,他已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在这里怀念他。蓝野老师是我的责任编辑,几年后我去《诗刊》见习,和他在一个办公室待了两年,缘分真是奇妙无穷!更有意思的是,这组稿子原本是当时《人民文学》编辑朱零老师约去的,他在博客上读到我的诗歌,便向我约稿,百感交集啊,我一次性给了他三十多首。但刊物版面有限,发不了这么多,于是他分了一半给蓝野老师,遂成我的“首次正式发表”。感谢这些师友,感谢写作道路上所有给予我温暖的人!
朱夏楠:可以简单说下你的成长环境吗?这个环境对你日后的创作,有什么鲜明的影响吗?
王单单:十多年前,我写过一首题为《滇黔边村》的诗歌,从中可以了解到我的成长环境,选段录于此:
滇黔交界处,村落紧挨
泡桐掩映中,桃花三两树
据载古有县官,至此议地
后人遂以此为名,曰:官抵坎
祖父恐被壮丁,出川走黔
终日惶惶,东躲西藏
携妻带子,落户云南
露宿大路丫口,寄居庙坪老街
尘埃落定于斯,传宗接代
香火有五,我父排三
邻舍出资,我父出力
背土筑墙,割草盖房
两省互邻,鸡犬相闻
有玉米、麦子、土豆、高粱烟叶等
跨界种植,一日劳作汗滴两省
余幼时顽劣,于滇黔中间小道上
一尿经云贵,往来四五趟
有时砍倒云南的树,又在
贵州的房顶上生根发芽
……
90年代后期,官抵坎
有女嫁人,有儿远行
剩下老弱病残留守空村
阔别十六年,梦回官抵坎
曾经滇黔交界上的小道
我从云南找到贵州
又从贵州找到云南
都找不到我少时留下的尿斑
我总觉得,每一个身陷困厄,在生活中挣扎的身影,都来自我们村,都是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写作无法回避那一张张欲哭无泪的脸,那一个个惊惶未定的眼神,那一条条窘迫不安而又卑微如尘的生命……
朱夏楠:有没有参加哪些诗歌社团?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王单单:我没有主动加入什么诗歌社团,影响更无从谈起。历史上诗歌“兴观群怨”中的“群”,从没像自媒体时代这么兴旺发达,有时朋友邀约进群,我也只是“端坐其中,沉默不语”。
朱夏楠:对你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诗人有哪些?
王单单:这个问题曾被多次问起,以往我会列出诸如杜甫、布罗茨基等古今中外的大诗人,以此虚立“诗设”,侧证我的诗歌“来处”,后来一想,此举何其浅薄。一个成熟的诗人,其诗歌观念和美学养成错综复杂,绝非单一通道所能抵达。平日里我阅读大量诗人的作品,从中获得抒情的慰藉或叙述的启示,这些诗人影响了我,与此同时,同样的慰藉与启示也会发生在别的诗人身上。于我而言,这种“影响”是浅层次的,真正能将我的写作与众多诗人区别开来的,必然是生命之初最早注入身体的爱与悲悯,是我在这人世间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避开的奔波与劳顿,是平凡人生里那些肉眼可见的挣扎与人性深处的光辉,是那些被命运之手反复捏造与戏弄的无名之辈。“我”才是对我诗歌影响最大的诗人。
朱夏楠:你迄今为止最为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可以大概做个介绍吗?
王单单:惭愧,我至今尚无最满意的作品集。第一部诗集《山冈诗稿》收集了早期作品,虽有沉郁粗粝之风,但也不乏稚幼之作;第二部诗集《春山空》,在写作技法和艺术风格上做过一些探索和拓展,但这种尝试并非全是成功的;第三部诗集《花鹿坪手记》是对自我写作能力和表达技巧的一次颠覆和挑战,我希望跳出情感与情绪的推动,在现代诗中回到“指物作诗”的传统,更多追求一种精神速写,如此一来,也有部分作品难免失之于单薄。等我老了,封笔之前我想出一本自选集,那应该才会接近我最满意的作品。
朱夏楠:诗歌在你生活中占据了怎样的地位?
王单单:忽然想起故乡那些年迈的农夫,无论房屋多么凋敝、简陋,他们都会在里面找出一个隐秘的地方,有可能是床铺或枕头下、柜子里、墙缝间、梁木上、瓦楞下,用于存放身份证、地契、贷款凭据、泛黄的信件、旧照、孩子们的出生证、亡父的半寸照等,这些在外人看来无用的东西,对他们却是无比珍贵,是绝对不能丢失的,他们活得卑微、毫不起眼,唯有这些物件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是生命的另一种赋形。我的诗就像农夫们潦草人生里那“隐秘的地方”,我在里面珍藏着各种各样的“我”,他们被时间击败了,退出命运和生活的前线,去那里疗养、复原,成为个人史的一部分,等待更多共情的人到来,一起复述从前的故事,重温心灵震颤的瞬间。
朱夏楠:对自己的创作,你有怎样的期许?
王单单:没有期许。就让我在诗里一条道走到黑吧,走到月落乌啼,走到星垂大荒,走到天边光芒乍现,走到四周孤峰突起,走到走投无路,走到绝处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