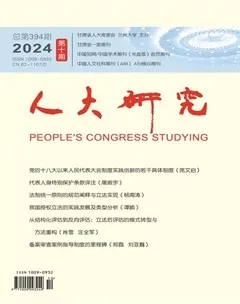宪法宣誓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当代法治教育价值
2024-11-21韩畅
内容摘要:宪法宣誓制度是宪法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历时性特点影响着公众对宪法宣誓制度的认知。狭义的宪法宣誓制度起源于英国,形成了“国王优于法律”的英国模式,并演化出“宪法法律至上”的美国模式和“广泛宣誓主体”的法国模式,这三种模式深刻影响着18至19世纪各国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宪法宣誓雏形初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逐渐制度化,但始终浮于表面,草草了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誓词深受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誓词的启迪和影响,至1982年宪法颁布后,理论界和实务界纷纷开始了“就职宣誓”和“宪法宣誓”的探索。2015年《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出台,我国宪法宣誓制度正式建立,并在2018年修宪时写入宪法,宪法宣誓制度作为一项正式的宪法制度规定于当代中国的宪法制度体系中。
关键词:宪法宣誓制度;历史变迁;法治教育;宪法教育
一、宪法宣誓制度的历史起源及域外主要模式
宣誓起源于古代社会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拜,在古埃及、古希腊时期都有体现宗教和政治色彩的制度性宣誓,中世纪以后,这种来自古典时期的宣誓传统以效忠宣誓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封建领主的主从关系之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宣誓制度受到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在各国法律体系中得以迈入规范化的轨道,表现为国家公职人员就职宣誓、公民宣誓、证人宣誓等不同类型[1]。就职宣誓往往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得以体现,而公民宣誓和证人宣誓较少规定在一国宪法中①。之后,就职宣誓逐渐演变为广义上理解的宪法宣誓制度,即无论宪法、法律是否明文规定宪法宣誓制度,只要国家公职人员举行宣誓效忠于宪法和法律的就职仪式,就属于宪法宣誓。而狭义的宪法宣誓制度是指在一国的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宪法宣誓制度的规程和行动准则,法定宣誓者依据宪法规范,在与之对应的要求下向国家、宪法、法律、国民等宣誓效忠,竭力履行法定职责的一种承诺仪式[2]。广义上的宪法宣誓制度意涵宽泛,所有政治性宣誓均属此列,本文着眼于狭义的宪法宣誓制度展开研究。
(一)英国模式:宪法宣誓制度的滥觞
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是宪法宣誓制度的开端。《自由大宪章》第六十三条首次将宪法宣誓制度通过宪法性文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确定1,规定了“国王”“伯爵”两类主体的宣誓要求,即“国家元首”“国家公职人员”两类宣誓主体构成要素,拉开了宪法宣誓制度秩序化的帷幕。英国的宪法宣誓制度有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分别是1215年《自由大宪章》、1534年《至尊法案》和1689年《权利法案》的颁布,历经这三个历史时期后基本确立了英国“王在法下”的宪法宣誓制度,即“法律优先于国王”的英国模式。
首先,《自由大宪章》中,英王作为公权力的代表,以宣誓的方式表示将忠诚善意地遵守各条款对国王权力的限制,基本确立了王权有限和个人自由的精神。接着,《至尊法案》的颁布,强化了国王权力的唯一性和最高性,君主限制、掠夺臣民权利的行为试图通过法律正当化,此时的宪法宣誓制度与《自由大宪章》的基本精神已经背道而驰了。最后,《权利法案》以及与之配套的《加冕宣誓法》《王位继承法》将英国的宪法宣誓制度予以固定,即在君主立宪制度下以法律优先于国王为核心的英国模式。《权利法案》《加冕宣誓法》对君主宣誓的程序和誓词作了详细规定2,《王位继承法》进一步明确了英国君主宣誓制度的稳定传承3,英国宪法宣誓制度中的宗教因素、民众责任的强制性不断淡化,彰显了更多“国家独立”“民族国家”的理念,在保留宗教传统的同时凸显民族国家时期对民众义务责任的明确,以及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二)美国模式:宪法法律至上
诞生于英国的宪法宣誓制度经过一系列变化最终成型。作为美国前身的北美殖民地,其宪法及其宣誓制度,也在部分来自英国的法律传统和部分源自本土的社会建构需求的双重影响下,逐渐走出全新的路径。由此,宪法宣誓制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被正式纳入成文宪法体系中。
美国的宪法宣誓制度起初受到英国殖民地的影响,后来在逐渐摆脱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结合本土社会需求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制度路径。美国宪法宣誓制度的确立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分别是1620年《“五月花”号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以下简称《美国宪法》)的颁布[3]。
殖民地时期,英国的部分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只来到了北美大陆,在“五月花”号上,他们就抵达美洲后可能面临的法律、组织、宗教等问题通过契约的形式进行初步的安排,订立了《公约》。《公约》中的宣誓内容大致分为宗教性宣誓和政治性宣誓,即前部分的“以上帝的名义”和后部分的“共同在上帝面前立誓签约”4。这种政治性宣誓抽离了英国宪法宣誓制度中隐含的妥协与服从因素,而呈现出一种各方地位平等的态度,在基础理念上的差异也决定了今后《美国宪法》确立的宪法宣誓制度将与英国模式渐行渐远。殖民地的自治模式招致了英国本土的不满,之后殖民地建设过程中,他们同步发展出了宣誓效忠英王的誓词版本,但同时也在探索政治领域的自治制度,期间不断有殖民地反抗英国模式的宣誓制度,君主符号在北美殖民地逐渐被剔除。至1776年《独立宣言》通过,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明确了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思想,美国宪法宣誓制度与英国模式的不同特质凸显。在经历了“州和联邦分权对抗的背景下官员如何进行宣誓”“宣誓誓词是否涉及宗教内容”两个主要问题的激烈论战后,美国宪法宣誓制度得以统一,《美国宪法》在第二条和第六条规定了宪法宣誓的内容1。美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构建,明确宣誓主体的拥护对象是宪法,意味着美国在“宗教”因素上对传统宣誓制度的清洗,改变了世界对宣誓模式的常规认识,标志着宪法宣誓制度美国模式的诞生。
(三)法国模式:广泛的宣誓主体
紧随美国独立而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整个欧洲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宪法宣誓制度以一种适应法国社会的形式被纳入宪法制度中。
法国动荡的革命历程深刻影响着法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法国宪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不断制定和废止之间往复。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法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历经多次更替,以政体的类别划分宣誓制度,主要有君主立宪时期的宣誓、法兰西共和国时期的宣誓与法兰西帝国时期的宣誓[4]。其中,法兰西共和国、法兰西帝国两个时期的宪法宣誓模式分别与美国模式、英国模式类似,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最终确立的宪法宣誓模式基本以美国模式为基准。但是,在君主立宪时期制定的1791年法国宪法则非常特殊,开创了有广泛宣誓主体的“法国模式”。
1791年《法国宪法》第二篇第五条2、第三篇第一章第五节第四条3、第三篇第二章第一节第四和五条4、第三篇第二章第二节第十二和十四条5、第七篇第七条6分别规定了法国公民的宣誓要求、立法议会代表的宣誓要求、国王的宣誓要求、摄政者的宣誓要求、修宪会议成员的宣誓要求等。法国这一制度设计下的广泛的宪法宣誓主体可以概括为主权者的人民与掌权者的公职人员的双重宣誓模式,其中的“法国公民的资格获取”要求第一次宣誓成为“积极公民”,而“积极公民”身份是担任国家公职的必要条件,宪法宣誓制度对掌权者的限制实际上由“公民资格宣誓+就职宣誓”的双重结构组成。尽管这种宪法宣誓制度最终未被法兰西共和国沿用,但是该“法国模式”依旧在临近地区得到了延续。
二、域外宪法宣誓制度的继受发展及旧中国的尝试
17世纪至18世纪英美法三国分别确立的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法国模式三种宪法宣誓制度模式,深刻影响着同一时期及后一时期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宪法宣誓制度。而随着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的立宪潮,宪法宣誓制度也开始出现在亚非地区等地,同时西方的一些思想理念也传入旧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初步尝试宪法宣誓制度的契机。
(一)英美法宪法宣誓制度的继受发展
英国模式是在君主立宪制度的影响下,以“法律优先于国王”为基本原则,将宣誓制度与国王加冕相融合。美国模式首先明确宪法的至高地位,以宪法制约公权力的行使,抽离了宗教因素,强制要求掌权者就职宣誓。法国模式以广泛的宪法宣誓主体为特点,实现了对公民与公职人员的全覆盖。
1.英国模式的发展
英国模式恰能适配资产阶级革命背景下专制君主制国家法律制度转型的需求,在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前中期深刻影响着欧洲国家、英属殖民地等地区[5]。
首先是欧洲大陆国家,欧洲18世纪晚期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冲击着传统君主专制制度,多数欧洲君主制国家接受立宪,这些君主立宪国沿用英国宪法宣誓制度模式,并以成文宪法的方式固定英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如1814年《挪威王国宪法》、1830年《比利时宪法》、1848年《普鲁士宪法》等。其次,英国模式的宪法宣誓制度被植入到英属殖民地,加拿大、新西兰等殖民地直接通过宪法将英国模式确定为本地宣誓模式,如1867年《加拿大宪法》;也有部分英属殖民地本土居民排斥这一制度,宣誓仅及于殖民地少数统治阶级。最后,随着英国的衰落及对殖民地控制的削弱,英国模式的发展陷入低谷,君主立宪国逐渐减少,民主政权影响日益加深,英国模式不再占据主流地位。
2.美国模式的发展
美国模式在19世纪中后期深刻影响着美洲、欧亚大陆、非洲等地区,美国模式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英国的道路,以成文宪法限制权力的行使者,对欧洲、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有着深远影响,并成为英国模式衰落后的主流参考模式[6]。
首先,拉美殖民地独立运动助推了美国模式的传播,独立后的拉美国家整体上效仿美国的宪法宣誓制度模式,仅仅在细节上作了本土化的调整。如1829年《乌拉圭宪法》、1857年《墨西哥宪法》、1897年《厄瓜多尔宪法》等。接着,美国模式从美洲地区迅速传播开,蔓延至欧亚大陆和非洲地区,取代英国模式成为主流的宪法宣誓制度模式。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部分君主立宪国家终结,转向共和制,宪法宣誓制度模式也由英国模式转向美国模式,如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宪法》。另一方面,一战中部分帝国解体建立新共和国,也参考美国模式确立宪法宣誓制度,如1920年《奥地利联邦宪法》。最后,在一战、二战的影响下,亚非殖民地纷纷进入革命时期,冲击殖民地区秩序。部分地区开始了民主共和的制度尝试,并将美国模式的宪法宣誓制度引入亚非地区,如中华民国制宪。二战结束以后,亚洲涌现大批民族国家,控权意味浓厚的美国模式成为这些国家确立宪法宣誓制度的主要参考对象。
3.法国模式的发展
1791年《法国宪法》确立的法国模式虽然最终未在后续的法国宪法中得到固定和沿用,但是法国模式依旧影响了部分国家和地区。
首先,法国模式在临近地区的大陆法系国家小范围传播,德意志地区有部分加盟国选择效仿法国模式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规定广泛的宪法宣誓主体,并且由于地区相邻的原因,文化历史传统类似,法国模式的传播和发展并没有过多的本土化调整,形态更为稳定。如1818年《巴伐利亚宪法》、1831年《萨克森宪法》、1879年《汉堡宪法》。接着,随着美国模式的不断扩张,以及法国模式本身与欧洲大陆旧有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特点,法国模式日渐式微。基本没有新兴国家选择以法国模式为基础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即便意图涉及广泛的宣誓主体,也会将公民宣誓和掌权者宣誓作出区分,逐渐转向公民政治宣誓和公职人员宪法宣誓并行的新双重模式。法国模式的宪法宣誓制度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也导致了其并不具备大范围传播的特质,仅在周边历史背景高度契合的地区有过短期延续。
(二)旧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尝试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域外宣誓仪式也随着革命浪潮一同传入,清末民初《外交报》《时事旬刊》等多家报纸刊登了国外宣誓典礼,这种国家君王加冕、元首就职时向宪法、全体国民的宣誓,与中国传统盟誓文化大有不同,冲击着中国本土的宣誓传统,渗透着民主共和精神的仪式文化。
1.北洋政府时期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举行了宣誓仪式,开启了民国政治宣誓实践的先河。当时正式约法尚未通过,临时政府组织方法依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自无宪法宣誓一说,但其影响颇为深远。1912年3月,南京参议院接受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并要求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袁世凯在临时大总统誓词中明确表达“谨守宪法”。随后,1913年10月《大总统选举法》中正式明确了宪法宣誓制度,规定宣誓誓词1,这是民国时期最早规定宪法宣誓制度的法律文件。《天坛宪草》虽继承了誓词,但并未生效。1914年5月,《袁记约法》颁布并未规定宪法宣誓制度,同年10月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则继承了之前的宪法宣誓制度。至此,宪法宣誓在我国雏形初现,但始终未有正式生效的“宪法”文件规定该制度。
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国内地方自治思潮盛行,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建立政权,并出现了“联省自治”运动。一些省军政府制定的“省宪法”“联省宪法”规定了宣誓制度。如1922年8月张君劢草拟的“联省宪法”草案。至1923年10月,曹锟操纵国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正式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方面的内容,将大总统就职宣誓写入宪法1。但贿选宪法本身就是企图用虚伪的民主自由形式掩盖军阀统治的本质,宪法宣誓制度的中国实践仍未踏上正轨。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30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宣誓条例》,使当时的政治宣誓制度走上了一条正规化、制度化的道路。《宣誓条例》规定了文官、军官、教职员等不同主体应在宣誓后才能任职,并规定了誓词、仪式。随后,1931年《国民会议组织法》也规定了宣誓制度,至1936年5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称“五五宪草”)增加了总统宣誓的规定,但未经国民大会决定并通过,1936年5月《国民大会组织法》采纳了“五五宪草”关于宣誓制度的规定。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正式颁布,规定总统应于就职时进行宪法宣誓2。
可以发现,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在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初步尝试,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逐渐有了制度化的呈现。但是,这一时期宪法精神并未普及,宪法的权威也没有真正树立,动荡的局势不断扰乱着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宪法宣誓制度只是浮于表面。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制度的产生及发展历程
(一)入党宣誓中的“永不叛党”与宪法宣誓中的“忠诚”要义
革命先辈对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誓词的探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誓词的影响颇深。有观点认为,我国当前宪法宣誓誓词中“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所体现的“忠诚”要义,即是受入党宣誓誓词中“永不叛党”的启迪与影响3。
1927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湖南炎陵县水口镇叶家祠主持了6名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带着6名党员第一次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24字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成为中共党史上最早记载且比较规范的誓词。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后,入党誓词几经变迁,大致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等多个历史时期。但无论哪个时期的版本,誓词核心内容都离不开“永不叛党”,“永不叛党”成为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一名共产党员最大的责任和义务,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宪法宣誓誓词中“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所体现的“忠诚”要义,与入党誓词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实质上目的相同。依法治国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和保证宪法、法律的实施。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的高度统一,确立宪法宣誓制度,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意志。宪法宣誓的“忠诚”要义与“永不叛党”连接紧密,中国共产党的惩戒体系对于宪法宣誓制度的完善、违背宪法宣誓誓言的惩处措施的落实极具借鉴意义。可见,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制度的探索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宣誓制度的设立影响深远。
(二)宪法宣誓制度的理论和实务探索
从1949年《共同纲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部宪法修正案,均没有将宪法宣誓制度作为关注对象,我国也并未专门立法,宪法宣誓制度一直未能建立。但实际上,八二宪法颁布后一段时间就有学者提议借鉴国外宪法宣誓制度的经验构建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1989年有学者建议设立“就职宣誓制度”,强调公职人员就职时的宣誓行为对于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7];2000年有学者提议我国应在宪法层面引入宣誓制度,从就职宣誓转向宪法宣誓[8]。至此,在当代中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讨论正式拉开帷幕,宪法宣誓制度的覆盖领域及功能作用显著拓宽,并引发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
实务界关于宣誓制度的探索可以分为地方探索和国家机关探索两个方面。
一是地方探索。2002年8月,原人事部组织新上岗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员进行就职宣誓,并将这一宣誓活动固化为公务员培训制度中的必要环节。随着就职前宣誓环节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可,各地方积极探索宣誓实践,我国的宣誓实践进入第一轮活跃期。例如,2003年河南荥阳市和2004年黑龙江哈尔滨市分别自行组织了政府公职人员的就职宣誓;2004年江苏省组织省级机关新录用公务员就职宣誓;2005年四川省制定了省公务员宣誓制度规定;2008年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人大常委会选举产生的地方领导人和任命的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身着正装,手持宪法,由该区区长领读就职誓词;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对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就职宣誓的决定》;2011年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规定了就职宣誓。而不同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早期摸索阶段,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较早将适用于本区域内的宣誓制度按照宪法宣誓制度的标准进行了规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明文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分别见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一、一百零二条1,在基本法相关规定之外,两地还分别制定了具体的宣誓制度实施办法,保障宣誓制度的顺利实施。
二是国家机关探索。国家机关关于宣誓制度的探索主要见于检察官和法官的宣誓制度。2010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宣誓规定(试行)》,规定初任检察官、检察官晋升时应当宣誓。201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宣誓规定(试行)》,要求初任或重新担任法官职务的人员应当宣誓。理论界的深入研究和实务界的充分探索,为国家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宪法宣誓制度的初步建立与完善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2014年《决定》),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树立宪法权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的表述首次出现在党的重要文件中。2015年7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2015年《决定》),对我国宪法宣誓的主体、誓词、组织者、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宪法宣誓制度。在此之后,2016年1月15日,时任福建省长于伟国登上宣誓台,左手按抚宣誓台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宣读誓词,成为全国首个面向宪法宣誓就职的省长;2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张德江委员长主持并宣誓。
2015年《决定》包括第一段“说明语”和10条内容,规定较为详细。第一条规定了应当履行宪法宣誓程序的主体,最大限度地将立法、司法、行政、国家主席、军职人员等国家工作人员纳入宣誓主体之中,表明我国宪法宣誓主体的广泛性和多样性2。第二条规定了宣誓誓词,以宣誓人员效忠于宪法为首要价值3。第三条到第七条规定了宣誓的组织形式,包括在就职之时应当履行宪法宣誓程序的相关国家机关组成部门的重要公职人员,以及主持宪法宣誓仪式的主体。第八条规定了宣誓仪式、场所和对组织机关的授权。第九条规定了地方应该履行宪法宣誓程序的主体及地方组织办法和备案要求。第十条规定了施行日期。面对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体系结构,此种规定较为符合实际情况,自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性决定的形式在中央层面正式确立了宪法宣誓制度。
2018年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订了2015年《决定》,修改后的《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2018年《决定》)开始施行。在此之后,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进行了宪法宣誓。11月,国务院在中南海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监誓,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在后方列队站立,跟诵誓词。
2018年《决定》也有10条,体例结构并未作出变化,内容上则更为充实。第一,扩大宣誓主体。根据监察体制改革需要,在第一、三、六、七、九条相应位置增加了监察委员会相关主体,为各级监察委公职人员履行宪法宣誓程序提供法律依据。第二,修改宣誓誓词。将宣誓誓词最后一句改为“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第三,完善宣誓仪式。增加了“宣誓仪式应当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规定,与2017年9月《国旗法》的规定相呼应1。这次修改契合了监察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回应了《国歌法》颁行的情势需要,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宪法宣誓制度。
(四)宪法宣誓制度写入宪法
2018年3月,八二宪法进行第五次修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进行宪法宣誓的内容写入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宪法宣誓制度顺利入宪并作为当代中国的宪法制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2015年《决定》的公布指引各地方陆续制定本区域宪法宣誓制度的实施办法,全国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区都在2015年通过了本地的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截至2016年1月1日宪法宣誓制度实现了国内绝大部分地区的覆盖。随着2018年《决定》的修改和宪法宣誓制度入宪,全国各地参照2015年《决定》制定的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办法也纷纷作出修改,使之与宪法、2018年《决定》保持一致。近年来,各地方仍在对宪法宣誓制度的实施进行探索创新,如安徽省的变通规定“对因特殊原因未能参加宪法宣誓的人员,另行组织宣誓”;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宣誓场所要求“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等。这些实践不断推动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发展与进步,促进宪法实施、树立宪法权威,维护国家共同价值观,助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四、宪法宣誓制度的法治教育价值
2014年《决定》不仅提出要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还明确指出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我国的“法育”概念从传统的“普法宣传教育”“法制宣传教育”正式迈入“法治宣传教育”的新阶段[9]。而对于法治教育而言,宪法教育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宪法宣传教育是法治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10],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应以宪法为核心展开,作为宪法实施重要方面的宪法宣誓制度则是促进宪法宣传教育的关键,对于法治教育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现依宪治国,深化宪法宣传教育
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与实施能够在全社会传播宪法理念,树立全社会的法治信仰,实现依宪治国。
宪法宣誓制度是普及宪法教育,以宪法凝聚社会共识的有效手段。首先,宣誓仪式本身就是一次良好的宪法教育。宣誓仪式可以使宣誓者本人和民众同时从庄严的仪式中获得神圣的体验,有助于聚合群体、弥合分化、传导影响。宣誓仪式的流程能够培育和塑造宪法文化,使全社会尊重、热爱、信仰宪法,更有助于民众更好地认知宪法,从内心深处产生对宪法的情感寄托,使尊重和维护宪法权威成为民众的心理基础。其次,宪法宣誓具备道德约束的属性。宣誓行为本身随着社会的实践已经成为一项公共道德评判领域的事物,宪法宣誓制度设计过程中将道德层面的制约因素植入了宪法的强制性规定中,直接体现在宣誓誓词的内容上,本质上是在法律规范的直接惩戒效力之外寻求第二种规制力量,以确保宣誓制度的落实。宣誓主体在因“宣誓行为”受到法律强制约束的同时,也因“宣誓承诺”而激活了属于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中良好德行范畴的“践行承诺”意识。最后,宪法宣誓是实施宪法的重要方式之一。宪法宣誓制度强化了宪法权威、提高了宪法意识,完善了实现依宪治国的具体制度支撑体系。
(二)增强法治自觉,强化领导干部依法履职
宪法宣誓制度有效抓住了“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增强其法治自觉,强化领导干部依法履职,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典范。
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法治观念深刻影响着法治教育的推行,人民群众首先会向领导干部看齐:其是否尊崇法治、敬畏法律;是否了解法律、掌握法律;是否遵纪守法、捍卫法治;是否厉行法治、依法办事——这些都是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的体现。只有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领导干部都树立了尊重法律、尊重宪法的理念,才能更好地落实政策,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规则、依规则办事的氛围。宪法宣誓制度要求经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庄严的就职仪式上向选民或代表机关宣誓,对国家法律和权力赋予者郑重作出承诺,有助于国家工作人员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
(三)塑造国家认同,凝聚社会共识
宪法宣誓制度能够有效实现国家认同、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宪法本身具有价值纽带功能,宪法教育需要具备认同统合作用的价值命题来具体展开,这些价值命题恰能通过宪法宣誓制度所表达。
宪法宣誓制度具有一种重要的传导效力,能够激活情感、深化认知、明确指向,将宣誓所蕴含的要旨传导至全社会并成为宣誓者和公众共同遵守的规则。首先,宣誓仪式能够激活人的共同情感。通过宪法宣誓仪式可激活宣誓者和公众一致认可的“宪法至上”的情感,宪法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不论任何身份都要遵守宪法,无一特例。这种特殊意义能逐渐扩散至全社会并固化为全社会敬畏宪法的共同情感,塑造“法治中国”国家认同的基本情感。其次,宣誓仪式能够深化人的共同认知,将某种行为赋予特别的意义。程序化的宣誓仪式行为已经逐渐超越了日常的行为活动,被赋予了更庄严的意涵,即该行为意味着宣誓者宣示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依法履职并接受监督,并逐渐内生成社会公众的共同认知。最后,宪法宣誓仪式能引领人们的同向行为。宪法宣誓仪式的固定动作表达出该行为被赋予的宣誓人承诺必须对宪法忠诚的意义,承诺作出之际既有对宣誓者“践行承诺”的强制约束意味,并逐渐形成宪法宣誓附加的“言出必行”的价值观。故而宪法宣誓承诺所构建的宣誓主体的自我约束也将在社会传递,形成宣誓者和社会公众同向的行为模式。
宪法宣誓制度深受宗教传统与宪法文化的影响。西方早期宪法宣誓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以英国模式为代表的宪法宣誓制度将宗教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宣誓与宗教联系密切,法律与宗教并未完全分离,随后逐渐在制度实践中脱离了宗教影响。以美国模式、法国模式为代表的宪法宣誓制度虽表面看起来处处体现着理性主义思想,有显著的民主法治观念,但仍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而在我国,宪法宣誓制度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相融合,迸发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目标面向,并与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相交织,一同融入中国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落实到中国法治运行的全过程。宪法宣誓制度具有强大的仪式、监督、约束效用,正是这些功能赋予其强大的生命力,在现代国家的宪法制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影响着宪法法律的制度设计和改革进程。
参考文献
[1]吴欢.宪法宣誓的机制原理及其完善:法人类学与宪法史学的视角[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102-111,148.
[2]赫然,王鑫磊.西方宪法宣誓制度给我国的启示[J].社会科学战线,2017(10):213-218.
[3]温泽彬,陈小鲁.宪法宣誓制度功效探析[J].重庆社会科学,2021(2):112-124.
[4]陈小鲁著.宪法宣誓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
[5]王亚平,谢天.实施宪法宣誓制度的几个问题[J].人大研究,2015(2):17-21.
[6]陈端洪.权力的圣礼:宪法宣誓的意义[J].中外法学,2018(6):1492-1518.
[7]钱卫清.我国应建立就职宣誓制度[J].理论探讨,1989(1):44.
[8]蒋伟.论建立忠于宪法的宣誓制度[J].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2000(5):58-62.
[9]雷槟硕.宪法教育与法治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10]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