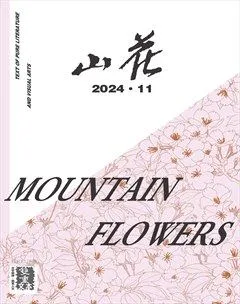浣熊先生
2024-11-20山眼
“周五晚间,一位女士在北温哥华参加社区园艺活动。一只野生浣熊向她的狗狂吠,这是一只从动物中心领养来的小狗,比浣熊小很多。女士赶忙呵斥,并抱起她的小狗。她感到浣熊爬上了她的后背,又咬了她的腿。其他人赶来……女士被送往医院,缝针并打了破伤风针。这是近期内,本地发生的第二起人被浣熊攻击的事件,上一次攻击发生在几天前,温哥华东……”
兰库太太弯着腰,一条腿跪地,另一条腿半蹲着,正在拾掇一丛新种的绣球花。电台中絮絮叨叨的本地新闻播报声,从开着的窗里传出来。晨光已很猛烈,兰库太太感觉背上晒出了汗。她将小铲收进塑料桶,扶着膝盖,稍胖的身子摇晃摇晃,终于站起身来。
兰库先生戴着橡胶手套在厨房洗碗,水声哗哗。他是个有洁癖的男人,不怎么喜欢和泥土打交道,因此园中的事儿都是太太做。他把洗好的盘子摆在晾水架上,想起去年有郊狼在史坦利公园伤人,后来被捕杀了。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和黑熊、浣熊、郊狼多年来和平共处,保持着适当的边界。不过,这几年,不少事儿都变了。
兰库太太进屋洗了手,坐在餐桌前,吃先生准备好的早午餐:一碗牛奶泡燕麦、半盘无油炒蛋、奶酪、火腿片、三五只小番茄。她谢了饭,用刀叉切开火腿片,送进嘴里,细细咀嚼。“迈克,”她说,“下午咱们去买点肥料,调绣球的颜色,我喜欢蓝一些的。”她这么说的时候不抬眼睛,声音柔和,嘴角的皱纹一坠一坠。
兰库先生答应着,随手在炒蛋上撒胡椒粉。“去一趟家得宝,”他说,“等我修完篮球架。”
他们有意慢慢吃。兰库太太抬眼看窗外,春风吹过那一片绿莹莹的草地,像一位亲切的朋友,抚摸着正在盛开的杜鹃花和已开败了的石楠。细草尖在树影的边缘,明暗的交界处在闪光。这个花园,她还是比较满意的。
老水手来到餐桌下,匍匐在兰库太太脚上,呜呜发出低鸣。它的头蹭着她的脚踝,尾巴一扫一扫。他们这顿饭吃到了十一点。兰库先生正起身收拾碗盘,兰库太太接到电话,是教会的姐妹打来的。兰库太太没去教会,她们特意问候她。今天是母亲节,每个母亲都会接受大家的祝贺,收到教会赠送的康乃馨。兰库太太从没做过母亲,不是她不想,他们试了很多办法——她认为那是她人生的重大失败,兰库先生不这么想,但没法说服她。他们约定,母亲节这天不去教会。六月份父亲节的那天,兰库先生还是会去。他想表明自己并不在意,愿意为其他的父亲祝福。
兰库太太和姐妹聊了好一会儿。兰库先生听见她们在说:物价涨了,牛肉贵了好多;航空公司改变航道,可能要从本社区上空经过,大家担心噪音……他上厕所时,顺手刷了马桶。然后他去看篮球架,那个架子搭在车道上,常有邻居的小孩儿来打篮球。他没事儿时也会和他们玩一会儿。他昨天发现篮球筐歪了,只能慢慢把它放倒,看是哪里松了。他跪下来,一只手撑在地上,凑近了看。水手跟了来,站在一边。有孩子来打篮球的时候,它总是很兴奋。兰库先生叫它把车库里的工具箱拿来。水手懂了。它嘴里拽着工具箱把手,急急地,好像也在想篮球架子哪里出了问题。
“迈克,你的电话。”太太把头伸出窗外来喊着。兰库先生这才发现,手机仍在厨房里。他不想接,没什么要紧的,真有什么事,会接着打。电话铃声停了,又继续响起来。
是斯图尔特太太,学校校长。她说:“迈克,七年级有个孩子,叫亚当,亚当·黄。”兰库先生的手还没洗,他抽出纸巾擦手,一面嗯嗯点头:“出了什么事?”
兰库太太啜着咖啡,看着丈夫的侧面。他头发浓密,体格宽阔,鼻梁上部有个棱,好像急速下降的山坡上的一小段平台。他听电话时一只手敲着桌子,这表示他有点紧张。她不免多看了他几眼。
他很快讲完了,说:“我出去一下,学校有点事。”“什么事?”兰库太太问。她总是好奇。兰库先生心中想着事儿,说:“篮球架我回来再修。有个学生在皇家哥伦比亚医院看急诊。我去看看他。”他找到车钥匙,发现放倒的篮球架挡住了车道,于是去挪开。走之前他不忘对兰库太太说:“莫丽莎,你今天很漂亮。”莫丽莎笑了,眼角纹荡漾开去——她穿着无袖上衣和短裤,完全没化妆。兰库先生想,回来时要记得买束花。
水手目送着兰库先生的福特车开远了,一直到兰库太太叫它进去。它有一双黑亮的小眼睛。
兰库先生赶到医院急诊室。等候室里人员密集,空气浑浊。呆滞、烦躁的病人或站或坐,护士、医生穿梭而过。他叫住一个护士,问:“这里送来个小孩,他叫亚当·黄,是在里面吗?”护士双手插兜,耸耸肩,用目光暗示他去排队。他说:“警察叫我来的,我是学校副校长。我听说他在里面。”护士和坐在柜台后的另一个护士小声交谈,然后对他说:“你跟我来吧。”
那孩子躺在病床上,一只胳膊上正在输液。他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兰库先生认出这孩子了,是的,他记得这孩子,是个国际学生,平时怯生生的,英语不怎么好。一个黑皮肤的护士进来,用眼神询问他。兰库先生介绍说,自己是亚当学校的副校长,问:“他怎么样?”护士看了看孩子,低声说:“胃肠炎,可能是吃了过期的、腐烂的食物,急性发作。”兰库先生一下子放心了——他曾担心是更严重的事儿……亚当微微睁开眼睛。兰库先生俯身看他,轻声说:“亚当,你好,我是兰库先生,副校长。”亚当羞涩地躲开他的目光,但又转回来看他。“你会很快好起来的。”兰库先生笑着说。
护士调整了输液管,说:“输过液之后,医生说他可以出院了。”护士示意兰库先生和她一起出去,她说:“他打了911,才被送过来。问他家里人,他说他们出去旅行了,也不让我们联系。我们只好找警察,发现他是国际学生,他的监护人一家去了美国。”
兰库先生点头,笑着说:“谢谢你,我来联系他的监护人吧。”然后医生来了,是个头发花白,留着络腮胡的老医生。他翻着手中的病历,飞快地说:“这孩子独自在家,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待着?”
兰库先生给学校秘书格利亚打电话,她找到了亚当监护人的号码。他打电话过去,打了好几次,那边才接通。
“啊?亚当生病了?!怎么回事……”女人的声音,然后是窸窸窣窣的交谈声,他们说普通话——兰库先生去过中国,听得懂一点中文。等他们终于商量完了,换了一个男声,声音很大,他说:“您好,副校长先生。我们这次出来,是有紧急的事情。亚当平时很健康,这是一次意外!我们出门的时候,都和他说好了,吃的在哪里,有紧急事件怎么做。你看,他不是叫了救护车了吗?他买了医疗保险的……”
听说医生希望他们回来,那边又是一阵商量。那男人显然着急了。他说:“我们在洛杉矶,周二下午才能回去,我们有急事……酒店订好了,不能退。”兰库先生只好说:“我可以把他接到我家里去住,但要监护人同意。”
“好的好的。”男人如释重负,“太好了,太感谢您了!”他们很快发了一个书面的授权书来。
这天晚上兰库先生很晚才到家。多年来这是头一次,在母亲节这天他忘了给妻子买花。
水手冲着亚当叫,是友好的叫,那孩子也许还分不清。他身体虚弱,人有点懵懵的。兰库先生领着他进了家里的一间客房,水手一直跟着他们。莫丽莎清理过房间,这会儿已经睡了。亚当紧紧地攥着双肩背包的带子,救护车载他时,他居然还记得带书包,兰库先生想着,不由地笑了。
孩子量过体温,仍有点发热,于是按医嘱吃了退烧药。兰库先生说:“亚当,明天你不去学校了,好好休息吧。”
亚当嗯嗯应着,眼睛仍是不敢直视兰库先生。兰库先生担心这孩子太害羞,问他:“你想跟你父母联系一下吗?”亚当的眼光闪烁,证明他心里起了波澜,然而他飞快地说:“不用。”兰库先生凝视他,他脸红了,解释说:“有时差。”“你确定?”兰库先生又问,“你不想和父母说说?也许跟他们说话,你会感觉好受一点。”孩子困难地摇摇头。
兰库先生拍拍孩子的肩膀,关上门。水手在门旁徘徊了一阵。兰库先生走下楼梯,做手势叫它,它才依依不舍地跟着离开。
莫丽莎并没睡着,她伸出手臂抱抱丈夫。兰库先生有些歉意,说:“亲爱的,我忘记给你买花了。花肥过两天买吧。对不起……这孩子是个国际学生,监护人一家去美国了,他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莫丽莎起身,趿上拖鞋去厕所,回来吃降糖药。她吞药下肚,说:“这么小的孩子……他多大了?”“十四岁。”她回到床上,“他们怎么想的,把这么小的孩子……”“那家人去洛杉矶了,说是有什么紧急的事……”莫丽莎翻身,说:“我说他的父母,是中国的吗?”兰库先生感觉困意席卷上来,他把被子盖住耳朵,说:“国际学生一多半是中国来的。我也觉得,这么小的孩子,但是学校,你知道的,要赚点钱……这算好的了,去年出了更大的事……”他说着说着,就忘了要说什么了。
莫丽莎好一会还没睡着。她自言自语:“不生孩子也不是什么坏事,是吧?”忽听楼上咣当一声,又扑通一声,她睁大眼睛侧耳细听,一会儿又没动静了。也许是那小孩绊倒什么东西了,应该没什么大事。可怜的小孩,这么小就离开父母。如果我有孩子,绝不会这么对他。这么想着,她在心里为这孩子念了祷告。
身边丈夫的呼噜声响起来。他总是仰着睡,张开嘴,起伏有声。她想推他,提醒他侧身睡,别打呼噜,想想他累了,便随他了。
亚当的书包里没有课本,只有一本日志,上面是些自己都看不清的涂鸦。在这间陌生的卧室里,他睡不着,老房子有股味道,闷闷的。副校长的家,房顶比较低,光线不那么充足。家具整整齐齐的,不像苏阿姨家里,房子大得多,家具却一点儿不讲究。白天,亚当鼓起勇气和副校长太太打了招呼,说了几句,早餐都没好好吃,就逃到楼上来了。兰库太太是温和的,但亚当觉得她不怒自威。亚当心里一直盼着兰库先生回家,觉得他更和善一些。
亚当从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邻居家的阳台,路上的电线杆;附近都是小房子,院子不大,到处都是松树、杉树;远处有山。他坐回到床上,开始刷手机,刷到快没电了。
这位兰库先生,学生们背地里叫他浣熊先生——他的姓兰库(Ranco)和浣熊(Raccoon)发音很像。亚当喜欢浣熊,它们身量不大,憨憨的,带点儿神秘感。副校长本人却是体格高大,声音洪亮,乐观开朗。亚当暗暗觉得,浣熊先生不会喜欢自己——自己和阿尔蒂诺中学格格不入:学校里三两结伴的同学,多半都是意气风发的样子,而他是个外来户,英语不好,总是避免和人说话,内心感觉矮了半截。亚当还特别不满意自己的外形:个子不高,瘦弱,高度近视。他也不喜欢自己的英文名字,那是妈妈起的。
兰库先生下班回家,带回一束康乃馨和雏菊混合的花束。莫丽莎接过花,脸色顿时鲜亮起来。她打开花束,一枝一枝剪好、插瓶。天气好热,但愿这花开得久一点。兰库先生问:“孩子呢?”莫丽莎说:“在楼上房间里。他不发烧了。”兰库先生去卧室,脱下衬衣,换上T恤和短裤,立刻觉得松快很多。
他上楼到亚当的门外,敲了敲门,然后推门进屋。孩子坐在床上,抬眼小声说:“兰库先生。”兰库先生一连问:“你不热吗?外面好热。把门打开吧,好吧?”他说话很快。亚当这才意识到是气温的问题,怪不得一直觉得热,还以为是自己不适应这房子。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兰库先生笑着说:“莫丽莎说你不发烧了,很好,晚饭前再测一次。别的怎么样?拉肚子和肠胃疼。”男孩摇头。副校长又说:“她说你午饭吃得不多,要多吃点,小伙子!”
亚当只是点头。兰库先生瞧着他,说:“也许明天可以上学了。你想念学校吗?”其实不想念,但他又点点头。兰库先生说:“试着走走,别总坐在床上,走走。”于是亚当下了床,其实他已经在这间房子里来回走了好久。“要么下楼来,去花园看看,小伙子。”兰库先生领着他,他们走下楼来。莫丽莎在做晚餐,亚当连忙和她打了招呼。水手不知从哪里蹿了出来,紧紧跟着他们。
围墙处有一条水沟,穿过花园。那旁边修了一个小喷泉,从一座水泥台上,流水汩汩而下。草地才修剪过,新鲜的青草味沁人心脾。他们在喷泉边的铁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想知道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吗?”兰库先生摸着水手的后背,问亚当。
“想的。”亚当说。
“今天有亚裔文化展,在学校图书馆里。这个月是亚裔文化月,对吧?展览会今天开始,到这个月底,所以没关系,你可以看到的。学生家长们准备了很多好东西,很有意思。”兰库先生微笑着说。他把目光看向亚当,亚当似乎不感兴趣。
“我去过中国。”兰库先生又说。亚当马上问:“真的吗,哪里?”“青岛,我在那儿待了半年。我还去了成都,那儿的东西很好吃,是吧?”他接着问,“你从哪儿来?”“江西省的一个小地方。”亚当说。
“哦。”兰库先生大概知道江西在哪儿。他等了一会儿,看来这男孩不想讲自己家乡的事。
男孩终于问:“你喜欢中国吗?”
“喜欢。”兰库先生想也没想就说。那时他还年轻,到处去看世界。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好看的女朋友,但最后没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心里算了一下,那时这孩子还没出生。
“跟你父母联系了吗?”兰库先生又问。亚当含混地点头。他看出,男孩不愿意父母知道这事——这总是不大好:父母缺席,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可不是好事,但他又能说什么呢?他也有些困惑,中国人讲究孩子的教育,越来越多的中国孩子来加拿大读书,有些像亚当这么小。离开了自己的家,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
“在学校里,谁是你的朋友?”副校长继续问,“吉米·江,弗兰克·刘……”他说了几个亚裔孩子的名字。亚当一个也不接。谁也不是,他刚来几个月,还没有朋友。而且他已敏感地发现,往往是那些外表和他相似的华二代,对刚从中国来的他,有一种嫌恶。
兰库先生拍了拍孩子的腿,说,“你在这儿坐着,或者上楼去都可以,我去帮着莫丽莎弄饭去。”亚当走上楼梯时,扭头看去,莫丽莎背对着她,一头金黄发白的卷发,无袖白T恤下露出晒得黑红的健壮臂膀。水手跟着男孩上了楼,卧在他的房门外。
兰库先生回到厨房,莫丽莎正在拌沙拉。“这孩子。”他摇头,欲言又止。莫丽莎看看他,“他叫亚当,是吧?”他点头。莫丽莎切了一些橄榄、牛油果、奶酪块,放进盆里,捏了一块尝尝,在纸巾上擦了手,回头看了一下,小声咕哝:“这么个名字?”兰库先生发现,那些移民家庭的孩子,如果是东欧来的,或是印度裔、伊朗裔学生,多半会保留他们的传统名字;东亚裔则会起一个英式名字作为常用名,五花八门,有些还会是很古老的、现代不常用的名字。
烤箱铃响了,兰库先生戴上防烫手套,取出烤盘。“烤鸡块,这孩子愿意吃吧?”莫丽莎说,但她觉得火候不够,于是兰库先生又把烤盘放进去,设定再烤五分钟。“今天学校的情况怎么样?”莫丽莎问。
“还好。”兰库先生说,“那些男孩很过分。有两个男孩骂德里克·维吉尔。德里克那孩子又高又壮,体育很好,很受欢迎,没想到还有人骂他。”他冷笑了一下:“骂他的那两个孩子,他们和他抢球,抢不过,就打起来了。听说他们骂他骂得很恶毒。”
莫丽莎说:“这些青春期的小孩,还不是整天胡说八道的?”兰库先生点点头。糙米煮好了,莫丽莎捞出来拌进沙拉,一面示意兰库先生切蒜和生菜。
兰库先生仔仔细细地切着,忽然鼻子里出气,说:“莱莎·米尔顿当选了教师联合会主席。”“哪个莱莎·米尔顿?哦,那个女人。”莫丽莎眨眨眼,一下想起了那个女人。早年莫丽莎也在学校工作,身体不好便早早退休了。兰库先生哼了一声,道:“现在,越是她这样的越得势。”莫丽莎没搭话。“有时候我真是不明白……”“什么?”“我对她没有成见,一点没有。可是她不适合做教师,我以前这么说,现在还是这话。”莫丽莎低低地说:“有什么办法?”
她拿过面包,切片,准备蘸料。“最重要的是她没有自知之明。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都以为自己要改变世界,结果是在挑战常识。”兰库先生说到激动处,身子靠在灶台边,反手撑着。“时代不一样了。”莫丽莎说,她有点担忧地抬眼看着丈夫,他的侧面还是那么好看,但鬓角已斑白了。
兰库先生噎住了。“时代,时代……也许我们都老了。”他讽刺地嘴角上翘。莫丽莎伸手来摸丈夫的脸,柔声说:“你不老。”她凑上来想吻他一下;她今天涂着粉红色荧光口红,愈显出嘴唇薄而平。兰库先生顺势吻了妻子,转身端起沙拉盘子,摆放在餐桌上,然后打开橱柜找出餐盘。
傍晚时分,亚当的体温又上升了,38度2,兰库先生让他再休息一天。问亚当明天有什么课,亚当说有法语、社会研究、体育课。亚当看副校长心不在焉,只怕他对自己印象不好。兰库先生将手插在裤口袋里,摸到车钥匙,想着何时去买花肥。
第二天下午,男孩儿看到女主人开车出去了。房子周围异常安静,有一些遥远城市的噪音。他打开门,伸出脑袋看了看。楼梯尽处是一扇小窗,窗台上有一只蓝灰色的花瓶,有茂盛的绿色枝条垂下来。他摸了摸,是假的。
楼梯正对门口,拐个弯儿就是厨房,另一边是客厅。水手不知从哪个角落里蹿出来,男孩险些从楼梯上摔了下来。狗儿颇为友好,呜呜地轻叫着,蹭上来舔他的手。男孩被狗舔得有点紧张。他坐在楼梯上,那狗趴在他的胳膊上,尖脸凑上来,在他的耳朵边闻来闻去,痒痒的。
它到处跟着他,他也学会摸它了,双手去摸。水手的皮毛非常柔顺,它是一只漂亮的狗。亚当在厨房接了杯自来水喝,这里的窗户面向花园,一座修建整齐、欣欣向荣的花园。他转身,面向客厅:窗帘没有全部拉开,屋内有些暗。窗帘缝隙透进来的阳光,像在图案繁密的地毯上割了一道口子。松软的旧沙发上搭着毯子,壁炉上方挂着大大小小的照片。那些照片里的人,除了兰库先生和太太,亚当一个也不认识。他远远看着。忽然想起自己的家,就是远在鹰潭的家。那是他和妈妈的家,爸爸偶尔来接他,胡子拉碴,怏怏不乐——他们离婚了。妈妈也有很多照片,每年她都去拍写真,放大了挂起来,总是浓妆艳抹,穿着闪亮的大裙子。他不太喜欢,但也没法说,她高兴就好。妈妈炒菜好吃,可是他们常吃外卖,她太累了,说在外面生意不好做,回家就只想躺着。
妈妈柔软又粗糙、风风火火的气息在一秒内复活了。他感到她就在身边,心中溢出要抓住她、搂住她的渴望;翻滚上来的还有沉重的心酸。他在同一瞬间内又清醒了,厌恶起了自己的软弱。他狠狠捏着腿。这里是加拿大,他在一个外国人的家里。这个家陌生、友好,而又令人敬畏。
有车子开近了,接着是引擎熄灭的声音。亚当拉住扶梯,一溜烟跑上楼。狗也跟着他,想要进门来。他硬把它挡在门外。狗儿在门外呜呜叫了半天,一直到莫丽莎从车库进来,叫它,它才下去。
晚饭吃麦当劳汉堡。昨天莫丽莎发现这孩子吃得很少,心想可能是他们的饭不合他口味。这会儿她看他大口嚼着汉堡,心里摇头,小孩子怎么都爱吃垃圾食物?她说:“冰箱里有橙汁,你可以自己去拿。”男孩倒了一大杯橙汁,却忘了关冰箱门。莫丽莎示意他,而他一心忙着吃,头也不抬。她只好自己去关了冰箱门。显然他是个极度害羞的孩子,这两天,他和她说话不过三五句。
“兰库先生去看他母亲了,去养老院。他晚点才能回来。”她有点像是自言自语,又有点像是对亚当说。丈夫的母亲利亚,跟着一个人莫名其妙走出了老人院,竟然没人发觉。是一个路人发现老人茫然地站在一棵树下。老人受了惊吓,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兰库先生责备老人院疏于照顾,他们说人手太少,没法儿照顾周全。
男孩终于从残留的汉堡后面抬起眼睛,他眨眨眼,什么也没说。
“你上七年级是吧?”她又问,实在也不知说什么好。看他那么害羞,她不免有点怜惜他。
男孩吃汉堡的速度慢下来了。他点头。目光下垂,盯着桌面。
他无声无息地吃完了汉堡,又吃了奶酪蛋糕。他甚至要了第二块,吃得津津有味。莫丽莎满意地笑了,蛋糕是专门给男孩烤的。她说:“我有些书,你喜欢看的话自己去拿。”她用目光和下巴指了指客厅。他什么也看不到。“在客厅门口,有个书架。”她放下吃了一半的汉堡,带着他一起去看。那是一座高大的旧式壁橱,上层架上摆满了密密麻麻的书。莫丽莎打开下面的柜门,里面也是书。她抽出两本书,《失去的Z城市》和《你当像鸟飞向你的山》,心想这个年纪的孩子也能看了吧。
男孩接过书,礼貌性地笑了笑。他盯着上层的几本厚书,莫丽莎看过去,正是《哈利·波特全集》。她脸上显出心照不宣的戏谑神情,说:“你爱看什么就自己拿吧。”亚当躲在眼镜片后的眼光闪了闪,他迟疑了一下,先把手中的书放在柜台上,终于上前,踮起脚抽出了那几本书。
他忘了带手机充电器,又不好意思借,于是一晚上都在看《哈利·波特》。里面还有很多生词,可他看得很起劲儿,好像忽然间,他能看懂英文版《哈利·波特》了。这真好。
第二天早晨,兰库先生吃饭时眼皮沉重,面色通红,心中还在因母亲利亚的事故而不快。昨夜他没睡好,想起母亲的过去,很是难过。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得了各种病,最后来的是阿尔兹海默症,他们不得不送她去老人院……他忽然想起今天有校董会,回卧室换上了衬衣长裤。再下到厨房,他看见男孩也来吃早餐。“亚当,早晨好,”他不由得轻快起来,就好像已经置身于学校,面对所有学生了似的。他从小烤箱中取出焦黄的面包,抹上菠菜酱,添几片火腿。“昨天我收到了你的监护人的消息,他们下午来接你。”男孩点点头。他看出男孩并不高兴。
女人介绍自己叫“艾琳娜·苏”,五十岁上下,也许更老——亚洲女人通常看起来比她们的实际年龄年轻些。她很谦恭地问好,并带来一盒亚洲饼干作为礼物,感谢他们这几天照顾亚当。莫丽莎笑说:“你太客气了。”她接过饼干盒,打开来放在桌上。艾琳娜问,“这几天的伙食费,要多少钱?我转给你们。”她看看莫丽莎,又看看兰库先生。他们面面相觑,兰库先生说:“不必了。”
兰库先生请她坐,看得出她有些拘谨。
“副校长先生,真是很麻烦你……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亚当竟然去了医院。还好没什么事。”她看看亚当,欲言又止。
“医生说他吃了过期的食物。”兰库先生说。
“哦,怎么会这样!”艾琳娜皱眉说:“我们都告诉亚当了,冰箱里哪些是留给他吃的,都是在盒子里装好的,足够他吃的。……怎么会吃了过期的食物?”她扭头问亚当,“你吃了什么?”
亚当没回答。兰库先生看着他说:“好像是酸奶,还有通心粉酱。”
艾琳娜既严厉、又拘谨地扫了亚当一眼,马上又笑了,她对兰库先生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的。这孩子没好好看。东西放在冰箱里时间长了,我们也太忙了。”
“这也是难免的。”一旁的莫丽莎说。
艾琳娜连连点头,感激地笑着,“就是嘛。”
“没有什么,”兰库先生把双手交叉握住,宽慰说:“他是个聪明孩子,打了911。”
艾琳娜不见得同意,她似乎是忍耐了一会儿,终于对亚当说:“冰箱里给你吃的东西,还有下面冷冻的,都给你说好的嘛。”亚当低着头。兰库先生和太太看着他们。艾琳娜更加小声地说:“你为什么偏偏吃了那些过期的东西?”她扭头面对亚当,背对着兰库先生和太太,好像用后脑勺可以屏蔽他们的交谈似的。
莫丽莎走开了。
亚当心中已经后悔了。他听到苏阿姨说,有几瓶东西过期了,准备扔掉或者捐给食物银行。他为什么要吃那些东西呢?他也不太明白了。那天天黑了,他特想跟妈妈说话,可妈妈正忙着取货去,只说:“你爸妈没本事,你可一定要出息。”就不再回复了。他连打了三个微信电话,她都没有接。他非常气恼伤心,唯一能做的是惩罚自己。他吃了一大堆坏了的东西,马上感到肚子不舒服。他害怕了,打了911。不到十分钟,救护车到了。
兰库先生问艾琳娜:“你们去洛杉矶旅游吗?”
“不是不是。”艾琳娜摆手,说:“我儿子在那边有个循环赛,游泳俱乐部比赛,他们拿了全温哥华的冠军,然后又去美国比。一家人一起送他。”她连忙加了一句:“我们问过亚当,他不去的。”事实是,苏阿姨说可以带亚当去,但他必须额外付钱,妈妈给的伙食费是不包括这些的。大概一千二,她让他去问妈妈。男孩没有问。为了给他凑学费,妈妈已经很累了。
艾琳娜说起儿子的比赛,讲个没完:她的大儿子叫吉米,拿了蝶泳第二名,他们俱乐部成绩也很好……至于是什么循环赛,兰库先生没听明白,这种比赛太多了。他一边微微点头,一边问艾琳娜:“吉米也在我们学校吗?”“没有没有,”艾琳娜说:“他们,吉米和蒂娜都在圣乔治中学。”——那是一所私校。她又扫了一眼亚当,似乎想解释为什么她的孩子和亚当不在同一所学校。兰库先生搓搓双手,笑说:“艾琳娜,孩子一人在家不安全,虽说他十四岁了。他才来半年多,对这里还不太熟悉。你们不在的时候,应该安排人照看他一下。”
艾琳娜沉默片刻,似乎感到委屈:“没想到他会进医院,他一向很健康的。”
“嗯。”兰库先生说,“这是个意外。”他看向亚当,男孩愁眉苦脸地低头坐着。他又说:“亚当是个好孩子,学习很努力,也爱看书。”
艾琳娜瞅着亚当,也有些发愁的模样,“唉,唉。”也不知她在“唉”着什么。最后她苦笑一下:“他总是看手机,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她一面说一面起了身。
男孩已收拾好背包。莫丽莎来和他们告了别,兰库先生送他们走出家门。亚当慢慢吞吞地跟着苏阿姨。又要回到那所大房子里去了。他们家有三座大房子,苏阿姨的女儿蒂娜曾经很自豪地说过。按说他们很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做寄宿家庭,赚他这每月一千五百块?苏阿姨整天忙着打理出租的事,还老是和她丈夫吵架。吉米和蒂娜都不爱搭理亚当。他不喜欢那所大屋,天井顶部高得吓人。
兰库先生叫住艾琳娜,低声说:“这些孩子,他们的心理健康也要注意。这个年龄段……”艾琳娜张开嘴,看了看亚当,满面惊讶:“怎么啦?”
兰库先生拍拍她,笑说:“别紧张。回去给他吃点好吃的,让他跟他父母多联系。”“有的有的,我们总是叫他跟他爸妈多视频,没有禁止他,真的。唉,这些孩子真不好搞。”她忽然停住了,是怕说多了。
“好的,多鼓励他。”兰库先生仍笑着,拍她肩膀。艾琳娜往后缩了缩。
艾琳娜等着亚当走近了,亲热地搂着他,走向白色特斯拉。水手追过去,嘴里扯着男孩儿的裤脚,男孩只好一瘸一拐地拖着它向前走。兰库先生喝住水手,它松了嘴,扭头看看他,又追上男孩——这次没扑上去,只是紧紧跟着,一直到男孩上了车,它还把前腿搭在男孩的腿上。这样亚当没法关门。“水手,水手!”兰库先生只好拉开它。他挥挥手,他和它一起看着白色特斯拉远去了。
水手呜呜叫着,兰库先生蹲下身,叫它张开嘴,看看它的牙齿,又摸摸它的耳朵,说:“牙龈炎好了。你还是喜欢孩子,是吧?你个老东西。”
狗儿将前爪搭在他手上,眼睛湿润。“来吧,我们来修篮球架。”他对它说,“完了有好吃的给你。”它立刻跟着主人走过去,一边欢快地摇尾巴。
阿尔蒂诺中学的校园里,春风弥漫。这才是五月份,女孩子们已趁着阳光,穿起了短裤;也有的穿着阔腿长裤,上身是紧身的露腰胸衣。她们甩着滚滚的一头金发,或是其他颜色的长发,着实青春靓丽。兰库先生想:是从哪一年起,女学生们开始流行这种装束?男孩子却没几个穿短裤的,他们双手插在裤兜里,耳朵里塞着耳机,头也不抬。
兰库先生在办公桌前坐下,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着手头需要签字的几个文件:新采购一批手提电脑(预备借给家里买不起电脑的孩子);暑假之前,会组织孩子们去本地最大的游乐场玩一天,孩子们都很喜欢,但这一项严重超支。
他不小心把咖啡溅在了文件上,赶紧找到一张纸巾,想把咖啡渍擦去,却没法擦干净,于是他将那页页脚折起来,挡住污渍。他忽然想起,在一次家长会上,有人问:为什么要一整天不上课,带孩子去游乐场?本校的排名不高,老师们应该更注重学业。他解释说:学校的排名并不能够真实反映学校的教学水准,那只是一次联考的成绩统计而已,完全由各个学校自己打分,并不客观。我们学校注重的是孩子的情绪、健康、能力的综合培养,而不仅仅是分数。
有些家长并没有被说服,他们非常在意学校排名。据兰库先生的观察,提这些要求的,多半是亚裔家长(这点他自然不会说出口)。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亚裔家长很少对学校提意见——这些年,亚裔移民越来越多;当然,各种族裔的都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也使一些事情复杂起来。
秘书格利亚进来说:“兰库先生,德里克·维吉尔又没来上课。这是第二天了,也没请假。昨天我们给他家人打电话,没人接。”兰库先生喝掉杯中最后一口咖啡,说:“电话号码给我,我来打。”——倒是很快接通了,孩子的母亲说,德里克在学校被欺负,他不想去学校——这自然是上一次,德里克被辱骂的后果。兰库先生耐心地请她安慰孩子。“学校有心理咨询服务,”他说,“我们会给德里克尽快安排一次心理咨询。你看怎么样?”“那得要他愿意去学校。”孩子母亲说。“是的。我们给他些时间吧,抱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学校。”他说。那位母亲忽然哭了,她说,这孩子的父亲在乌克兰战区,生死未卜,她非常心疼孩子。在加拿大这个以包容和尊重著称的国家,他们居然遇到了歧视。她伤心透了。兰库先生听着,除了说抱歉,无从安慰她。
这个电话打了足有半小时。接下来兰库存先生去上厕所,回来又喝掉一杯咖啡。他起身在办公室里走了走。重新坐下来不到一分钟,他收到两份电邮投诉。
一份来自八年级老师尼尔森先生,他说学生安德鲁·费舍在社会研究课作业中使用了ChatGPT给出的答案——实际上不是别人发现的,是安德鲁自己告诉了所有的人,显然他为此还很得意。
还有一份投诉,是针对莱莎·米尔顿的,由一位九年级老师转来。一位学生家长投诉她举止不当,兰库先生读了两遍,内容不完全清楚,像是说她骚扰学生。这可是个麻烦事……兰库先生揉揉鼻子,虽然他很不喜欢莱莎·米尔顿,而且感到她对很多事怀有敌意,但还是感到惊异。他以为米尔顿小姐就算遭到投诉的话,也会是因为别的事,比如说教学疏忽,对学生过于严厉等等。他把这封电邮转给斯图尔特太太。她今天没来上班,说是去做产前检查了。
课间时分,兰库先生在走廊里跟路过的老师和学生打招呼。他知道他们背后叫他浣熊先生,他不大喜欢这个——浣熊是种狡猾的动物,但也没关系。他相信他们是喜欢他的,至少,大多数吧。至少,以前是这样,现在不能说还和以前完全一样了……不管怎样,他在这个学校已有二十五年了。棘手的事越来越多,就是这样。你不可能等到一切都顺利,才开始生活。
一群女孩围在一起,站在路中间,叽叽喳喳说着什么。他从她们身边绕过去,有个孩子低着头,从女孩子们的另一边绕过去,脑袋都快垂到腰上了——是那个国际学生亚当·黄。他的眼镜掉在地上,他匆匆忙忙拾起来就跑了。兰库先生想叫住他问问,但想想还是算了。
放学之后,他远远看到那孩子在操场边上。他一个人坐在树荫下,低着头玩手机。兰库先生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亚当,你还好吗?”那孩子茫然地抬起头,看见他,吓了一跳,想赶紧把手机藏起来(学校规定,校内不能使用智能手机),脸上浮现出战战兢兢的笑。兰库先生瞟了一眼,是一些短视频。他在男孩身边坐下,问:“还不回家?”“哦,他们会晚点来接我。”亚当扶了扶眼镜,关掉了嘈杂的短视频,看副校长不在意,这才放了心。
兰库先生微笑着看男孩,“身体完全好了?”孩子点点头。操场里还有些学生,在大太阳底下追逐玩耍,他们的嬉闹声很响亮。一阵热风吹过。男孩低头蹭着脚下的石子儿。“这棵树,”兰库先生说,“我记得是在我来的那年种下的,二十五年了,你看,它都长这么高大了。”男孩抬头看树顶,“它很高,在它下面很凉快。”他说,光斑透过树影在他的脸上摇摇晃晃。
“我告诉过你的,我去过中国。”兰库先生说,“那真是个不同的国家,很不一样。”他找不到确切的词来形容。他感到这是一次机会,于是问男孩:“告诉我,你喜欢加拿大,喜欢阿尔蒂诺中学吗?诚实地说吧。”男孩的脸色阴沉下来,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过了一小会儿,他说:“不喜欢。”很小很小的声音。
兰库先生拍拍男孩的肩膀:“我明白那种……到一个陌生国家的感觉。亚当,你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搓着双手,提醒自己,语气尽量柔和。男孩仍不看他,垂着眼睛,嘴唇抖动,也许想说什么,然后才有点慌乱地点头。他不知道和副校长做朋友是怎么回事,他自然更想和同学们做朋友。
“我刚来的时候,学校没这么多学生。那时我是数学老师……”兰库先生正说着,见男孩伸直脖子,抬头望着学校栏杆外面的马路。一辆白色特斯拉徐徐停下,是接他的车来了。也许是艾琳娜,或是她丈夫。“他们总是这么晚来吗?”兰库先生问。“吉米今天有课外编程补习……”男孩话没说完,就咬着嘴唇,冲到烈日下面去了。兰库先生等着他回身挥挥手,但男孩没有,他穿过操场,出了学校的后门,头也不回地跑到特斯拉旁,钻了进去。
兰库先生站起身,走回办公室去,想着还有几件事没来得及处理。斯图尔特太太很快要休产假了,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做,而她选的代理校长却是别人。他明白,是自己老了。
“再干三年就退休了。到时写本书,写写这些孩子们,”他走进教学楼内,突然这么想。“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到时又忙着别的。”有个女孩正向外跑,差点撞到他。他赶紧伸出一只手扶她。“哦对不起,浣熊先生!”女孩笑着,头也没回地冲了出去,完全没意识到她说漏了嘴。
浣熊先生耸耸肩,尬笑片刻。秘书格利亚正巧路过,她冲着鬓发斑白的副校长眨眨眼,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