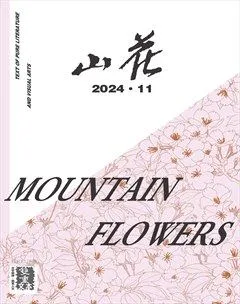醉坡浪
2024-11-20王彤羽
1
女人船在外沙桥停泊五日,林弋就醉了足足五日。让林弋醉的不是酒,是坡浪。
“晕陆不晕海的女人。”一说到林弋,外沙桥人都抚着嘴笑。通常只有首次出海回到陆地的人才会醉坡浪,而林弋,出海四年,一直没事儿,自从去年秋天那次返航后,一踏上陆地就犯晕,晕得比旁人厉害,更比旁人久。旁人晕个三五日便没事儿了,她要晕足七日才能缓过劲儿来。而女人船可不待她,只在外沙桥休息四五日便又出海了。这么一来,林弋脚踏陆地的那些日子就都是在醉坡浪中度过的。
外沙桥人都见过林弋醉坡浪的模样,有人啧啧称奇,有人说伤风败俗,有人明着指指点点,也有人偷偷学了她那姿态。可林弋对此不管不顾,照样打横了走,跌跌撞撞的鲁莽,扭扭捏捏的妩媚,眼睛随着身姿的摇曳顾盼生辉,说话还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像是真喝了半斤泡了海马的米酒。有一段日子,外沙桥的姑娘们走起路来一摇三晃,说话也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有心人一瞧就都晓得是学了林弋那丫头。外沙的长辈们对此是隐隐担心,逮着船长英姐就问她何时出海,巴不得林弋立马上了船,离了岸,这外沙桥才能清静。可女人船仍然停在港湾里,像两条沉睡的大灰鲸。
有人曾苦口婆心地劝林弋,你不是醉坡浪不醉船吗?回到船上不就不晕喽?林弋扬起醉眼矇眬的丹凤眼,双手叉腰,母鸡下蛋般咯咯一通笑,脸色一变说道:“姑奶奶我偏不上船,就堵这硌着你们的心,硌着你们的皮。”说罢她摇摇晃晃地离去,还甩了一方帕子,嘴里哼着咸水曲,如果抹上胭脂,倒真像戏台子上唱戏的青衣了。
而林弋远不似青衣那样的柔弱,她是女人船上名声在外的神枪手。那时正是海上的多事之秋,自从去年海上遇见美军飞机后,每次返航,武装部的人都带着女人船上这三十六个女人去练打靶。练归练,女人们心里难免有一个疑问——真要冲突起来,那把土掉牙的枪能顶得住飞机炮弹?疑惑归疑惑,打起靶来也定是不会有半点儿怠慢的。特别是林弋,练得比谁都狠,在海上打活靶她是一打一个准。非但如此,她还能以各种姿势射击,比如从这船过卡到另一船的同时,她还能保持很高的命中率。
外沙桥人常常无法把那个走路东倒西歪的女人和神枪手的身份联系到一起,觉得就像太阳和月亮,南极和北极那样的互不相干。长辈们嘴里夸的林弋和批评的林弋仿佛就是两个人,也许这才是他们能接受的事实。可后辈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无论是作为神枪手的林弋能做出这样的姿态,还是作为做出这样姿态的林弋恰恰是个神枪手,都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情。
2
林弋以前并不醉坡浪。女人船上的赤脚医生麻婶先前断言她是中了邪,病根是在去年女人船开往越南扁山取水的时候落下的。
“是吓出来的毛病。”雀儿很肯定地说。
“可也没见其他人吓出这毛病。”振西提出疑问。
“一起去取水的还有我呢,我就好好的。”二妮翻了个白眼。
“你还好好的?是谁发誓说宁愿变成一头海猪也不再去白井了?”雀儿抚嘴笑。
“这前有飞机炮弹后有鬼的,换成你也会惊死去。”二妮猛一跺脚,不乐意了。
最后还是英姐作了总结性发言:“林弋那丫头身体没毛病,是心病。”大家都点头表示赞同,而至于心病从哪来,一时半会儿又都说不清楚。
去年夏末,女人船去公海邻近越南扁山一带捕鱼,那次随船带去的淡水用完了,只好到一个叫白井的水源地取水。当地人都在那儿取水,从凌晨四点到晚上十二点都排着长队。女人船想去取淡水只能错开时间,在凌晨一点到三点的时候前往。当地人迷信,在那几个时辰里是不会去的,说阴气重,生人斗不过野鬼,去了怕是魂儿都要被收走。怕归怕,淡水还是要取的,船上没水可没法子生产了。于是,那夜十二点刚过,七个女人便坐着小船靠了岸,只留下阿水看守小船,其余六人分别挑了两个水桶,步行四十分钟到白井去。必经之路全是坟山,腐尸味一阵比一阵浓。女人船上的女人号称天不怕地不怕天王老子来了都不怕,唯独怕鬼。那夜里黑不溜秋,只有远远近近的鬼火一闪一闪的,似紧跟着她们行进。阿细姐胆子最小,一路脸色发白,牙关紧咬。她想说回去吧,可这话又实在说不出口,只能硬着头皮夹在几人中间机械地朝前走。
白井那一带全是大大小小的坟山,接水处被坟头包围着,要仔细绕开才能来到那地。出水也是小得稀奇,女人们蹲在地上一瓢一瓢地接,等接满了六桶就由三个女人先挑回小船,等她们再返回时,另外六桶刚好装满。这样两组对着走,节省了不少时间,但要挑满一船的水,时间就快到凌晨三点了。
那夜的水仿佛要捉弄这帮女人似的,水流越来越细,到最后一担时,半天接不来半桶。有一组人先行离开了,估摸着早已回到了小船,留下来的一组人是林弋、二妮,还有阿细姐。
二妮等得心里发毛,使劲儿踢了那桶说:“这水比尿还细,接个鬼。”
阿细姐脸色一变:“你说啥?”
二妮气头上又恨恨地哼了句:“接个鬼!”
阿细姐惊恐地看向二妮身后,那里闪烁着几团鬼火,像是越来越靠近的样子。她结巴了起来:“阿妈说夜里说不得那东西,你一说它就要来,还会一直跟着你。”说完尖叫一声抱头蹲了下去。
二妮被阿细姐此举吓得不轻,想回头看又不敢,麻麻刺刺的感觉从头皮一直蔓延到脚趾。“听越南船上人说这一带还有老虎。”二妮本想转移话题,不料却哪壶不开提了哪壶。
只听阿细姐拉着细细长长的声音哭了起来:“我怕鬼又怕老虎——”
“听说老虎还吃人哩,刚刚走过来时路边还有白骨。”二妮没心没肺地又补了一刀。
阿细姐干脆坐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哭声不大,却传出老远,但又像忽然遇了山,钻了谷,又或是被某个庞然大物给一口吞掉了似的,戛然而止。二妮上前一把按住阿细姐的嘴,说:“你作死啊,要真引来老虎,把你丢给它吃了换我们走。”
阿细姐气急,用力挠了把二妮的手。
二妮吃痛,回了她一巴掌。
俩人掐在了一块。
一直没吭声的林弋呼一下站起身,拎起水桶,把里面刚接到的小半桶水往她俩身上泼去:“要打回去打,离姑奶奶远点儿。”
俩人冷不丁被浇了一身湿,想发作,看看林弋铁青着的脸又不敢。
“我们走。”阿细姐似忘记了方才还在和二妮干架,扯了扯她的衫尾小声说。
二妮不作声,身上被浇了一身湿,心里赌着气,扁嘴瞪着林弋。
“都给我滚,省得在这丢人现眼。”林弋有些不耐烦。
阿细姐这时候也顾不得义气了,小声撂下了句“那我们先回船上等你”,便拖着二妮,挑起水桶飞快地往回走了。
3
白井一带静悄悄的,只有细细的水流往下淌时发出的微弱声响,但再微弱的声音在这夜里也显突兀。林弋警惕地盯着四周,耳朵敏锐地捕捉任何一个异样的声音。
此时水流变大了些,两个桶轮流着被接满了。林弋把桶挑上,原路返回。路上照样有鬼火跟着,林弋想唱歌,可喉咙像锈掉了,出来的声音又细又颤,像哭一般,反而增添了奇怪的氛围,便住了嘴。她绕过一个又一个坟头,碎步疾走,生怕水桶里洒出更多的水。空气里的腐臭味依然很重,她憋着气,怀里像藏有一个秤砣,压得她快喘不过气来了。
快了快了,凭直觉,离海边越来越近,林弋都能闻到海水的咸腥味了。此时,一道刺目的白光射向天空,把周围照得如白天一样明亮。林弋停下脚步,看向天空,愣了一下。接着她听见了“隆隆”的巨大声响,一个像大鸟的黑色物体向她冲来。林弋惊叫一声,马上蹲下。大鸟从她头顶飞过去,不一会儿又飞了回来,如此反复。当第二颗照明弹射向天空时,林弋终于明白自己是遇上美军的飞机了,霎时间吓得腿软,但越是想跑越是跑不动,双腿像被钉在了地上,肩上还挑着老沉的担子。此时飞机降低了高度,在她脑袋上方盘旋,扔下了一堆什么东西。林弋心中一慌,猜想这是向自己发射炮弹了,便闭上眼,绝望地等待着。等了一会儿,没听见爆炸声,反倒是有什么东西拂过自己的脑袋,也不疼,伸手抓来一看,是一些宣传单。
林弋回过神来,猜想对方也许并不想要她的命,她得趁对方改变主意前赶紧逃。这么一想便撒腿跑了起来,跑出几步,惦记着那两个水桶,犹豫了一下,又回头挑上了再跑。
美军飞机像和林弋玩起了捉迷藏,她往哪儿跑,它就往哪儿飞,仿佛林弋是斗兽场里的一只小兽。
桶太沉了,腿像被灌了铅。
快跑啊林弋。
跑不动了跑不动了。
听天由命吧。
林弋停了下来,撂下担子,弯下身体,双手撑着膝盖,抬头望向飞机,张开嘴巴大口喘气。
不跑了,不跑了,要杀要剐由你们。
飞机在她头顶停了一会儿,忽然飞走了,大约过了半分钟,又绕了回来,并对着林弋俯冲。林弋闭上眼睛,死就死吧,她铁了心。可飞机又飞了过去。然后她听见了枪声,就打在她旁边的地上,石块“砰砰”作响,泥土一片飞扬,碎石弹起击中了她,她哎哟叫出声来。
此时海边传来长长的鸣笛声,林弋猜测是女人船发出的。也许她们在找她,示意她快回去,也许她们也遇见了美军飞机。不,她不能死在这儿,死也要死在女人船上,而不是这里。林弋便又来了力气,挑起两个水桶,铆足了劲儿向海边跑去。
机枪还在射击,偏不打她身上,左几枪右几枪前几枪后几枪地和她闹着玩儿。她要边跑边判断下几枪会射在哪个方位,是前?后?左?右?然后决定跑快,或是跑慢;跑左,或是跑右。这些看起来没个准,却又似有一定的规律。每次,林弋都能逃过子弹,她不禁要为自己的好运气欢呼了。只是这一路她跑了个歪歪扭扭,头晕眼花,喝醉了酒似的。
终于在子弹的追击下,林弋回到了海边。
小船还在原地等她。
凌晨三时一刻,六个女人看见林弋挑着两个大桶,跑着“S”形的路线向她们冲来,她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挥手欢呼;当看见美军飞机在后紧追不舍时,几个女人又齐刷刷地卧倒在船板上。
林弋摇摇晃晃地回到了船上。胳膊、大腿,就连嘴皮子上的肉都在急剧地跳动着,她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仰面就倒了下去,不省人事。
“飞机呢?”醒来后她问小船上的姐妹们。
“飞走了。”
“什么时候?”
“你倒在船上的时候。”
对此,林弋百思不得其解,仿佛那夜她不过是做了一个荒诞的噩梦。而那次后,林弋落下了一个后遗症——醉坡浪。只要脚一踏上陆地就犯晕,就心慌,就摇晃。
她也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
4
女人船在外沙桥停留五日后,又出港了。女人船是一对185马力的机帆冰鲜船,由一条公船和一条母船组成,外沙桥人又将其称为对仔船,三十六个女人分成两拨在两条船上作业。外沙桥有传言说这些女人在海上如鲨鱼那样的凶猛,她们此次返航就收获了近十万斤渔货,把外沙桥的汉子们都比了下去。收成好,自然有额外的福利,每人发了五斤鱼。女人们高高兴兴地拎了鱼回家,或在岸边和其他回来的船交换了渔货。只有林弋,她拿到那五斤鱼,转身就换了酒吃。
你说我醉坡浪,姑奶奶我就真醉了给你瞧瞧。
每回上岸,林弋心里都会提前打起小鼓。别人下岸都如小鹿那样优雅地行走,她倒好,脚才踩上陆地就开始打醉拳。只要女人船靠岸,外沙桥码头便早早挤满了人,都看热闹来了。看女人船上的女人,看收成,还有的专门来看林弋醉坡浪的姿态,仿佛那比戏园子里的贵妃醉酒更有看头,比武松打虎更能上头。
林弋当然不乐意了,可也不能躲着不下船,你越躲,他们越是要看,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除非你一辈子不下船。一开始,林弋是借酒壮胆,仿佛观望的人群是吃人的老虎。可酒精一上头,管他是谁,不过是姑奶奶眼里的一只小病猫。尝到甜头后的林弋就和酒过不去了,下船喝,上船喝,白天喝,夜里也喝。一喝就醉,不管真醉假醉,反正醉态是名正言顺了起来,偏不让你等闲人看了醉坡浪的笑话。
这不,今儿女人船启航,三十五个女人早在船上候着了,左等右等,还没见林弋的踪影。
“定是又喝上了。”振西摇头叹气。
“五斤鱼也够她换酒喝这五日了。”二妮说。
“林姐姐喝了酒更勇猛,上杆过卡有如神助,连雀儿都比不过哩。”鸽子笑着说。
雀儿不乐意了,腮帮子一鼓,说:“那比比看。”
“林弋来了——”英姐打断了一堆女人的叽叽喳喳。
岸上,晃悠悠走来一女子,头戴垂檐海笠帽,看不清神态,身穿翠绿上衣和深蓝宽腿七分裤。乍一看,就一个地道的外沙桥女子,没啥特别。如果你盯上一阵子,名堂就看出来了——此人醉了个七荤八素的模样。虽为大脚,走路却不太稳当,一摇三晃的。马蹄袖唱戏般甩动着,手还得不时扶一把被海风吹得几欲翻飞的垂檐海笠帽。海边风大,衣裳全往女子身上裹,显出壮实健美的体型。走出那样袅娜且风情万种的姿态在外沙桥人看来也是新鲜,不知道的还以为哪家戏楼的花旦呢。最抢眼的是林弋手上拿着个绿得发亮的酒瓶,一时间你还真不晓得她是醉了酒,还是醉了那坡浪。
这光景就连女人船上的女人们也爱看。
“林姐姐也只有在岸上才像足一个女人。”鸽子抚嘴轻笑。
“船上呢?”二妮问。
鸽子笑而不语。
“像老虎。”雀儿想了想又笑嘻嘻地说:“这是外沙桥人说的,咱船上的女人个个是老虎。”
“呸。”阿细姐啐了一口,不高兴这称呼。
再看那厢,林弋准备过木板桥了。
醉坡浪的林弋最怕过木板桥。那是一截窄窄长长的木板,一头搭在船上,另一头搭在堤坝上。要是以前,小小木板哪能难倒林弋,闭着眼睛都能过。可现在,林弋一瞧那木板就怵了。
岸上人都在看好戏。
真是龙游浅海遭虾戏诶。
林弋已到了木板跟前。她低头盯着自己的透明胶鞋,犹犹豫豫地伸出右脚。
她站上了木板。
好大一阵晕眩啊。
明明硕大一个太阳,却似有乌云盖顶,脑袋上方仿佛罩着一只大鸟,一只会发射子弹的大鸟。
她本能地抬脚想往旁边跨去。踏空了,身体猛然一个踉跄。
“落水,落水,落水……”岸上有人开始带头起哄。
林弋一扭颈脖,回过半截身子,把垂檐海笠帽一摘,露出黑里透红的脸蛋,竖起两根眉毛:“呸,想看姑奶奶笑话,除非龙王到了岸上来。”说完,把那顶垂檐海笠帽往船上一旋,帽子稳稳地飞落到甲板上,再拎起酒瓶子猛灌了最后一口,扔掉空瓶,把大辫子咬在嘴里,在木板上翻起筋斗来。
林弋几下就过了木板桥,并响亮地拍了几下巴掌,整理好衣裳,也不望人群一眼,挺起胸膛进了船舱。
岸上人这才反应过来,哪个哥仔又率先暴喝出一声——“好!”
林弋回到船上,霎时间精神起来,说话大声了,走路利索了,也不晕眩了,大有蛟龙得水之势。
女人船此时也缓缓驶出了外沙港,向公海驶去。
5
此次女人船去的是河静与万里长沙一带。上次之后,她们也不敢再到扁山,宁愿在沿岸一带接一些牛窝水、水沟水和石隙水。水收集回来后不能立即喝,要用布过滤澄清后才能饮用。她们宁愿多做几道工序也不肯再到白井取水了。
第一周顺风顺水。
那日,天气格外的好,海面风平浪静。女人船已经下了三次网,有一网拖了大约四十石(每石一百斤)渔货。第四网已在海底拖了近三个小时,还有两个小时便能起网了。此时已是深夜,劳作了一天,大家都累得不行,女人们便轮流值夜,林弋是其中一个。鹂娘是女人船上的大副,是响应时势头一批跟船出海的女人,她三十出头了,已是两个娃的妈。几个年轻女子喜欢围着她有一句没一句地唠着闲话。
“鹂娘,给我们讲讲你刚上船那会儿的事情。”鸽子说。
“她们几个都听过无数遍了,耳朵怕是都起老茧喽。”鹂娘笑起来眼眯眯的,旁边有几道深深的皱纹。
“我们爱听,多少回都不腻。”阿细姐最爱卖乖。
“对。”振西说。
“也没啥好说的,就是我们那会儿没有现在这么开明,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传遍了外沙桥,可女人上船仍然像个笑话。我是头一批上船的,那时我才十八岁啊,和你一样。”鹂娘看了鸽子一眼,接着说,“组织上把我们这批人送到海南学习下网和起鱼这些捕捞技术,很快就上船实习了。当时是有男同志跟船出海的,船上的大工,副大工和桅尾工这些技术活还得男人来做。第一次出海一共三十一人,其中就有十个男同志。那时候没人看好女人船,反对的声音一大片,还分给了我们最旧的船,不光旧还渗水,没风没浪时一天也要舀三四次水,遇到刮风下雨就不得了了,这船就像个聚宝盆,总有舀不完的水,有时一天要舀一千多斗水。那时候连一件雨衣都没有,浑身水淋淋的,只能硬挺着直到风雨过去。忙乎一天下来,大家甩着那两条胳膊像甩两根袖管一样,都不是自己的了。在船上干的都是体力活,上船的如果尽是些弱妹子,台风一来,少一分力气就多一分危险,所以挑第一批女人上船的法子就是和男人掰手腕,很多男人掰不过我。我七岁就去做背篓妹帮补家用,就是帮人一边背小孩,一边煮饭,打小就练成了一般人比不了的大力气,可别看我瘦,当年比拔河,两个年轻人都拉不过我哩。”鹂娘豪爽地笑了起来。
“鹂娘,给鸽子讲讲台风那段。”阿细姐插嘴说。
“对于女人船上的人来说,遇见台风都不算是啥新鲜事喽。说来也是奇怪,其他船经常有翻船死人的事情,女人船又旧又烂,反倒是每次都有惊无险,可能是老天爷不敢收我们这帮拿命去搏的女人吧。”鹂娘抚嘴笑了几声,接着说,“我们那时的船可不比现在的,一来台风,海浪全往船上扑,海水积得把船板都浮了起来,船随时会下沉。我们是一人分身好几人,要忙着舀水,要抢救船板上的物资,要一会儿升帆一会降帆,还要把被海水浮起来的船板捆起来,稍不小心就要被海浪卷进海里。船头一直被海浪压得浮不起来,都以为没命了,可还都不想死,只能拼命地往外舀水。最怕的就是在台风天过卡到对仔船上帮忙,你想啊,那可是两只在滔天大浪中摇晃不定的船,要从这船荡到另一只船去,技术不好或运气不好随时会撞上船帮,或者掉落大海,能活下来的都是艺高胆大的。”
“女人船出海至今不但从未翻过船,每次都有大收成,后来外沙桥人都刮目相看了。”阿细姐想了想,憋出了一个成语。
“可不是?谁说女子不如男。在船上,男人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不比他们差。为了尽早在新的工作岗位多作贡献,女人船几乎不抛锚,白天黑夜都作业,任那艘旧帆船漂到哪儿算哪儿,所以我们的产量在所有渔船里面是最高的,这就活生生堵了那些说闲话之人的嘴。”鹂娘吐出一口气,脸上一副自豪的模样。
“接下来就到结婚生娃了。”阿细姐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抢着说。
鹂娘叹了口气说:“结婚后一切都不同了。我男人也出海,对于我来说,家就意味着在不同的船上吃苦。我返航来他出海,一年下来也没见着几回。这还不是最难的,难的是后来生下了海螺妹,丢下不忍心,带着也不省心。我那会儿也是倔,孩子还没满月就带上了船,一直到现在,只在生老二那会儿下船了两个月。海螺妹今年六岁了,从出生就一直跟我出海,遭罪啊。”
“还好这船上的娃都不孤单,都快能组成一个排球队了。”振西说。
“明年海螺妹就到了上学的年龄,我男人还在另一条船上待着,老二一直让他姨婆照顾,再把老大撂过去他姨婆一个人怕是忙不过来。我明年还不晓得能不能上船哩。”鹂娘眼眶一下子红了起来。大家都晓得女人船对鹂娘意味着什么,一下又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语,都沉默了起来。
一直不说话的林弋这时开了口,她说:“鹂娘,你跑船十几年,遇见过多少回美军飞机?”
鹂娘想了想说:“也有过五六回了,每回都想着没命了,每回又都活了下来。”
林弋说:“害怕吗?”
“怕得要死,我们都是砧板上的肉啊,真是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几十个女人手拉手站在甲板上一起喊口号,那腿抖得像筛糠一样,可越怕就喊得越大声,几十个人这么一喊,像打雷一样响,可以壮胆。”
“如果再遇见美军飞机,还会害怕吗?”林弋又问。
鹂娘认真地想了想说:“会,但现在的害怕和以前不一样了。”
林弋说:“哪儿不一样?”
鹂娘叹了口气说:“海螺妹在船上哩。”
大家沉默了好一阵子,只听见海浪轻拍船舷,船儿轻轻地摇啊摇,摇啊摇。
振西哼起了咸水歌——
煮熟弹虾一身红
船上女人乐融融
飞机炮弹掉落海哩
当作烧炮轰隆隆
……
一时间,几个女人又笑成了一团。
6
凌晨一点,海面黑如生铁,反出钝钝的光。耳朵习惯了海浪微弱的翻卷声后,如不刻意听,反倒听不见了。船舱里的女人们熟睡着,值守的几个女人开始犯困,没有精神再说话,只在甲板上偶尔走动巡查船的状况,望一眼海面,关注着那一拖网,还有半个时辰便能起网了。
此时,一道刺目的白光射向天空,照亮了整片海面。
“美国佬飞机!”振西眼尖,看见三个巨型黑鸟向女人船飞来。
“我们被包围了——”阿细姐尖声叫道。
随着又一个照明弹射向天空,她们才发现四周海面还有十几艘军舰在靠近。三架军机在头顶盘旋,强大的气流把风帆吹得呼啦作响。其中一架飞机离她们很近,能看见穿着棕色飞行服的飞行员。飞行员瞪大眼睛看着船上的几个女人,嘴里喊着什么。
“林弋,降帆。”
“阿细,把大家叫醒。”
鹂娘一边观察,一边喊道。
把女人船团团围住的舰队不肯离去,也不见有进一步行动,只是一会儿亮灯,一会儿灭灯,一会儿发射照明弹,不知意欲何为。
此时英姐已带着一帮女人来到甲板上。
“振西,加大马力冲出去。”
“林弋,断网爪,掉头。”
英姐果断下令。
那厢,对仔船已率先断了网爪。林弋和另一水手各拎起一把斧子,冲上去飞快地斩断网爪。
女人船开始调头突围,可多次尝试,也未能冲出包围。对方只围不攻,你快,他也快,你慢,他也慢,双方就这么你追我赶地在海上跑了一个多时辰。就在女人们疲惫不堪打算放弃突围时,飞机开始扫射。
先是船头被射穿了几个洞,接着飞机俯冲射击右船舷。船上不时传来尖叫声和哭喊声。
“二妮,升国旗——”英姐喊。
二妮跑进船舱取出国旗,和鸽子一起冲向桅杆,把国旗绑在绳子上。可国旗还没升到顶部,飞机再一次俯冲下来,子弹打向桅杆,接着飞机又向船尾飞去,扫射挂在那里的救生艇。
船舱里的五个小孩此时已从梦中惊醒,跑到了甲板上。几位母亲正在各种忙乱,没发现他们,他们便随着飞机从船头跑到船尾,又从船尾跑到船头。娃娃们不懂害怕,反而觉得新鲜,像做着游戏一般的欢乐,好几次子弹就和奔跑的孩子们擦身而过。
“船体打破了,大家快舀水。”
“鹂娘,林弋,把小孩赶回船舱。”
英姐的声音传来,打在了鹂娘的心头上,第一次令她感到了恐惧。她扑向在甲板上四处瞎奔跑的孩子们,母鸡护小鸡一样一把抱住三个,连推带拽地赶进了船舱。林弋也一手拖住一个,一边哄着一边硬拉回了舱里。
船舱里,鹂娘示意林弋一起帮忙,手忙脚乱地给五个小孩每人套上几件衣服,每件衣服的口袋里都塞上一点钱,胡乱缝几针,再把两个灯光船上用来做浮标的塑料桶绑在他们的腰间。
做完一切后,鹂娘声音哆嗦而又坚定地对他们说:“如果一会儿船下沉了或是起火,一定要跳进海里,朝陆地的方向游去。不管到了哪里,用口袋里的钱买点东西吃,再想办法回家。”完了她让海螺妹背了一遍家里的地址,亲了亲她的额头,才狠狠心回到了甲板上。
几个腰间绑着塑料桶的小孩茫然地站在船舱里,空间显得拥挤起来。
“姐姐,我们会死吗?”三岁的小海牛瞪大了眼睛奶声奶气地问林弋,脸颊上出现了两个可爱的小酒窝。他并不晓得死亡的含义,就像在问什么时候回家一样。
林弋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倒是五岁的黄鳝仔像小大人一样认真地说:“不会,但会泡在海水里,就像平时我们游泳一样。不怕,我会保护你们。”
其他小孩用力地点头,向他靠近了一大步。
林弋朝外面走去,一个稚嫩的声音从后边追了上来——“姐姐,你告诉我妈妈我在海里等她。”
林弋回头看去,是海螺妹。海螺妹眼里闪着泪光,但脸上还在努力微笑。“好——”林弋心里猛然一紧,在泪水涌上眼眶之前跨出了船舱。
她朝驾驶室奔去,如一头被围猎的公牛,生怕自己还没到达便被击倒。心在怦怦乱跳,不在胸腔里,几乎是在嗓子眼那儿,一下又一下地急速蹦跶,妨碍了她的呼吸,她一边跑一边大力咳嗽起来。
“林弋,别过来,这里危险!”掌舵的振西发现了她,大声吼道。
驾驶室的上空,飞机像一只巨鸟俯视着她们。
林弋不管,她蹲下,翻箱倒柜,找着什么。
找到了。
林弋的手触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冰凉的,硬硬的。她把它揣进了怀里,左手环抱胸前用以掩饰,右手伸进怀里握住了它。
然后她站直了身体,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飞机上的飞行员,怒火像快要从眼里喷射出来一般。
“你疯了,别挑衅他们。”振西冲她喊道。
林弋右手握着那个东西,忽然就来了底气,她像石头墩子那样站着,保持着先前的姿态,脸上露出一丝奇异的笑容。
“我有枪。”她低声对振西说。
振西愣了一下,终于明白过来。上次遇见美军飞机后,武装部不但训练这帮女人打靶,还给女人船配了一把手枪,放了有大半年,一直没用过。
“他们人多,我们只有一把枪,冲突起来我们死定了。”振西说,她用眼色警告林弋不要轻举妄动。
林弋的眼眸闪动着,她知道振西说的有理,可她又不甘心。自从上回在扁山遇见美军飞机后她一直不甘心,可不甘心什么又说不上来。外沙人都说她命大,在敌机枪口下死里逃生,只有她知道当时有多害怕多狼狈。她在心里已经觉得自己死过一次了。她拼命练枪法,为的就是等这么一天,可当这一天到来,她发现自己连把枪掏出来的机会都没有。
不,她不甘心。
飞行员似乎也发现了驾驶室里这个奇怪的女子,嘴里似乎嚷嚷着什么,并做着让她走出来的手势。
正好,姑奶奶正想出去呢。林弋心想,她不顾振西的阻拦,走出驾驶室,直挺挺地站在甲板上,左手张开护着腰腹部,右手伸进衣裳里握住手枪。
“不要挑衅他们——”英姐的声音传来。
十几个女人的眼睛都瞪着林弋。
飞机在头顶上盘旋。
“不能连累她们。”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林弋快速地朝桅杆跑去。
飞机开始向她射击,林弋没有停下,也没有躲闪。子弹却逗她玩似的,并没有打中她。
林弋跑到了桅杆下,左手拽起从上面吊下的绳子,右手紧握手枪,起跑,飞快地朝对仔船荡了出去。
子弹贴着她的身体射到了船舷上,射进了海里。
林弋的身体荡到了对仔船的上空,飞机追了过来。强大的气流冲击着她,照明灯刺得她睁不开眼。她果断地放开绳子,下跳,但错过了跳落的最佳时机。
她没有落到对仔船上,身体继续往下坠落。
她朝飞机扣动了手枪扳机。
她掉进了海里。
她确定自己听见了枪声,孤单而又清脆,像小时候用筷子和竹筒做来打小仗的噼啪筒……
半个月后,女人船回到了外沙桥。遭遇美军飞机和军舰却无一人伤亡,使得女人船再一次引起了轰动。据说那一夜,女人船把敌人耍得团团转,最后在黎明时分成功甩掉了他们。当然,这是外沙人自己编的故事,后来还改编成了粤剧在禧园上演。
那次后,外沙人发现,林弋再也不醉坡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