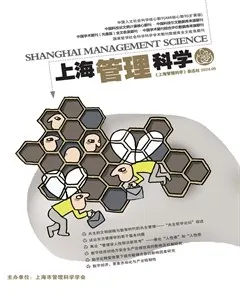共生的文明探微与数智时代的共生管理
2024-11-01陈春花乐国林秦子忠
摘 要: 数智技术正在深度推动社会加速演进,人类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前所未遇,“共生”是应对挑战,化危为机,促进社会与文明发展的重要选项。共生源于人类最本源性的共同价值基础,要在差异化要素的有机聚合中建立积极的文明共生。共生在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存在文化差异甚至冲突,而人机的共生关系和共生的心智逻辑在AI技术条件下具有更加复杂形态和运作形式,由此基于价值理性与整体协同的共生管理与治理孕育而生并有待系统研究。我国的文化传统蕴含丰富的共生哲学思想和管理智慧,可为当前人类发展的时代危机贡献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 共生;哲学;文化传统;AI;管理
中图分类号: C 93-03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2024-07-04
作者简介:陈春花(1964—),广东湛江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组织管理、组织数字化转型;乐国林(1975—)(通信作者),男,江西抚州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战略管理、企业文化;秦子忠(1986—) ,男,海南东方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人性-心智哲学。
文章编号:1005-9679(2024)05-0001-07
Exploration of Symbiotic Civilization and Symbiotic Management in theAge of Intelligence—Overview of “Symbiotic Philosophy Forum”
CHEN Chunhua1 YUE Guolin2 QIN Zizhong3
(1.Shanghai Chuangzhi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2, 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266520, China;3.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re deeply promoting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society.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human development are unprecedented. “Symbiosis” is an important option for responding to challenges, turning 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Symbiosis originates from the fundamental common value founda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positive civilized coexistence through the organic aggregation of differentiated elements. Symbiosis exists cultural divergence or even conflicts i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countries, and regions,and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cognitive logic between humans and machines in the AI technology condition have morZrThv485YVB5MtCnrSITu95m13mC+XIG3NZIeQWdJss=e complex forms and operational modes. So based on value rationality and overall coordination, Symbiosis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have been emerged and need b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contain abundant symbiotic philosophical ideas and management wisdom, which can contribute wisdom and strength to the current crisis of hum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symbiosis; philosophy; cultural traditions; AI; management
数智技术正在深度推动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世界变局也在加速演进,人类生活的诸领域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前所未遇之危机。“共生”或许是我们化解这一危机的正确选择,机械时代的“普遍性”,将被异质文化共生的时代所替代,并有可能成为当前这个时代的新秩序(黑川纪章,2009)。在此背景下,一场关于“共生哲学”的跨界交流论坛于2024年3月16-17日在上海创智组织管理数字技术研究院进行。论坛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海南大学等高校的哲学、管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26位专家学者进行跨界的思想交流。论坛划设有“人机共生”“心智共生”“文明共生”三个主题,但在实际的分享和交流中,三个主题的边界被打破了,“跨越穿透”“交替共进”成为共生哲学论坛的“共生行动”。本文回溯三个主题的交流讨论,以论坛的“哲学”特征为开端,以跨学科的宽度展示学者多角度对共生的交互问学,把管理之论作为专家落实共生的管理求解,对本次论坛的成果进行综述。
1 共生:人类文明发展的恒久主题
1.1 共生的源流
“共生”(Symbiosis)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始于19世纪晚期,但人类社会对于文明进步的共同追求和共生发展的活动却是古已有之,并且不断更新发展,可以说共生是“一切文明实践的底色”。海南大学贾冬阳通过对“共”与“生”的中国古文字学的考据为共生的“一切文明实践底色”提供了文字考古语料支撑,他据《说文》和两个字的古体字形演变,指出“共”有“祭祀敬奉,交互拱卫”的征象,“生”为出土上进,“依时而变”之状。两者并合,乃“立足自身,独立而互补,与时偕行”,这反映共生在人类早期文明发展中已经暗合道妙。而中国国家博物馆郭海潮以考古图像和文明物证为线索恰好展示了人类文明从早期产生到文明交汇和文明共同成长的进程,例证了古老文明超越时间、空间限制与当代现实共生的实情,展示了文明的交流与交融是文明的本能。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共生来源于人类最本源性的共同价值基础(尾关周二,2003),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共生,“共生”是人类走向成熟的必修课,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这是论坛的广泛共识之一。
1.2 共生的哲学理据
陕西师范大学袁祖社认为世界的本质应该是相濡以沫、互生共享的有机共生体,自然、生物、植物、动物都应该如其所是、如其所应。自然界的共生遵循的是古典经济学哈耶克所讲的自由秩序意义上的自生自发的自然演化逻辑,而在人类社会中,共生关系具有仿生学意义,共生体、共生态、共生力以及各种复杂关系网络的形成,都是我们人类主观性的或者理性自主建构的逻辑。海南大学秦子忠从文明的历史演化与跨文化比较角度,提出文明的图式至少包含人造器物、社会秩序、身份认同与价值信念等维度,可作为文明共生的理论分析的维度,化解文明的冲突主要在于去除任一维度的排他性,重建这些维度的关联性,而人工智能时代,要关注共同体(组织)随之新旧交替,身份认同成为可选项,使心智共生与文明共生互为表里。北京大学李四龙认为人类社会的共生需要夯实理论基础,“和实生物”中的“和”,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哲学基础,8f2d7b55a67313e69127d449d48a899d是共生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阴阳五行的交感互补,是本体论层面的共生哲学基础。
进一步,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明进步需要共生。人类是有限理性的,它所部分认知、所理解和把握的群体间的价值生成,需要通过共生才能汇聚无数的有限性使人类适应自然和宇宙的无限性,这样才能促成自身的进化和共创文明的繁荣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世界、历史社会实践的本质都是基于共生、拟共生、向共生而生成。海南大学程志敏从人类的成长成熟角度指出,人类需要“共生哲学”,深入理解并学会“共生”,人类才能稳健成长,人类社会才能渐次发展成熟“长大成人”,反之则可能还等不到“长大成人”,就会夭折。不过,从现实来看,人类至今还远未成熟,其欲望的自我无限膨胀和狂妄理性的反噬,使人类社会遭遇多次浩劫而面临生存危机,要走出危机“长大成人”,只有真正开始自我降低身位,以共生之心理解这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存的根基和意义,才能重回正轨。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则进一步将人类的共生问题提升到人类正义的高度,他借用罗尔斯正义不是从某种完备性学说(宗教、道德、哲学)中推导出来,而是公民运用“公共理性”所达成的“重叠共识”之观点(钟英法,2006),提出共生文明基于诸文明,但不是诸文明的简单加和,也不能从现有诸文明中的任何一种文明中简单推导出来。它是超越冲突之诸善的公共善,是从作为“多”的诸文明中达致的公共性的“一”。正是由于文明共生生成的公共性,因此,共生成为人类社会的正义之所需。
综上,现代“共生”的哲学核心可能是一种互利共生现象的哲学抽象与概括(袁年兴,2009)。共生是自然演化的重要逻辑,也是人类“长大成人”的成长逻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公共正义”。就人类身处技术理性泛滥、资本逻辑横行、霸权依然恣肆的新全球化时代而言,也许我们最缺少的、同时也是最需要的就是“共生智慧”。
1.3 文明何以共生:共生可行的关键
共生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甚至是世界的本质,人类需要以共生之姿态自生、互生而“长大成人”,那么人类社会何以做到共生,在共生道路上应注意或应避免什么,这是共生哲学关注的重要课题。
袁祖社认为共生应遵循人类公权力、人类共同福祉这个最大化的基础,文明共生的最理想的、最原本的形态就是未来社会超级信息的智能原模态共生。进一步,文明共生的存在逻辑是差异化要素的有机聚合的本体性表征,文明共生的实践逻辑是确定性目的驱动下的多主体、主体间性的一种交互生成。从自然角度来说,理想的共生关系遵循存在整体性、过程有机性、要素并在性、机体互构性、自主纠错性和价值共享性。沈湘平教授认为,共生文明本质上是人类众道之公道,是人类诸文明之公共文明,我们要避免消极性文明共生,要以差异性文明存在为前提,以更好共存(公共美好)为目的,要靠一种文明间性(Intercivilizationality)的共生文明来保障,用人类整体的视野和情怀、人类共同主体的自觉、人类原则高度的规范来建构积极的文明共生形态,这是人类避免危机、自我拯救的积极谋划。程志敏教授聚焦达到“共生的前提”,他指出人类共生的发展需要3个前提:超越论前提是整体、大全、天道、宇宙、世界,对于西方来说甚至是神,共生必须在这样一个“场域”里面,并且还要承认在这个“场域”中,有比我们每一个共生的个体更高的存在,所以需要降低人的位置;存在论前提是我们该如何活着、如何存在,共生不是扁平的,而是全方位的,立体的,丰富的,充满活力的,“共”只是它的手段,而关键在于“生”,即富有生命力;人性论前提是人要成为“真正的人”,超越了“主客二分”的存在,一个齐物而无我的存在者,一个无限趋近神性和圣哲的新物种。我们需要降低人的地位,恢复天道的神圣性,才能构建生生不息的共生的新世界。
总而言之,在文明共生的路径探索中,要注意不是所有的“表象共生”都是真正的共生或者有价值的共生,要识别和区分“伪共生化”“虚假共同体”,识别消极文明共生与积极文明共生;充分重视文明共生的前提条件,要警惕多元主义将“存异”颠倒为首要目标,导致共同体的瓦解;要充分重视通过公民的“公共理性”建设达成文明共生的“重叠共识”,找到共同生存的根基和意义,使“共生”成为人类走向成熟的必修课(袁祖社、沈湘平、王志强、程志敏)。
2 AI时代:人机共生与心智共生的交互问题
随着AI技术发展,人工智能不仅在智力方面赶超人类,而且具有向复杂的心智、情感智能发展的趋向。这意味着,它的应用带给人类生活更多无限可能的同时,也在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霍金甚至发出完美人工智能的出现预示着人类终结的警告。由此,在AI时代,人类文明共生的主旋律离不开人机共生,和人、机器、组织之间的心智共生主题。
2.1 人机共生的哲学思考
人工智能是人类思维程序化的形式系统,其智能进化方向,既取决于以文本知识呈现的文明性质,也取决于以意识观念呈现的思维形式。2024年2月,OpenAI发布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即以“从Sora到元宇宙:重思人与后人类”为题,认为Sora为我们理解人与后人类的“共生”提供了全新视角。Sora能够生成60秒连贯性视频使世界被“压缩”,然后重新生成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世界。Sora的能力意味着它既能理解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则,也能理解人类互动的方式。作为“世界模拟器”的Sora,使得世界的生成成为可能。这意味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并不仅仅是物理的,同时也是生成性的——人类与后人类的共同生成,因此人机共生至关重要。南京大学蓝江借用电影《机械公敌》和数字社会中机器“监控”“指挥”外卖员、白领的例子,并引述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的观点,反思人和机器的博弈关系,任何新技术的产生都会摆置(Stellen)、订置(Bestellen)、促逼(Herausfordern)人类的存在。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反思以理性个体为核心的主体理论,不能将人与智能体看成竞争和博弈关系,而是要看成共生关系。进一步,共生的哲学关系不仅仅是主体间性,也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需要建立人与物、人与人和物与物之间物体间性关系,才能重新思考在智能关系下人与智能体的共生哲学。未来万物互联下的生命形态,是人与非人行动元在数字生态的共同进化。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则针对AI植入生命体大脑中的人机关系进行哲学思考,他以“脑机接口”——脑控、意念控制来概括这一人机生化物理形式,认为其根本意义在于人机融合主体的出现,它的主要风险在于改变了现有人类主体的存在方式。
2.2 人机关系的共生求解
在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来临的AI时代,人和智能机器人的共生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能够有质量的共生,或者共生的地位与身份不会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人机共存后,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在人机关系中人类如何看待自我概念,机器人有无“自我”,人类中心主义是否还要/能否维持等(乐国林、程广云等)。面对这一现象和问题,程广云提出要跳出“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跳出“主体和自我”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叙事策略,以“可能世界”的“反事实”的思维模式,为人机共生重新绘制可能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图谱,我们的科学工作、哲学工作就是要去发现世界图谱,这是AI时代未来哲学的任务。上海创智组织管理数字技术研究院陈春花认为AI的出现对人与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当前数字智能技术降低了人人可及“意义的空间”的门槛,促使人感受到须要通过人际互动才能确定“此在”的意义地基。由此,人的生命运动过程从有限运动到了生命的无限可能性——生命的时间意义具有了无限“打开性”,个体的内外部的“意义”评价,要求由其所在或参考的“文化坐标”来决定,突破人、组织、时间、空间的限制并使之达于共生,人人可创造新的价值空间、意义空间。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则提出要通过大学的教育改革、打开边界、创造性思维来提升AI时代人的能动性,要让AI拓展人类的知识领域,使人更具有创造力,大学教育改革应重视知识的民主化,解放人的心智、释放内在潜力,形成独立人格、道德价值,并具备创造性思维和行动能力。
越来越高能级的智能机器人的出现,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类的世界,也改变了“想象的世界”甚至宇宙的世界(吴冠军),要建立新的主体间性来求解人机的共生关系。蓝江指出人类社会很可能进入后人类时代,“主体间性”的主体身份、跨主体关系的结构与内涵都将发生变化,不仅人与人之间,而且人机之间、(万物互联的)物物之间都存在“间性”关系(蓝江),这将是一种巨大的变革。进一步,AI引起的人工智能伦理、管理伦理问题应引起专家的关注。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陈凯先在“人工智能对生命科学发展”的分享中指出人工智能既可能对科技进步和新一轮产业变革带来有力的推动,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始料所不及的影响,如:人工智能对人类自身、社会职业分工、教育、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的影响。南京大学的蓝江、复旦大学的苏勇都特别提到机器(人)对人的工作监控、管理及“(算法)算到骨子里”的实例,无不显示对人机共生的“伦理治理”规制多么迫切。认为AI的发展不能再翻版“泰勒制”问题,数据不能漫无边际地获取,模型不能不加限制地运用,要考量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祛除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要对AI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伦理规制,实现AI时代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价值共生。
2.3 心智共生的心性和间性问题
《江海学刊》主编赵涛以“全球脑,心智共生的最终归宿?”为题,对心智共生领域做了主题分享。他首先梳理了全球脑的思想来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和中世纪,正式提出则是1983年的英国学者彼得·罗素,是指一个关于分享人类知识,所有人类智力的思想、创新和发明的总和的概念。在AI时代,人工智能将会超越人类智慧,人类个体有成为人工智能外设的趋势。这种情势下,全球脑可能对个体认知主体地位造成影响,有可能导致人类思维能力闲置,可能会摧毁人的原创意识,人类要规避或最大限度降低其负面影响。当然,全球脑绝不仅是对个体认知带来巨大冲击与挑战,它也改变了知识的出场方式、表达方式、布展方式和生产方式。秦子忠认为人类心智的内部是与人类生命体同在的思维空间,其外部是关联于生命体的文明空间。在当前的数智时代,人工智能作为思维空间的程序化,表现为代码系统与海量数据,它的加速迭代正在推动着社会秩序演化,共同体(组织)随之新旧交替,在多重共同体中,身份认同成为可选项并与个人的价值信念关联在一起,而“共生”在这个多重演化中则是信念的取向,由此心智共生与文明共生互为表里。
“主体间性”一词是这次研讨会中学者(陈春花、蓝江、乐国林、郭毅等)用来描述、分析人机共生、心智共生甚至文明共生中的心性哲学词汇。蓝江教授提到要把“人类主体与智能主体”之间的互动纳入到伦理与法律程序之中;青岛理工大学乐国林关注到AI智能化、自主性不断升级中人机之间的“主体间性”将带来的身份与心理“同一性”危机;华东理工大学郭毅基于主体间性探讨AI时代组织管理的心智共生。扬州大学吕力引述新儒家牟宗三的“心”有五意:心体、心能、心理、心宰、心存,提出创造儒学中的心智共生理念。东北财经大学巩见刚则聚焦心智共生中的“人性”问题,主张以儒家的“性善论”作为心智共生的理据,并以东西方人性假设的比较和批判性分析肯定性善论的全面与深刻;程志敏把人性论视为文明共生的前提之一,要压制甚至消除人身上的兽性,挖掘和发展神性,使人成为“大写的人”。
3 共生与文化传统
在此次共生哲学论坛中,专家一致认为文化和文化传统对共生的理解、共生理念至关重要,应该关注共生现象、共生行为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差异。与会专家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丰富的“共生哲学”“共生管理”“共生治理”的智慧。
3.1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共生智慧
“共生”在中国历史文化当中具有丰富的元素和传承,中国的文化传统蕴含着深厚的共生精神资源,无论是文明共生、人机共生、心智共生都能从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共生智慧。李四龙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生哲学”为题对此做了比较系统的分享。他以佛教的传入和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例,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异质文化共存,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难能可贵的,“殊途同归、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万物共生现象的理论概括,“共生”的基础应是“和实生物”,要寻找差异,只有在差异中才能创造新事物,要基于人文教化的儒释道三教合流,把世界观上的“互补共生”推进到伦理学的“会通共生”。中国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美美与共”等文化都蕴含着“共生”的思想和文化传统。
扬州大学吕力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出发,提出“创造儒学”的概念,指出(商业)儒学的创造包括“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成务,在止于至善”的精神之创造——“良知即创造”,“盛德日新月异、永不停息”的财富之创造,“开物成务”的器物之创造,“元亨利贞”的事业之创造。创造儒学的基本范畴“生生、日新、和合”与“共生”“创造”密切相关,可以视之为儒学视域下的“共生哲学”。东北财经大学巩见刚教授主张以儒家的“性善论”作为心智共生的理据,性善论在强调心、性统一的同时也辨析了彼此的区别,主张尽心方为知性,由此穿过种种表象看到了人性深处那份永恒的善。
3.2 共生的文化差异
文化的多元性让世界各地种族或民族之间的异质文化的文明共生变得更有生命力、更有价值共创性,然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价值观、信念、文化个性之差异,和不同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容纳性(彭小妍,2022),将可能使文化之间文明共生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调适。我们应高度重视共生的跨文化基础差异特别是共生的文明实践面临的挑战及风险。
复旦大学的黄洋以“希腊文明中的共生哲学”为题,从历史与哲学角度展示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共生”思想基础的薄弱,他认为尽管希腊古典哲学当中也有“共生”,如以斯多葛派创始人芝诺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中蕴含共生的理念,但是希腊哲学和思想的基本方式是二元对立的——如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共同体内部不同阶层的天然对立与冲突,希腊人世界观中的希腊人与蛮族人的对立。古希腊人的二元对立思想对现代西方人的思维产生深远影响,这是我们构建共生哲学和开展共生文明实践需要直面的挑战。沈湘平以东方文明是植物隐喻、西方文明是动物隐喻说明两种文明的共生文化的基础差异,西方更加倾向于文明的冲突,共生理念或许是实现利益的某种修辞或计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王志强编审指出,同质性共同体建立在实质性观念的强制之上,其维持团结的方式会抑制组织活力和进化;从共和原则出发,应承认共同体内的异质性共生,保护自由和活力。程志敏以哲学中存在论为例,认为西方的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存在和自我实体性,而中国文化的存在更强调利他之大德、生生不息的存在,如《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是造就“百物生焉”,《老子》的大道是“生而不有”,可见,西方文化更强调“自生”,而东方文化则蕴含“共生”。
4 共生管理:价值理性与整体协同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时代,人类在知识、智识和文明变迁方面面临共生发展的挑战,在社会生产、产业经济、商业组织方面面临共生管理的挑战。本次论坛围绕“共生”主题展开了组织、管理和治理方面的开放性探讨,具有了“共生管理”的思想意象。
4.1 共生管理的价值理性与共生治理
陈春花从共生理念的规范性维度探讨启题,认为组织不仅仅受技术环境的影响,也受制度环境的影响,当前数字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合法性”与发展空间具有“规约力”,即要求组织建立互为主体的关系契约、形成共享使用权的资源配置、信息共享和合理价值分配、建立内外部协同共生的大系统等。进一步,她基于斯科特的组织的制度三要素的规范性维度提出共生管理的四个理念:①互为主体,以主体-主体关系强化作为“共生理念”的出发点;②互作效用,多个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效应;③价值共创,两个或多个主体共同生活在一起,各方基于相互的依赖和生存而利弊平衡;④整体进化,各主体有更高的生存能力,导致种群整体适应环境的能力增强和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四个理念引领了共生组织在社会价值观与社会规范之约束的行为方式。华东理工大学郭毅从主体间性角度关注数智时代的科学组织与管理问题,他认为在“AI+”或“+AI”的时代,单纯依靠组织管理者“想出法子”,而其他人只负责服从、执行“伟大战略家”指令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真正卓越的组织,只会属于那些探索出如何让各级员工释放出最大潜能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以主体间性为视域,建立智者型领导:通过汲取个体或群体的“隐性知识”,化为有高共识性的组织知识,日积月累,会使组织获取高承诺和高绩效导向的组织文化。他进一步提出基于主体间性的组织共生与协同要充分重视“场”的机制运作——“共享知识的动态语境或意义空间”的管理效能,包括成员的具身性的“场”管理、隐性知识在“场”中被激活、成员在“场”中分享隐性知识及其整合、成员在“场”中的显性知识整合。
《外国经济与管理》副编审宋澄宇关注共生管理的“价值共生”,他重点引述米塞斯的理论,认为目的世界的达成是人的主体性行动的来源和人的自由实现的基础,价值的产生和实现都与目的世界、目的自由息息相关,且目的价值高于手段价值。价值共生也要以目的世界的达成、目的价值的实现为目的,价值共生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价值互生”,它包括目的相生、手段相生、目的-手段相生三个条件,其实现的途径是价值交换和价值共创,前者作为手段,自愿交换能够创造价值,后者是个体或群体之间通过分工协作共同创造价值。他进一步认为价值共生实现的最合适的机制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经济是最精妙的价值共生生态系统”,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人的目的自由与手段自由的和谐共生,因为市场经济的自发的分工合作机制本身就是价值共生机制,它有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鼓励每个人通过分工合作获得更多资源和机会,从而拥有更大的目的自由和手段自由。因此,“为了实现人的目的自由,人类需要共同维护市场经济这个精妙的价值共生生态系统”。
在共生治理方面,乐国林以“AI时代人机关系的组织社会学思考:共生何以可能”为题,从管理学、社会学并兼及伦理学的跨学科视角检视了工智能技术不断向高级化、自主性发展中,人-机、人-组织、组织-社会之间关系存在的冲突、危机和治理问题。他提出AI时代的人-机之间的共生关系并不一定与人的“合意性”相符,而是存在角色关系与身份认同、人的自我效能、人机之间的“主体间性”、精神情感交互等问题;人-组织在加入AI机器人之后存在组织关系的解组与重构问题、价值贡献问题、规训控制与效率异化问题等;组织-社会层面的技术理性“僭越”与资本利润本性的“合谋”问题、阶层鸿沟扩大问题、“生活世界”空洞化与社会变迁方向问题等,然后他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思考人机关系良性共生的组织社会学对策。苏勇在“工具理性与价值共生”的分享中,提出对数字化进程中管理伦理问题的忧思,认为从科学管理角度来看数字化、智能化对效率的提升有三大利器:数据、模型、算法,具有非常强的工具理性,将导向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造成以算法“算到骨子里”的翻版“泰勒制”问题,甚至会发生如马斯克所说的人工智能未来会因为它需要完成一个目标而消灭人类的悲剧。据此,他主张要对AI的商业应用进行伦理治理,更要考虑价值理性和管理伦理治理要求,AI时代的企业要坚持四种价值观: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用户价值高于生产价值。
4.2 共生管理与文化传统
在共生的组织管理中与会专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内涵比较丰富的共生管理思想。江西财经大学吴照云首先对共生论坛在中国管理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做出贡献予以学术期待。其次他提出“天人合一”对共生管理具有非常好的思想启发性和指导性。天人合一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在“一”下才能谈共生,共生可视为“天人合一”下万物一体,没有比传统文化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更宏大的“人性假设”。共生管理要突破当代管理学中的“人财物”中的“人”是以“小我”的人性假设,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智慧,建立共生管理的“一”的稽式和模式。华东师范大学贾利军受益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道-象-器”的分层智慧,以中国营销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例,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整体论世界观、天人合一方法论内含的分层之学,更适合当代人类文明的共生融合性发展,有利于中国管理知识体系和理论的建立。
华南理工大学晁罡在“文明共生”视野下,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元素,提出 “天下格局”的管理观,通过对11位代表性企业家及其企业长达10年的跟踪调研,沿着“修身立德”“成就员工”“多方共生”和“天下为公”路径,创造性提出 “天下格局”这一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展现新时代的中国企业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和共生的社会责任感。“天下格局”是文明共生的一种立场、一种价值观,其多方共生的原则体现了共生管理的科学要求与伦理价值。“富民厚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北京大学尹俊研究员以“儒家传统共生哲学在管理学中的创造性转化”为题,详细分析了儒家的秩序观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从生产资料、交换、消费等多个维度指出,共同富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财富观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相互会通,均富共生。
5 结语
来自不同学科专业和工作背景的学者围绕“共生哲学”的论坛主题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带来了思想的智慧融合和知识共同体的共感,展现出不同学科在同一主题、同一问题上的独特角度、多元范式和学者智慧,成果超出主办论坛的预期。
尽管不同学科之间存在学科范式、概念不同和理论通约力的学科跨界难题,但是大家凭借“敞开”的心态,通过学科的“跨界过渡性”(MALDNEY,1991),探求学者之间、人机之间、组织之间、物物之间的多样化的“共生”关系,寻找人与世界之间的动感的、有生气的、多样化的“共生”之路(姜丹丹,2015)。正因为如此,本次论坛凝聚了许多共识性的观点或论题,例如:共生是广泛存在现象,在当下探讨共生具有现实必要性甚至紧迫性;共生尽管是人类的期待,但确实存在跨文化差异,文明冲突与文明共生就是对待不同文明关系的两种文化价值观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共生文化“矿藏”,对于共生管理学发展有文化优势;人机共生为人类发展打开了新篇章,但也挑战了人类的智慧、人类的主体性、人类中心主义;人机关系的发展亟须管理和治理;等等。
当然,一场围绕“共生”的跨界交流研讨,不同学科之间话语体系差异比较大,对话的难度高,彼此互动交流还不够深入;共生论坛虽然设计了“人机共生”“心智共生”“文明共生”三个主题,但一些学者交流的论题还不够紧扣主题,论坛议题发散性好但聚焦度还不高,期待今后改进论坛形式、提高论坛质量。社会学家、管理学家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自己的研究肯定还是非常不完善的。唯有凭借严格的专业化,学术工作者才能终有一天(也许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正充满信心地认可自己:我达成了能够流传千古的成就。”(韦伯,2020)我们期待“共生哲学”和“共生管理”可以成为一批中国学者创造传世成就的志业,达成“与共之美”。
参考文献:
[1] 黑川纪章. 新共生思想[M]. 覃力,杨熹微,慕春暖,等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49-53.
[2] 尾关周二.共生的理念与现代[J].哲学动态,2003(6):32-37.
[3] 钟英法.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2-57.
[4] 袁年兴.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J].湖北社会科学,2009(2):100-102.
[5] 彭小妍.何谓“跨文化”:自我与他者的吊诡共生[J].探索与争鸣,2022(6):132-138.
[6] MALDNEY,H.Penser Vhomm etla Folie[M]. Grenoble: Jerome Million:1991:306-311.
[7] 姜丹丹.世界与共生:亨利·马尔蒂尼的现象学思想之跨文化对话[J].哲学研究,2015(9):87-95.
[8] 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M].李菲,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