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现代性到崇高现代性
2024-10-29陈正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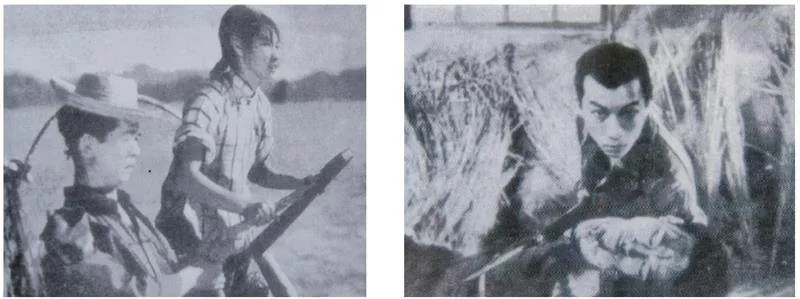
摘 要: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早期红色电影沿着思想启蒙之个性解放、国家寓言的革命抗争、抗敌救国的民族独立的现代性路径演进。这些电影饱含内忧外患时期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理想和美好愿望。具有进步思想和革命理想的电影人通过底层叙事、革命叙事和抗战叙事等叙事策略,表现特定历史时期从知识分子觉醒到工人农民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团结抗战的文化现代化路径及社会发展现实。审美表达上,这些电影以“人的解放”和“民族解放”此消彼长的螺旋双线进程表现了启蒙、革命与抗战的现代美学精神。
关键词:红色电影;底层叙事;革命叙事;抗战叙事;审美现代性
20世纪前期,当艺术家们自觉和不自觉拿起思想武器,利用艺术号召被压迫的人民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之时,艺术创作的主潮就从“为艺术”转向“为人生”。这种转向在电影中表现为从20年代的“影戏观”转向30年代的“武器观”。左翼电影与国防电影就是贯穿着“武器观”的典型艺术,这些电影作为中国红色电影的早期形态,虽然在主题思想和叙事视角上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红色电影不同,但其饱含的红色底蕴,为后期红色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电影与文学、音乐、戏剧一道,鲜明反映出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之“人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的双线螺旋发展进程。
一、冲破黑暗的红色之光:
早期“红色电影”的诞生
中国早期的“红色电影”在白色笼罩的黑暗中诞生,却在曲折发展历程中成为照亮中国前进的文化之光。综合学界有关“红色电影”的界说,本文研究的“早期红色电影”是指革命战争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革命、抗战、救亡主题紧密相连的电影,具体包括左翼电影、国防电影和抗战电影,即主要研究左翼文艺观指导下产生的那些底层叙事和革命叙事电影。诚如丁亚平所说:“中国电影的革命表达源于左翼电影,红色意识形态来自左翼电影运动。”[1]“实际上,‘红色经典电影’的起点和源头,均为1932年出现的,以阶级性、暴力性与宣传性等特征见长的左翼电影。”[2]170
在白色恐怖年代,由于文艺工作者难以在作品中直白表达革命斗争精神,左翼编剧和爱国导演迫于审查制度,只能在电影中隐喻和暗示。正如李欧梵所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左翼剧作家对中国观众的思想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向他们灌输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审片制度),而是在故事层面上带给观众一种新的叙事模式,描写那些活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的小市民,以此来折射社会等级,并用善、恶世界之间的比较来隐喻城市和农村。”[3]夏衍回忆左翼电影人“想尽办法在这个既定的故事里面加上一点‘意识’的佐料,使这个影片多多少少能有一点宣传教育的意义。这当然是不足为法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至今还引以为慰的是,我们终于通过这种方法,转弯抹角、点点滴滴地在资本家经营的电影商品中间,加进了一些进步思想,而执拗地把电影引向为政治服务的方向”[4]。
从创作主体来看,早期“红色电影”得益于夏衍、L6cITAi6/bG8D2n1FG1J0Q==郑正秋、张石川、沈浮、史东山等电影先驱所践行的电影“影戏观”及其强调的电影道德和教育功能。对此,郑正秋曾提醒电影人,要“加一点改良社会提高道德力量在影片里”[5]。从创作话语背景来看,启蒙、教化思想为左翼电影发展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承载着政治革命意识和具有“武器”作用的左翼电影为何能得到导演和观众的认同呢?主要是因为此前通俗剧、启蒙剧与左翼电影之间具有一种传统伦理的联系,即电影理论家尼克·布朗所说:“最复杂、最有力的流行形式总包含传统伦理体系和新国族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妥协,这种形式能整合这两者之间的情感冲突的范围和力量。”[6]
二、银幕中的红色律动:
早期“红色电影”审美现代性的变化向度
在内忧外患的年代,“红色电影”的精神指向随着中国文化现代性之启蒙、革命、抗敌的时代主潮起伏。从红色电影发展来看,可将早期红色电影划分为反封建、反专制和反帝国主义三个类型:反封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便掀起了以“科学、民主、自由”为武器的革命高潮,此时的红色电影处于孕育萌芽期;反专制主要是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至抗日战争爆发,此时革命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和革命思想在斗争中成长,此时的红色电影处于生长发展期;反帝国主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掀起了抗敌救亡的高潮,此时的红色电影以抗战为主题。对应不同的主题及表达,红色电影的审美指向与叙事策略可从四个向度阐释。
第一个向度是以《渔光曲》及其底层叙事为代表的觉醒与抗争意识的隐晦表达。早期红色电影是左翼进步文艺工作者和具有爱国思想意识的导演合作完成的左翼电影。如夏衍编剧、孙瑜导演的《野玫瑰》和《火山情血》,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春蚕》和《上海二十四小时》,阳翰笙编剧的《铁板红泪录》,沈西苓编导的《女性的呐喊》,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等,这些电影表达的是现实主义美学观念,都采用底层叙事的策略去隐晦表达觉醒与抗争意识。
《渔光曲》是一部隐含着抗争与反抗意识的电影。影片以东海渔民徐福家一对双胞胎降生场景拉开序幕,哥哥小猴、妹妹小猫的出生使徐家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为了能活下去,徐父租借船王何仁斋的船出海打鱼,不幸惨死海上,妻子徐妈被迫到何家做奶妈抵债以维持生计,两个孩子则在奶奶的抚养下长到十岁。后来徐家又经历了徐妈失明、渔村被海盗洗劫、兄妹被迫流落上海拾荒、找工作无门、小猴与舅舅街头卖艺、母亲和舅舅死于火灾等挫折。经历种种磨难的兄妹即使艰难而坚强地走在打鱼为生的道路上,也仍然遭遇了更大的挫折——哥哥打鱼疲劳成疾而死。临死前,他让妹妹给他唱《渔光曲》。电影就在这“东方咏叹调”中结束,呈现出底层渔民的不幸和社会的罪恶。其故事实为蔡楚生强烈的民生意识、民族情感和民族家国意识的艺术表征。由于当时的电影审查,导演没有通过角色去叩问“为何底层人民世代穷”这一主题,也没有给出答案,而是三次唱响蕴含丰富的《渔光曲》,唱出底层人民的“人生之问”——为什么捕鱼的人儿世代穷?情节处理和形象塑造上,蔡楚生实践的是其现实真实呈现的理念,而不是加入想象的革命意识。正如他本人所说:“我所以用这样改良主义者型的人物出场的缘故,是觉得自从1932年发生了电影内容的转变以后,对于剧中的主人翁,是有过不少的仅由于剧作者幻想的强调,使这些莫名其妙的主人翁成为革命战线中最前卫的人物,这种不合逻辑的蜕化,我以为是非常错误而不敢同意。而我一贯的创作态度是把社会真实的情形不夸张也不蒙蔽地暴露出来。”[7]
由于当时电影受众主要是城市市民,电影创作必然要迎合观众的口味。正如蔡楚生在影片放映后所说:“在看了几部生产影片未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以后,我更坚决地相信,一部好的影片最主要的前提,是使观众发生兴趣……为了使观众接受作者的意见起见,在正确的意识外面,不得不包上一层糖衣……很可惜的,现在的工人和农民能够有机会观电影的很少很少,而观众中最多数的,则还是都市的市民阶层分子。”[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期的红色电影在表达革命和反抗意识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审核制度、投资者意愿和观众趣味。
第二个向度是以《挣扎》及其革命叙事为代表的号召民众反压迫的革命理想表达。在电影商业化主导下,具有革命理想的编剧们由于缺乏财力,无力自己拍电影。作为编剧或参谋,他们难以在资本主导的电影中完全实现电影“革命武器”的理想,只能通过与具有进步思想和正义感的投资人、导演合作,逐渐加入其革命思想。1932年孙瑜编导的《野玫瑰》《火山情血》,由于首次鲜明确立了左翼电影革命性、抗战性和宣传性特征而被称为左翼电影的源头。对此,袁庆丰指出,这两部电影“之所以是开山之作,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部影片基本确立和奠定了左翼电影的革命性特征及其艺术表现范式”[2]171。1933年,夏衍、程步高拍摄的《狂流》,进一步凸显了左翼文化思想的革命性、抗战性和宣传性,将阶级性、革命性的斗争思想巧妙置入当时商业性主导的电影,为后来实践电影“武器论”艺术观积累了经验。
真正指明革命道路的早期红色电影是1933年于定勋编剧、裘芑香导演的《挣扎》,洪深改编、陈铿然导演的《香草美人》和洪深编剧的《压迫》,郑伯奇与阿英合作改编的《盐潮》等作品。这些作品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受压迫者的觉醒和反抗。《挣扎》讲述的是青年农民冯根发从被迫逃离、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到参加义勇军抗敌救国的曲折故事。在父亲因欠地主耿大道稻租而被毒打身亡的境况下,他带着即将被逼迫给耿大道做妾的小兰逃到上海谋生,随后经历被诬陷入狱、爱人被杀的悲惨经历。随着淞沪抗战的爆发,冯根发参加了义勇军抗敌救国,最后他因前往炸毁敌人的铁架车而牺牲。影片通过冯根发从反抗地主压迫到追求自由生活再到抗敌救国的转变及其曲折的人生经历,实际上表现的是当时电影观念及社会思想的转变,主题上具有浓郁的反帝反封建倾向,艺术表现上呈现出鲜明的革命叙事风格。
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的《逃亡》也是这样的作品。整个故事呈现的是日本侵略下的中国社会状况。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下,底层百姓无论如何拼搏都无法摆脱颠沛流离、贫病交加、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诸如冯根发、黄少英这样的青年农民,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终于觉醒,自己拿起武器并号召青年拿起武器投身抗日救国战争。正如电影主题曲《自卫歌》所唱:“对准敌人,举起所有的武器,(白:我们要自卫,我们要救自己!)上前线去!大伙儿在一起,驱逐我们的敌人出中国去!今天是被压迫的民族;明天一切属于我们自己。”无论是主题曲还是片中觉醒后的少英的号召——“大家投义勇军去,打回老家去”,都是时代的呼声。
再如文学与民族电影联姻的典范之作《春蚕》,此片开创了中国民族电影和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现实、改造社会的新天地。诚如丁亚平所说:“《春蚕》的改编以其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性,在处于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承担起‘救世’和‘启蒙’的功能。”[9]1341930年代初期,尽管电影在商业化、娱乐化、启蒙教育化、革命斗争化的复杂语境中还存在“软硬之争”“‘为艺术’与‘为生活’之争”,但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打响则将电影凝聚到抗敌救国的“为现实”道路上,叙写抗敌救国精神的抗战叙事随即成了电影的主要美学风格。
第三个向度是以《大路》《风云儿女》为代表的抗战叙事及其自强救亡精y0/9Svz9bpxNI0zpKFEVrTxqyPojojfPvrJMgII2YhM=神表达。“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怎样在民族抗战下挣扎求存,如何在创作中灌注抗日救亡精神,成为田汉、夏衍与史东山、阿英、蔡楚生、阳翰笙等人自觉而迫切的使命。他们意识到,早期的底层叙事、革命叙事模式显然不能有效发挥团聚全民族抗敌救国的作用。因此,转向国家民族主义叙事以完成其凝聚全民族力量救亡图存的使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一·二八”抗战背景下,涌现了一批号召积极抗日救国的作品,如孙瑜编导的《大路》,田汉、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孙瑜、史东山、蔡楚生等编导的《共赴国难》以及诸如《抗日血战》《十九路军光荣史》等抗战纪录片。
《大路》可谓从革命走向抗战的时代精神表达代表作品。筑路工人所唱的《大路歌》吹响了时代进步号角。电影讲述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底层百姓汇聚到一起筑路,虽然筑路工作非常艰辛,但他们在烈日中高唱《大路歌》《开路先锋》,一路向前;在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獠牙吞噬中国的紧要关头,他们团结起来,与敌人汉奸进行坚决的斗争,即使面对汉奸的严刑拷打和敌人的狂轰滥炸,也毫不畏惧地投入抢修军用公路的事业中。电影通过筑路工人坚毅朴素、不畏强暴、奋起反抗的精神和思想蜕变来表达抗敌救国的社会理想。实践社会派电影人以电影反映时代生活、反映社会理想并干预现实的艺术观念。正如导演孙瑜所说:“《大路》是叙写在弱小民族普遍的反帝运动里,我们的筑路工人,已经或应该热烈地加入战线。”[10]同时还以主题曲《大路歌》唱出时代之音:“大家努力!一齐向前!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我们好比上火线,没有退后只向前!大家努力!一齐作战!大家努力!一齐作战!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11]此片表征的是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下的全民反帝抗日的社会精神,蕴含的是革命叙事向抗战叙事转变的审美现代性方向。
《风云儿女》是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改良向革命抗战理想转变的表征。影片描写了从迷茫走向觉醒的知识分子辛柏华的抗日救亡之路。电影和歌曲都是抗日救亡爱国思想的艺术表征,也是进步电影人实践“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文艺思想的典型作品。其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作为电影的互文文本,为唤起民族抗敌救国的崇高使命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风云儿女》可谓是一部极富抗战崇高美学精神的作品。这不仅可从其书写的知识青年放弃安逸生活走上抗日前线的故事内容中看出,也能从电影剧本、插曲歌词的创作及其蕴含看出。此片首先由田汉编写故事梗概和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其被捕后,夏衍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写完剧本并组织拍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为聂耳谱写;电影最后由许幸之导演。这就使《风云儿女》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主体精神到创作对象及其表达方式都充满了革命抗战艺术的审美张力。尤其是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铿锵激昂的旋律和响彻中国大地的声音激励着民族斗志,将中国电影的抗战崇高审美理想推向了新的高度。
30年代中后期,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残酷压迫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抗帝国主义、追求国家和民族自强成为时代的思想主潮。此时的红色电影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自觉实践革命诉求和抗敌救亡诉求的思想武器。这些电影在创作观念上完全抛弃了“软性电影”的商业娱乐观,极大突破了注重思想启蒙和浪漫表达的“影戏论”束缚,自觉实践反帝、反压迫的抗敌救国的“武器论”电影观。夏衍、田汉、阿英、阳翰笙等左翼知识分子和具有进步思想的导演郑伯奇、蔡楚生、许幸之等人,都在实践这样的电影思想: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电影的出路就是要关注现实,以民族主义思想来唤醒全民族的团结抗敌意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史东山、阳翰笙等人开始反思,抗战电影的表达不应是抗战初期那种口号式宣传,而应注重电影本身的表现技巧,才能实现其宣传教育和启迪功能。对此史东山在《抗战以来的中国电影》里指出:“民众对单纯的正面宣传、毫无自我批判、过分乐观的电影诉求有了清醒的认识”,电影人应“避免单纯的正面宣传,尽可能的多做自我批判”[12]。自此,红色电影在延续抗敌救国精神的同时,开始将反思、批判、国家民族意识与抗敌救国号召结合起来。
第四个向度是以《延安与八路军》为代表的抗战叙事延续及其表征的党领导下的民族精神之光。最明确也最能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英勇抗敌理想及抗敌军民生活的电影,当属《延安与八路军》和《四万万人民》。前者是“延安电影团”拍摄的抗战纪录片,后者是荷兰电影艺术家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抗日战场拍摄的前线战事及在周恩来关照安排下拍摄的新四军、八路军在汉口一带活动的纪录片。这两部电影不仅开宗明义地表达出中华民族抗敌救国的时代强音,而且还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事业的光辉前程,既是抗战叙事的延续,更是自强救亡崇高美学精神的升华。
《延安与八路军》是一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映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和抗日的作品。导演以纪实手法真实呈现爱国志士和有为青年突破敌人封锁奔赴延安、加入八路军、奔赴前方参加战斗的生活;影片极大地激发了抗日爱国热情,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斗志,对抗战胜利发挥了很好的鼓舞作用。正如当时的“电影团”团长谭政所说:“在革命的战争年代,许多电影摄制工作者,冒着敌人的炮火,拍摄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如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业绩,为我们党的历史、军队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成为教育人民、鼓舞斗志、战胜敌人的精神武器。”[13]
《四万万人民》通过纪实手法表达八路军顽强抗战的英勇事迹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中国人民抗敌救国的主导作用。影片客观上向世界反法西斯集体传递了中国抗战的力量,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抗战的决心和精神。“伊文思在影片中用抗战形势图的方式表现站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冲上这旷古绝今的战场的英姿,歌颂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四万万中国人民。”[9]284
三、硝烟过后的悲愤与反思:
《八千里路云和月》及其社会改良追求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未迎来人们所期望的和平与民主,更没有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商业化、消费娱乐化及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化三重夹击下,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电影在国统区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即便如此,具有进步思想的电影人始终在努力寻找一条干预现实、改变中国的艺术之路。以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陈白尘、沈浮、陈鲤庭、郑君里等为编委成员的昆仑“社会派”仍然坚持以电影教育、启蒙和改造社会的艺术观,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松花江上》等直面社会的作品。
如《八千里路云和月》,田汉曾称赞此片“替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一个基石,找到了一个水准”[14]。电影讲述了大学生江玲玉加入抗日演剧队,历尽艰辛北上抗战,其间与音乐家高礼彬相爱并结婚,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到上海却遭遇无业、无居的窘境,目睹颓废、腐朽社会现实的故事。题材上,此片结合了爱情与战争两种类型,但主题上艺术家不是写战争的惨烈和爱情的悲壮,而是利用镜头调度和蒙太奇艺术手法将抗战者(江玲玉)与投机商(表哥周家荣)的境遇和心理、战时与战后社会mrVsTAi3HyscdBvu/lES6sHMLGAVV6oFTcwSWcv341k=生活进行对照,以此批判投机横行、政府无能、民主被践踏的战后社会现实。从艺术观念来看,此片继承了战前社会派电影“改良社会、干预现实”的观念,但在艺术形象的塑造和表达上,摆脱了战前知识分子“革命者成长”形象和战时“壮士”“英雄”等艺术形象塑造的旧路子,而是借助普通知识分子的经历及其对战后所见、所思而表达艺术家对社会的批判及自身的现代性焦虑,以此唤起人们对自身和社会现实的关注与反思。
再如《万家灯火》,这也是反映战后国统区城市小资产阶级生活及其对社会人生反思的经典作品。电影以公司职员胡智清及其家庭的生活变迁,映射城市小资产阶级由于错误信任并依附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官僚资产阶级而导致生活陷入泥潭的社会现实;呈现了钱剑如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与胡智清代表的小市民阶层、阿珍和小赵代表的工人群众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社会关系。通过胡智清的家庭生活遭遇及其个人反思,引导人们反思造成战后黑暗现实的原因——统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压迫广大人民,要想改变现实,只有团结一致奋起反抗。迫于战后国统区政治的原因,具有进步思想的电影人在此只能通过隐晦的表达方式,以此实现唤醒人们团结抗争、改变社会的目的。这种隐晦表达反思、觉醒、抗争主题的策略,使作品充满了启蒙与革命交织的审美张力。
四、结语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民国时期的红色电影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红色电影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左翼电影,真正拉开了中国红色电影的序幕,其深蕴的民族奋发精神和家国情怀是1949年以来中国红色电影的显性基因,这种基因通过隔代遗传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与新时期红色电影的审美表达。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民国时期红色电影的故事内容、形式风格、艺术观念及美学精神和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表现了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从启蒙到革命再到抗战以及反思的演进轨迹;同时也以其底层叙事、革命叙事和抗战叙事的独特叙事风格,区别于后期的伟人、英雄、改革先锋以及新时期的主旋律叙事,彰显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现代电影美学风貌。
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电影相比,早期红色电影在艺术观念、审美思想、表现方式和叙事风格上都有其独特性。观念上,其体现的是特定历史时期文艺的“武器观”思想;审美思想上,其体现的是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社会理想,即体现了从底层叙事的人文反思到革命叙事的国家寓言现实干预,再到抗战叙事的崇高审美的现代美学精神演进逻辑;表现方式上,其注重人物角色及其人生历程与家国命运的联系;叙事风格上,其表现为初期浓郁的启蒙意识及其叙写的早期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发展期鲜明的阶级斗争意识及其唤起底层民众斗争意识的现代性追求,高潮期强烈的民族独立使命感与崇高的政治意识及其表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抗敌、自强奋发的爱国、救国社会理想,表征的是20世纪前期从“人的解放”到“民族独立”的审美现代性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丁亚平、冀心蕾.电影的革命书写:左翼意识形态与百年中国电影[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3-20.
[2]袁庆丰.红色经典电影的历史流变——从左翼电影、国防电影和抗战电影说起[J].学术界,2020(1):170-177.
[3]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毛尖,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35.
[4]夏衍.以影评为武器 提高电影艺术质量——在影评学会成立会上的讲话[J].电影艺术,1981(3):1-4.
[5]郑正秋.请为中国影戏留余地[J].明星特刊,1925(1):3-4.
[6]布朗.社会和主体:论中国通俗剧的政治经济[C]//布朗,毕克伟,索查克,等.中国新电影:形式、身份和政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40.
[7]蔡楚生.八十四日之后——给渔光曲的观众们[J].影迷周报,1934(1):9-10.
[8]蔡楚生.八十四日之后:给《渔光曲》的观众们[C]//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364-365.
[9]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
[10]孙瑜.“大路”导演者言[J].联华画报,1935(1):18.
[11]陈钢.上海老歌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64.
[12]史东山.抗战以来的中国电影[J].中苏文化,1941(1):81-123.
[13]谭政.贺延安电影团成立50周年[N].人民日报,1988-8-24.
[14]田汉.八千里路云和月[N].新闻报·艺月,1947-2-3.
作者简介:陈正勇,博士,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