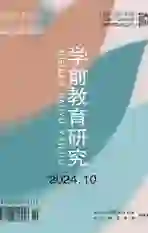现象学视野中的时间及其对幼儿园生活的意义
2024-10-29贺刚许婷
[摘 要] 当前以计数通达时间的方式将幼儿园生活转化为可被充分现成化的对象,然而在现象学视野中,人原本体验到的时间却并非被统摄、收拢于当下现成之中,而是具有盈余出现时的“晕圈”性的意义生发背景。这一发现的启示在于,幼儿园生活的运作在根源上需建基于非现成的、有其动态的意义生产机理的时间结构,而这尤其意味着,应该深入探索身为“人”的学前儿童对时间的原发体验。进一步经由现象学的运思发现,学前儿童体验到的时间具有“失焦”的晕状结构,这种独特的时间结构不凝聚、置身于任何现成对象,还原了人之存在的原初面貌,并进一步揭示了学前儿童的生活本身是有想象力的、时境化的,且富含美的体验,总之有其原发而饱满的意义性。幼儿园生活应该从学前儿童原本的、鲜活的时间体验出发,但又不止步于此,在更深层的现象学意义上,还需引入“社会—历史”性的时间力量,来晕染、滋养并扩展幼儿个体生活的时间结构。从现象学视野来重构时间的意蕴,将为幼儿园生活现有的时间实践带来重要变革。
[关键词] 现象学;时间结构;儿童时间体验;幼儿园生活
*基金项目:2023年度江苏教育科学规划青年专项“关系视角下中国式学前教育观念现代化的江苏道路研究”(编号:C/2023/01/54)
**通信作者:贺刚,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
一、问题缘起
时间之于幼儿园生活而言,看似是再平常不过的现象,但若真要问起“究竟何为时间”,恐怕一时还是会令人茫然。不过,只要联系日常经验就容易发现:在幼儿园中,时间是同钟表及精密的计数相互联系的,指导幼儿园生活的时间作息表——它由多个紧凑的交替接续的教育与生活活动构成,每一活动的划分和计算有对应且严格的时限——最为明显地揭示了这点。
将时间与计数关联有其哲学根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指出“时间正是这个——关于前后的运动的数”,[1]他认为能用“前”“后”衡量运动,通过对这段运动过程从前端迁移至后端的间隔多久予以计算,从中计算出的数即时间,时间还是连续的,一段终止可以是另一段起始。亚里士多德以计数通达时间的做法在后世影响巨大,推动了俗常时间、钟表时间的产生——一种“在计数活动中呈现出来的、作为现在之前后序列的时间”。[2]
计数是时间之理所当然的本性或理想状态吗?由计数通达时间的突出特征是现成化,即计算时间需要的所有要素,如运动的先后位置、过程的多久和发展的顺序,都必须是设定的、当下可直接把握和衡量的,否则时间无从作为被数出的精确的数而存在,时间的先后来去在这里就仅是现成可见的当下的变体和附庸,是可充分计量、分配和促逼其即刻展现出标准的行为意义和有效益的计量价值的现在序列。而在幼儿园生活中,有教育研究发现,过度建构的现成化的时间计量制度因其“平均的短时段”“精密的时间结构”和“集体同步转换”,已造成了对幼儿行为的强控制、幼儿缺少对活动的深度投入以及紧张的“赶时间”等一系列现象;研究者还敏锐指出,时间本身具有生动的体验性,不能被纯粹计数的、测度的形式所裹挟,以儿童为本的立场呼吁教育者应当去研究儿童自身对时间的体验,但目前这方面的探索相对稀少。[3]
而从现象学视野出发,将有益于我们探索体验的时间及其对人的生活的原本性意义。胡塞尔(Edmund Husserl)经意识现象学考察指出,人对事物的内感知体验其本身就伴随带有一种动态的时间性体验,“非实显的体验的‘晕圈’围绕着那些实显的体验;体验流绝不可能由单纯的实显性事物组成”,[4]此非实显、非现成体验到的“晕圈”即“时间晕”。[5]具体而言,当我们感知事物如听一首歌时,不会只感知到每个当下现成呈现的声音对象,脑海中还会自发滞留(Retention)、回荡过去的声音,也会不自觉以前摄(Protention)方式对将来要出现的声音有初感或预觉,由此才能体会到音乐本身畅快的旋律,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必须有一个过去性与未来性相交织的时间体验场域,提前去环绕和晕染现在,于“不显眼”的边缘伴随性地参与到现时感知的构造中,为其供给盈余性的意义和可能性,才能令其得以灵活伸展、流动。如果没有“时间晕”作用,当我们听音乐时,意识就只能接收到一个个即刻性的声音印象的无意义来去、切换,或只能靠事后联想去构造完整旋律,但这已跟不上当场感知的要求了。[6]因此人所原本体验到的时间在其结构上,不是被统摄、收拢于当下现成之中,反而任何当下的意向唯有返回到过去与未来交叠的“晕圈”中,才会获得一种“活”的意义和生发背景。胡塞尔后来将此思考更深刻地引入对“生活世界”的讨论中,指出“世界是空间时间的世界,空间时间性(‘生动的’而不是逻辑—数学上的空间时间性)属于作为生活世界的世界固有的存在意义”,[7]“现象学家的兴趣并不是指向现成的世界,并不是指向现成世界中的本身是被构成的东西的外在地有意图的行为”,[8]他严肃批评了用数学化的、现成对象化的静态形式,来取代作为生活世界源头的人的意义体验流、时间流(时间的发生构造晕、构造域)的做法。
综上,回顾既有研究并引入现象学视野对幼儿园时间问题的启示在于:幼儿园生活的发生与展开,必须建基于非现成的、有其鲜活的意义生产机理的时间结构(这尤其意味着,应该深入探寻身为“人”的幼小儿童对时间的原发体验及其在他们生活中的价值,幼儿园只有从学前儿童的时间体验本身出发,才有可能真正生发出其独特的教育生活形式)。此一本源问题,在我们将预制的、现成化的时间体制视作理所当然的教育实践背景下,被一定或相当程度忽视、跳过了。而本文试图进一步经由现象学的运思并结合学前儿童相关研究来弥补此一缺憾。
二、学前儿童对时间的原发体验及其价值
(一)学前儿童体验到的时间具有“失焦”的原发结构
学前儿童对时间有一种原本而自发的现象学意义上的体验吗?皮亚杰(Jean Piaget)的研究指出,由于生命最初缺乏对客体永久性的理解,所以对极为年幼的孩童来说,“宇宙是由许多忽隐忽现的移动着的画面构成的,这些画面一旦不见了,也就没有空间位置了”,[9]这喻示着,幼童早期几乎仅能感知到可见的当下,其生活没有潜伏着的过去和未来之分。而这种情况至少要到生命发展的十八至二十四个月之间——随着符号功能和表象性智力的出现——才有机会发生一定转变,把客体安排在先后秩序上至少成为一种可能。[10]
但和皮亚杰的这种传统解释截然相反的是,鲍尔(Patricia J. Bauer)通过对文献深入回溯后指出,随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对幼儿记忆研究的不断深入,心理学家们已发现,生命的最初两年中,事件记忆得到迅速且显著的发展,即使六个月的婴儿也能对较短事件的发展脉络有持久(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外显记忆,并且这种持久的外显记忆并非突然出现,综合现有证据有理由推测,在六个月大以前就存在一种近似的记忆模式。[11]此外,阿道夫(Karen E. Adolph)与伯格(Sarah E. Berger)通过对幼儿动作发展的多个研究进行总结,发现婴儿的行动很早就显示出对未来的预觉,基本上一个月大时,婴儿就可用眼睛连续而流畅地追踪移动事物,尽管这只发生在短时间内,但表明了婴儿有通过从刚才看到的运动中推断出事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潜能。[12]从现象学视野看,这些区别于皮亚杰的新近探索无疑揭示了,人从来就不是生活在无时间性或时间性残缺的浑然、随意中,而是一开始,在童年的开端处,就有潜能去形成一种超越当下,并让过去、未来同现在产生更多维而有层次的交叠及呼应的时间体验。
相较于成人或学龄期儿童,学前儿童原发体验到的时间还有更为独特的结构,而这可从儿童画问题谈起。儿童画研究先驱吕凯(Georges⁃Henri Luquet)发现,幼儿会将事物遮挡的、并不直接可见的方面画下来,呈现出事物的多个维度或侧面,而吕凯指出,这种绘画形式体现了幼儿感知的幼稚性,其未能理解透视原理;在皮亚杰看来,直到八至九岁,儿童进入视觉现实主义阶段,才能掌握透视法等原理,绘画之物才符合是从固定视角所看到的对象。[13]但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却认为,儿童画其实是在试图“表达事情本身”(to represent the thing itself),在这方面,幼儿似乎比成人走得更远,即使牺牲了画面的视觉外观。[14]何以如此?实际上当从某一视角看事物时,当下的确仅能看到某些固定的现成面向,但我们肯定知道,事物本身并不只是由可见方面构成,如果我们曾完整环顾、感知过它及其各个方面,那么从固定视角看它时,意识中滞留的过去印象就会自发与可见面向结合,内在的前摄性感知也会参与进来,以使我们看到特定面向时就能预料、意识到其为一个实质上是盈余出这些当下侧面的完整而真切的事物。基于此看儿童画问题便可明晰,幼儿正是基于这种对时间的晕圈结构的原发体验,从而来感知和描述事物本身的,也即他们将对事物的这种带有过去、现在与未来交叠晕染的时间体验过程,以真诚如实的方式整个还原在了其绘画之中。尽管能成功从固定视角展开绘画讲述,甚至更需自如掌握时间的结构,但问题在于:到学龄期尤其至成人期,对透视原理的重视,使得当下及其主导的方面成为时间结构中的突出焦点;而学前儿童原发体验到的时间,在其结构上却并不存在这种“对焦”特征。
心理学家高普尼5200bd87d0343aa0a267b3f31628572960534dca15aa2812328fad89c880661b克(Alison Gopnik)的观点进一步支持了上述看法,她比喻说:成人的意识域如同“聚光灯”(spotlight),是“一道周围环绕着黑暗的狭窄而专注的光束”;而年幼儿童的意识域则如同“边缘更加明亮”的“灯笼”(lantern),“对一切都有着生动的感知,却并不特别聚焦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事物”。[15]而之所以如此,高普尼克主要基于神经科学研究解释道,其是与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发展成熟的时间很晚(到二十五岁左右)有关,前额叶皮层有参与“抑制”的功能,可帮助关闭大脑其余部分,实现经验、思想与行动的集中,尽管前额叶皮层在童年期也非常活跃,但尚且不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这使得幼儿对周遭的感知更加有意识和想象力,能发现和思考其中存在或可能潜藏的各种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细节及关系。[16]
从生理不成熟(带来独特优势)的角度,来揭示童年早期同成年期体验到的时间性差异,虽有一定解释力但仍不充分,在现象学视野中,可基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时间哲思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海德格尔看到,人的本质并非可现成定义的“存在者”,而是“去存在”,[17]即能以非必然的方式去不断铺展自身存在的意义。这就是说,人于开端处不由任何主宰性的目的、身份或命运支配,其存在呈示出时间的“出神态”(Ekstase)——存在本身在将来、曾在和当前始终相交织的出神入化的可能性势能而非任何现成意义中赢得自身[18]——而人的这种开端状态乃是一种幼童状态。海德格尔指出,儿童是“存在者整体的主宰”,[19]赤子之态即让人生一切意义得以涌流的先在源头,“海德格尔哲学是有童年的,它回到这个‘前’领域里来了”。[20]据此来看,童年早期所原发呈现的时间性之所以“失焦”(无特定焦点),并非单纯由于生理不成熟,这种“失焦”不凝聚、置身或坍缩在任何现成的面向或对象化(“对焦化”)的意义之中,恰恰还原了人之存在的原初面貌。根底上,“失焦”的时间结构乃是一种“虚”结构,“虚”有“消极”的意味,它没有“实底”因而恍惚不定、无明显用意,所以不易把捉,但正是在此“消极”的“虚”中,又有先于现成化、对象化的意义性关联,表现为时间的三个向度之间无止息的“自由游戏”,这种神妙的、纯粹“气晕”性的时间性交错变换、晕染互流,又能够去生发、构成和包容人生不竭的可能性,由此生活、周遭事物及其多维向度的意义在童年开放的时间域中,得到了自发的、动态的而符合其“活”的本性的涌流与显现。这种“前对象化”(“前对焦化”)的——相应也是“前主体化”的,不以自身已据有的现成视角为中心的——生命时间性,无疑表明了童年早期是主客(物我)未分的。但随着人生渐进,人的“自我”将变得越发突出。皮亚杰已明确揭示人的发展存在主客逐渐分化的过程,在笛卡尔以降的近代西方哲思中也能清晰看到,有“理性”的成人往往将主体性的“我思”作为认识外界事物的支点,这个被认作给定的、不动摇的“我思”立足现成的当下,而世间事物的过去与未来被当作有待现在的“我思”去衡量、确立甚至算计、操纵的客体对象。因此,自我之主体性的擢升,会极大凸显“现在”在人所体验到的时间结构中的地位,聚焦当下并利用它影响甚至统握过去和未来,将成为成年期的常见时间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的哲思与这种全然成人式的时间理路有别,他介于近代西方哲学与海德格尔之间,看到的乃是有“赤子之心”的成人是如何去体验和构造意义的,因此形成以现时向度为焦点,但原初的过去与未来仍在边缘潜伏运作,而能使现在活转生息的时间结构。
(二)“失焦”的时间体验赋予童年生活以饱满的意义性
人在原发体验着时间及其结构的过程中,也随之推进和实现着对事物也是生活意义本身的发生性构造,时间体验即意义体验、生活体验,二者本互不分离。那么童年早期“失焦”的时间性与时间体验,将喻示着学前儿童的生活具有如何的原发面貌呢?
首先,“失焦”的时间体验喻示着,学前儿童原发就生活在可能性而非现成性当中。幼儿内在意识的滞留与前摄,皆不必然如胡塞尔所言,仅是对一连串能现时知觉到的原本印象即“原印象”(Urimpression)的持驻和预期,前述基于海德格尔的思考已反映出,现时对象已不再是幼儿感知体验到的时间结构的中枢,幼儿意识的滞留与前摄因其“失焦性”反而还原为先于任何实际对象而又能够让对象予以持留的纯粹滞留性,以及能够对对象予以期望的纯粹前摄性本身,二者可“凭空”运作,即不以现成性为发端和根据,但又能利用现成材料而行天马行空之势,这本质上乃是想象力的体现。非再现性的纯粹想象力即一种本身还不是对象却可以自发构造出对象出现的可能性的能力。[21]因此,幼儿的生存状态就是根本性的生存想象状态,亦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去存在”状态。幼儿自身能“凭空”对生活予以发生性构造,赋予任何现时的体验以“去习惯化”“反必然化”的可能性,从而使体验本身重获想象性的时间发展线索。这其实也表明了,幼儿感知到的现时本身也必然是“空心”的,不可“自立”,即不会以“实”的、不动摇的原印象为自身的终极依据,而是可以“腾空、悬浮地飞翔与遨游”,在同过去与未来之间“闪转腾挪”的灵活“舞蹈”“游戏”间呈示出自由变换的想象性意义。总之,在幼童眼中,生活总是存在开放的多维关系,这种有想象力的幼年生活也是未来人生一切创造与建树得以可能涌现的先在枢机、意义“蓄水库”。
其次,“失焦”的时间体验喻示着,学前儿童生活的目的与过程是浑然一体的。一个精于理性算计的人总试图改变生活的轨迹,追求当下执着目标的达成,对功利得失的计较已凌驾于生活过程本身,因此总可说,他从未真正生活过。但对幼儿而言,除生活本身外,没有别的目的追求或者意义来源。在“失焦”的时间体验中,当下没有塑造过去与未来的强权性,反而任何当下的生活意图都有出自幼儿过去持留的生活体验的铺垫,它也因幼儿对未来生活变化的预觉、期待,而有自发的推进或更迭。也就是说,幼儿任何的意义趋向都有其得以发生的时境(时机化的生活情境),联通着过去与未来。就像一个孩子感到与母亲分别已久,而他也不禁遥想与母亲相聚有多么快活,于是哭喊着想要妈妈的热烈意图才会“正当其时”地迸发而出。幼儿生于时境的内在意图,总如对母亲的此般思念,是真情实意、完全投入的,符合儿童的本心、生活的本性。这种生活过程与其内在目的的统一性,甚至还可从前述的意识层面进一步还原至身心现象中去探讨,梅洛-庞蒂尤为揭示了意识(心灵)根底上不能脱离开身体,人最为原初的身心交融状态本身就带有一种构造意向目标的知觉域、知觉时间域,而已有的学前教育研究也已表明,幼儿的身心在自然的生存发展过程中,就能够时机性地涌现出一系列被称为“敏感期”“关键期”“年龄阶段特征”的发展取向、目标需求。
最后,“失焦”的时间体验喻示着,学前儿童是能自发在生活中感受到美的。美对人总有触动,此触动乃一种在人心中难以抑制、歇息的“余波荡漾”,美感是难以被把捉的,挑明了美常常就逃散、殆尽了,美只能盈余出此把捉,而引人以遐思,给人以不可预料、回味悠长的深切滋味。总之,“这种感知对象和美感对象里边都有一种内在的、可能性的空间和自由度”。[22]而“失焦”的时间体验,恰恰使幼儿很容易能脱开无(触)动感的静态对象对自身的吸牢以“神游其外”,而成人常视此“出神”为贬义、是幼儿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却不见此“出神”解构了现时的“实”,而使其泛起“灵光的涟漪”,进而增大、明亮了幼儿内在感知的过去性与未来性那盈余出现成构造的“晕环”,而呈示“心醉神迷”之态,这其实是一种更为深刻VWAbQcM/gqz1P8IcEXGMEA==的自我投入。在原发的回忆、期待与想象的光晕中,在体验时间多维向度的缠绕与叠加中,幼儿总能自然而然将感知对象的意义晕染、“荡漾”开去,意义由此能够自由“舞动”起来,幼儿随顺这意义的流动之舞,而能迎来丰溢的人生乐趣的奇袭。这无疑揭示了,“一个小孩,一颗赤子之心,他感受世界的时候就是带有美感的……他的生活就是欢乐的、意义无端涌现的”。[23]
总结上述可见,学前儿童的时间生活本身有其原发而饱满的意义性。然而,当前幼儿园教育实践所基于的非(完全)原发的“二手”时间体制,却在一定或相当程度上遮蔽了童年早期原本的时间结构,导致生活的现成性大过可能性,生活的过程被迫要不真诚地附和外在于生活本身的目的,对明确划一的狂热多过了对原发的美感的欣赏。杜威看到“教育即生长”,而“哪里有生活,哪里已经有热切的和激动的活动。生长并不是从外面加到活动的东西,而是活动自己做的东西”,[24]这有益于提醒教育者,要学会善待和善用幼儿时间生活原有的意义生产力,而不应败坏、浪费如此宝贵的原初资源。让幼儿随顺其原发的时间体验,能以“热切的和激动的活动”去领略和生长出更为广大而深厚的人生意义,才是幼儿园生活真正要追寻的发展方向。
三、从现象学视野重思幼儿园生活的时间
(一)幼儿园生活应由儿童个体的与“社会—历史”的时间性交叠生成
从学前儿童原发体验到的时间结构出发,幼儿园生活的确能够形成鲜活的意义发生机制,不过需进一步讨论的是,幼儿园的教育生活是否完全由学前儿童个体体验到的时间性而构成。若经由胡塞尔的现象学视野,将幼儿园生活带回到作为其源头活水的“生活世界”中会发现:个人的意识域无法仅凭由自身而构造出整个生活世界,个人意识的运作要依赖于身体,“我们自己按照我们的有身体的个人的存在方式,生存于这个世界之中”,[25]而个体性身体及其所能直接知觉的时空范围及层次终究是有限的。在更为原本的意义上,“我们将世界意识为存在着的对象的普遍的视域,意识为统一的宇宙,我们,每一个‘我这个人’以及我们大家,作为共同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人,正是属于这个世界”。[26][引用时有改动,原译文中的“地平线”被改动为“视域”,皆为对德文“Horizont”的可能翻译形式。这里之所以改动为“视域”是为了与本文语境更符合,即“视域”与上下文的“意识域”(也即“意识视域”)、“时间域”和“晕”结构等表述有彼此呼应的意蕴关联。下文相关引用中也存在此改动]因此,生活世界是人类共同体的世界,“我实际上处于周围人的现在之中,处于人类的开放的视域之中;我知道自己实际上处于世代的联系之中,处于历史发展的统一之流中,在其中,这个现在是人类的现在,人类所意识到的世界是伴有历史的过去与历史的将来的历史的现在”。[27]由此,从生活世界而来的幼儿园生活,同样也就带有了这种超逾个体性意义发生的“社会—历史”[28]的时间结构(同样是晕流状的,如胡塞尔所言,是人类意识到的“历史的将来的历史的现在”,彼此交叠晕染与翻涌),而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够“额外”对幼儿个体施加教育影响的缘由所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历史”的时间性并不凌驾于个人的时间性之上,以往的幼儿园生活形式往往容易在此走向偏误,将前者现成化、对象化为用于规训后者的制度体系和知识主题,而胡塞尔看到“这种历史的世界只有通过每个个人的内在历史性才能在历史上存在。并且作为个别的世界存在于与其他被共同体化的个人的内在的历史性结合在一起的每个人的内在的历史性中”。[29]因此对幼儿园生活而言,其所带有的“社会—历史”的时间结构及经验,只有有效参与和融入到(每个)幼儿原发的时间体验的发生构造过程中来,才符合其活转生息的本性并因此能真正迸发出重要的教育意义。这种教育意义体现在,当幼儿本身的时间性,能与来自他者的也是“社会—历史”的时间性产生相互的呼应、彼此间的感通激荡,幼儿意识的时间晕结构就能随着这种融合相通的发生而持续伸展、扩大,即幼儿意识的感知范围不再以其个体性为限度,而是流向了更远、更自由的也是更多维深层叠加的过去和未来。这一切在不背离而是增益于童年早期原发的时间本性的前提下,将进一步意味着:童年的想象力能够去涵摄并构造出生活越加充溢的可能性;而生活过程在其时间维度的拓展、深化,也为激发幼儿去追寻更高、更广阔的人生目标创造了有利的时境条件;生活事物在不同意识域、时间域中的自由变形以及相互间的激荡和联通,同时还使童年早期的美感体验得到更为尽情而尽兴的舒展。
总之,幼儿园生活从其现象学意义而言,是由幼儿个体生活的时间性以及晕染和滋养它的更为开放的“社会—历史”的时间性所共构的一种独特生活形式。
(二)幼儿园时间实践应激活与促进童年生活的原意义构建
从现象学视野重构时间的意蕴来看,这将会为幼儿园生活现有的时间实践带来怎样的变革呢?当前幼儿园时间实践受计数逻辑的过度影响,而在这种计数逻辑背后又折射出成人“我思”的权能运作,“我思”试图排除、止息人生的恍惚流变,以计量的、体系性的手段促逼童年生活展现出明白无疑的时间程序与价值,从而使其获得一种“对焦”的当下实在性。这种“聚焦性”努力,寻求并制造着可现成化的、对象化的童年意义。然而,学前儿童“虚”而“失焦”的时间性及其体验却清晰揭示了,教育者唯有回返到一切现成对象化之先,才能够真正发现童年生活的意义,此意义已不再是任何已呈示而出的“实”意义,而是童年本身能够去构意(构造意义)的原意义性(意义之源),它由时间三个向度潜在的氤氲交织而生成。Z1C4TKHIBgvvnSgQ+71B4w==现成对象化了的意义是“冷”的,它“脱开了正在进行的过程或正在投入的意识,站在另一个更稳定冷静的层次上来理解这个过程或意识”;而原意义却是“热”的,它始终处在正在发生与构造着的体验过程中,内含着时间的多维“晕流”,彼此卷席、腾空激荡而热力蓬发、生生不息。[30][31]面对童年的原意义性,教育者唯有完全投身去迎接和感受此原发意义的热浪涌动,在不离开其发生构造性的胚根处来关照、追随和培育它,而不能强行掺杂外在的意图作为更高位者,来对童年生活予以观视、操纵与塑造。现成对象化方式——无论其构思多么精巧,意图多么善好——终究脱开了经验的热流,会面临使童年生活立体多维的时间性构意“遇冷”,而收缩于成人静态、单向的当下欲念及视点,因此失去“活”的生命力的深层危机。总之经由现象学视野的变革使我们看到,时间本身不再是成人视域下用以支配生活过程的现成坐标或体制,而是那能让幼儿自发进入到一个意义涌流的生活之中的原初构意机制;而幼儿园时间实践的根本使命,就是要通过多样化的实践途径,来保护和激活童年原本热力涌动的“时流”,并进一步以“社会—历史”的势能扩大它,从而使幼儿园生活的“船”能随顺此“意义热流”的涌息与翻腾而“扬帆航行”。
那么在幼儿园生活中,为促发童年意义性、体验性的原初“时流”,教育者可以有哪些具体的实践途径及方向呢?其一是,要卸掉沉重冰冷的现成对象化设定,[32]给予幼儿在园生活过程以宽裕的自由度,以唤出幼儿热切活泼的自发活动。由成人教育者直接设定的一日活动环节、步骤、规则及其意图,只是实现了幼儿园生活的“冷启动”,却不足以唤起幼儿对生活的原发热情与投入,从现象学视野看,教育者恰恰首先应尽量悬置起对幼儿园生活何以开展的自我预设,(所谓悬置,其“根本不是一种执态,恰恰相反,它是摆脱一切执态,是对一切执态的抑制”[33])唯有融化掉成人自我的主体性欲图统握一切过程,而要为幼儿的在园活动“立(实)心”的执念,才能让童年原本的时间生活现象先行现身。我们不要担心离开了教育者“我思”性的筹划,幼儿的活动会走向失序、缺乏质量,当成人动心忍性,让幼儿在充分包容与悦纳的自由度中,能够真诚无伪(装)地展现自身、做回自己时,就会发现:幼儿会非常热切地投入自主的活动,因为内在原发的时间性构意机制总是驱动着幼儿自然而然地投身生活,通过自由变换的想象、构造时机化的情境和出神的美感体验等,来赋予生活以意义;而幼儿的自发活动,虽不具有成人那般可理智对象化的实体性意图及规划步骤,但其“凭虚而行”的势能,却会促发如维果茨基所言的,让幼儿有可能获得比其日常行为“高出了一头”的表现。[34]这是因为对活动的深切的自发投入,会让幼儿内感知的滞留与前摄同当下产生更加原本而紧密的交叠互融,从而“虚构”出超溢于一般现实的更多意义与体验的可能性。总之,教育者应提供幼儿以充分的自我活动的机会,这种自主自发的活动——它符合学前教育领域中的“活动”的本意,即幼儿内在力量向外部的舒展与生长[35]——能自然而然带出童年原意义性的时流,实现幼儿园生活的“热启动”。
其二是,要尽可能多地为幼儿创设和提供具有开放结构的活动材料及场地。我们不仅需要鼓励幼儿自发活动,并且在自发活动中,教育者所提供的园内活动材料与场地还应当给予幼儿以开放性的交互体验反馈,才能更有利于童年时间性的原意义构建。如果幼儿园的材料物品与空间场地仅具备固定的使用机制或装饰、展示的效果,那么其内在结构就相对封闭、板结而无机化,从时间性角度看,这些物品与空间在设计上,更多是以当下可见的现实功能向度作为其突出本质,却不具有足够的在时间的多维层面游刃变换、有机互通的潜在活力。因此会导致幼儿在使用它们的过程中,总有可能遭遇一种显眼的不称手、不自在感,这些过“实”之物在幼儿“凭虚而行”的自发活动中“挡着路”了。用具本应助力幼儿更得心应手地去自主构造意义,而非反过来因自身功能的限制而制约幼儿活动的意义发挥,这则进一步要求,幼儿园的活动用具在其创设过程中就应被先行赋予开放的结构。开放结构是指,用具近乎仅含有构成自身的天然的或是最为基础的元素,但是在此基础之上,又余留下了无限灵活的可建构性和变换性,并且不同用具及其可能引发的活动之间不存在明确的边界,彼此的内在元素常能“交相辉映”“互补相生”,从而激荡出“多声部的共鸣或协奏曲”。从时间性角度来看,开放的结构相当程度地弱化了园内用具即时发挥特定功能的现成向度,它们的意义犹如被“延迟”了,(总可追问其意义究竟为何,却不能马上得出对象化的客观答案,因为这“延迟”有自身可回旋腾挪的余地和自由度,总可能随后呈示出更多)现实在这里就不再作为幼儿感知意义性的终极来源,而是要成为反向促发幼儿由“实”入“虚”的引子、通道。也就是说,活动用具的现实状态,由于没有道尽或限制住用具本身的意义性,因而它总是暗中邀请、促发幼儿进一步以盈余出此时此刻的原意义性、时流性的活动方式——实显的现在由此回到了其非实显的母体中,再度被“自由的、随机的、涌动的、旁通的”[36]过去与未来气晕所托浮和活化——而继续不断地去探究、激活、创生并赋予和道说出,这些活动用具以及它们在彼此组合关联间可能呈现的,那些不可计量的“活”的意象、故事和生趣。
其三是,要推动意义交流的关系共同体的构建。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考揭示了,他者是“我”所可能遭遇的更远的过去和未来的可能性,“我”的身体及心灵所能感知的时空域是有限的,但当能与他者的“我”及其感知视角(视域)产生有益的交流时,却可构成一种“我们”的关系性共同体,这是一副拓展了的“大身(心)体”,每一个体的“我”虽仅犹如归属其中的一个感知器官,但却能在此“大身(心)体”有机联通各感官的“活”的运作中,凭之感知、体验到生活时空更为广阔且深远的意义涌流。在幼儿园,儿童所体验和构造着的意义时空域,也唯有在与其他幼儿、与教育者的富有生命力的意义时空域的交汇中,才可获得进一步勃发伸展的超越性、连续性势能。但幼儿园教育实践,应该如何去构造关系化的意义交流体呢?
一方面,应激活幼儿自我本有的交互性潜能。幼儿的“我”不具有囿于当下实在的“我执”性,其内在时间性的三向度在原发的“虚”态中彼此舒络活通,所以本身就有开放地迎向他者的主客未分的流通性、感通性,也即幼儿的“我”本质上就能够去承载“我们”。对此,瑞吉欧教育的领头人马拉古奇(Loris Malaguzzi)曾称赞道,“幼儿并没有一味地过度执着于他们自己的想法,而是不断地建构并修正观念,幼儿倾向探索、发现、改变他们的观点,喜欢以各种形式与意义来转变自己”。[37]教育者需珍视和保护幼儿的这种先天的交流本能,提供宽松的生活氛围,容许儿童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能够通过身体的自由移动、彼此亲近,而自发与同伴、成人建立起对话和合作,以此推动意义时空及其构造方式的分享、流通与共创。
另一方面,教育者还应积极变革自我。教育者的“我”要不再倚重于其当下统握的现成权能,而将自身同幼儿之间的关系异化为单向性的控制与服从,缺乏对幼儿心声的倾听就无所谓真正的交流。虽然当前在“以儿童为本”的立场影响下,前述情况于实践场域已有很大改善,但教育生活中仍存在成人虽以幼儿的想法为起点,却又总欲图从中嫁接上自己设定的各种对象化、概念化的生活意义的现象。①而“如果一个人在预先确定他的行为形式的方式中与他人发生关系,那么可能只有非本质的关联产生”。[38]教育者变革自我,是要让自我更加具有时间本身的流动性,而能逾越出“我思”性的当下中心,让意识灵活地游走于过去与未来的边缘。时间的边缘处是成人进入儿童心灵的通道,它要求成人放弃用即刻性的观念立场与价值标准,去定义、把控幼儿的心理及其活动,因为任何当下的印象与判断,不过只是成人的自我所能设想或把捉到的,关于幼儿或童年现象本身的一个实显的侧面,但任何童年现象却都具有时间三向度潜在沟通而生成的立体动态的意义性,也就是说,成人内在拥有的平面化的现成意义框架是不足以去解释和容纳童年现象潜藏的各种意义可能性的,而时间的边缘处就是挑战、震荡、超出甚至解构这种当下既有设定的意义开放处,它要求成人的自我意识必须向外朝向幼儿本身,以“热”的运思去持续欲望、追踪、支持、看见、倾听和迎接幼儿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进一步的自我呈现与表达,让成人对幼儿及其想法行为的任何当下发现与理解都建立、生成并修正完善于因有这种时间边缘的生发背景的参与而构造出的“活”的时境中。在具有整体性的时境里,成人的思想才能时机化地找到与幼儿心灵真正的交汇相生之处。与此同时,一名专业的教育者还应将自我的意识引向更为辽阔深长的时空边缘,而能在人类的视域中来看待和指引幼儿的活动及生活的发展,使交流更富有成效。“视域”不同于“视点”,前者还涉及溢出实际视点以外的边缘所隐含的各种可能性,如人的视点专注于一本书的内容,但其视域却可容纳并能去注意到书的周围其他可能的背景事物,以及它们与书之间在时空上的意义关联。而当胡塞尔谈到由人类的多重视域构成的“生活”或说“生活世界”时,他本质上想强调的不是任何具有实体意义的生活,而是一个使人能够不止息地去追逐、发现、知觉和体验到生命意义的无限开放的生活时空域。[39]因此,当教育者不再局限于用自身单一的视点以至视域去理解生活,而是将自我置身于人类的“社会—历史”的思想文化的纵横中时,教育者就能运用多方位而有层次的历史与未来的意义线索,不仅能够发现幼儿正在构造着的生活所显示出的“活”的意义,还会看见这些活动体验所可能拓展、生长及与其他意义体验相联结的多元化的潜能趋向。教育者的视域所能触及的时空边缘越是深远悠长,就越能去看见和促发意义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可能性,而非让童年种种意义的流动止息于有限的个人目光与教育尝试之下,因此也就会让教育的交往与指引越发带有人性的包容、善意及智慧。
总之,幼儿园教育实践应怀有对儿童的活时间、活体验及其发生发育过程的深层迷恋,②这种迷恋会让我们的教育生活更加忘却时间,同时也更加惜时——忘却现成对象化的计数时间,珍惜生命体验的意义时间。
四、余论
如果说,随着儿童成长的过程,其未来生活的时间结构必定会再反转为以当下、现时为中枢,那么教育或者说幼儿园教育何必还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去保护和维系童年早期的时间生活与原意义性呢?除上述已阐发的缘由外,从现象学视野来看,最为“终极”的理由在于:“无论思想如何变形,都不能扯断它的现象‘脐带’,因为现象本身的丰富、微妙和生动远超出了一切对它的抽象、重构和超越。抽象与超越是我们构想出来的,或概念化的,如果它们不是服务于对现象的体验和理解,而是要管制和规定现象的话,那么就必将导致哲思品质的萎缩。”[40]童年这一人之现象的“脐带”、童年独特的也是人之原本的时间结构,不是随着成长而可以逐渐丢弃的虚而无用的“边角料”,而是“无用”之中总藏有意味深长的“有用”,“去预设一个对于无意义事物不再有知觉的人,这是很糟糕的。这样的人已经落入意义现象的物化和表面化,这种趋势将他固定在完全确定的价值和目标之上,并且在他之中维持了一种信仰,即本己的‘生活的意义’应该是通过完全确定的意义预先设定和目标设置而被充实的,但是情形并非如此。人总是需要无意义的和意义缺失的事物”。[41]一颗“童心”及其所激活的现象、体验,就是无论如何都会在人的一生之中去护佑人自身不至于走向完全现时的故步自封、自我沉沦甚至自我终结与毁灭,而是能不断“游戏”在边缘的、缺失现成意义的、整体性开放的意义流、时间流之中,从而又能以动态发生的、立体交叠的时间体验去塑造出他成年过程中所要面对的概念世界、抽象世界的“生命肉身”,赋予它们以“活”的意义,将这些抽象的、超越的产物和构架,用于服务自身也是整个人类的生活体验及其发展。而在当今这样一个高度技术化的世界中,上述所论或许还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教育必须先行护佑人的“童心”,“童心”才有可能庇佑操纵技术的人免受技术本身的现成对象化操纵,使得人总能在“游刃有余”的时间边缘“绝处逢生”,生发出生活发展、社会进步及万物整体共存的崭新的、生生不息的可能性。
注释:
①对此有较为生动的案例作为佐证,案例引自《幼儿教育》杂志2019(Z4)版的“卡壳的西瓜虫探究活动”讨论话题。此案例中,教师带中班孩子去幼儿园的小花园寻找小动物,孩子们对无意间从一堆枯叶中翻开的西瓜虫尤为感兴趣。教师认为这是一个开展关于西瓜虫项目活动的有利契机,随后想引导孩子们去探究“西瓜虫住哪里”,但过程并不顺利,幼儿总是忙着抓西瓜虫玩,并且喜欢触碰它的身体逗它卷成球,本来的任务却忘了。教师认为这样不能培养孩子的学习品质和科学探究能力,于是又想主动引导孩子聚焦于探究“西瓜虫究竟有几只脚”“西瓜虫吃什么”等问题,仍然没有获得积极的反馈。教师不禁困惑:为什么孩子明显对西瓜虫感兴趣,但在探究活动中却一直满足于抓西瓜虫,而把探究问题抛在脑后呢?仔细分析会发现:在这一案例中,孩子的兴奋点在于寻找西瓜虫、玩西瓜虫,感知和探索与这一小小生命的互动带给自己的乐趣,而教师认为孩子应该将兴趣主要集中在了解西瓜虫的相关知识上。这二者之间有意义起点(西瓜虫这一小生命)上的交织,但在此之后,教师与幼儿在意义涌流的趋向上就背道而驰了。
②此论述是对范梅南“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参见《教学机智》2001年中译本第18页)的改写。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物理学[M].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5.
[2]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M].丁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79.
[3]黄进.重塑时间生活:幼儿园时间制度化现象审思[J].中国教育学刊,2019(06):57-63.
[4]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21.
[5]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9KZgEVA7QnCauxUfR4htew==6.
[6][18][40]张祥龙.什么是现象学[J].社会科学战线,2016(05):3,7,1.
[7][8][25][26][27][28][29]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12,223,69,138,314,375-376,469.
[9]皮亚杰.皮亚杰教育论著选[M].卢濬,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2.
[10]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M].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2-27.
[11][12]DEANNA KUHN, ROBERT S, SIEGLER.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ume 2: cognition, perception, and language[M].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2006:373-425,185.
[13]卫俊.试析梅洛-庞蒂如何捍卫儿童画超越线性透视法的价值[J].美育学刊,2021(04):48-55.
[14]MAURICE MERLEAU-PONTY. Child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the sorbonne lectures 1949—1952[M].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0:169-170.
[15][16]ALISON GOPNIK. The philosophical baby: what children’s minds tell us about truth, lov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9:125-130,12-13.
[1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3.
[19]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50.
[20]张祥龙.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49.
[21]张祥龙.想象力与历时记忆——内时间意识的分层[J].现代哲学,2013(01):65-71.
[22][23][36]张祥龙.现象学如何说明“美感”与“神秘”[J].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2023(01):29,29-30,29.
[24]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49-50.
[30]赵炎,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儒学,儒学转化现象学[J].当代儒学,2011(01):330-335.
[31][32]张祥龙.复见天地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44-61,54.
[33]郑辟瑞.张祥龙的胡塞尔研究——回答意义现象学如何可能的问题[J].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2023(01):187.
[34]维果茨基.社会中的心智:高级心理过程的发展[M].麻彦坤,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8.
[35]罗瑶.幼儿园教育中“活动”概念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澄明[J].学前教育研究,2023(12):14-26.
[37]爱德华兹,等.儿童的一百种语言[M].罗雅芬,连英式,金乃琪,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4.
[38]罗姆巴赫.结构存在论:一门自由的现象学[M].王俊,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35.
[39]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4-37.
[41]罗姆巴赫.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结构存在论的问题与解答[M].王俊,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49.
Time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Horizon and Its Implication to
Life in Kindergarten
HE Gang1, XU Ting2
(1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2Kindergarden of Hunan Normal O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setting time by counting transforms the essence of life in kindergarten into a fully given object. However,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horizon, the time as originally experienced by humans is not confined or condensed into ready⁃made; instea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 genetically and meaningfully background halo that transcends the present. The enlightenment from this discovery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 kindergarten should be based on a temporal structure that is non⁃objectivated and has its dynamic mechanism for the genesis of meanings. This particularly implies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a profound exploration into the primordial experience of time by young children. Further findings through the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reveal that the time experienced by preschool children has a halo⁃like structure which is inherently “defocused”. This distinctive structure is not situated within any ready⁃made object, thus restoring the original state of human existence. It also further illuminated that the temporal life of preschool children is inherently imaginative, contextualized, and rich in aesthetic experiences. In sum, it endowed with original and profound capacity for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Life in Kindergarten should emanate from the primordial and vivid temporal experience of preschool children, but it should not stop there. Within a deeper phenomenological horizon, it is essential to draw upon the “societal⁃historical” dynamics from the “life⁃world” to surround, nourish and expand the temporal halo of the individual life of young childre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nature of time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horizon will also lead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current temporal practices of life in kindergarten.
Key words: Phenomenology; temporal structure; children’s temporal experience; life in kindergarten
(责任编辑:刘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