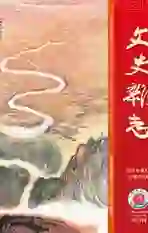时空述行与媒介考古:天地人模式下的“地—文”结构、文学图志及地理共同体史诗学
2024-10-13颜亮
摘 要:《家园》是作家达真的“康巴三部曲”之一,书写了以“水之链”为象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交往交流交融,给人以心灵安抚和精神动源。该书以“天地人”模式下的“地—文”结构叙述,在现实界、想象界、象征界的空间聚焦中完成文本的创造性构筑,呈现出中华地理诗学上的四维度空间指向和意识文化认同。
关键词:家园;中华民族共同体;地理诗学;水
作家达真在其《“康巴三部曲”的总体构思》中说,“我计划用20年时间创作百万字的长篇——康巴三部曲(《康巴》《命定》《家园》),目前《康巴》和《命定》已出版发行进入市场。我希望这三部小说能重铸民族灵魂,给人类以心灵安抚”。如今小说《家园》(天地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也已面世。从清末民初近百年多元共存的《康巴》世象,到近代史上康巴籍抗日远征军的《命定》故事,再到作家宏大视野下以“水之链”为象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家园》命运的书写,作家达真以中华精神与华夏文明本原构素中的“万物莫不以水生”之情势,完成了《康巴》《命定》《家园》的“水循环”百年史诗叙事。其既有大江大河般滔滔不绝的事件生成,又有润物细无声、空阶滴到明般的情愫构式。正如作家达真在《家园》创作时所述“水之链成为传递、输送生命信息的唯一纽带,我们能否在长江和黄河的流动中读懂一种传递、一种链接、一种上源和下源的息息相关?”我们能否在水之万象的链接景观中读懂“命运刻在中华民族每一个个体心灵上的永恒的胎记”这一胎记?
从感性上讲,在读《家园》时,我恰好是汉藏团结家庭的一员;在读《家园》时,我恰好因为要完成博士论文,在康巴的三江流域走了三年并依然生活在香格里拉;也是在读《家园》时,我恰好在那曲班戈县佳琼镇驻村。故事人物王本昌诸多的经历与我共鸣,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读到很多细节时会潸然泪下的缘由。一部作品的完成,并不是罗兰·巴特所说的作品诞生后,作者便没有了主宰地位。在我看来,《家园》这本书,以及它带给我的这份阅读的机缘,成为我个人总结反思的一个契机,也是我继续生活的精神动源。
从学理上讲,小说《家园》涵泳着“海纳百川”式的创作内涵与艺术表征,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对《家园》的自我理解与剖析。
一、水之媒介与地缘根性:
中国传统“天地人”模式中的“地—文”结构生成
(一)空时坐标的构素。正如康德所言:“历史和地理学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扩展着我们的知识。历史涉及就时间而言前后相继地发生的事件,地理学则涉及就空间而言同时发生的现象。”[1]如果说“康巴三部曲”之一的小说《康巴》早已为后来的故事事件奠定了“天地”场域的基础构境,那么小说《家园》单体文本中的故事叙述则在空间所承载和重建的文本时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创作者在“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2],“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3]。实际上作家达真在小说《家园》中的艺术化的时空体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具有中国传统“天地人”叙事模式的根性所在,只是地缘性让作家开启了“生于斯长于斯”凝聚于故土的经验式书写。正如藏学家谢继胜先生在其论著中提到以念神、赞神、鲁神为代表的藏族古代时空意识,其实与汉地所谓的“天地人”时空观不谋而合,其共性展象为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地或神、天与人连为一体,自然与人是和谐的统一体”[4]。这种纵向垂直构织才形成了横向水平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我时间和空间的复合体以及叙述的整合范式。著名学者加布里埃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提出了“时空层”概念,即地形层(地志学)、时空层、文本层,意指空间结构通过事件和运动(也就是通过时空体)作用于空间。在小说《家园》文本层之中,作家以生生不息、天地循环、落地成形的“水”为媒介,链接了横向空间上海与康巴两个地形层,以及汉藏两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势下共时关系和历时关系中人物、环境、物体、事件、心理、历史、文化等构素综合下的创作构式中的运动/静止、叙述方向、事件轴心与陈述力量。
(二)地理文化的构素。人本地理主义学者段义孚先生在其《空间与地方》等专著中提出“地方感”是生存个体/群体经验对地方性知识的某种说明,“人与地方的情感关联”是凝结于个人经验之中的人与地方的情感连结。当这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感、恋地情感与地理文化转向文学,试图在地理信息、人文知识和人类想象力之间建立一种更好的平衡时,一种“以地释文”“以地生文”的创作就生成了文本场域。布尔迪厄对“场域”本意的解释是“场域是指受共同行为规则制约,并由一组符合惯例的言语情景构成的活动领域”[5],也指“各种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网络结构,一个场域代表了社会生活的某个亚领域”[6],不同社会客观关系构成的关系所建立的社会实践空间就此展开。作家达真因地方性知识的情感性和场域构织生成了独特的文本场域二分景观。如果说《家园》小说文本场域中曲扎、王本昌因时代浪潮下的家族变故,展开了文本场域空间中出逃与入藏张力下的叙述亚场域,二分的亚场域因人物情势的进一步变化,生成了次级场域中以人物斯郎措、达瓦志玛、尤格谢福、土登等为主体的叙事场域,各种人物、故事线、事件情势构成了家园故事上层建筑,那么康巴的地方性知识则称为显性故事下的“神秘的领域”——这一隐性的文本场域由主线、次线小说人物感知、行为和自然人文环境的影响构成,其核心便是场域之中各种力量构素的和合共生,纳含了政治力、文化力、经济力、宗教力等诸多共生合力表达。
(三)人的事件的构素。在作家达真所构境的以“水”为链接的文本空间之中,不断涌现的人物、环环相扣的故事、和谐嵌入的情势,实际上主体是人的事件话语的他者性、创新性、独特性,其构素就是中国传统叙事模式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自我的“和合相生”横向铺陈。表现在《家园》小说文本之中,“人与人”是曲扎与斯郎措之间单向度的承诺守护,是王本昌与达瓦志玛之间的相濡以沫,也是土登与德杰之间的仇恨释然;“人与自然”则是作家润物细无声、漫天星斗般自然流动在字里行间对康巴地方性与地方感的话语构建;“人与环境”从一开始曲扎家族对外部环境所表现出的焦躁反应,去留不定的占卜预测以及王本昌在政治力下的心理行为、一路向西之后的下放生活,无不显示着人之命运与环境的纠葛斗争;“人与自我”在小说文本之中更多地显现出典型人物在经历一系列人间苦难、世事难料与时代变迁中由外而内的自我思考与反思。这里有反思后的爱情坚守与背叛,有历经苦难后的冰释前嫌,有生死过后的生命感悟,也有苦尽甘来的感恩永存。人性的复杂与亮色在一个文本世界之中因为叙述事件的不断延伸与拓展,继续着每个人物差异性的自我对话与精神样态。
二、现实界、想象界与象征界: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文学图志述行范式
(一)现实界叙事中的空间聚焦。拉康认为现实界“对主体是现实的一切”[7],创作主体将原始无序、混乱无章的个体经验(包含自我经历、他者吸收、无意触动等综合现实的发生),以朱光潜先生所述有言之美/无言之美双重创造的方式予以新的文本现实。现实是具有伦理的现状,是“人性中赤裸的属性”[8],是作家心灵创造的全体真实界沿着单线进展,而不断拓展的复线生展。正如意大利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所述,创作就是“当覆盖在物之上的那层面纱——那个聚集着社会关系中人类经验的象征网络——被撕开,真实界的骇人一面就显露出来”[9]。作家达真在现实界叙事中空间的聚焦是现实真实书写令人惊讶的技艺,这一地方感情结动力为驱动的创作集聚于恋地/虔地情结、地方感与家园三维性的合力之下。这些内在情感与力量持续变现为小说文本中家园——他乡之维中曲扎、土登、王本昌的精神望乡;城市——乡土之维中达瓦志玛上海栖居的心路历程;本土——异域之维中王本昌的身心转换以及最终文本典型人物在现实——超越之维中所实现的个体释然与群性融通,皆是在空间聚焦中完成了文本的创造性构筑。
(二)想象界叙事中的漂泊皈依。作家的想象力、语言与创作规则构建了其文本世界的想象界,建立在“实在——非实在”这一哲学逻辑对偶之中,按照生命主义者“柏格森的方式下定义:实在是合理的连接,是现实事件的连续衔接;非实在是对意识突然打断和意识的不持续,是实在化的一种潜在”[10]。在这种潜在之中作家论及自我镜像、他者形象组成想象界的多元认同以及对社会文化符号构成的想象界认同,德勒兹认为“想象界是一个不很确定的概念。它必须严格地置于一定的条件之中,条件就是晶体,而人们所达到的无制约者便是时间”[11]。在地方性知识、人物有机动态化发展以及精神性重构的文本创造过程中,作家的想象力乃于个体/群体的漂泊并皈依主旨中予以凝塑。表现在:一、随处可见的格萨尔神性描述与精神想象中;二、“罗兰·巴特把爱情看作在想象界的经历”[12]——曲扎与斯郎措、王本昌与达瓦志玛以及无数复线中存在的爱情想象界就成为小说文本起承转合重要的叙事结点;三、“望乡叙事机制”中的想象界展现了“精神望乡”前置条件的双重性,即离开家乡身处异乡,相思哀愁故土眷恋,两者相伴相生。作家在不同人物命途中设置更为具体的“精神望乡”的内涵层序性,那就是归属于何处、拥有家园与身处之地的融合。例如小说中对曲扎家族、王本昌家族以及作为复线存在的尤格谢福家族,作家将故乡、家园、民族、国家、祖国的差序性,利用叙事想象力巧置在同一个意涵序列之中,从而把人物设置由家而国最终达至“齐一”认同的价值内化。这实际上也体现出作家作为创作者在想象界构建中的精神想象的饱和度。
(三)象征界叙事中的主题重构。象征界是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联动构筑下“实现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13],“意识到自己、他者和世界而逐渐使本身‘人化’或者说‘主体化’的”符号凝塑界域。“象征包含着空间上的共域性和实际上的共时性”[14],象征性符号则“是对日常生活的突破,可被视为一种象征性的和富于表现性的行动,一种制度化的创造特殊时空的手段,个体在其中可以体验到自己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的感知与认同。小说《家园》文本中的“水”的象征界构筑贯穿文本始终。从小说一开始讨论“水是有听觉、有视觉的,水知道生命和灵魂的答案”“我就出生在长江的源头”,到后来叙述中水无处不在,再到最后“碗上的两条龙围绕着碗中的水,就像长江、黄河绕缠着被称为‘亚洲天然水塔’的藏东,而这个天然水塔滋养了中国和南亚的众多国家”。悠久的中华水文化不仅成为创作者宏观创作中的精神主旨,而且也成为小说人物链接、情节链接、地理链接甚至成为人类共同体链接的重要象征符号,其本原就是中华民族水之象征符号的多重意涵。从上古神话中关于中华民族先民居住水边的记载,到中华元典河图洛书的水之源叙述,夏商周水与阴阳之气的记述,再到诸子百家水生万物思想的建立,乃至后来水助力于精神有了“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水乳交融”,以水为象征早已内化为中华各民族独特的水思维和水精神,也成为作家达真在创作《家园》中追溯源头、融入大同的重要主题构建动力。
三、诗性符号与精神考古:
中华地理诗学中的四维度空间指向与意识文化认同
(一)地理诗学中的符号基础。中华地理诗学是米歇尔·柯罗所谓的一种融合苦难与奋斗、充满人性拷问栖居的诗学,也是一种把文学创作与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的思考。肯尼斯·怀特《信天翁的高原:地理诗学导论》说,其“以在人类的精神与大地之间的关系为地基,它构成这种关系在知性、感性与表达层面上的发展” [15]。作家达真在小说《家园》中的地理诗学不仅仅类似于“脚印同牲畜的蹄印混在一起”“女人是男人的帐篷”等表层化诗意的语言,而更是深层次所涉及的一种精神游牧主义的“诗意栖居”,涵泳了一种作家独特的精神描绘法,一种内/外部日常生活的概念。神话、信仰、民俗、生死、山水……诸多概念以表达生存感的内容,富有节律的语言陈述于小说文本间;但更为具体的则是创作者与土地能量、形态、节奏之间的一种默契把控,从而以文学为主体,交织史诗、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由此强化了作品文本张弛有度的生成学价值与意义,推动了作家达真地理诗学结构中空间诗学、地形诗学、地缘诗学的不断延伸与拓展。此即文本内层中生死循环的圆形构建、整体—延展—融合的诗学内涵、在过去的忆念与现实的真相之间,挖掘迷失与救赎的内在,并希冀温暖的意蕴以及“真善美”相遇场域中诗意是存在的唯一的基本形式。
(二)四度维向中的精神考古。小说即使依旧以故事取胜,《家园》之中也仍然存在作家达真一次次的冒险式的精神考古,如同手术刀解剖一般直面个体命运、家族前途,以独有的复调式写法和圆形结构的设置,将概念世界、现实处境、精神象征一一予以多面展现。正如皮尔斯所述“在我们熟悉的经验的三重宇宙中,第一重宇宙是由观念构成的。诗人、纯粹的数学家或其他人可能在心灵中为这些空气般的非物(Airy Nothing) 赋予所在和名字……第二重宇宙是物和事实强横的现实性(Brutal Actuality) 。我相信它们的存在是在于对强制力(Brutal Force) 的反应之中,尽管对此有不容忽视的反对意见,需要经过仔细、清楚的检验才能确证。第三重宇宙由一切具有在不同的对象之间、尤其是在不同宇宙的对象之间建立联系的积极力量的存在构成。这些存在本质上就是符号——不只是符号的身体(Body) ,还是符号的灵魂(Soul) ,它存在于对对象和心灵的媒介功能中” [16]。在作家文本的精神考古中一度维向是“水之链”——水的精神是与中华民族哲学之“道”齐一的精神性根基,以抽象概念/具体江河海形态播撒文本叙事当中,完成了宏观统摄性的精神“元在性”。二度维向以叙事具象的方式聚焦了差异性空间,共时性视域下的家、家族、家园,通过“三重摹仿”完成了精神指向,即是日常生活中对‘经验的叙述性质’的前理解——建立在话语内部的叙事编码——叙事对现实的重塑、精神隐喻的显现。三度维向直指文本人物感知世界,凝塑为人类精神内质的恋土情结,并以事件、行为赋意给克里斯蒂娃所谓的“子宫间”理论更多的文化和主体话语意涵。这种意涵,精神意义就向四度维向满溢,在叙事话语中潜移默化地展开文化释义与开放之态,“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 [17]。
(三)家园主题中的文化认同。作家达真的“家园”主题在文本世界中不仅仅是曲扎的逃离与眷恋、王本昌的异乡与融合、尤格谢福的上海记忆,而且也是家、家族、家园、家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次由具象到抽象的“家园意识”凝塑与人类生存性认知,这种意识与认知存在着漂泊与皈依的哲学指向。古往今来,中西方文学家多以漂泊与皈依为主题,书写了巨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漂泊二字皆从“水”字,一指身体性漂泊,一指精神性游离。从《诗经》中的流浪之歌伊始,屈原《离骚》中的精神远游,汉乐府、魏晋南北朝的行旅,唐宋诗人的流浪情结,元明清诗人的侠气江湖,这种在漂泊之中与孤寂、沧桑、悲凉、死亡意识相伴的精神审美,直至走到五四运动之后,因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生命形式在文学中的出现,才有了新的精神品格。进入到20世纪中国文学家园主题中的漂泊之意,一则显现出了空间家园体验的失根性反抗;二则为实践家园体验的碎片空洞性;三则为性格家园的差异性体验和危机焦虑陈述。作家达真的“家园”主题在找寻漂泊破局,解决千百年来中国文学漂泊母题的精神性指归,展现出一种更为厚重与新的创意。主体表现为:其一,文化寻根的精神指归,作家达真避开了像叶舒宪先生所述“寻根”措辞的一种隐喻,如叶落归根、狐死必首丘等,而是直接抓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性之中的哲学“基元”——水之本质,其背后的实质则是大同思想的融合与生命的存在意义;其二,信仰原型的精神指归,包含了格萨尔史诗的英雄精神、崇尚自然的生态精神、经历苦难的革命精神等;其三,综合伦理的精神指归,按照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的伦理结构,即乡土—国家—民族的序列范式,以儒家为主体的伦理横纵间构筑了偏向于人与人之间的仁义礼智信伦理思想,而作家达真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汉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内容,实际上补充加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自我更为全面的伦理思想。同时,这一思想将乡土—国家—民族的序列范式,拓展到乡土—国家—民族—人类序列范式,这种动力也是天下大同、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自然地理学”,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163页。
[2][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第269—270页。
[4]曹娅丽:《青藏高原生态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民族出版社2021年版,第57页。
[5]郭鹏:《思想政治教育网络传播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0页。
[6]范叶超:《岁岁炊烟:中国乡村的日常生活与环境变化》,载洪大用总主编《中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研究丛书》,河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页。
[7]王善钧:《由结构走向解构》,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
[8]刘介民:《原典文本诗学探索》,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9]罗伯托·埃斯波西托:《人与物:从身体的视点出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版,第74页。
[10][11]吉尔·德勒兹:《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第89页。
[12]尹乙:《勇于逃避》,章科佳、张蕊译,海南出版社2022年版,第64页。
[13]夏基松、张继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7页。
[14]周雷编《人类之城:中国的生态认知反思》,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15]Kenneth White,Le Plateau de V'Albatros: Introduction à la Géopoétique(Paris:Bernard Golbid.)p.200.
[16]Peirce,Charles S.,et al,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1958).
[17]卡西尔:《人论》,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后,西藏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