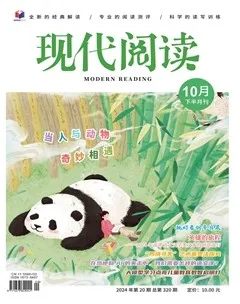挑灯看剑辛弃疾(节选)
2024-10-11祝勇

淳熙十四年(1187),太上皇赵构去世,走完了长达八十一年的漫长人生。两年后,对政事心生倦怠的宋孝宗把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惇,是为宋光宗。
绍熙三年(1192),辛弃疾终于再被起用,做太府少卿,后又做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安抚使。只过了两年,宋光宗就禅位于次子赵扩,成为太上皇,赵扩即宋宁宗,与辛弃疾关系甚笃的赵汝愚升任右丞相。
但韩侂胄因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有功,以“翼戴之功”上位,很快把持了朝政。韩侂胄的当政,终结了宋孝宗时代相对宽松的局面,回到严酷独裁的“绍兴十二年体制”上。宋孝宗或许不会想到,他对相权的控制与打压,到了宋宁宗那里,却出现了权臣的专政(韩侂胄虽然未当过宰相,最高职位是太师,而且太师是虚衔,最高实职只是枢密都承旨,但权势已在宰相之上)。自韩侂胄之后,史弥远、贾似道这些权臣“你方唱罢我登场”,如南宋名臣王居安所说:“一侂胄死,一侂胄生。”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宋朝政治走到了最昏暗的时刻。
像秦桧一样,韩侂胄有恃无恐地打击政治对手,右丞相赵汝愚首当其冲遭到贬逐,与赵汝愚关系密切的辛弃疾、朱熹、陈亮也在劫难逃。庆元二年(1196),赵汝愚在衡州暴卒(一说服药而死),辛弃疾亦被罢官。
辛弃疾平生努力,再一次被归零。只是这一次下岗更彻底,平生获得的所有官职,全部被撸干净了,变成了一介白丁。他曾在信州闲居十一年,这一次赋闲,又是长达八年,直到嘉泰三年(1203),才被重新起用,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那一年,辛弃疾已是一位六十四岁的老人,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四年。
嘉泰四年(1204),人心尽失的权臣韩侂胄为了提振个人威信,怂恿宋宁宗挥师北伐,“立盖世功名以自固”。由于辛弃疾出生于北国,而且是著名的主战派,因此宋宁宗赵扩召辛弃疾去临安,请他献计献策。出发前,辛弃疾到鉴湖拜谒陆游。那时陆游已年逾八旬,住在鉴湖边上的陋室里,“皮葛其衣,巢穴其居”。辛弃疾一直想为他改善居住条件,陆游一直没有答应。那一次,陆游给辛弃疾写了一首诗送行,最后两句是:“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意思是不必像汉代李广那样,复出后追杀曾羞辱过他的灞亭尉,也就是不必纠结于曾被韩侂胄迫害的过往,而积极协助朝廷兴师北伐。
六十四岁的辛弃疾,依然怀揣着他二十四岁的梦想,穿越阴沉沉的荒野,携书仗剑,奔赴朝廷,向皇帝进呈北伐金国的策略。要说恢复北方,没有人比辛弃疾更急迫,但在辛弃疾看来,汲取隆兴北伐失败的教训更加重要,所以他向皇帝进言,切不可像当年那样草率行事,一定要经过一二十年的准备才可行。他还向皇帝暗示,北伐大业,光靠韩侂胄身边那些只会摇舌鼓唇的小人是不行的。
这样的准备,其实辛弃疾已在暗中进行,比如任浙东安抚使时,他曾派人深入“敌后”(山东、河北一带),探听金国虚实,还亲自把侦察来的金军兵骑之数、屯戍之之地、将帅之名统统绘在“方尺之绵”上。但韩侂胄急于取得“政绩”,决不会等上一二十年,也不会做这样细心的准备,更不会把深谙兵韬武略的辛弃疾派到战斗第一线。他想独揽北伐之功,担心这天大的馅饼会掉到辛弃疾头上,等辛弃疾献完了策,就让辛弃疾卷铺盖走人,把他打发到远离前线的镇江做知府。
果然不出辛弃疾所料,韩侂胄仓促出师(史称“开禧北伐”)即遭惨败:“一出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
连韩侂胄自己,都被史弥远和杨皇后合谋,在上早朝时,提前部署军士,将他劫持到玉津园夹墙内,以铁鞭一击致命,首级作为见面礼送到金国,使两国重新达成议和,规定:两国国境如前,金尽以所侵之地还宋;改依靖康故事,世为伯侄之国,宋主称金主为伯;宋增岁币为银绢三十万两匹;宋别以犒军钱三百万贯与金。
这是继绍兴八年(1138)、绍兴十一年(1141)、隆兴二年(1164)三次和议之后的第四次和议,也是宋、金之间的最后一次和议。
暗弱的君上,酷烈的党禁,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还有轻率的战争,辛弃疾纵然心怀壮志,王朝的政治泥淖也让他寸步难行。他的所有努力,都不过是瞎子点灯罢了。他面对着“无物之阵”。“醉里挑灯看剑”,他的掌中剑,只能刺向一片虚空。
(来源:《当代》2021年第5期,有改动)
悦读拓展辛弃疾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练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真正的诗人只有被政治大事所挤压、扭曲、拧绞、烧炼、锤打时才可能得到合乎历史潮流的感悟,才可能成为正义的化身。(作家、学者梁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