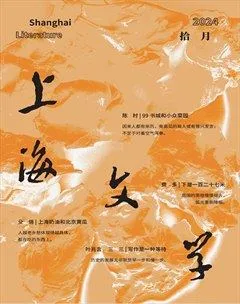小说是对生活可能性的赋形
2024-10-09邱华栋张执浩陈丽汪若
费多的新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可供谈论的空间却很大。几位评论者看到了其中不同的景深,各自从小说的细节、叙述节奏、架构布局等角度切入,最后却殊途同归地意识到这则小说最终触及的是人生的无常以及由此延展出的生活的多种可能性。这固然是小说的一种共性,但在费多身上的显影自有一番独特的风景。
唯有细节知道秘密邱华栋在谈论费多的小说之前,我想先说点别的。
一篇好的短篇小说会把一个故事变成很多个,这会造成一种奇异的阅读效果:读第二遍的时候,知道的要比读第一遍时要少。
波浪所有的秘密都在表面,但它涌动之时,我们会窥见隐藏在其中的“例外”。小说就是“例外”的艺术,对于不少小说,情节可以忘记,人物退到深处,但有些细节,却时不时地被一束记忆的追光灯打亮。人物是细节的总和,情节是细节的异动。无细节,不小说。
好的细节都溶化在小说中,但它们又是一个个陌生化的“刺点”。我在《现代小说佳作100部》里曾提到大卫·格罗斯曼的《到大地尽头》,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名叫奥拉的以色列母亲,因害怕收到儿子的阵亡通知书而离家出走。与她同行的,是昔日好友和恋人阿夫拉姆。书的结尾是:“一阵微风带来墨角兰、蔷薇的芬芳和忍冬的香甜气息。在她的身子底下,是凉爽的石头和整座山,巨大、坚实,绵亘无尽。她想:大地的外壳是何等的单薄。”这个细节的惊异之处,就在于最后这一句:“大地的外壳是何等的单薄。”它击穿陈词滥调,并撕开一个巨大的秘密。
现在来看费多的小说。短篇《下潜一百二十七米》的情节并不复杂,讲的是一个名叫任戎戎的女人,洞潜到水下一百二十七米的经历。而那个深度,正是她女儿溺亡的地方。这个题材属于一个古老的母题:人如何面对丧失?“和解”和“治愈”是可能的吗?何种情况下才得以可能?我自己就写过一篇与大海和救赎有关的小说《唯有大海不悲伤》。所不同的是,我那篇的人物关系是父子,而费多这篇,则是母女关系。
这篇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视角,按照我多年读小说、写小说的经验,不要低估所谓客观视角的“主观性”,也不要低估主观视角的“客观性”。“告密”的总是细节。它们不声不响,甚至绷紧嘴角,但秘密却在悄悄泄露。
在《下潜一百二十七米》中,有很多关于洞潜的技术细节,这构成了这篇小说的物质层面。其中最核心的细节就是“狼牙灯”,它几乎是这篇小说的引擎,参与人物关系的构建,推动情节的发生。这一点并不难辨识,但更富有意味的是那些看似“无关的细节”,这才体现了这个短篇的独特性,以及心理深度。
因为篇幅关系,我主要分析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在小说的开始部分,女主角在错过很多个电话后,偶然得知女儿溺亡的消息。当时她正因为生意关系在打一场高尔夫球。小说如此描述:“任戎戎把球车开得飞快。经过时,她看见他们脸上惊喜而模糊的表情。后来,任戎戎觉得自己当时还喊了一句:小费我已经结了。”死亡就是这么平常地和给小费并置。很日常,也很荒谬。我几乎能听见日常的惯性是如何拖曳着人物,即使她正在承受偶然性的打击。
在小说后半段,任戎戎依靠那个“狼牙灯”,完成了洞潜,心里却觉得“即使下潜到一百二十七米,我也没有改变什么”。结尾,是一段极具生活质感的场景:“花店的门口,一把黄铜色的水壶的壶嘴在滴水。滴答。滴答。临街的钟表店里,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师傅正在用镊子拨动齿轮。阳光下,露天的座椅上,一些男人和女人喝着啤酒,黑色和琥珀色的啤酒冒着泡沫……”这段描写融合了视觉、听觉和触觉,几乎是生活的赞美诗,但就在这时,乐曲突然变调,任戎戎的那个叫“老狗”的潜水教练,死于洞潜一百零七米处。而他曾经创造出亚洲洞潜记录。
像这样的细节贯穿了小说始终,比如死去的女儿,“鼻孔却有些外翻,好像在闻空气中的什么味道”;还比如那堆绳结,“盘在那里,像一堆蛇正在往外滑动”。再比如,关于女儿的死因,人物有一段内心独白:“意外?不是自杀?那一刻,任戎戎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感觉,仿佛这个判决更容易接受。”这是独白,也是自欺,还是忏悔。这些陌生化的细节,是一种时间和心理的双重拍号,它驱动一个故事,又在催化更多的故事。
从一个死亡开始,到另外一个死亡结束,《下潜一百二十七米》用一种圆形结构,再次逼视人内心那些“严肃的饥渴”。小说中,“老狗”在谈到为何要从事如此危险的运动时,讲了一句:“水下有我的庙。”关于这个问题,费多曾经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所有的挣扎都如此平静,所有的挣扎都如此神圣。”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用细节“斜斜地讲出”。因而,我愿意把这篇短篇再读一遍,因为它,已然逼近了好小说的顶峰。
此刻大于命运张执浩费多曾写过一首令人印象深刻的诗,题为《此刻大于命运》。在阅读他的这篇小说《下潜一百二十七米》时,我不禁又想到了这首诗中所描述的一个片段:“那时,我正开车穿过戈壁,/后视镜中,落日正在缓缓下降,正被天空一口口地舔着,/很快就会溶蚀。/我靠边停车,儿子大声叫着跑出。/他追着落日,我追着他,/身后,交叉的道路追着我。/此刻,命运不会追上来,因为他也知道,/这一刻,大于所有的命运之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篇小说与这首诗之间具有很强的互文性,唯一的差别是,写诗的时候他叫“刘晖”,而写小说时他换成了“费多”。但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深刻触及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此刻与命运。前者是肉身在场所呈示出来的矛盾与挣扎,后者是看穿世相之后生命的顿悟与觉醒。两者互相牵掣,互为表里。
《下潜一百二十七米》讲述了一个关于生活与生命的关系、关于沉沦与自我救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人物关系也清晰明了:失踪的父亲、洞潜溺亡的女儿、试图寻找真相的母亲,这三者之间看似很少有日常生活中的交集,甚至不像是一个正常的家庭组合,但却构成了故事内部紧张的近似于“勒箍结”一般的冲突、对峙与和解,且互为因果。小说的主人公是这位名叫任戎戎的母亲——一位身在职场、外人眼里的“成功人士”,工作作风当属强悍之列,但内心深处却有着外人不易察觉的脆弱和不堪(这也符合文学作品里常见的“人设”)。任戎戎是在得知女儿遇难的消息后,才产生出亲近女儿愿望的,而这一亲近的过程却是在她一步步的“下潜”中完成的。死者带着生者走向遥远的九顿,那个“水母天窗”,在漆黑的水底洞穴深处终于窥见了生命之光:“弧光重新降临”,她也终于相信“女儿是勇敢的”。
作为小说家的费多不太像作为诗人的刘晖,在面对主人公如此重大的人生变故时,他采用了极为平静的语调、极为简省的笔触,耐心、细致又专注,深度刻画了任戎戎内心世界里的感情波动与起伏。整篇小说都是在回忆中向前推进的(不是简单的倒序,而是情感的并进),而且是以不断沉坠的方式,让真相慢慢“浮现”出来。如果说,失踪的丈夫是这个事故的诱因,那么,女儿的离家出走和妻子的尾随而至,则是这个故事的必然结局,而这,其实只是生活的表象,真正促使这一连串故事形成完整闭环的,应该是主人公对生命意义的寻找。
“远方”之所以成其为远方,从来不是因为距离遥远,而是源于我们对近处生活的不满,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一种生活能够让人满足于现状。因此,对未知世界无止境地追寻,才最终构成了人之为人的奇特性,它迥异于那些满足于本能的动物性存在。在这篇小说里,哪怕是已经身在天边的那位潜水教练“老狗”,其生命最后也终止在了不断深潜、试图再进一步的过程中,这应该视为人的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的庄重感其实来自于我们对极限生活的挑战,无论是任晓风,还是她的母亲任戎戎,甚或那位失踪的父亲,都应该获得命运的原宥,因为他们都尝试过从前未曾经历过的生活。更何况,任戎戎从女儿留下来的“狼牙灯”那里,还能感受到某种获救的力量:“任戎戎有时会想起,当年她提着一个小箱子来到这个城市时的场景。午夜的车站,灯火闪耀。那个年轻的女人正在一步步地向自己走来。”这是故事的结局,也是一个曾把自己弄丢过的人最圆满的回归。也就是说,故事的主人公在这里才完成了对自我的终极确认。
好小说也许应该就是这样的面貌:故事仅仅是一个外壳,内里包含着丰富的人性。但是,我们对好的小说家总是会提出各种要求,希望他能用独特而高超的语言技艺,讲述我们尚未完全认知的生活情态与面貌,从而达到“替我生活”,并不断拓展我们的生活边界。在我看来,作为小说家的费多,至少在这篇小说中做到了,而且极为专业。进入幻影深处陈丽费多的小说是一场奋力的追忆,这正是他的小说意味深长的地方,因为我们虽然也常常回忆,但通常不会那么努力。在他先前的三篇小说——《底片》《到底开了多少公里》《自行车、猫和港口》的开篇,费多就描摹过一种相似的图景:在我们以为人物当下的生活就要缓缓展开的时候,记忆总会突然干涉,打断正常的进程。如果不去寻找并讲述关于过去的故事,人们就无法重新开始面向未来的、正常的生活。在这些故事里,仿佛一个人的过去与当下有着宿命式的关联,于是小说让追忆成为它的人物的命运——
女儿看见父亲遗物中一张底片上的女人,前去寻找父亲年轻时的秘密;儿子独自开车前往沙漠深处,寻找消失的父亲;出狱后打零工的男人,回忆起在狱中那个“永不消退的夏天”里,排演话剧的过往。这些故事莫不如此。人物们无不开启宿命式的回忆,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完整的故事;但同样相似的图景还有,他们并没有因为讲述了记忆,就拥有了正当的生活,当下生活的可能性依然悬而未决。因为他们只不过是看见了幻影,而没有(或无法)进入深处。
这一次,《下潜一百二十七米》也遵循了同样的法则。任戎戎的女儿在一次洞穴潜水中去世,她来到九顿,跟“老狗”学习洞潜。小说的开头,是任戎戎第一次独自深潜的场景,目标一百二十七米。“水下,”费多写道,“女儿的面孔像一片叶子在那些光亮中漂浮。”于是,一次关于女儿的追忆,和任戎戎从十米、二十米下潜到一百二十七米的整个过程,在叙述中交叉呈现:女儿的“影子”和一个家庭过去的故事,出现在任戎戎当下充满具身性的行动中——她在水下感知到自己的身体,并努力维持着“心流”不断——而女儿,或女儿的影子所承载的记忆,在打断这次危险的行动的同时,也构成了行动的连续性,从而让任戎戎当下的生活得以继续,尽管这看起来并不那么寻常:一种极限运动进入并成为了生活。
这是一个寥寥数语就可以讲完的家庭悲剧。任戎戎的丈夫无故消失,女儿在父亲缺席的环境下长大,与母亲的关系十分疏远。女儿去世后,母亲来到事故发生地。这样概括这个故事,难免具有一种新闻式的残酷,因为它过于简洁,每一句话都如此确定。但费多的小说所赋予这个故事的形式,却如同一首诗中复调的诗节,它们缓慢而充满阻力地连接在一起;就如同母亲任戎戎当下的生活,在水下的行动与过去的记忆之间得到存续。这样的连接与存续,怎么看都不是那么容易,其中充满了断裂与错位,这既是人物的,也是小说形式的。当这种双重断裂被置入故事,小说意图让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断裂如何让生活变得正当的过程。
只是这种生活的正当性并不那么稳固。任戎戎没有找到女儿遇难的原因,完整而连续的故事并不存在,所失去者无法在追忆中重新寻回,而一个母亲的自我救赎也没有完成:任戎戎从水下回来的那一刻感到“茫然”,好像一切又复归空白。也就是说,那种正当的生活,其实只是它变得正当的艰难而危险的过程,而不具有一个可以存续的形态。尽管如此,这种“正当性”依然是珍贵的。不同于《底片》《到底开了多少公里》《自行车、猫和港口》中的人物在追索记忆的过程中,记忆却随之消失了,因而人物的当下依然是破碎的,或是如同沧海一粟,只能融于沧海之中,在恍惚的江景、楼景、街景中,在与过去的无限纠缠中,如同《底片》中那个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在与世界之间形同幻觉的关系中,继续一种绝对孤独的生活,《下潜一百二十七米》中的人物在断裂中,在生活变得正当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完整性——它存在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任戎戎和女儿)之间真实的而非幻觉的关系中;这一关系处于“自己”与“他人”之间,为生活重新置入了“为自己”还是“为他人”的永恒难题——任戎戎下潜一百二十七米是“为自己”还是“为女儿”的问题,在小说中没有答案——小说也因此具有了伦理纬度。
但那源自人类生活的伦理维度,常常并不只是日常关系的网络,有时也会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从而拓展了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如果我们回过头去再看《底片》等小说中的人物,会发现他们在寻求日常关系的过程中反而越过或失去了这种关系,只剩下破碎的幻影;这是因为在那些故事里,要进入幻影深处而不只是看见它,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此时单纯的伦理问题超越了自身,变成笼罩在个体生活之上更大的力量,小说就不得不面临讲述真实关系的失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让追忆成为人物的命运,是费多小说意味深长的地方,它在探寻的是一个人可以寻获怎样的记忆,可以抵达记忆的哪个位置,而当一个人对此一无所获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力量是什么。正是这些构成了一个人生活的界限。充满暗流的水下汪若作家写小说,原本是一个人围绕素材和故事进行漫长而孤独的建构工作。而我很幸运,虽非文学编辑,却从一开始就读到了《下潜一百二十七米》的初稿,得以目睹了费多这次写作的全过程。
读罢小说终稿,我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作家们的写作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类如同雕塑家从一整块大理石中凿出自己想要的形象,再在素材中不断去掉“我不需要”的部分,最终让故事成型;另一类则像喜鹊搭窝一样,四处寻觅“我需要”的材料,不辞辛劳拖回来,按计划逐步码放成堆。
费多应该是前者,而我是后者。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某种开放性,我则有可能陷入到“非如此不可”的执拗中去。
要说明这两类人的区别,只要看看我们围绕这个小说进行的两次对话就会明白。
第一次对话发生在读完初稿后,我喜欢他对洞潜的一切描述,却唯独对其中的一个细节“耿耿于怀”。主人公任戎戎收捡女儿的遗物时,看到一枚女儿平日挂在胸前,来自挪威的狼牙灯——“狼牙做成了一个小小的灯,轻轻按一下就能发光”。在初稿中,这枚狼牙灯是任戎戎买来给女儿的。我却觉得无论如何不该如此,“这应该是父亲买给女儿的才对”。
费多问我理由,我思考良久后回答说,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母亲的故事,而是一个中年女性被迫直面分崩离析的前半生,进行自我清算的故事。如果因此产生了“女儿心中还是有我”的想法,狼牙灯发出的这抹幽光,在充满了复杂水流的黑暗水下,就显得太过温情脉脉了。对一个成熟作家的作品提修改意见,如果没有充足的论据,恐怕很难获得对方认同。但这是我在费多的小说中辨认出的一个带有“我需要”印记的细节——它释放出了强烈的信号,让我忍不住提出了这种听上去有点没头没脑的建议。
他回应我说,要思考一下。
第二次对话则发生在看到定稿的时候,他重写了结尾,改变了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潜水教练的命运。本已熟知故事结构的我看到此处,不由得“哎呀”了一下,很是诧异,一是原本我认为初稿中的结尾很完美,无需再改,二是我私心里很喜欢这个人物,于心不忍。是啊,换了像我这种千方百计找到“我需要”的素材搭建成自己想要的房子的人,可能很难更改如此重要的结构——总有一种抽掉一块砖,整个建筑就要轰然倒塌的恐惧。
我自然要跑去问费多,为什么会这样改写结尾?他回答我说,这个运动的死亡率本来就极高。全世界洞潜者只占潜水员的万分之一,死难事故发生的几率却占了潜水事故的大半。就在这一瞬间,我才忽然清晰地意识到,《下潜一百二十七米》其实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原来,在下潜到一百二十七米之前,他笔下的这个女人一直怀抱着某种无法启齿的求死之心。只有在那一刻,在幽暗的水下,她才下决心剥离掉了笼罩在自己身上的死亡阴影,安然回到了地面。
就在我为主人公安全返回松了一口气时,费多却让潜水教练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对我说:一切都是开放的,她依然在挣扎。
真冷酷啊,是不是?
但,正应如此,也只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