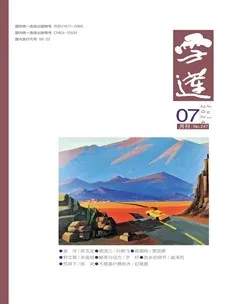留 守
2024-10-09陈玉龙
【作者简介】陈玉龙,江西都昌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青年文学》《雨花》《天津文学》《广西文学》《四川文学》《清明》《安徽文学》《山东文学》《飞天》等。
刚走进办公室,主任就对我说,正好有个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办。我以为主任开玩笑,可看到主任眉头紧皱的样子,才相信是真的有事。主任比我年轻多了,挺白净的一个小伙子,个头高,显得英俊挺拔,戴着眼镜,满满的书生样子。只是遇事有点急躁,不会藏着掖着,明目张胆地表露出来。这样的人好相处,与他共事多年从没闹过什么不愉快。果然,主任从桌子上抓起一张信纸,对我说,真是头一次哩,还真有人举报这个事。说着,主任把那张信纸,准确地说是举报信交到我的手上。信是手写的,很潦草,好像是匆忙赶时间而一挥而就,我连猜带辨把信看完,心里松下一口气,开玩笑地对主任说,人家是看着我没事干,找个理由让我去跑跑腿吧。主任这才舒展眉头,露出一丝笑意,说,任务就交给你了,有什么情况再联系。
我们的办公室叫精神文明办,事儿确实不多,主任还是兼职的,他的正职在宣传部。每年评选一次小城最美家庭的工作就落到我们头上。这个活动已评十届了,这是第十一次评选,刚在当地新闻媒体上进行了公示,哪想还真有人写来了举报信,指出里面有一个家庭不符合条件。办了十多年这样一个活动,出现有人举报的事还真是头一回。
我把手上的举报信晃得哗哗响,并信心满满地在主任面前表态,一定会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主任严肃地说,别把这事当成小事一桩,要认真核实调查。我嘴上答应着说那是肯定会的,心头却想,正好趁这机会到乡下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或许是人家开的玩笑呢。
被举报的这个家庭的主人叫王建平,一家四代同堂,据说是和和美美的一个大家庭,还有全家福照片作为佐证。所有参评的家庭都是由各单位和社区推荐来的,且有盖了章的推荐材料,我们办公室组织妇联等相关部门评审,一般也没什么差错。举报者是实名的,叫王小虎,他在信中说王建平虐待他的父亲,把他一个人丢在乡下一个破屋中,根本不配最美家庭这个称号。王小虎没留联系电话,只留下一个家庭地址。看来,首先就要找到王小虎。
根据王小虎提供的地址,我发现他竟然是王建平乡下老家村庄上的人,这样说来,举报的内容应该不是人家的恶作剧吧。参评的申报材料上有王建平的联系手机号,我想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想想还是放弃了。这事还是先不要惊动当事人为好,先把他父亲的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再作道理才是。
老王庄坐落在小城的最北端,属于偏远的山村,开着导航,开车都要跑一个多小时。正遇上大雾,车子不敢开快,路上还碰上有追尾的,又耽误了半个多小时。早上八点动身开的车,十点半才到达目的地。大雾早散尽,太阳一出来,让人心头亮堂了许多。
村头的大树底下有块大场地,正好可以停车。我把车子停好,一出车门,跑来一个几岁的小孩,也不怕生,捡起一个瓦片上来要往我车门上划字。我吃了一惊,情急之中一下子把他手中的瓦片扒拉出来摔碎,并吓唬说,小孩子不要乱划,车子里面会伸出刀来割你的手。
割你个头哇,有这样吓唬小孩子的么。
树底下突然站出一个影子,恼怒地对我发火,紧紧抱住孩子,对我怒目而视。这是一个老妇人,白发很长,却稀疏,像深秋田野里的枯草,随风飘摇,风一大,似乎要连根拔走。她的个子太小,以至我下车时都没发现。
我尴尬地站在那儿,老妇拉着孩子转身进了场地旁边的屋子,随风飘过来一句话,有车显摆么事哩,现在哪家没有个车子?
乡下妇人,真的这么没素质么。我望着两个矮小的背影,在心里自问。本来还想向她打听王小虎呢,看来得到村里面找别人了。
一眼望去,村子里有几十户人家的样子,奇怪的是,却很少见到人。虽说村里年轻人都外出了,老人小孩总该留守在家吧。有两条狗一直跟在我身后,我一回头,它们又跑远一点,好像我是它们稀奇的猎物。

终于见到一个光头大爷,正在门口喂着小狗狗,我上前向他打听王小虎的屋子,光头大爷紧盯着我说话的嘴巴,身子靠近过来,似乎想闻出我早餐吃的卤面味。我看出来了,大爷有点耳背,听不清我的话,我的嘴巴靠近他的耳根,大声地再说了一遍。光头大爷迟疑了一下,问我是找王小虎要账的么。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王小虎欠了许多债务?我使劲地摇头,光头大爷蹲下去抱着小狗进屋,我正要跟进去,他空手出来了,往外走。我站在原地不知他意思,他回头对我招了下手,这才理解他是要带我去王小虎的屋子。此时已是春天了,光头大爷还穿着冬天的棉袄,黑不溜秋的显得破旧,脚下倒是穿着一双新皮鞋,跟在后面看着总觉得有点像某位大佬演的小品里的人物。紧跟在光头大爷身后,在一个楼房前停住,光头大爷回转身对我说,这是他屋子,自己进去吧。说完就回转身,太阳光照射在他头上,让我有些恍惚。
咦,这不就是刚才那老妇人的屋子么,王小虎就是她的儿子?
我站在屋外徘徊不定,向里张望了一下,希望看到一个年轻男人的身影。屋门半开着,门洞里什么也看不到。我只好向着里面大喊一声,王小虎在家吗?半天没回音,又喊一声,出来的是那个老妇人。见了我,脸色一冷,说,找他做什么?我露出笑脸,点头弯腰说,我是小城一家单位派来的工作人员,王小虎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反映有关情况,我来找他核实一下。老妇人再认真打量了我一下,面无表情地说,走了,不在家。我说,他给我们写信的时候也不过几天时间呀。老妇人说,前天坐火车走了。我失望地收回目光,还不死心,问她有没有王小虎的手机号码,老妇人没好气地说,他换手机号比换衣服都快,我哪有他的号码?这时那个小孩从屋里跑了出来,身上弄满了饭粒,看到我,目光缩了回去。老妇人见状,骂道,讨债鬼,吃个饭也不清爽,又不愿意跟你爸去,明天你自己去找狠心的娘去,省得在家祸害我。
我本来还想向她打听王建平的屋子,亲眼见证他父亲的真实生活,看到老妇人指桑骂槐般的怨声咒语,只好赶紧离开。
村里人少,屋门都关闭着,找个人问询都不容易。找来找去,终于看到有个大娘站在屋檐下张望着什么,我走过去亲切地喊了一声大娘好。大娘刚才是在远眺,好像根本没发觉近前的我,似乎吓了一跳,有些恼怒地说,你是哪个,莫挡住了俺的光。我也站在大娘同一水平位向前望去,前面是一口大池塘,再前面是山,山那边是什么,不知道。我问,大娘你在望什么呢?大娘往前走了两步,双手遮住刺眼的阳光,说,你看那是什么?我再顺着去看,前面还是山,挡住了一切。我问,在哪儿?大娘说,抬起头,一只好大的鸟呀!我抬起头,看见云层里钻出一架飞机,没有半点响声,大概还要等些时候才能传来声音。我扑嗤一笑,说大娘真会开玩笑,那是大鸟么?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老头,大声呵斥道,又在胡说些什么,还不进屋去!大娘见了老头,脸色一紧,听话地转身进屋。老头见了我,不好意思地对我苦笑着说,老伴头脑有点不灵光,整天就只晓得站在屋前远望,落下的这个病根医生说治不好,怕是要带到棺材里边去哟。
我得抓住这个老头,向他打听王建平的屋子。老头看样子还算强健,头发稀疏,却乌黑,说话声音宏亮,中气足。见问起王建平的屋子,老头摇头说,他哪有屋子,早卖了。我急问,他父亲不是在村里生活么,没屋子他住哪里?
你是说古仔呀,他有屋呀。我这才知道,王建平的父亲叫古仔,或许这是他的小名吧。他们不是一家么,怎么说儿子的屋卖了老子又有屋呢。我被老头的话给说蒙了,急着想请老头带我去古仔的家。老头说,你现在去也见不到他的。
出远门了?
lUMLNVPWkpWl111mPJWjUDLkKKDdjjrGTy5sltVRkfc=哪里哟,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哪有什么远门出,真要是远门那是不能回来的哟。他是去看戏去了。邻村有个百岁老人做寿,演三天三夜的戏,今天是最后一场。
怪不得呢,村里也没见什么人,大多都去看戏了?
老头点点头说,都去了,都喜欢看戏哩。
我突然问,你为什么不去呢。
老头一愣,叹了口气说,要守着她哩,我一走,她就要跑出门,一直往前走,不会拐弯,哪怕前面是水是山是树是墙。老头停住,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是来找古仔的呀,可能还要等半个时辰了,到时他们都要回家吃饭,演戏的也要吃饭哩。要不,先进屋里坐坐吧,喝口茶。
也好,反正要等他们回来,口也渴了,跟老头进屋喝口水吧。我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
屋是二层的楼房,建设得有些年头了,没个清爽的女人收拾屋子,乱糟糟的像进了贼一样。老头精神却好,给我倒了一杯茶后,拉过一把椅子给我坐。大娘的身影在我眼前晃了几下,被老头喝斥了几句躲进里面去了。
我问,就你们三家没去看戏?
老头说,是呀,我们都是走不动身,要不也要跟去瞅热闹。
趁这机会,我向老头打听王小虎的情况,见不到举报人,他的情况还是要搞清楚的,好回去给主任一个交代。
老头啧啧撇嘴,说他呀不说也罢,村庄最窝囊的一个男人,老婆都守不住,跟着别人跑了路,自己又不务正业,赚不到一分钱不说,还倒欠着许多债,把孩子留给家里的老娘,奶粉钱都不寄。
我真没想到,王小虎竟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为什么还要写这个举报信呢?自己的事儿烦都烦不过来,还要多管这份闲事?
是呀,自己的事还管不过来,他要管人家那个闲事做什么呢。老头也跟着说出这话,拍着脑袋一想,便笑了,王小虎也是个小肚鸡肠的人,莫不是还记得十多年前的那个事?
十多年前有什么事呀?
俺还说不出口哩,具体的什么事就不说了,反正王小虎在城里犯了一个事,找王建平帮忙,没想王建平一口拒绝了,还给他上了一场人生政治课。后来王小虎回到村里时就老说王建平的坏话,让村里人对王建平有了另一种看法。
老头抽出一支烟自己点着,冲我笑笑说,烟太差了,就不敬你了。我不抽烟,出门时身边特意带上了一包烟,老头的话提醒了我,我赶紧撕开烟的包装,抽出一支给了老头。老头也不客气,接过来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夹在耳后说,你的烟好,我就不客气了。大娘又从里屋走了出来,老头大声骂了几句,我忍不住问,大娘生病多久了?老头一愣,站在那儿似乎在思索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烟气向上卷着圈儿,贴着屋里蛛网般的电线爬行,隐藏在灰不溜秋的墙缝中。
不长,也就一年多吧。她开始还正常,只是站在屋檐下远望,后来就说出胡话来,越来越不正常了。
没上医院看过?
去了,也没有多大的效果,医生说,这是心病,还是回家调养吧。
可以去大医院看呀。
老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婆,还去上什么大医院,那不是把钱往水里丢么。老头看我的眼色有点不友好,狠劲地抽了一口烟。我赶紧转移话题。
儿女都在外打工了吧。
是哟,儿子一家人都在外买了房,孩子也在那儿读书,过年才回一趟。女儿么,远嫁了。
你女儿不回来看望你们么。
回来呀,开始是一年一次,后来是三年一次,现在不回来了,老伴天天站在那儿望。
不回来?
回不来了,前年的一个事故。老头说出这句话后,抹了抹眼泪说,老伴就是想不开,人生在世有什么放不下呢,到头来谁不走那条路?他把烟屁股在地上按灭,从耳后抽出我给的烟再点上,烟气贴着他脸面爬行,使我的眼睛不由模糊起来。
老头给我添了一下茶水,茶杯沿上结有许多茶垢,刚才没看清,一口喝了大半,索性闭着眼再喝了一口,老头高兴地对我说,你们城里人总讲究许多,其实太讲究了也不好,别看俺村子不大,托现在好社会好政策的福,八十岁往上的老人有几十个哩。我说,那应该叫长寿村啦。老头笑笑,算是默认了我这种说法。
比如那个光头老汉吧,你刚才不是说他带你到王小虎家嘛,你晓得他多少年纪呀。
看样子也有八十来岁吧。
嘿嘿,他可是俺村里最高寿的老人,今年九十六了。
我暗吃了一惊,光头大爷虽耳有点儿背,看样子身体还不错呀。我问,这么大年纪,家里也没个人陪他么。
他哪有家人哟,除了一个小狗跟着他。
家里人都——
人家一世没有结过婚。
那真是孤单呀。
他年轻时走南闯北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了,人活一世,见过一些世面,经历过一些事情,也不算孤单吧。再说他现在有五保,一个人活得滋润。
老头说的话不错,我点点头,又低头喝了一口茶。现在,我该走向正题了,了解一下王建平父亲的情况。这时,外面有了吵吵嚷嚷的声音,老头起身往屋外一望,高兴地对我说,他们看戏回来了,你可以找古仔了。他的屋最好找,全村最小的房子,往南走到村头。
全村最小的屋子。我心头隐隐有点不快,看来,王小虎举报内容不假呀。
走出屋子时,我再给老头递了一根烟,老头双手接过,粗糙的皮肤触到我的手指,那是一种硬梆梆的碰撞感。
村里有些喧闹,女人和小孩子的叫声最为尖锐,各家开门的吱呀声渐次传到我耳边,鸡飞狗跳猫上墙,村里突然之间有了生气。我在村里各个屋子之间穿梭,有人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对他们笑笑,算是打个招呼。那人也回了个笑,进屋,大概是赶着做饭吧。村子的最南边,果然有一个低矮的小屋,四五十平米的样子,屋前有鸡在吃食,想必是饿了,抢着,跳着。忽地从屋里奔出一个老人,金黄的稻谷一撒,大声喝道,抢什么抢,都有份,大黑,你乱窜什么哩,净在里面捣乱,等下再给你。一条小黑狗被老头从鸡群里赶了出来,一见我的到来,瞪着乌黑的双眼看着,忽地后退一步,汪汪大叫起来。
老头回过头来,见了我,以为是路过,没有理会。待我停下来,站在他面前时,他抬手遮住额头前的阳光,问,你找人?
大爷好,你是王建平的父亲吧。我抽出一支烟给他。老头举手推开了。
他在城里,你到乡下来找什么?老头目光冷傲地看着我,在衣服上擦了擦手上的谷屑。我不恼,依然笑着,看着眼前这个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老人。
正午的阳光照射在他的脸上,连胡子都闪耀出金光。别人的胡子要么是黑要么是白,他的却是一片金黄色,让我想起金发外国人。头发少,围着一个圈,好似《西游记》里的沙和尚。粗粗看上去,肩背稍有点驼,手掌骨节大,看样子没少干过体力活。
我靠近他一步,再次把烟递上,他只好接过来,夹在耳后。我说,我是专门来找你的,进屋坐坐可以吧。
老头警惕地看着我,说,莫不是那小子又找人来做工作吧,我跟他们说了多少遍了,不去他们住着笼子一样的城里,让我在村里自由自在多活几年吧。
我赶紧声明不是他儿子派来的,临时编了个理由,说是记者采访的,听说村里有许多长寿老人,想写个稿子宣传宣传。
老头这才客气地把我领进屋,说,正是中饭时间,不嫌脏的话,就在俺屋里吃个饭吧,先喝口茶,俺得先做饭哩。下午的戏场两点多要开演,俺还得赶去看戏哟。
我本想拒绝,转念一想也就爽快地答应了。看着老人麻利的身影,我在心中感叹,这么一大把年纪,住着这么一个低矮的屋子,还有这么好的心态,对现代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了。
屋子只有两间,红砖绿瓦,外墙粉成白色,内墙没有粉刷,简单朴素。屋内墙上钉着一排钉子,上面挂着许多物件和袋子。地面是用红砖铺的,缝隙处填满了沙子,显得十分平整。里间为卧室,床底下好像堆着东西,前面墙上挂着一个40寸的电视机,也许,唯有这个才算是现代化的东西吧。厅堂一分为二,前边是饭桌客厅,中间拉上了一个布帘,后面放着农具什么的。屋里真的很简陋,但摆放得齐整,一点也不显得乱。
我一抬头,吓了一跳,屋顶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圆形摄像头在转动,像一双眼睛那样盯着我,我忽然感到浑身不自在。这个东西肯定是老人的儿子王建平请人安装的,让它时刻监视着父亲,或者说在保护着他。我估计,老人的卧屋肯定也有。父亲再犟,终究是斗不过儿孙们的,一切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而老人却浑然不觉。
屋外有个狗窝,旁有一个鸡圈,而鸡笼却摆放在大门的右角。我想,白天鸡们是关在鸡圈里的,到了晚上才让它们进屋里的鸡笼,这样才安全。记得小时候在乡下,经常会有偷鸡贼。
从刚才的交谈中,我可以看出并不是王建平不接他去城里,而是他不愿去,那么,王建平应该多来乡下看看父亲,这样才是一种和美。黑狗进屋来,它不再对我吠叫,围着我转了几圈,趴在我不远的地方盯着我,好像只要我有什么不好的举动,它就会一扑而上。厨房是在屋外搭建的一个小屋子,辣椒味儿直扑我的鼻子,连着打了几个喷嚏。我站起身,走出屋门。
这屋地势较高,向北一望,差不多整个村子尽收眼底。房屋的结构都差不多,但有高有低,外墙都粉得雪白,像是一个老人换上了一件新衣服,光鲜亮丽,估计是刚搞了村庄整治这个项目。前两年,我们单位的主任还下去兼任过一个村委会的第一书记,那里的村庄也在搞村庄整治,我给主任送材料去过,印象深刻。
炊烟从各个屋顶飘出来,飘上去,连在一起,像是一片云,又像是一团雾,飘在村后树林的上空,一白一绿形成两个鲜明的对照,是在城里很难看到的一种风景。现在很多农村做饭都不用柴灶了,他们用煤气或者电,这样用起来方便干净。而这个村庄依然是用传统的柴火灶,或许这与村里老人多有关吧。
炊烟缭绕的村庄确实是一种美景,我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听见身后传来老人的呼叫,吃饭啰,饿了吧。我一回头说,这么快呀。看见老人手上端着一个大盆子,黑狗兴奋地跟着他走到刚才鸡吃食的地方。咣当一下,盆子放在地上。原来老人刚才是向黑狗说话。老人见了我,也说,吃饭啰,饿了吧。我的脸色通红,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

菜只有三个,却是大碗装着。一个辣椒炒肉丝,一个油淋小白菜,还有一盆红鱼块。另外还有一大碗鸡蛋紫菜汤。菜清爽,不油腻。见我坐下来,他又从墙边的木柜子里拿出半瓶酒,问我喝不喝,我连忙拒绝了,说开车不能喝酒。老人也不坚持,而是给自己倒了一杯,又从柜子里端出半碟花生米。老人举起筷子说,让你看着我喝酒也不好吧,要不你倒杯开水。好。我看出老人也是个爽快人,正好要跟他聊聊他们家庭情况,以水代酒,也是可以的。
话从哪儿说起呢。我先敬了老人一口,菜的味道还真对我的口味,不像许多老人那样喜欢吃咸的。老人大喝了一口,我说,慢慢喝,先多吃菜。老人笑笑说,你是怕我喝醉了吧,这大半生,喝下去的酒也不知有多少坛了,还没有醉过。我伸出大拇指说,海量。老人呵呵大笑,哪有什么海量,俺喝酒从来不超过两杯。我心头暗忖,老人还真是有自制力的人,这样一比较的话,他不去儿子那儿生活似乎就说得通了。
酒真是个好东西,老人喝了酒,话多了起来,不用我先问,他就自个儿说起了自己。
我知道你心里有疑问,一个人住着这么低矮的小屋,不去城里儿子家里享清福。其实,早先三十年,我是想去的,那时,老伴儿也只有五十多岁,脸蛋儿摸上去还是光滑的。说到这里,老人低头喝了一口酒说,让你见笑了,你没见过俺老伴年轻时的样子,也算个美人儿。说着话,老人停住筷子,去住房里翻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这是一张有点发黄的照片,过了塑,可见老人是用心保存的。女的笑得很甜,弯弯的眉,嘴角上扬,给人一种调皮样。男的露着一口雪白的牙,乌黑的头发有点卷曲,胡子像刚出生的小鸡仔身上的绒毛。
我连声赞叹,老人说,照这个相的时候老伴儿正怀着孩子呢,你没发现她大起来的肚子么。我再仔细看了一下,果真看到女的穿了一件大袄子,下面的边角大开,我以为是匆忙之间没有系上扣子呢。
你们真的很般配。我发自内心的感叹。
老人摇了摇头,儿女大了,做父母的要随着他们的愿望生活,三十年前,老伴就去城里给儿子带孩子,现在又要带曾孙子,你说,人这一辈子,非得为孩子忙么,就不能为自己活活,你说俺老伴是不是有点傻了?
我摇头说,你应该去城里给老伴帮忙呀。老人瞪圆着眼说,你以为我不想去么?那个时候,儿子一大家子都挤在一个小屋子里,说到这里,老人站起身来双手比划着说,跟我现在这个屋子差不多吧,老伴跟孩子睡在一起,你说,我睡在哪里?
那个时候,儿子工资低,一家人的开销大,我在乡下隔段时间就要去城里一趟。
看望你老伴儿吧。
老人摇了摇头,是我给儿子家里送菜送米送油,反正,家里出产的东西我都拼命地往城里送。那时,他的工资也低,媳妇身体又不大好。
大娘总不会是整年忙得没有空闲吧,她也可以回乡下来看你么。
年轻人,你说的话不错,老伴儿也是有空儿下来的。
有一年夏天,老伴儿回来看我,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被儿子接了过去。
这么急,儿子家里有事么。
哪有什么大事呢,他们一家享受惯了俺老伴的服侍,再说孩子也都喜欢老伴做的饭菜,他们一刻也不想让俺老伴儿离开。你不晓得,俺老伴可能干啦,尤其是炒得一手好菜,那个豆豉爆肉啊,全村都可闻到那个香味。村里有什么红白喜事都想请她去厨下掌勺。老人说到这里,喝了一口酒,细细品味着,鼻子一吸,好像真的闻到了豆豉爆肉的香味。
那时,我跟老伴说过多少遍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放下吧。可老伴儿就是放不下。说句话不怕你笑话,那年老伴出门,我们竟抱头痛哭了一场。
后来,你再也不上儿子家的门了。
老人没有回应我的话,又喝了一口酒,说,先前和老伴倒有个电话联系,现在电话也懒得打了,年轻人,你不知道,人只要长时间不在身边,感情也就淡了,现在么,也没什么念想,倒觉得一个人快活。
老人的脸色渐红,也不知是喝了酒还是回忆和老伴的往事而激动。我又敬了他一口,提示他说儿子和家人们对他好不好管不管他给不给他零花钱,我把手机的录音功能打开,回去我得给主任有个交待。老人轻笑一声,说我现在巴不得他们离我远点,当初为了想让我死心进城,儿子避开我把村里的老屋都卖了,以为我没屋子就过不下去了。笑话,老子当年建那个房子时也是我一块砖一块瓦建起来的,老伴只是打个下手帮个忙,没屋子我自己可以动手建吧。你看,屋子是小点,可我一个老人,住在这儿绰绰有余。这里又在村头高处,一站在屋门口,全村都在眼皮底下,心里开阔,有什么不快的事也会烟消云散。
万一有个头痛脑热的怎么办?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的实际问题。
小小毛病我从来不找医院的,自己扯点草药就好了。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踏进过医院的大门。
万一有事怎么办?
老人放下酒杯,说,人一生都是有定数的,有什么大病,我也会自己解决。
怎么解决?我紧追不舍。
老人又坐下来,喝了一口酒,说,你们年轻人不懂,不说这个话题了。
老人转身到厨房给我盛来一碗饭,说,喝个寡味的白开水没意思,吃饭吧。他转身给自己添了一杯酒,自个儿喝了一口说,你不是想采访村里的长寿老人么,还有几个人等下我带你去。我说采访你一个人就够了,下回再去找别人吧。老人认真地打量着我说,你细皮嫩肉的没见过太阳吧,你们城里人就是过多讲究,其实到田畈里做做事晒晒太阳那才好,黑点有什么不好呢,越黑身体越强壮,就像我的小黑狗,精力旺盛得把鸡都赶得到处飞跑。等下,我带你到地里去看一看,那是我的菜园,你要带个什么菜随便你去摘,新鲜哩。
我笑着说,多谢大爷的好意啦,菜留着自己吃吧。
那块地呀,可是我的聚宝盆呀,记得四十多年前刚分到我家时,还是没人要的石头荒地,我和老伴从池塘里挑来塘泥,硬是把地皮给换了一层。那个时候呀,有老伴在身边,一点不觉得累,有时为了把活儿干完,老伴就给我送饭,老远,我就闻到了那个熟悉的菜香味。
老人又喝了一口酒,低头道,许多年了,再也闻不到那种味道了。
你回到城里去不就有那种味道嘛。
老人摇头,目光里有些湿漉,说,淡了,就像跑了气的酒一样,时间越久越淡,最后就像水一样寡味。
我说,现在你也差不多做不动了吧,到城里儿子家去养老,现在他房子也大,跟老伴儿在一起,不管什么都好有个照应呀。
习惯了,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在乡下的生活。城里么,房子那么高,不接地气,人就像飘在天上,看着都让人头晕。早先俺也住过一阵子,不到三天脚肿脸浮。城里没菜园地,水泥路上车子跟流星一样闪过,有草的地方又不让人坐,就连那树也被修剪得齐整整的跟假的一样。屋里地板上擦得光亮亮的晃得眼睛痛,出门进屋都得换鞋,俺真的不习惯了。俺这一辈子,是土里寻食的命。我那老伴,又是陪伴小孩子的命。有一年我把老伴接了回家,叫儿子请了个保姆。可保姆干了不到十天,就被儿媳妇给赶走了,世上哪有自己的亲人做保姆好呢,老伴舍不得孙儿,现在又舍不得曾孙女,你说,我一个糟老头子,还会跟他们争什么。
你问我他们给不给我钱,我要他们的钱做什么,吃的地里可种出,穿的他们捎来,每个月国家还给我的农保卡上打上一二百,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到哪儿去花钱哩。
老人喝完杯里最后一滴酒,站起来时身体摇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问没喝多吧。老人用劲一把推开我说,哪能呢,不是俺吹牛,年轻时没个一斤以上的酒量不叫喝酒。俺平时一个人总是喝一杯,今天有你这个贵客,多喝了一杯。老人的脸色黑里透着红,喝得高兴。
吃完饭,我想给老人留下几张票子,想起他刚才的话,我又把手缩回。人家是好意留你吃饭,如果一较真,也许会惹他生气。
我告辞出门,老人看了一个手机,说快两点了,戏还有会儿就要开演,我也不留你多坐了。我们挥手告别,黑狗向我追赶了几步,便回了头。
从村南到村北,看到有一些老人聚在一起做着出门看戏的准备。来的时候留我喝茶的老头正在拉着远眺的大娘进屋,老头发现了我,我对他笑笑说,让大娘多看会儿吧。走过光头大爷屋门时,我把头伸向昏暗的门洞,一只小狗跳出来咬住我的裤管,立马走出一个身影,踢了小狗一脚,骂道,教你千遍万遍都记不住,再要咬人衣裤就把你剁了炖着吃。我忙退出来,向他招了招手。
我刚爬上车子,王建平的父亲急急地跑了过来,喘着粗气对我说能不能等一会儿帮个忙给他儿子捎个东西。我问捎什么,老人说,我到菜园里摘点新鲜菜果,老伴常说我捎去的菜有股清香味,城里是有钱都买不到的。见我点了头,老人辙转身,脚步竟跑出咚咚的响声,不输于年轻人。
王小虎的屋门一直关闭着,大概是老妇在带着孙子睡午觉吧。我对着那门轻喊一声,王小虎,你的举报信我们主任很重视,专门派我来调查了。
不一会儿,我看到老人背着一个蛇皮袋子跑了过来,脚步咚咚响。我赶紧下车接过袋子,真心地说,大爷,我们一起进城吧。
老人嘿嘿笑着,对我摆了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