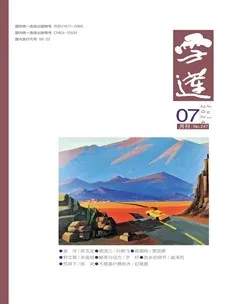县城电影院
2024-10-09王俊
【作者简介】王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人民日报》《文艺报》《散文》《美文》《安徽文学》《山东文学》《湖南文学》《星火》《四川文学》等报刊,曾获观音山杯美丽中国散文奖、孙犁散文奖。
进县城后,骤然远离熟悉的人和环境,莫名的孤独和惶惑裹挟着我,仿佛自己的生命成了心无所依的落叶,飘在半空中,没有归属感。我感到心力交瘁,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一天,葵用秋水般的眼睛望了望我,甚是认真地说:“去看电影吧,说不定你还能谈一场恋爱。”葵是我在这个县城唯一结交的朋友。她是房东的女儿,二十岁出头,面如芙蓉肤如凝脂,正是一个女子的好年纪。葵高考的分数委实差得离谱,家里人便花钱托人在电影公司给她找了一份清闲的工作。我颇好奇葵的生活,她不像我们奔波在朝九晚五的路上。凌晨时分,处于浅睡眠状态的我,常听得到女房东打开院门,迎接归来的葵。两人低低的说话声,凝成一团神秘的雾翳,被推搡出院墙之外。葵通常睡到下午两三点钟起床,穿着灯笼裙和松糕鞋出门。她轻盈地走着,每迈出一小步,裙角微微扬起,身上特有的体香在空中停留,弥散。
一个傍晚,我走出单位。日头朝西山慢慢撤退,光线若千万只拖曳着金黄色尾巴的飞虫,发出轰鸣声,奋勇扑向大地。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随风晃动,在地砖上切割出许多奇异的幻象。地砖天天被行人踩踏,已经失去应有的质感和光泽度。有的地砖鼓翘起来,行人踩在上面,一不小心就崴了脚;有的破了相,显出粗粝的形貌;还有的地砖空着,雨天凹洼积着水,摩托车飞驰而过,污泥浊水溅得路人一身。
街边的店面挨挨挤挤,汇聚了服装店、理发店、照相馆、饭店、旅馆、小百货商店。店面看似不打眼,却管着人们的吃穿用度,便利得很。服装店隔三岔五就易主,多是外地人来此做生意,兜售廉价的内衣和过季的T恤,门口的广告牌上一年到头都写着“血本无归”。我曾在店里花了二十五元买了一套保暖内衣。质量确实不错,穿了两年,照旧很暖和。我从不敢踏进理发店。里面灯光幽暗,电吹风的嗡嗡声响里总飘来热烘烘的香气。照相馆是我一个同事的妹妹经营的,成了我常去的去处。楼下摆放复印机和打字机,二楼装修成影楼。单位同事的证件照、年轻人的结婚照、孩子的满月照,都是出自这里。我对照相馆的老板娘心存感激之情,时不时地将单位需要打印的材料带来照顾她的生意。记得初到县城时,同一个办公室的大姐听说我没房住,热心地介绍我去找她开照相馆的妹妹。照相馆里忙的时候,老板娘经常请葵的母亲去打扫卫生。
照相馆的斜对面是电影院。我不知道,每个县城是不是都有一个气派的电影院?想想,有多少青葱的时光在电影院里疯长?县城的电影院很高很大,门前矗立两根大柱子。水泥浇筑的台阶犹如半个括弧,慢慢由大变小,层层围上去。隔着街道能望见放学了仍旧不急着回家的小学生,趴在台阶上玩弹珠。被弹出去的弹珠闪着光,滚来滚去,孩子们欢呼雀跃。外墙铺着花岗岩,铁门两边设有醒目的窗栏,配着透明的玻璃,里面张贴着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和当时火遍天的明星写真。忙碌一天的人们爱往那里扎堆,畅谈自己喜好的主角以及扑朔迷离的情节。绚烂的霓虹灯亮了,电影门口落满小商贩的摊位。夏天背着木箱吆喝棒冰和汽水,冬天则推着炉子卖烤红薯和炸年糕。当然,最常见的是卖瓜子和花生。彼时,瓜子装在卷成圆锥形的旧报纸里,新上市的花生包在荷叶中,散发着近乎甜腻的清香。白天在电影院门口几乎看不到那些小摊贩,仿佛黑夜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
在县城待了大半年,我的生命一如钟面上的时针,沿着固定好的轨迹行走。可是,那个傍晚仿佛是被赋予了某种寓意似的,我并没有和往常一样绕过电影院,而是停了下来。黄昏的光线笼罩周围,电影院弥漫出一种遥远而温柔的气息,不经意地触摸到我日渐趋于麻木的神经。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里,电影是一枚钤满青春和记忆的印章,慰藉了曾经荒芜的精神世界。记得最早看的电影是乡下的露天电影,幼时的我懵懵懂懂,尚不明白为什么放映机咔咔对着银幕,就能看到古人的生活,看到遥远的未来。真正懂得看电影并逐渐爱上它,其实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学校每个周末都在镇上的电影院包场,规定学生看完电影写一篇影后感。电影无疑是向我们敞开了一个个斑斓世界,在电影塑造的形象里,我们感动着人性的种种,并企图探入人心斑驳的景象。
那天,窗栏上面通知晚上七点放映的是侯孝贤执导的《海上花》。我决定走进电影院。然而,我去得太早了。电影院里冷冷清清,只有售票口站着两三个工作人员,交头接耳,谈兴正浓。我一眼认出葵就在当中。她涂着鲜艳的口红,分外耀眼。葵看见我,略带惊讶地说了句:“你怎么来了?”我没有作答,拉着她的手傻笑。她递给我一张电影票,却执意不肯收下我的钱。葵悄声对我说:“你以后来看电影,只管找我,我给你留票。”我顿时觉得沾了她好大的光,浑身有些不自在。葵似乎觉察出我的心思,笑着说:“电影散场后,你记得请我吃夜宵。”我连忙应允下来。
攥着电影票,拐过楼梯的转弯处,我看到一个规模很大的影厅,座位分为上下两层,估摸可以容纳好几百人。雪一般白净的银幕,宽大。座椅软和,干净,坐上去一定很舒服。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县城的影厅,无论是它的场地,还是银幕,都令我十分着迷。红色的地毯由我的脚下一直铺向舞台。数十盏灯同时亮着橘红色的光,将电影院映照出几分温暖。一个清洁员弯腰在清理座椅底下的垃圾,见我进去,抬头嘟哝了一句:“出去,看电影还早着呢。”我来不及找到自己的座位,仓皇退出,不料竟走错通道,闯入后院。
后院的南侧与教委职工宿舍楼衔接。教委职工宿舍楼的每套房子有如一个小格子,摆放着相似的物什。人影在小格子中晃动,成了建筑物的布景。有老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有女人走到阳台收晒干的换洗衣服,或是孩子围着大人嬉闹。稀落的灯火漂浮在窗口,仿佛是一支支含混不清的歌声。西侧有两个小花坛,种着一些植物。按理说,植物到了初夏,原该以不可阻挡之势去生长,去开花。可眼前的花草呈现一派了无生气之态,叶片近似烧焦般卷起来,显露出褐色的枝干。我实在想不出这枯萎的背后透出的讯息是什么。蹲下身,仔细辨认一番,方瞧出是山茶。花坛上立着木牌,写道:禁止随处小便。花坛的尽头盖了一个简易公共厕所,边上撑起遮阳伞,一个老人坐在矮凳上听收音机。我经过老人的身边时,他并没有看我,伸出右手巴掌晃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往地上的铁皮盒子扔了五毛钱。等我上完厕所出来,再次经过他的身边时,他还是没看我一眼,依旧垂首听着收音机,安然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我想,在他的异次元里,我就是一阵烟,风吹过了,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花坛走过,我忍不住又将目光投向那些干枯的山茶。蓦然,我嗅到一股无法形容的怪味。无妨想象一下看电影内急的情景:他们急匆匆地跑出电影院,只缘吝惜囊中之物,遂踏入花坛中小便。一泡泡尿对于园子里的蔬菜来说,是无上的恩情。有它们的滋润,蔬菜长势喜人。然而,对于素来喜欢酸性土壤的山茶来说,无异于致命的凌辱,难怪要香消玉殒。
天色瞬间暗下来,外面物象的色彩全褪淡,被勾勒成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我匆忙返回影厅。影厅里人不多,像《海上花》这类片子,不可能获得小城人的赏识。头顶上的灯已关闭,仅亮着墙上两盏小灯,便于人们找座位。我在自己的座位坐下,不一会儿,电影开放了。《海上花》是一部老上海里弄的叙事史诗,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向观众展开一幅倌人与恩客之间爱恨的日常画卷。这是一部特别适合在电影院看的片子。橙色光影营造出来的场景,迷蒙而魅丽。所有萌动的情欲幻化为一粒粒小珠子,混迹于微尘中,碰撞着,拼命从裂开的缝隙中挣脱出来,争相抵达欲去之处。银幕上每一件服装和帘帷、每一件桌子和床以及装烟酒果盘点心茶的小器皿,是触手可及的浮华,也是无可替代的风情和极致之美。高中时,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总是无法理解老上海纸醉金迷的生活况味,是电影让我窥探到旧上海的具体人物、事物和场景,有了具体的感受。
电影演完,我恍如从一个冗长的梦里醒来。站起身,一回头,瞥见离我不远有个女孩沉浸在影片中,抱着头低声抽泣。她的旁边坐着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子。哭了一会儿,女孩拽着男孩的衣角擦拭脸上的泪水。男孩顿时无所适从,愣怔住了。女孩憋住笑,斜觑了男孩几眼,神色中略带撒娇的意味。看情形就知道他们两人是情侣关系,我的心里溢出异样的感觉。走出电影院,天上的月亮被云层拱出来,淡淡的光晕明亮了夜晚将露未露的心事。我的影子投在地砖上,是那样的小。藏在我体内的一块锈迹斑斑的铁,似乎被什么唤醒了。
我像是陷入热恋中的男女似的,勾了魂般地往电影院跑,几乎将当年放映的片子都看遍了。《胭脂扣》《花样年华》《滚滚红尘》《卧虎藏龙》《蓝色生死恋》《泰坦尼克号》等都镌刻着我纯真的情愫。我是多么羡慕葵的工作啊,挖空心思想着调到电影公司上班。如果不是考虑它是企业单位,或许我的愿望早就实现了。
当人置身一个可以让自己放松的环境,一些顾忌自动解除了。端坐在影厅里,我那些焦虑不安的情绪似乎获得了安抚。看电影时,我全然忘记还有旁人,在一个个悲欢中走进走出,可以跟着电影的人物去肆意的哭泣,也可以跟着他们恣意地放声大笑,丝毫不怕丢人现眼。遇到不喜欢看的电影,我就躲在暗处,如同偷窥者般审视身边的观众。看电影,实际是看人,电影里演的无非是人所作所为之事。个中演绎的故事,不就是人间翻来覆去的生活场景吗?电影院里时常发生一些有趣的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看电影《卧虎藏龙》。那天影厅坐满人,观众被周润发和杨紫琼的演技所折服。看着看着,两个小孩趁大人不注意,爬到了台上。他们模仿着银幕上人物的招式,你来我往地斗起来。银幕上的人物打得难分难解,两个小孩在台上斗得不分胜负。人群中有男子吼道:“谁家孩子,管不管?还让不让人看电影?”可是没有人在意他的不耐烦,反而都饶有兴趣地围观着两个孩子。曾经的曾经,谁的心里不拥有一腔豪情?谁还没有一个武侠梦?至于看电影嘛,不就是图个乐。
电影散场后,我和葵每次都去电影院边上一家小店吃夜宵。夜风吹来,我们一边嘬着田螺,一边讨论着电影里的演员,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因为电影,葵喜欢上林青霞,我成了梁朝伟的拥趸粉丝。我们搜集各种海报,将他们在电影里不同的造型剪下来,贴在书本里。有时电影散场早,我们不想回家,就去电影院三楼的旱冰场。一群年轻的男女穿着略为厚重的冰鞋,一步一晃在旱冰池子里走。起初,我还能晃到旱冰池子里。后来,摔了一跤,膝盖摔肿了,躺在床上足足养了十几天。伤好了,却把胆子摔小了,只能坐在边上看人家溜冰。
舞厅兴起时,电影院日渐式微。和所有的老建筑一样,电影院也摆脱不了一个宿命:毁于拆迁。我们都清楚,有些事物任谁也挽留不住,终究要远去;有些事物任谁也阻挡不了,它终究会来的。只是,所谓的永恒在哪里呢?我们又该以何种心态去看待这样的转变呢?我们沉迷于过往,认识不了自己,往往忽略了永恒就是存在的意义。在电影院的旧址上,新盖了一栋大楼,有七层高,比原先电影院更高大,更气派。我依然每天路过那里,依然会停下脚步——流连于电影院的过往点滴,总是猝不及防地使我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