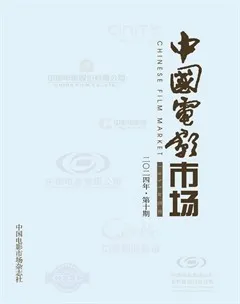国产儿童故事片的创作与传播研究(2013—2023年)
2024-10-08汉雨棣
【摘要】在当下的国产儿童电影市场中,动画片在内容创作与商业发行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儿童故事片数量和质量无法得到保障。本文从题材类型、人物塑造、院线传播三个维度出发,对近十年来的院线儿童片进行整理与分析。研究发现,当前儿童故事片中,现实主义题材占据大多数,具体主题从传统的家校教育延展至社会关系,农村儿童、少数民族等议题成为近年的热门议题,“儿童公路片”随之出现。在这些多元类型的影片中,儿童形象的主体性仍然未能得到保证,常常作为“他者”被观赏和被审视。在电影的宣发方面,大IP类影片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发挥IP的长效价值,非IP类小成本影片在主流的“影展+院线”的发行模式外,也可与官方或网络资本合作宣发。
【关键词】儿童电影 故事片 他者化 电影宣发 IP运营
新世纪院线制推行以来,国产儿童电影在其中成了一种“不可或缺却占比不大”的存在。近年来随着流媒体与媒介融合的加深,儿童电影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格局。第六代导演以儿童题材来反映和探讨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院线的国产儿童电影中,动画片仍然占据主流,故事片在数量和质量上无法得到保障,并呈现出低成本、票房分散、大IP稀缺等商业困局。如何开拓儿童故事片的创作类型、寻求艺术表达的创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学界对儿童电影的概念尚无统一标准进行表述,一般意指为少年儿童拍摄的并适合他们观看的、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角色、以表现少年儿童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各类影片。参照这一界定,本文论述的儿童故事片指以儿童(0-13岁)为主角,讲述儿童及其家庭故事的影片。受篇幅限制,本文研究对象限定在中国大陆出品(或参与出品)、在院线放映的儿童故事片。该研究从儿童故事片的题材选择、人物塑造、院线传播三个维度出发,对近十年来的院线儿童片进行分类与整理,参照优秀的纪录片与海外电影,还原其中的社会关系与创作困境,并呈现各生产要素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关联。
一、儿童故事片的现实关照:从家、校到社会
中国电影诞生之初,以儿童为题材的故事片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dd8aa68c97a986509742d6011dc87e0e500af1c0ba0ccc703a860ec589343778纪二十年代,中国电影的主要功能是启发民智、教化民众,以儿童为题材的影片也多以伦理教化为主题,《孤儿救祖记》《弃儿》等都试图通过家族内部的道德自救解决社会冲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的兴起引领了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在“山河破碎风飘絮”的环境背景下,大银幕成了宣传爱国主义情怀、救亡图存的文化主阵地。“十七年”时期,《鸡毛信》《马兰花》《小兵张嘎》等儿童影片,塑造了海娃、张嘎子等一批机灵睿智、极富革命色彩的儿童形象。1974年《闪闪的红星》讲述儿童潘冬子在党的引领下成为红军的革命故事。直至80年代,儿童的形象逐渐走向多元化与生活化。1988年的《霹雳贝贝》作为首部国产儿童科幻片,以手上带电的“超能力”小男孩放弃超能力融入集体、寻求友爱的故事,既展现出儿童特有的奇幻想象,也真实描摹了儿童成长的心路与感触。2009年,动画剧集《喜羊羊与灰太狼》推出了首部大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牛气冲天》并收获了1亿票房后,大IP动画片逐渐占据了儿童电影的“半壁江山”。《熊出没》系列9年间推出11部大电影,收获了逾77亿元的票房,《哪吒之魔童降世》以50. 35亿元位列2019年度票房总榜第一。相比之下,近十年来,儿童故事片则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处于劣势。
从近年可查的儿童电影看,儿童故事片以非儿童本位电影为主。大多数从成人创作者的视角出发,围绕社会问题、家庭生活、成长历程等三个维度讲述故事,以此或追忆成长经历、反思社会问题,或进行自我表达,旨在唤起成年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以社会题材的儿童故事片为例,儿童并不是其中的主角,而是一种社会现象的符号与表征。2023年的《学爸》以孩子的成长折射学区房等社会现实问题,通过小品式的情节设计展示现实生活的荒诞与教育体制下的亲子百态。同年的《人生大事》以小女孩和殡葬工作者的双重视角对“死亡”“离别”等哲学命题进行了阐述。
在社会题材的儿童电影中,农村儿童电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13年的《山间传来牛铃声》、2014年的《我要上学》、2021年的《红辣椒》、2022年的《千里送鹤》,均以留守儿童上学、盼望父母回家等传统宣教故事为内核进行叙事。相比于21世纪初的《留守孩子》《春风化雨》等影片并没有明显的故事核的进步。在这些模式里,儿童对于父母的陪伴的向往仍然是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这样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将留守儿童的形象窄化,展示的是成年人视角构建的儿童世界与儿童形象,价值取向上呈现出的也是经成人世界教化的儿童。[1]
在这些农村题材的电影中,以少数民族为背景和题材的儿童故事片逐渐呈现出“黑马之势”。2017年的电影《米花之味》,讲述了傣族妈妈陪在女儿身边重新认识与融入乡村的故事。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美学特色,从众多描绘农村儿童的影片中获得了关注,凭借其“清淡的叙事和影像风格”赢得了较高的口碑和评分。2020年内地儿童故事片票房第一名是藏族青年导演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这部影片与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吉迪的知名儿童电影《小鞋子》一样,都是从儿童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孩子想要得到一双新鞋子”的故事。2022年的内地儿童故事片票房第一名《小马鞭》同样是以藏族孩子守护与捍卫自己的马为故事主线进行叙述。这些电影中,寺庙、马匹、农田等独特的场景多次出现,牧民们企盼天晴等特殊的需求也成了推动电影情节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在奇观化的美学特征下,仍然难掩故事内核的趋同。
在校园题材的儿童影片中,儿童们因共同的目标或任务被聚集在一起。如2023年的《萤火虫的天空》讲述一群临近毕业的小朋友因为共同的街舞梦想相聚奋斗的故事; 2020年《四年二班》讲述一群儿童在校园生活中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中,每个儿童都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色,代表着不同的家庭,甚至家庭所属的阶层。他们之间的摩擦与碰撞影射的是不同需求、不同观念的成人和家庭教育之间的碰撞。
此外,近年还出现了一种不局限于校园或家庭,而是在开放的空间、集中的时间内,儿童与成年人共同构建场域、完成目标的“儿童公路片”。以2020年《拨浪鼓咚咚响》和2019年的《过昭关》为例,两部电影都讲述了成人和儿童怀揣着不同的目的踏上同一段旅程,在旅程中互相理解、解开心结的故事。好莱坞电影中,公路片是一种对常规生活的反叛。导演在这里选择公路片的范式,借助“公路”作为一个开放与流动的地理空间,对流动景观进行奇观化展现,通向的是儿童与成年人心中共同的“远方”。在这样的空间中,成年人完成了“摆脱世俗规则”的逆反,儿童则是初识复杂的成人世界,二者在此实现了微妙的对话。
二、无法成为行动者的儿童
儿童形象的被动主要分为以下四类:首先是作为“背景板”的被动。2021年票房达到8. 6亿的家庭电影《我的姐姐》以幼年弟弟和成年姐姐的视角对中国家庭的“长姐”形象进行了塑造。弟弟作为剧情发展推动的关键人物,说出了大量如“你冷静一点”“我只有你了”等此类推动剧情的关键话语,甚至在行为动机不足的情况下成了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人物,这对于一个学龄前儿童来说是不现实的。2019年《银河补习班》、2023年《学爸》、2023年《人生大事》等,均以儿童为背景,但真正的儿童议题却被更宏观的社会问题、生活困境所遮蔽,儿童视角并非是第一视角,而是连接故事的线索。
其次是作为“无助者”的被动。以农村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为题材的故事片,剧作结构大多数围绕“见到父母”这一线索展开。这一过程中儿童看似采取了多种行动,但决定权并不在于他们自己,儿童的主动行为实际也是一种唤醒成年人注意、获取成年人同意的“被动”。早在留守儿童群体刚刚出现的21世纪初,农村留守儿童在电影中的形象即为“盼望见到父母的苦孩子”,直至2022年的拉华加《千里送鹤》中,幼年丧母、跟随奶奶生活的多杰和格桑仍然是盼望父爱的陪伴,在救助小黑颈鹤的过程中与父亲达成了和解。这一过程中儿童仍然是等待关爱的天真者形象,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其三是作为“小大人”的被动,即儿童作为“成人世界的微缩景观”被塑造和观赏。《小熊的夏天》开篇,电影便借用主人公的口吻介绍每个同学的性格标签:“在加拿大出生,英语特别好/特别爱干净,有点洁癖/最聪明的/总穿得像小公主”。随后儿童们在相处的过程中,这些被成人世界规定的特质以各种情节呈现出来。此时儿童不再是儿童,而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社会”更像是成人意识中的社会,而非是儿童眼中的世界。而《红辣椒》《小初》等以农村儿童为主角的电影中展现出留守儿童家境悲惨、极度贫穷、年幼无知、行事幼稚或过于完美,其生活状态、人生经历与城市儿童和大多数受众存在明显的区别。在此形象下,儿童与学校老师、家长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也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等有明显权利差异的关系。
其四是作为“对比组”的被动,即这些儿童正处于认知世界与确证自我的阶段,他们的心理活动往往有着本真的人性与后天建构的社会规则的冲突。如《旺扎的雨靴》中,旺扎在得到雨靴后便一心企盼下雨,甚至和朋友一起到寺庙中祈求下雨以便他可以穿上雨靴,而此时此刻成人世界中全村人则希望不要下雨,不然全年待收割的庄稼就要“泡汤”。创作者将儿童作为“未经教化的天真者”来与成年人进行对比,以此实现“童趣”的彰显。
通过大量差异对立的方式,儿童成了被成年人观赏与审判的对象,也就失去了相应的主体性,创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完成了对于儿童的“他者化”塑造。这样的“他者”与“自我”相对,二者的二分也界定了主体的权威,加诸儿童身上的活泼可爱、叛逆顽皮等品质,更像是社会对于他者的标签与规训,“他者化”的儿童是一种媒体塑造的“产品”。在这种霸权式建构下,儿童想要“走上正途”,脱去“他者”身份,只能通过“融入集体/顺从成年人规则”这一选择。
在对儿童故事片的题材进行归纳的时刻,要将其放置在主要的社会关系的参照系中进行关照。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指出,童年是晚近的发明,作为社会结构和心理条件的“儿童”的发现伴随着文艺复兴对人性的发现。在电影等公共话语空间中,成年人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儿童处于“空白的、天真的、无知的”的弱势地位,被放置在成年人建构的话语体系中进行衡量与判断。在这样的大设定下,儿童形象呈现出与成人对立的、被动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儿童的主体性,导致了该类型故事片中儿童形象的他者化。因此,直接从儿童的视角引入主线情节,对儿童眼中的外部生活环境与内部心理进行平实、深入的描绘,才是将儿童本位和非儿童本位统合起来的儿童电影。
三、小成本儿童故事片的传播困境
尽管21世纪以来儿童故事片呈现出多种题材和样态,坚持正确导向、履行社会责任,但是经济效益并不突出,而传播效果不佳也会影响到社会效益的实现。就整体数据而言,虽然《我的姐姐》《人生大事》等电影均获得了可观的票房,但此类电影以儿童为“背景板”,其宣发重点与对象均不在于儿童,而真正面向儿童、描绘儿童的影片,往往有小成本、受众窄等传播缺陷,大量影片票房仅有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出现了票房仅有几百元的案例。究其原因,有电影市场环境、出品方性质限制等客观因素,也有作品自身创作、宣传方式的问题,如极端的情境设置、固定的模板叙事、单一的电影题材,以及低幼化的视听语言导致了影片的表达与效果乏力,出现了上述他者化与标签化的现象。
影片的小成本与分散的受众也是导致票房不佳的重要原因。在《拨浪鼓咚咚响》的宣发期间,影片宣传副总监肖副球在采访中表示,此类影片数量太少,尚未形成成熟的类型。他同样指出,此类小成本影片并非没有观众,而是比较分散,加上没有明星和名导加持,因此很难第一时间吸引观众走进影院,“我们的策略是通过精准点映找到第一波核心观众,再通过口碑发酵去逐渐破圈。但想要破圈确实非常难”[2]。
从数据方面看,在各年度票房最佳的儿童电影中,已有成熟IP的电影占大多数。以剩下的非IP、小成本电影为例,“影展+院线”的传播模式为其中有效且持续的宣发手段。电影节作为培育与发掘好的电影与电影人的盛会,先在影展中“破圈”,赢得一定的关注度,再投入市场是许多小成本儿童故事片的必经之路。以《旺扎的雨靴》为例,该片于2018年2月入围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同年获得第十二届FIRST青年电影展的最佳导演奖及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国际展映单元最受注目编剧奖等奖项。在2020年在院线首映之前的两年时间内,该片在业内已经获得了关注与口碑,对其院线上映后的票房大有助益。
对于儿童电影而言,与学校或基金会等官方组织进行公益合作是其天然的宣发优势。2017年上映、在第十七届华表奖中荣获优秀少儿题材奖项的影片《旋风女队》,讲述了黎族女孩在足球教练的带领下走出山村的真实故事。起初宣发团队立足于“中国女足”这一热点发起了一系列线上线下结合的宣传活动,但影片在影院上映初期的票房收入不足30万元。随后影片发行方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及其下属的光影童年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调整了发行策略,将《旋风女队》作为公益电影引入到全国各地的中小学和青少年宫。这种发行模式具有半官方性质,确保了稳定的观众基础。同时,公益放映不向观众单独收费,而是通过学校和青少年宫的活动经费中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这种新的发行方式有效地解决了票房低迷的问题,实现了电影制作方、观众以及教育机构之间的互利共赢。
在电影节与公益放映等传统渠道之外,流媒体的兴起为“网生代”电影提供了更多发行渠道。儿童纪录片《棒!少年》是流媒体公司和独立纪录片创作团队的良好合作范例。该片由互联网资本主投,加之分众下沉的网络市场,其同名衍生剧集在爱奇艺视频平台上线,实现了“棒球少年”的IP长尾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影片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四、儿童故事片的IP运营
2020年以来,院线电影受疫情影响较大,加之流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与扩大,以及VR等可家用设备的普及,观众对“进影院观影”的需求度逐渐降低。在这一特殊情况下,长线IP良好捆绑观众,成为票房主要支柱。“熊出没”系列电影从2014年起,连年在贺岁档共推出11部大电影,票房总计超过77亿元。在动画片如火如荼的同时,本就不是院线主流的儿童电影份额被动画电影瓜分,故事片所占的市场份额极为狭小。
在近年上映的儿童故事片中, 2014年春节档上映的《爸爸去哪儿》(6. 96亿票房)、2015年《爸爸去哪儿2》(2. 22亿票房)作为连续两年票房最高的儿童电影,均脱胎于当年湖南卫视的综艺《爸爸去哪儿》。2013年的《巴啦啦小魔仙》(5100余万元票房),故事世界观与人物关系均来自2010年的同名儿童电视剧。2021年的《皮皮鲁与鲁西西》改编自郑渊洁的小说,取得了达到了4195万的票房,是当年儿童电影的票房之首。上述故事片依托成熟的IP,自带流量与长效受众,有些作品票房却不尽如人意。
内容方面,国产儿童动画电影的内容改编值得儿童故事片借鉴。《爸爸去哪儿》大电影拍摄周期仅六天,演员来自综艺节目嘉宾,剧情设置被指与综艺太过相似。《巴啦啦小魔仙》的电影豆瓣评分与评价均低于其电视剧作品。相比之下,《姜子牙》《哪吒之魔童降世》《青蛇劫起》等脱胎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动画电影,却并不是原有作品形式的直接移植,而是进行了以原有的故事核与价值观为蓝本,参照其原本的仙侠、魔幻等世界的背景设定,展现了古代神话中的美好品德。IP类电影改编,需要将现代的观众需求与电影叙事接轨,展现出人类共通价值观与美好愿景。
从世界儿童电影的维度来看,中国虽然有着大量值得改造的IP,却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商业和文化价值。以《皮皮鲁与鲁西西为例》,该丛书拥有全套30册,连续出版了三十余年,积累了大量受众,却仅由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公司推出了一部电影,其IP并没有得到充分和长期的挖掘。相比之下,知名的英国儿童电影《哈利·波特》从1997年开始,由时代华纳公司对其进行跨媒介开发与粉丝社群维护,在10年间共推出了八部系列电影,全球票房累计为77. 4亿美元。在这些年间,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经过了动态的、历时性的发展,电影观众为此见证了主角们从儿童到成年的成长,同时推出了相关的游戏、周边,满足了多层次、多群体粉丝的情感需求,成功地增强了粉丝的黏性,大大提升了粉丝的忠诚度。也成就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五、结语
于蓝先生在谈到1981年受命组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以及1985年设立童牛奖时谈道:“编剧和导演要熟悉儿童生活,而且作品一定要孩子们喜欢和认可,儿童电影就是要给儿童看的。”[3]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故事片的创作主体多以第六代、新生代为主。在以儿童为主题的影片的发展过程中,故事片与纪录片都呈现出逐渐“下沉”的态势,其表达的内容越来越多元:从家庭学校到藏地、公路,议题也在从传统的成长历程到社会问题、人生哲理。然而儿童的被动化、他者化仍旧严重。创作者需要真正将儿童逐渐置于主体地位,并且将好的内容通过合适的方式进行商业化传播,提振影片的关注度,才可能真正实现儿童题材影片的价值与意义。
注释
[1]张晗.“儿童本位”意识下国产儿童电影叙事特色[J].电影文学, 2020 (13): 41-44.
[2]谢楚楚. 《拨浪鼓咚咚响》:小成本电影勇闯大众市场[N].经济观察报, 2023 - 03 - 06 ( 019) . DOI: 10. 28421/ n. cnki. njjgc. 2023. 000394.
[3]徐玥楚.从童牛奖优秀故事片看中国儿童电影创作变迁[ D].西南交通大学, 2020. DOI: 10. 27414/ d. cnki. gxnju. 2020. 001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