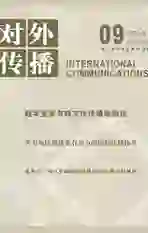数字变革对跨文化传播的重构
2024-10-02许向东范林钦
【内容提要】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深层次变革。在传播路径方面,数字化存储有助于实现文化永生与创新性转化,多模态与虚实共生的叙事话语激发了受众的情感共振,数字平台的产销结构促使文化交流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传播;在文化秩序方面,技术的局限性带来文化内容真实性与表达力的消解,交往方式的重构使全球文化社群进行结构性变迁,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数字化介入也会产生跨文化传播目标的偏向。对此,应坚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建构,让数字技术真正赋能多元、平等、包容的全球文化传播格局。
【关键词】数字技术 跨文化传播 传播路径 文化秩序
一、引言:数字技术介入跨文化传播场域
文化总是与技术相伴而生。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社会机制运行的时空束缚,激发了更为复杂的文化转换与重新结盟的传播系统①,催生了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跨文化传播是一个“话语间(interdiscourse)”的过程,其有效性的实现和文本构成、符号系统、传播结构与接受方式密切相关。②数字技术主要产生两种跨文化传播形式:一种是基于媒体平台分发的融媒体文化内容,如图文、音频、短视频和直播等;一种是基于信息载体变化的新型文化产品,如数字藏品、虚拟数字人、交互式游戏和漫画等。在此基础上,通过沉浸式、多模态的叙事话语与精准个性化的信息分发,实现了跨文化传播的全路径变革。
与此同时,数字变革也重构了跨文化传播的秩序逻辑。文化实践不仅包括各文化背景中的个人、群体、组织与国家等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也涉及文化与技术发展、传播主体与数字媒介、文化内涵与权力关系之间的交互。因此,数字技术赋能的跨文化传播,不仅是全球文化交流互鉴的关键机制,也成为文化价值观与社群重塑、诸种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场域。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技术变革为认知路线,深入探讨其如何影响跨文化的传播路径、具体实践和秩序建构,正确认识内在机理并提出建设性思路,期冀推动多元平等的全球文化传播新格局的形成。
二、数字技术助力跨文化传播的路径变革
数字技术既拓宽了媒介传播思路,也进一步指导数字时代跨文化媒介体系的构建。数字技术的底层逻辑是大数据和算法,借助人工智能和精准的信息投放技术,实现跨文化传播中文化形态、叙事方式与产销逻辑的全路径变革,消弭了传播的时空区隔,充分利用既有的传播资源激发用户参与分享、沟通和再创造,让跨文化传播焕发新的活力与生机。
(一) 数字载体:重塑文化的生命形态
数字技术变革跨文化传播的基础层在于文化载体的转换。融媒体、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主动介入文化采集、存储和处理过程,使文化成为永生的生命形态。数字化的文化形态可以在源头上保存和传承文化资源,并借助计算机图形学(computer graphics,简称CG)等现代数字技术建构虚拟现实交融的跨文化生态,极大拓展文化承载力和文化资源的阐释空间。
一方面,数字化的文化形态延展了跨文化传播的时空跨度。数字技术将文化内容转化为“0”和“1”的二进制形式,这种形态的信息可以不受任何物理介质的限制,在各种数字设备、终端和传输渠道之间自由流通。在共时性文化传播方面,移动设备和社交平台使跨文化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历时性文化传承方面,非同质化代币(NFT)与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数字藏品等形式恒久保存文化遗产,兼顾了版权确权与艺术灵韵,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产业链的生态繁荣。
另一方面,数字化的文化形态广泛应用于跨文本转录与传承。在文化展览方面,数字技术将静态的、凝固的文化艺术复刻为高清图片或视频,让电子屏幕成为移动的数字文化馆;在文献典籍方面,人工智能构建的文化数字化体系,以可视化建模的方式提供知识传播服务;在古迹文物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AI)提供图像增强与智能修复技术,有助于历史遗迹的保护与传承。总体而言,数字技术将厚重的、物理性的文化本体转化为轻量的、同频共振的文化产品,实现不同形式的文化再现、复原与分享,让跨文化交流更加生动可感。
(二) 叙事话语:感知体验与情感召唤
文化形态的数字迭代和媒介技术的时空演进也带来跨文化叙事方式的转变。首先,数字技术的全方位应用赋予个体感知与交互的能力,极大增强了大众主体的参与性与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其次,人工智能独有的技术特性打破传统叙事的时空壁垒,形成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跨文化叙事话语。本质上,数字时代的跨文化叙事是一种协调文化内容与传播形式的文化包装方式。
数字跨文化叙事话语首先表现为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即借助多媒体平台传播并吸引受众参与的叙事策略。③凭借简洁而生动的表达方式,短视频成为跨媒介文化叙事的主要形式。④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AI Generated Content,AIGC)借助虚拟数字人、人工智能翻译来降低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成本,并通过多模态交互、虚拟现实技术营造沉浸式参与和互动的文化数字空间。基于此,进一步发展出互动数字叙事(interactive digital narrative),即允许用户借助角色扮演、人机对话等形式参与叙事,用户的行为可以改变叙事过程或结果,进而增强用户的参与体验。⑤
以上的跨文化数字叙事呈现两种特征:一是营造感知体验,二是注重情感共鸣。感知体验是为适应媒介内爆的数字化语境,调动多种媒介与感官要素提升内容冲击力的叙事方式。人工智能的情感计算、分析功能,深入挖掘并精确掌握文化的深层情感,借助感知体验不断重构受众对于自我与社会的认知结构,二者共同唤起全球性情感共情。例如,《原神》世界的“海灯节”与中国龙年春节同步,游戏借用非遗技艺推进剧情,全球玩家可以在游戏世界中沉浸式体验传统舞狮等中式美学;在参与剧情推进的过程中,用户产生与角色的情感连接,进而引发关于永恒、亲情、忠诚等情感价值的共鸣。事实上,数字媒介重新语境化和压缩的不仅是信息,数字空间中超社会、超情感的互动,反而容易激发大众的情感能量。⑥
(三) 产销逻辑:多元协同的一体化结构
数字技术催生了海量庞杂的传播主体与复杂多变的传播方式,使跨文化传播的组织生态从单一的大众传播模式转向多元协同的一体化结构。目前的跨文化传播格局主要包含以报刊、广播电视媒体组成的传统媒体矩阵和以自媒体、数字平台组成的新型传播结构。随着中国国际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相继在X(原推特)、优兔、脸书等海外社交平台开设账号,后者逐渐占据跨文化传播格局中的核心生态位。
平台型媒体并不从事具体的文化内容生产,而是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一个数字化传播情境。其中,生产主体是以数字平台为基础设施、自媒体为内容源头的多元生产主体,个人、组织、机构和政府均可注册为自媒体账号,产出用户生产内容(UGC)、专业生产内容(PGC)、职业生产内容(OGC)和机器生产内容(MGC)等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生产关系表现为数字平台为自媒体制定生产规则和提供技术支持⑦,统筹分发自媒体产出的跨文化产品。例如,“中国日报双语新闻”在微信平台分为订阅号、视频号、课程和商城等多种内容输出和服务提供的形式,并遵循相应的发布频率规则。分发方式则是根据受众的特定偏好,算法推荐个性化文化信息和产品,满足跨文化传播群体的具体需求和长尾效应。
总体来看,数字平台中的产销结构实现了文化内容的无限供给与品类的细致分化,也赋予个体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得跨文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区域传播和专业实践状态,转向“人人可成为跨文化中介”的全球性交流互通。自媒体产出个人经验之上的跨文化叙事,使得不同圈层的话语共振成为可能,“网红”群体、“Z世代”逐渐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主力军。⑧⑨数字平台所提供的跨文化传播通道和协商空间有效补充了人文交流渠道与传统媒体的不足,彼此形成互为生态支撑的传播矩阵。
三、数字变革重构跨文化传播秩序
数字技术在深刻改变跨文化传播路径的同时,不断扩张的技术权力也对大众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心理施加了前所未有的规约,并难以避免地成为政治和资本权力运作的表征。同时,媒介技术本身具有非理性要素,在人-技互构互驯中产生文化表达受限、文化身份区隔和文化传播屏障等一系列新问题。在此背景下,应继续审视和反思数字变革所形成的新型文化传播秩序。
(一)技术迷思:文化真实性与表达力的挑战
数字技术主动性介入文化生产过程,获得了内容孪生、智能创作、智能编辑在内的内容创作力。⑩但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也引出一系列工具理性的相关命题。概言之,人工智能技术依赖于预训练阶段的监督学习,受限于数据规模并难免带有人类思维的固有偏向;囿于算法黑箱的遮蔽性,人类难以纠偏其中的错误逻辑,以至于难以把控跨文化生产和传播过程,甚至失去自身的主体地位。
其一,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化内容的可信性。信息过载和深度媒介化本就分散了受众注意力,产生后真相、社交媒体倦怠和理性反思减退等现象。AIGC深度伪造的照片、视频和文本进一步削弱受众的辨别能力。当虚假信息被政治阴谋、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等价值观所裹挟时,跨文化传播的舆论场域便会走向混乱。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参与文化对话过程中也会受自身训练模型所限,有意或无意地出现文化遗漏和误读。如ChatGPT在中文知识问答上容易出现错误,并可以用流畅的语言继续阐述编造的虚假事实。11
其二,数字技术在文化转换和呈现方面存在一定的表达困境。在数据转化方面,文化的思想、审美与情感难以被直接数字化,数字技术本身也存在分辨率与色彩还原性方面的局限。12这均带来文本编制时的文化折扣,削弱了文化独有的美学蕴含。在文化呈现方面,基于用户的兴趣与需求,算法分发技术倾向于提供大同小异的文化产品,形成一个个“内容同质”的信息茧房,使整体的文化传播格局呈现碎片化、分层化的形态。从某种意义上,算法的固化限制了文化的多元流通。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数字技术的转译与呈现不仅可能产生内涵缺失,也可能使人们沉醉于技术支配的快感,从而逐渐丧失对文化美学的感知和创造力。
(二)受众互动:身份与社群的流动
在跨文化交往不断发展的动态语境中,交流互动方式与文化身份流动之间相互制约或促进。13文化符号通过跨文化交往产生相应的意义,符号意义附着于交往个体的内部形成身份认同。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文化符号系统,也重塑了跨文化交往方式,个体的身份认同也会随之改变,产生全球文化社群的结构性变迁,呈现社群“区隔”与“桥接”两种状态。
一方面,数据的集聚效应带来跨文化受众的部落化身份认同。个性定制与算法推荐使得用户不断接触到符合其文化背景和兴趣的内容,形成具有共通经验与偏好的文化社群。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不断强化社群内部的身份认同,选择性接触和数字鸿沟则会加剧社群之间的割裂与区隔。因此,这种部落化的文化社群具有明显的同类强化和他者排斥的特质,形成一个“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螺旋闭环。集体的渲染与重复一旦使社群意识走向非理性,便会带来极端的群体情感,使得文化社群更为疏离和分散,极大削弱了跨文化有效理解和对话的可能。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催生了更多“桥接社群”的出现。这种文化身份的群体往往具备多个文化背景的相关知识和多种文化的情感认同,可以灵活游走于不同文化图式之间。14社交媒体为“桥接社群”提供多样化的表达空间。例如火爆全网的“City不City”视频,博主用中文句式结构与英文单词混搭的表达方式,在记录中国旅游的场景中诙谐幽默地展示中国城市风貌。总的来说,“桥接社群”所参与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往往是更为积极主动的个人沉浸式体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与情绪感染力,在灵活的互动中增进文化间的接合与交融。
(三)价值旨归:政治与资本权力的介入
数字媒介充分激活了跨文化传播群体的共情感知,促使国际政治与经济权力更为积极地介入文化传播过程。作为重要的传播中介和基础设施,数字媒介开始重组跨文化传播中的权力结构,乃至重新定义国际文化竞争秩序。面对技术变革下文化体系在权力关系中激烈的碰撞与互构,我们不得不反思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传播格局是服务文化本质主义与霸权主义的目标还是服务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15
数字平台不仅掌握或控制着文化数据来源的多元性,还能够借助技术手段影响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与效果。技术体系的价值标准会影响跨文化交互关系的建设,也对媒介技术的应用产生巨大限制。一方面,资本逐利所产生的信息泛娱乐化遮蔽了文化应有的美学魅力;另一方面,霸权护持还会扭曲跨文化传播的叙事结构与文化价值。比如,奈飞(Netflix)平台在购买《三体》版权后对其加以改造重制,刻意保留黄种人的刻板样貌,并加入大量美国文化元素,展现出平台权力背后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
此外,对数字媒介的争夺也成为国际话语权竞争的重要场域。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征用数字传播手段来规约跨文化传播主体的认知与偏好,势必影响国家形象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某些西方国家利用技术、资本优势,通过设置技术壁垒和制造虚假信息等方式加固既有的“舆论藩篱”,试图维持其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随着人工智能在数字媒体的应用,2024年5月23日,美国通过《加强海外关键出口限制国家框架法案》(《ENFORCE法案》),将AI模型出口纳入国家监管框架。此外,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知更鸟计划”,还是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债务陷阱论”“新殖民主义论”等舆论攻讦,在其中,媒介往往成为国家操纵大众舆论的工具,数字传播中大量难辨真伪的信息更能激发或凸显极端价值观与偏见。
四、未来愿景:善用变革之器,建构文化合意空间
数字变革深入到跨文化传播的各个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对此,应始终坚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建构,协调和凝聚多元主体搭建文化共融互通的合意空间。首先,继续加强数字技术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开发落地。坚持发展大语言模型、多模态技术和多媒体融合,拓宽跨文化交流渠道。同时,提高文化符号表达的精确性,避免传播过程中叙事话语的不完整和内涵扭曲,促进对话,增进理解;其次,针对算法歧视与偏见、信息茧房和深度伪造等技术风险,应继续完善人工智能的多维治理体系。其中,企业平台应加强内容审查机制,提高算法透明度与可解释性。国家和政府应借助法律法规夯实数字文化的良法善治根基,完善用户监督反馈机制,使其具备数字跨文化交流的批判思维;最后,各国应秉持开放包容与兼容并蓄的理念,积极开展表达自我与倾听他者意识之间的对话,建构数字空间的全球倾听模式。既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智媒文化传播,也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对文化交流互鉴的赋能效应,才能促成超越国家、种族、宗教界限的全球性文化共识,实现数字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愿景。
本文为人大“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研究成果,项目号:MXG202301。
许向东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林钦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Hannerz,U.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Routledge,1996, p.7.
②Scollon, R., Scollon, S. W., & Jones, R. H.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Wiley-Blackwell,2012,p.18.
③刘煜、张红军: 《遍在与重构: “跨媒体叙事”及其空间建构逻辑》,《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9期,第26页。
④常江、杨惠涵:《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国际传播:趋势与检视》,《对外传播》2024年第6期,第19页。
⑤李媛:《主题出版中的互动数字叙事策略》,《科技与出版》2018年第11期,第94页。
⑥[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 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12年,第198-199页。
⑦高阳:《新媒体的逻辑 内容生产与商业变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45页。
⑧季芳芳:《社交媒体时代的跨文化传播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4日,第3版。
⑨黄日涵:《未来已来:Z世代将成为对外交流的主力军》,中国日报网,https:// cn.chinadaily.com.cn/a/202204/27/WS6268e423a3101c3ee7ad2c36.html,2022年4月27日。
⑩Das P., Varshney L. R. “Explai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ion and Creativity: Human Interpretability for Novel Ideas and Artifacts”,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vol.39,2022,pp.85-95.
11张华平、李林翰、李春锦:《 ChatGPT中文性能测评与风险应对》,《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3年第3期,第21页。
12申峥峥:《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理论月刊》2024年第5期,第145页。
13朱婕:《跨文化交往与文化身份认同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年,第252页。
14田浩、常江:《桥接社群与跨文化传播:基于对西游记故事海外接受实践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1期,第40页。
15赵月枝:《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6卷第1期, 第128页。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