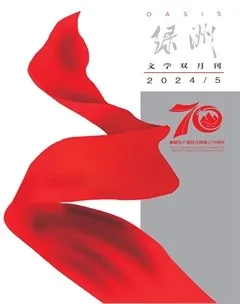开垦莫索湾
2024-10-02杨耀龙
在天山北麓,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南缘,有一大片戈壁,地图上显示这里是莫索湾。
1957年秋,第八师副政委、副书记刘丙正率七人勘测队进入莫索湾。刘丙正带上勘测规划草图,同兵团领导张仲瀚一起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研究开发莫索湾。同年11月由老八路肖凤瑞带领第一支小分队开进莫索湾西营城旧址,点燃第一堆篝火。
1958年5月,一支20人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在老红军张德华的带领下,背起简单的行囊,怀着吃大苦的决心,在荒滩上开疆拓土,筑路开渠,挺进莫索湾最边远的西古城。
随后,大队人马开进了莫索湾。
这群军垦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吹过最冷的风,淋过最寒的雨,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个个从骨子里迸发出最坚定的执着,在荒芜的戈壁荒滩上,用血汗把大漠南缘的荒滩变成绿洲良田。仅在我国经济困难时期,莫索湾就向国家贡献了七千万斤粮食。
光阴似箭,时间如梭。勤劳勇敢的军垦人从昔日的“天当房,地当床”“住地窝子,喝涝坝水”,到现在的高楼林立,过上了小康生活。
七十年来,几代军垦人的艰苦创业,才使荒漠戈壁变成了莫索湾粮仓,才在野狼出没的荒漠上崛起了崭新的城。
现在,光荣的老军垦们有不少已经过世,健在的也都到了暮年。他们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里,蕴含着伟大的兵团精神。
兵二代,兵三代以及兵团的后来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人民和国家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1
1957年9月的一天,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一辆嘎斯车从小李庄出发,颠颠簸簸地向北驶去。车上坐的是刘丙正和基建处长、勘测队长等七人。所带物品有:一支枪、七根棒子、一枚指南针、一些烙饼和十几个西瓜,还有一大桶水。
“刘书记,不是有枪吗?还让我们每人带一根木棒子干什么?”汽车颠簸着,唯一的女同志卫生员李英在车上问刘丙正。
“小李,有枪也不能随便打野生动物。沙漠里除了狼对我们人类有威胁,其它的像黄羊、野兔、野鹿、野马、野骆驼一般不攻击人。我们遇到狼,只要它们不攻击我们,我们也不要用枪打它们。野生动物也是要保护的。它们真的攻击我们时,手中的木棒子挥起来,它们害怕就跑了。”刘丙正笑着说。
“那它们不跑,咬我们怎么办?”李英追问。
“那我们就吃狼肉!”刘丙正指着小伙张铁成怀里的步枪说。
“好好好!棒子是警告,它们如果和我们硬磕,我们就吃狼肉。”
“吃狼肉!”大家高兴地喊。
“哎?张铁成,你的枪打得准吗?”李英问。
“正因为我枪法准,才被选派来负责这次师部勘探队的安全保卫工作。”张铁成晃晃怀里的步枪,自豪地说。
“看你年龄不大呀,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枪法呢?”李英好奇地问。
“俺今年十七岁。上学时书包里总是带个弹弓,口袋里装一些小石子。放学路上用弹弓打斑鸠、麻雀。我从小学三年级就打弹弓,开始打不准,后来慢慢摸索到方法了,打得可准了。秋天,还到野地里打过野兔子呢!那时我家经常吃斑鸠、麻雀和野兔子肉。”
“野兔子,你的弹弓能打死吗?”李英问。
“打不死的,瞄准头打,只要打上了,兔子在短时间之内被打晕,有的叫着在地上打滚,有的转圈圈,也有的就不动了。人过去用小绳绑了拎回家就行了。”
“哎呀!小鬼你能得很!什么时候来新疆的?”基建处长问。
“我去年十六岁初中毕业,就报名支边来了。石总场老鸹窝(连队所在地)成立了民兵排,打靶训练了一个月。最后实弹打靶,每人五发子弹,我四十九环,第一名。两位老转(转业战士)都没比过我,这和我多年打弹弓有关系。不然,这次勘探莫索湾小分队哪能轮到我来!”张铁成说着,看看刘书记:“刘书记,野兔子可以打吧?”
“可以,但是用枪打野兔子太浪费子弹,还是不要打!”
“放心吧,不放枪。只要看到野兔子,百步之内它跑不了。我保证让大家吃上野兔肉!”张铁成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一把弹弓,抓出一把小石子。
“你是有备而来呀,好!”刘丙正高兴地说。
“晚上能不能吃上野味,就看你小鬼的了!”大家在颠簸的车上一阵兴奋。
汽车开进了准噶尔盆地南缘的莫索湾,这里北邻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干旱缺水,遍地梭梭、红柳等沙漠里植物。这里既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野狼猎杀黄羊、野兔的地方。汽车一路奔驰,看到过不少这样的场面。
不远处真的发现了狼群,狼群在远处,有站着的、蹲坐着的,看到嘎斯车这个庞然大物,它们也不敢贸然近前。只是发出阵阵嗥叫。人们生怕从车边的梭梭、红柳丛中突然蹿出一群狼,神情不免有些紧张。
刘丙正看到大家紧张的情绪,命令小张朝狼的方向空放两枪。砰!砰!两声枪响,狼群四散奔逃,就连开始人们没看见的野驴、野马、黄羊、野兔,也不知从哪片红柳丛中蹿出,惊慌失措地向四周狂奔。梭梭林、红柳丛被动物们冲撞和奔跑带起的风吹得来回摇动。
“野兽真多啊,跑起来好壮观!”李英兴奋地说。
小分队的人员下车后,人人手握一根木棒子,喊着给自己壮胆。叫了一阵,感到平静了,才认真观察四周。梭梭树枝干呈灰白色,针叶是淡绿色;红柳枝繁叶茂,垂柳丝丝,紫红色的花开遍了戈壁荒漠。红柳是戈壁中的精灵,不畏风沙酷暑,霜雪严寒,和梭梭一样将粗壮的根系深深地扎进几十米深的沙土里,生命力极强,克服了艰难万险,把大片火红的美丽留给大漠。“哇!太好看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喊出。
大家听从刘丙正的安排,低头看向荒原戈壁。这里地势比较平坦,土地肥沃,地面覆盖着二十公分厚的黑褐色腐殖土。踩上去,尘土蹿起好高。七人都兴奋的捧起一捧土,在鼻子闻,刘书记高兴地说:“怪不得传说这里撒一杯芝麻,能打七八担哪!”
小分队在勘探中发现了几座废墟,他们来之前,从地方志中知道这些废墟叫西营城、野马城、东阜城和西古城。据记载,清朝同治年间,曾有人在这里屯居,后因河流改道,没了水源,人们被迫迁徙。
在东阜城的废墟中,他们还捡到一块长方形的青砖。刘丙正说:“把它带回去做个纪念吧,我们的前人曾在这里铺下屯垦的基石。但是他们当时缺乏战胜自然的能力,干旱将他们逼退。今后我们一定要站稳脚跟,在这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刘书记,张铁成已经用弹弓打了四只野兔了!”
卫生员李英身上背着药包,一手提着两只野兔子,兴奋地说:“这下回去有肉吃了!”
“太棒了!太棒了!”几个人在空旷的沙漠欢呼起来!
勘测小组在茫茫的戈壁中,穿梭梭,钻红柳。四周沙山走势都一个样,梭梭、红柳都是一个面容。汽车轧过的痕迹早被风沙填埋。小分队成员迷路了。
“这可怎么办?”一些同志发了愁。
刘丙正说:“莫索湾,莫索湾,就是要摸索着进来,摸索着出去。今晚走不成,咱们就在大漠里宿营,与豺狼野兽共眠。不是有人说嘛,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与凤凰同飞必是俊鸟!我们军垦人不怕困难,不怕流血牺牲!今晚就来个‘天当房,车当床’,我们先燃起篝火,烤着野兔子肉,享受大沙漠夜里的风光。等明天睡醒了再找路。”刘丙正到底是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钢铁战士,多年的政治思想工作者,几句话说得大家都有了胆量和豪气。
“张铁成,晚上如果在车厢歇息,你挨着大姐睡啊!”李英看着张铁成说。
“哎哟!现在就寻找保护了。放心,我们所有男人都会保护你的。”测绘队长说,大家记好了:“晚上在车上睡,把棒子放身边,即便有群狼来,它也一下跳不上车。它往上扒,咱们就在高处用棒子打。”
“放心!到那个时候,小张可以开枪打,咱们吃狼肉!”刘丙正看着张铁成说。
“是!坚决执行命令!”张铁成向刘丙正敬个礼,“我一枪一只,干光它们!”
“张铁成,你带了多少发子弹?”基建处长问。
”40发,够了!一枪一只,硬和我们较量的只有死路一条!”张铁成一下兴奋了。
驾驶员小马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术,硬是拉着小分队闯出一条路来,很晚他们才赶回到小李庄基地。
接下来,小分队开始进行具体的测量、规划。把帐篷搭在莫索湾的进口处,每走一段,就在较高的沙包顶上燃起一堆篝火作为路标。一站一站地往前走,用标杆测量做出规划,画出了草图。
规划、草图都出来了。而这片荒芜的大漠戈壁,从区域划分上属于玛纳斯县,开荒造田肯定要和玛纳斯县协调。刘丙正驱车赶到乌鲁木齐兵团司令部,向兵团领导张仲瀚政委做了汇报。张政委非常高兴,两人一直谈到深夜。
“开发莫索湾这是件大事,要请示自治区王恩茂书记。”张仲瀚边说边拨通了王恩茂的电话。
“好啊!张政委,明天早上赶到上班之前,你俩到我家来谈!”电话那边王恩茂书记说。
第二天一大早,在王恩茂家里,刘丙正把勘测规划图摊开在桌上,汇报具体的开荒方案。有三个方案:最低方案,石河子垦区要在莫索湾开垦40万亩,中间方案是60万亩,最高方案是80万亩。
王恩茂稍加思索,对张仲瀚和刘丙正说:“开垦莫索湾,既要照顾兵地双方的需要,也要考虑双方的开发力量。取中间方案吧,给兵团60万亩。其他的给地方留下。”开发莫索湾的方案,就这样一锤定音。
2
开发大漠南缘的莫索湾,首先要解决水的问题。没有水,一切开发都等于零。
石河子的东北处有一座水库,名曰大海子,实际只能蓄水400万立方米。为了发展生产,八师党委召开会议,决定要扩建大海子水库。
1954年,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曾到垦区视察,同行的有一名外国水利专家。垦区当时把扩建大海子水库的方案拿出来向这位专家请教,这位洋专家到水库现场观看后,摇着头说:“不行!不行!不行!它将使水库下游大片土地的地下水位上升,造成土地次生盐渍化。”洋专家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圆圈,表示水库,然后摇摇头,在圆圈上重重地画了个“×”,这个方案被洋专家枪毙了。他的结论给在场的同志们泼了一大盆凉水!
随着开发莫索湾计划的制定,扩建大海子水库的方案又重新提出来讨论。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焦鸿钧说,“洋专家”的见解不无道理,但建山地水库造价太高。平原水库虽有弊端,但可在水库下游植树造林,进行生物排水。况且大海子水库周围的地层中有一层黏土,可以起到防渗作用。他的发言给了领导和参会人员很大信心。于是被枪毙的大海子水库扩建方案又起死回生了。扩建后的大海子水库,库容由原来的400万立方米增加到1亿立方米。
担任大海子水库扩建施工任务的是兵团水利工程人员,调集了近万人,昼夜两班施工。水库大坝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夜间灯火通亮,汽车、翻斗车、架子车、独轮车来往如梭,干部、战士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这个热气腾腾的场面,大有百万雄师过长江一样热火朝天的感觉。
工程师焦鸿钧和战士们并肩劳动。在一次拆迁大坝护坡养架时,上面掉下一块木头,木头上有一根铁钉将他的背划破了一道一厘米深的口子,伤口愈合后,留下了一条光荣的疤痕。今后一摸疤痕,就想起大海子水库了。”
经过军垦人的拼搏努力,原计划两年完成的大海子水库扩建工程,一年就竣工了。十二米高,十一公里长的坚固大坝,拦蓄了一泓浩渺的碧水青波。大海子真是名副其实了。风儿吹来,水库的水拍打着大坝,好似击掌庆贺!
大海子水库到莫索湾的引水总干渠长二十六公里,总土方量近一百多万立方米。总干渠工程是由垦区基建部队承担的,基建部队投入了两千多名施工人员。刘丙正又从老场调来一批精兵强将参加大会战。
动员大会上,刘丙正提出:“我们要在明年(1958年)3月27日竣工放水,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有!有!有!”会场上口号声惊天动地。当时正是严冬季节,最低气温达到零下40多摄氏度,战士们睡帐篷、喝雪水,向冻土开战。一个个的眉毛上、衣服上挂满了冰霜,而衣服里却热汗流淌。一根根镐把震断,一把把钢锨卷刃,但战士们的决心和意志坚如铁。小战士张铁成还编了一条大标语贴在工地宣传栏里:“军垦战士干劲大,地冻三尺咱不怕。开动脑筋想办法,老虎嘴里敢拔牙。”
军垦战士有勇有谋,创造了很多制服冻土的办法,老红军张德华和小青年张铁成还在冬季修渠挖冻土劳动中想出了“黑虎掏心法”“火烤化冻法”“盖土防冻法”等等,使平均工效由每人每天挖八立方米提高到十二立方米,加快了施工速度,争取了时间。同志们都说这老张和小张,真是开发莫索湾的功臣!
总干渠上要修筑七座大型管理水利建筑,需要上万立方米的砂石料,可就在要放水的半个月前却遇到了困难。基建办公室主任从工地回来反映有一段十公里的道路,开春化冻翻浆,拉运砂石料的汽车无法通过。若不及时解决,就会停工待料。这时,刘丙正以过去战争年代指挥战斗的魄力,从老场调来了十多台斯大林80号拖拉机,把石料一趟又一趟地拽过翻浆地段,保证了砂石料的供应。
“放水了!放水了!”整个总干渠工程按计划提前十二天峻工。胜利的喜讯像长了翅膀似的,从渠首飞到下游开荒的工地。这天,大渠上下盼水迎水的人们欢声雷动,一直等到深夜,谁也不愿离去。有人提着马灯,有人举着火把,有人在渠岸上燃起一堆篝火,张铁成把耳朵贴近渠旁倾听水的脚步声。
水来了。水像奔腾的骏马,唱着胜利的欢歌来了!浪花飞溅,像旋转的青春舞者,欢快地向人们跳着、唱着跑来了。
人们欢呼、跳跃,有的用双手捧起那浑浊的渠水畅饮,老红军张德华干脆跳进渠里,任由天山的雪水浸泡双脚,让清凉的快意沁入心脾。张铁成和几位年轻人在渠埂上跟着水奔跑,送了一程又一程。人心沸腾,渠水奔流,满天星斗和两岸灯火映入渠水。干旱的荒漠来了水,军垦人激动得流着热泪,奔走相告。
3
开发莫索湾,兵团石河子垦区有序进行。1957年11月下旬,下了场大雪,新疆天气骤然变冷。垦区派出了一支规划、建设莫索湾二场的七人先遣队。先遣队带着七桶水、四袋面粉、十多斤咸菜进入了莫索湾。张铁成主动请缨参加,队长肖风瑞看张铁成年龄不大,开始并不同意。
刘丙正说:“让他去吧!小伙子很能干,他去了,你们可以经常吃到野兔子肉!让他负责先遣队的安全,带上枪!他的枪打得可准了!”
先遣队来到西营城的废墟旁,铲去积雪,支起帐篷,在这里安营扎寨。也就是这个帐篷所在地,后来成了莫索湾二场的场部。也就是从这天起,一百多年荒芜的莫索湾,燃起了一堆篝火。
刘丙正给先遣队的任务是迅速查清场内的土壤分布情况,规划轮作区,确定连队分布点,尽快建场,争取当年开荒当年生产,解决大批开荒部队的吃饭问题,以减少补给运输困难。
先遣队扎寨的第二天清晨,老八路肖风瑞就带领同志们出去踏勘土地了。他抓一把黑土放进嘴里一点嚼了嚼说:“好土啊!能嗑出油来呢!”先遣队人员身带水壶、干粮,一出去就是一天,要到天黑才归营。一天傍晚,他们又在梭梭林中转得迷了方向,摸不回来了。留在帐篷里的通信员小吴见出去的同志很晚还没回来,就出了一个点子在西营城的城堡上燃起了一堆篝火。回来的同志都激动地说:“篝火是我们先遣队生活中的好朋友,它给我们温暖,给我们指引方向,还给我们以憧憬和欢乐。”晚上,先遗队队员围在篝火旁烤着野兔子肉,吃着聊着,聊莫索湾的传说、莫索湾的未来,聊到很晚很晚……
一天夜里,梭梭林里传来了几声猫头鹰的叫声。有人说:“坏事了!夜猫子叫,祸事到。这是不祥之兆。”可小战士张铁成却诙谐地说:“不!这是夜莺朝凤,乃吉祥之兆。”
“朝什么凤?吉祥何来?”大家问。张铁成这时露出了他的辩才。他慢条斯理地说:“猫头鹰乃捕鼠能手,益鸟也。我们开发莫索湾,它应当向我们这些开拓者祝贺!”他这样一说,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先遣队中有一个女技术员郭荣荣,是农学院农学系的毕业生。因为生活上有诸多不便,垦区党委决定,开荒初期不允许女同志进莫索湾。“我要去,坚决要去!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这是国家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当缩头乌龟!”郭荣荣坚决要求上前线,加上工作又需要她,垦区党委就破格批准了。她和男同志住在同一个大帐篷里,特殊的是她在大帐篷里挂起了一顶军用蚊帐,同志们风趣地说她住的是大帐篷里边的小帐篷。她性格开朗,工作积极,从不说苦和累。白天踏勘土地时,她把笑声撒遍了荒野,晚上聊天时,她的笑声又使帐篷里充满着欢乐,同志们都叫她“笑观音”。还有人调侃说:“累了一天了,听到郭荣荣的笑声,马上不感觉累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是有道理的!”
年底,一辆辆汽车,一台台拖拉机挂着拖斗,载着开荒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莫索湾。开荒造田的战斗打响。开荒、运荒、犁地、修渠,使沉睡的荒原沸腾了起来。同志们住的是帐篷、地窝子,吃的是咸菜,喝的是雪水。为了吃水,每个连队都积了大堆的雪,用篷布和柴草盖着,一是怕风沙刮脏了,二是怕日晒融化得快。为了节约用水,每人每天只分配一茶缸子用水,早晨几个人共用一盆水洗脸,洗了脸还要留着,晚上再洗脚,洗衣服。到了三四月份,雪水化了吃水就更困难了。部队曾试着打了一些井,可井里的水苦,难以下咽。总干渠虽然挖通了,但支渠、斗渠还未建成,各连队仍要到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以外去运水。
一天晚上,张铁成背着枪出去挑水,在梭梭林里迷了路,担着这一担水转了一夜,却不忍心把水倒掉。第二天早上回到宿营地,还带回了三只野兔子。他把水一放下,倒在地铺上呼呼就睡着了。
开荒造田,战士们挥汗如雨,口干舌燥,嘴唇皲裂。可当伙房送来一点开水时,大家又互相推让。当时工地小黑板上曾有这样一首诗:“太阳当头汗水淌,人多水少供不上。口干舌燥嘴唇裂,有水大家互推让。”这自然也是张铁成编的顺口溜。
张铁成年龄不大,但是不甘落后。他生怕自己早晨醒不来,就用一根背包绳子,一头拴在自己脚上,一头拴在帐篷门上。无论谁想悄悄地提前上工,都会无意中把他“叫醒”。
当时,战士们虽然用的是坎土曼、镢头等落后的工具开荒,但每人每天的平均工效却达到了十五亩。开春后,道路翻浆,汽车不能把蔬菜和油及时运过去,战士们半个月没有吃上菜和油,但大家仍是豪情满怀,干劲不减。有诗为证:“半月不吃菜,干劲照样在。半月不吃油,干劲照样有。”后来,两台拖拉机加入了开荒造田的行列,大大提高了开荒的日工效。两位驾驶员互相配合,两台拖拉机相隔五十米,中间拉起钢丝绳,机器轰鸣,齐头并进,所过之处摧枯拉朽,真有排山倒海之势。这项革新技术不仅使工效大大提高,而且使开荒造田的造价也降低了三分之二。
农八师原计划1958年在莫索湾建三个军垦农场。“有了这项技术,这个计划岂不是太保守了吗?”刘丙正当机立断,第二天在开荒前线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同志们,我们这支虎狼般的军垦队伍,加上机械开荒运荒的先进作业方法,真是如虎添翼!开发莫索湾的这一仗完全可以扩大规模,加快进度了。”刘丙正信心满满地动员干部们。
随后,从莫索湾一场到莫索湾七场,全面实行大兵团作战。分别组成开荒造田、兴修渠道专业队。开荒大军展开劳动大竞赛,你追我赶,齐头并进。
自从刘丙正主持的那次动员大会后,开荒造田掀起了高潮。莫索湾的开荒工作由点点星火,发展成燎原之势。1958年,一下建起了七个军垦农场,开荒造田三十六万亩。随后三年共开荒造田九十多万亩,远远超过了最初的计划面积。后来,为了加强领导,垦区将七个场合并为三个大型的军垦农场,就是后来的西营城、东阜城和西古城,一个大的莫索湾垦区。
1958年5月,张铁成又和老红军张德华一起作为骨干力量开进了莫索湾七场。
大漠深处的莫索湾农场,军垦人用忘我的劳动,到1965年,创造出林带成网,粮食盈仓,道路成荫,瓜果飘香的莫索湾粮仓,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漠绿洲。当年二十二兵团首任司令员陶峙岳视察莫索湾时曾留下诗句:
莫索湾边共青场,
防风沙障树千行。
稳保丰收先抗逆,
操之唯我破天荒。
1957年,刘丙正看到莫索湾荒滩变绿洲后也曾赋诗一首:
驼铃梦坡忆当年,
摸索勘察沙海边。
见证军垦盛衰史,
西营遗址一青砖。
书记政委亲拍板,
千军万马战荒原。
冰天雪地挖水渠,
双手开出万顷田。
绿树成荫阡陌连,
汗水浇灌粮和棉。
军垦战士多壮志,
浩瀚荒漠变江南。
奠基亲历五十年,
魂牵梦萦莫索湾。
临终遗言定归宿,
融入沃土水相伴。
老书记回望率领勘探人员勘探莫索湾、开发莫索湾、开渠引水、开荒造田,茫茫戈壁荒原变成绿洲良田的艰苦岁月,感慨万千。他情系莫索湾,留下诗句,安排子女在自己去世后,将自己的骨灰撒在莫索湾大地……
dc8a343ed1de208b53aeeef3a82849c20620595d697b416d9b1d68519306f0ed一片绿洲出现在大漠南缘,“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莫索湾粮仓在全国闻名遐迩,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知道了“莫索湾”!越南当时的主席胡志明来中国,还提出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莫索湾农场参观学习。当时正值五月初,场部青年宫前桃花正在绽放,没有鲜花献给外宾怎么办?欢迎队伍中,莫索湾中学的彭建民同学跑到桃园,折了几枝桃花献给了胡志明!胡志明还高兴地抱着他,亲了他的脸。莫索湾的名声从此就出了国!
我在莫索湾上学,曾在莫索湾工作多年,在兵团退休。对兵团,尤其是对莫索湾情有独钟。七十年来兵团人的艰苦卓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总想写点文字宣传莫索湾,歌颂军垦人。我现已过古稀之年,为不留遗憾,就把平时写在笔记本上的诗歌抄录一首。借以回忆莫索湾那段艰苦的岁月,歌颂老军垦们特别能吃苦的无私奉献精神。
忘不了的最美画卷
六十年前的冬日里
我来到了莫索湾
母亲用沸腾的冰雪融水
煮熟了大年三十的饺子
地窝子里蒸出了过年的白面馍
支边姐姐漂亮的脸蛋
早已变成了古铜色
写满了大漠孤烟
记载着气候的恶劣
大雪飘飘,北风呼啸
马车进大漠深处拉柴火
车中间放着一大盆熊熊的火
军垦人在火盆两边坐
红褐色的脸被一闪一闪的火光抚摸着
“叭叭叭”
马车驭手的鞭响起
奋蹄如飞的马儿呀
口鼻中呼出的白雾
和雪花一起打着旋
落到马鬃上
瞬间就变成了一串串冰穗穗
在马头马颈的两边倒挂着
叮叮当当的声音
和马身上的铃儿一起
伴随着马蹄的节奏
奏起了一曲交响乐
六十年虽过
那美妙的音乐
时常在我耳畔
滴水成冰,寒风凛冽
拉沙工地上热热火火
挑担的你追我赶
拉车的相互超车
脱下了黄军装棉衣
摘下了老羊皮军帽
人人头上都冒着烟
个个心中有盆火
屯垦戍边靠的是苦干和实干
艰苦创业肯定要流血和流汗
金色的麦粒是汗珠的结晶
棉花叶脉里流着鲜红的血
这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六十年虽过
像一幅战天斗地的生动画面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悬挂着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荒漠
变成了绿洲
变成了粮仓
崛起了一座座崭新的城
“戈壁明珠”获联合国“人居环境改善最佳范例
迪拜奖”
这全是一群军垦人的血汗洒泼
铸剑为犁,屯垦戍边
要把荒漠戈壁变绿洲
张仲瀚风餐露宿天山南北
军垦农场星罗棋布
已在镇边将军的腹中定夺
两万山东女兵
八千湘女进疆
扎下了根
婴儿呱呱啼哭
才有了生生不息的兵团后代
河南六万姑娘小伙支边
加入了打头阵的军垦行列
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
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
这片大漠里
流了多少军垦人的血和汗
这最美的画卷
永远不会忘却
责任编辑蔡淼宁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