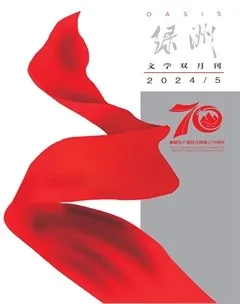矗立沙海的足迹
2024-10-02任茂谷
1949年12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五师十五团,奉命从阿克苏日夜兼程,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1953年,该部队30岁以下的官兵编入国防军,30岁及以上老兵就地转业,屯田生产。十五团三营发展为兵团农十四师四十七团,在沙漠腹地,屯垦戍边。第一代老兵扎根,第二代子女坚守,第三代,第四代……沙海变绿洲。这里的每一寸土地,融入了几代人的鲜血和汗水。
每一条小路,每一双脚印,几乎都有一个故事,我选取了三个故事,试图把沙海里的足迹连在一起呈现出来。
1949年的进军
1949年,黄诚和他的战友们,日夜兼程,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和田。这样的进军,在黄诚的记忆中,绝对不会被淡忘。
翻开四十七团简史,黄诚的名字出现在1949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编制,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蒋玉和任团长,龙炳初任政委,孟梅生任参谋长,黄诚任政治处主任。
井冈山时期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参加过五次反“围剿”,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编为一二〇师三五九旅。1938年,黄诚16岁,成为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的一名战士,挺进华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百团大战”,频繁战斗,屡建功勋。1940年,七一九团回师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完成了“南下北返”“中原突围”等重大作战任务。
1949年4月,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5月解放西安,7月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部主力4.3万余人,8月攻克兰州,马步芳部主力4万余人覆灭。9月24日,解放酒泉,兵临玉门关,挥师新疆。9月25日,新疆警备司令部通电起义。第一兵团急速进军,一路改编平暴,接收驻防。六军到北疆,二军去南疆,在进军新疆的行军序列中,十五团是二军五师的前卫,出兵玉门,千里戈壁徒步行军,历时48天,11月28日抵达南疆重镇阿克苏。
短短100余天,十五团在战斗中行程万里,进驻阿克苏,本该喘口气,进行必要的休整。
到达阿克苏的第二天,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来到十五团,下达指示:一定要迅速地进驻和田,制止反革命暴乱。
黄诚由政治部主任接任政委。军情紧急,历史的重任落到肩上,十五团刀锋未收再出发。
从阿克苏到和田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沿公路经喀什、莎车至和田;一条是由巴楚沿叶尔羌河到莎车,再到和田;还有一条是沿和田河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插和田。徒步行军,前两条路是大道,沿途有人有水,但要多走五六百里路,多用5-8天时间。敌人要暴乱,时间紧急,十五团兵分两路。团长蒋玉和率80人小分队乘汽车,经喀什快速赶往和田接防,像一把快刀,扎往敌人的心脏,为大部队进军争取时间。他们要面对的是国民党军警特务、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政委黄诚率1800人,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维吾尔语意为“进去出不来”。茫茫大漠,随时可能有吞噬生命的大风暴,或因缺水而干渴致命……这里自古以来是人类无法逾越的死亡禁地。
两条路都有无法预知的凶险,只要有一方不能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双方对接出现差错,后果将不堪设想。
读黄诚的回忆录,这次行军是一次对灵魂的洗礼。那时,人民解放军在胜利中前进,理想高于一切,藐视所有困难。
1949年的12月,1800人徒步进入沙漠,之前的万里进军,似乎只是这次进军的前奏与练兵。仅仅五天的准备,营、连、排、班层层动员,把这次进军看作解放新疆的最后一次“长征”。在阿克苏得到物资支援,群众送来骆驼300多峰,马和毛驴200多匹,大米、白面和马料十几万斤。有经验的当地青壮年拉骆驼、牵马、赶毛驴,为部队运送物资。
12月5日,军号响起,十五团向沙漠进军。官兵每人肩负一支步枪或机枪,加上弹药、铁锹、背包,负重数十斤,高唱战歌走过阿克苏广场。
12月7日,部队踏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中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每天凌晨三点出发,一个拉着一个。如果被什么绊倒了,站起来迷迷糊糊继续走。太阳像火球从沙漠里滚出来时,部队也活跃起来,讲笑话,拉歌子,一天平均走近100里。
沙漠行军,1800人的庞大队伍,包括向导和负责管理牲畜的群众,以及马匹、骆驼和驴子,水成为生存的关键要素。巨大的需求,靠驮带无法解决,只能就地寻找水源。行军到第七天,进入沙漠腹地,实在找不到水。炮兵连占到“便宜”,因为炮由马驮,每人只背一个背包,看到马要撒尿,拿盆子接上,每人可以分上一小口。步兵连的战士则不得不喝自己撒的尿。嘴唇干裂,渗出的血珠,舔入解渴……
这一天部队夜间三点出发,走了12个小时找不到一滴水。战士们一个个嘴唇干裂,渴得不敢张嘴。有的战士还得了怪病,身上起小黑疙瘩,皮肤发青,眼窝深陷,身体撑不住,有几个人晕倒,处境十分危险。黄诚带警卫员魏建立和向导阿不都大爷去找水。他让老人细细想,附近哪儿有过水,哪怕是苦水、咸水、臭水。老人记起附近有一个小水潭,到地方下马一看,原来在河床中间的积水潭,完全干了。阿不都沮丧地坐到地上埋怨自己。魏建立不死心,抓起小铁锹往下挖,黄诚帮着挖。谁知越挖沙土越干,越挖越没希望。
黄诚沉思了一会儿,知道自己不能泄气,翻身上马继续找,只要见到长草处,遇到干水坑,都要趴下身挖半天。黄昏时,大部队到了预定的宿营地,他们还在找水。突然发现远处有一小块地方明光闪闪,走近看到一个死水潭,上面结了薄冰。几个人欣喜若狂跳下马,阿不都大爷趴下尝了一口,全是腥臭味。正在绝望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堆烟火,黄诚想可能是侦察排发出的信号,赶上前去,得知打前站的战友找到了水。这一天,全团在进一步退半步的流沙中走了180里。
行军第十天,大风暴袭来。患有严重胃病的一营二连排长李明同志永远留在了大漠之中。
第十二天,部队走出沙漠的中心地带,到了有水的肖尔库勒。黄诚刚松一口气,一个衣冠不整,疲惫不堪的人被扶到跟前,一看是跟蒋团长先期到达和田的参谋陈跃俭,喘着粗气掏出团长的亲笔信。
大部队和沙漠搏斗之时,蒋团长与敌人面对面激烈地战斗着。伪副专员王肇智、专员安筱山等死硬分子,表面响应起义,背后几股势力妄图残害这支80人的小队伍,若事不成,则血洗和田,再逃往国外。
时间就是一切。路程还有400余里,黄诚把老乡支援的40匹驮马集中起来,组建了一个加强排,他亲自带队飞驰和田,目标定为一昼夜赶到。大部队同时急进,计划12月19日行军150里到达伊斯拉木阿瓦提,12月20日急行军250里赶到和田。
急!急!急!快一步是胜利,慢一步可能是失败。
加强排带上干粮,挂上冲锋枪,骑上有的缺鞍子、有的短嚼子、有的只在马背上搭条棉被的“赤兔(肚)马”,飞入黑沉沉的前方,一夜赶到伊斯拉木阿瓦提。稍事休息,吃点干粮,喂了一下马。还有250里路程,黄诚留下来迎接大部队,作战参谋高焕昌率加强排继续急进。
次日大部队到了,黄诚带一支小分队在加强排后面轻装挺进,当天赶到距和田30里的英艾日克。夜幕来临时,大部队也赶到相距不远的阿塔栏杆驻扎下来,以观动静。部队形成有序的战斗梯队,给敌人以压迫之势。
高焕昌率加强排先绕城跑了三圈,踏起滚滚黄尘,迷惑城里的敌人,让他们看不清到底有多少人马,然后威风凛凛进了城。
黄诚晚一天乘夜带三十人悄悄入城,与分手半个多月的蒋玉和会合。按预定的进军计划,不差分毫,圆满对接。
12月22日清晨,十五团官兵走出“死亡之海”后,浩浩荡荡开进和田。18个昼夜,1580里行军,古老的和田城,万民欢腾。
和田解放后,黄诚先后担任和田地委书记,和田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伊犁州党委书记等职务。1980年去世,年仅58岁。
母爱的极限
“戈壁母亲”有一双神奇的手,绿洲是她放大的手印,条田、林带、渠道是她的掌纹。戈壁母亲的手,是一双操持家务的手,也是一双开荒造田的手,靠着这双手,家里有了温馨和笑声,地里有了麦香和丰收,屯垦事业兴旺发达……骆驼一样的母亲,戈壁上留下足迹;耕牛一样的母亲,荒原上记下艰辛;大树一样的母亲,边陲上扎下深根。
翻开“戈壁母亲”张秀英的档案,一张张发黄发脆、规格不一的纸张,记下她的事迹。
我摘抄了1960年12月28日的一份档案。
(一)劳动事迹。春播,日点播花生5.3亩,定额为2亩,获春播特别能手。定苗时,她和男同志张敬喜、李瑞祥等劳动竞赛,5人小组每人日均5.7亩,她本人7.28亩,是全队第二名。中耕和夏收,主动参加只有男同志干的浇水工作,两天两夜,浇水130亩,提前一天完成任务。日割麦4.97亩,实现定额497%,获特等能手。秋收,拾棉花单日纪录330斤,获“一等跃进能手”称号,获挖花生优胜红旗两次。一年获得各项生产能手7次。
(二)领导青年突击队工作,一年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割青草积肥5万余斤,打沙枣1万斤,夏收时该队15人,人均日割麦2.97亩,获得场党委锦旗一面。她是青年中的先进人物,领先带头,认种卫星田0.7亩,收玉米508斤,额外种地头、地边、地梗合计17亩,增加收入。
(三)学习,她1958年是文盲,1960年达到高小程度,督促全班测验时都达到3分。
(四)她全年劳动日折效,累计完成劳动量按日均劳动定额折算为363%,有高工效能手证30多张。
我用一整天,读张秀英的先进材料。每年至少一份,个别年份有好几份。1956年被评选为“自治区劳模”,1957年立三等功,还被评选为妇女代表,1958年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奖章……2008年,兵团授予她“十大戈壁母亲”荣誉称号。
我心里发出阵阵惊叹,一位平常女性,用最简单的工具,一次次超越体力的极限,她是怎么做到的?她的身高、体重如何,脾气怎么样?性格怎么样?如何对待家庭和子女?那么多的超级能手证书,在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物质奖励,是什么力量日复一日支撑着她的内心呢?我从各种渠道探访她的信息。
张秀英1932年生于甘肃张掖,16岁与后勤骆驼队的军人黎嘉美结婚,1950年,进疆成为一名随军家属。1955年随丈夫转业到十四师四十七团,由家属转为农场职工。
张秀英单纯得像一泓泉水,领导让她做什么,她就快快去做,什么活都抢着干。一整天重体力劳动,晚上回到家胳膊疼,指头疼,拿酒精擦一擦,睡一觉,早晨起来继续干。她当过青年突击队长、排长、副连长。1980年退休,退休金59.36元。搬到干休所,大家选她当活动室主任,领导老太太、老头扭秧歌,编节目,锻炼身体,经常去和田市参加演出。
1997年,丈夫去世后,子女们劝她搬到条件较好的城市,她一次次拒绝了,她告诉孩子们:“这块土地和你们一样,都是我的孩子。我亲手把它带大,亲眼看着它成长变化,你们的父亲在这里,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
点点滴滴汇集在一起,张秀英给我的感觉,是一位亲切、谦和、特别能忍耐的平凡女性。这片曾经毫无生机的沙海,因为有像张秀英一样无数母亲的孕育,这片土地才焕发出新的生机。
我采访张秀英的子女,从他们那里寻找一位母亲超凡的力量。
第一个联系到在墨玉县工作的小儿子黎洪文,他和爱人胡筱雪来四十七团见我。黎洪文身材微胖,言谈间透出宠爱中长大的直率与单纯。
我问他母亲的身高。胡筱雪说自己一米五八,婆婆比她矮,应该有一米五六。他们翻出手机里“十大戈壁母亲”的合影。张秀英上身穿桃红色衬衫,胸口绣一朵乳白色的茉莉花,下身是一条白裤子。端庄的国字脸,一头灰白短发,略带微笑,满面和善,眼窝有些凹陷,看得出,她年轻时面容姣好。她站在前排,是“十大戈壁母亲”中身材最矮小的一位,与档案里记载的那些惊人的数字,怎么能画上等号呢?身材高大的不一定能顶天立地,可是如此瘦小的人,就算有一颗智慧的大脑,一双灵巧的双手,超人的体力从何而来?我心中的谜团没有解开,反而越来越大。
我问他母亲的工作、个性、对家庭的付出。黎洪文憨笑着回答,他是最小的孩子,小时候上托儿所,5岁上学。每周六接回家,周日送到学校,对母亲的印象就是忙。他从小穿得好,吃得好,自己什么都不用操心。胡筱雪说,和婆婆相处好多年,虽然是最小的儿媳,年龄小,身体却不好。婆婆照顾她,给她做饭,收拾房子,提醒她按时服药,特别细心。两个年轻人讲不出具体的事例。情急之下,拨通了大哥黎甘泉的电话。
黎甘泉的爱人是上海知青,退休后去了上海与孩子团聚。电话接通后,聊了几句,他用微信发来好多照片,还有一篇缅怀母亲的短文:
“……旧社会历经苦难的母亲,勇于挑战极限,常常与身经百战的老兵们较劲打擂台,一天翻3亩多地,一般男同志是2.5亩;打埂子定额150弓,她要打到300弓(一弓等于1.667米);推沙包一天30立方米。天天在地里干重体力活,十指伸不直,右手小拇指变形,去世时都是弯的。她在地里加班加点,怕下班晚了饿着我们,提前做些饼子,买些馍馍,放在家里的桌子上,我们回家就可以填肚子。从小到大,衣服都是妈妈做的,她心灵手巧动作快,卫生也特别好,做的饭样样可口。她经常告诫我们‘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道理,培养四个子女,各有所成。”
一位母亲勤劳节俭,心灵手巧,细心周到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第二天一早,黎甘泉的爱人又发来一段话:
“我是1966年支边的上海青年。婆婆对我像女儿,那年头布料紧张,没布票别想买到一寸。记得快过春节了,婆婆把全家的布票拿出来,买布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格子布中式罩衣,灰色卡其布裤子,特别好看,当时在团里是独一份。我穿着新衣服过年,外表时尚,心里感动。团场供应的口粮大米很少,婆婆考虑我是上海人,爱吃米饭,平时舍不得吃,省下等我们回家时,专门给我蒸一碗。我捧着饭,一滴滴眼泪流进碗里。我不会做针线活,婆婆手把手地教,直到学会为止……”
婆婆对儿媳掏心掏肺的爱,儿媳对婆婆刻骨铭心的感恩,让我感到亲情的泉水四处荡漾,在时空里静静流淌,仿佛有一双温暖的手,抚摸在我的肩上。
回到乌鲁木齐,我去拜访张秀英的次子黎珠江一家。他和爱人退休后,在乌鲁木齐和儿子住一起。黎珠江1954年生于皮山,爱人卜玉新生于陕西,1965年跟姨姨进疆,在四十七团四连当卫生员。
卜玉新说婆婆干活利落,做饭特别好。手指弯曲,还是左撇子,但揪面片特别快,又薄又匀,汤汆得清亮,特别香,吃了一碗想第二碗,饱了还想吃,经常吃到撑肚子。婆婆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办法,生活中处处显智慧。
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点着煤油灯做针线活,自己糊袼褙,给全家人做布鞋。20世纪70年代家里买了缝纫机,她就给全连队的人做衣服,身边经常是一大摞布料。后来缝纫机多起来,她还是帮别人裁剪衣服,做衣服样子。给孙子黎毅做的海魂衫,邻居看到都羡慕。
黎珠江说,妈妈给他做了一件皮大衣,羊皮里子,黄色卡其布面子,军大衣款式。穿到乌鲁木齐,卜玉新的姐夫见到很羡慕,回和田后,让妈妈又做了一件,给姐夫捎到乌鲁木齐。
卜玉新说,婆婆熬夜熬坏了眼睛,直到临走的前几年,嘴上说做不动了,还是给三个儿媳每人做了一件棉衣。她一直舍不得穿,留作纪念。
张秀英干地里的活,超出常人很多,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黎珠江的眼睛红了。他说妈妈是苦干加巧干,每天比别人去得早,回来晚,是多干好几个小时熬出来的。
任何事情都有极限。人有体力的极限,肌肉和骨骼磨损有极限,睡眠缺乏有极限……张秀英竟然超越很多的极限。我不明白,但只能承认,是母爱的极限,支撑起她的所有超越。她的聪明,她的忍耐,她的好强,她永无止境的爱,超越了人生平庸,实现了爱的极致。这样的爱,融化坚冰,化解强硬。柔弱的小草,可以顶起冰封的大地,生长出整个春天,张秀英则像一棵参天大树。
2014年7月,张秀英被查出肺癌晚期,黎珠江两口子陪她到乌鲁木齐、北戴河、海南旅游。她特别开心,没有在子女面前表现出痛苦。2015年3月回到和田,最后在和田地区医院去世,享年83岁。
笑声里闪烁的泪花
老兵镇的京昆小区,我敲开3号楼1单元301的门,见到72岁的钟明昌。
听说我来采访,站着就聊开了,还是我请他落座。两人各占茶几的一边,在沙发上坐成很近的夹角。目测他身高一米八以上,讲话声音很高。
他说着笑,笑着说,笑声里闪烁起莹莹泪花。大概是注意到了我对他嘴巴的疑惑。他说牙齿早就掉光了。我问他没有镶假牙吗?他说不用镶,习惯了,吃肉吃菜都不影响。说着自顾自“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他的笑声,像一些大小不一的石头,砸得我心里隐隐作痛。
钟明昌是沙海老兵钟高的次子,1959年,父亲把他和姐姐钟明英从贵州凤冈县接来四十七团,从此再没有回过老家。
他当时12岁,来到这里,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他从二年级上到六年级,17岁小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分到机修连,团里来了东方红拖拉机,他开了一台,犁地,拉东西,突突突来,突突突去。他的语气里充满自豪。
1966年,团里来了第一台推土机,他就开上了,真是威风。轰隆轰隆,黄尘滚滚,四十七团所有的沙包,都是他们动力组推平的,白天黑夜干,冬天不休息。机器不停人轮班,除非机器坏了要停下来修理。
他说,沙尘呛得咳嗽,开推土机时间长了又瞌睡,只有抽烟。刚开始越抽越咳,慢慢上了瘾。一天一包,两包,最后三包都不够。
他最喜欢劳动竞赛,经常是第一名。1976年生病了,气管炎,特别严重。调到轧花厂看动力,还管一连和二连的照明。1978年又回去开推土机。1986年,实在开不动了,转到机修队干修理工。最后调到电厂,在配电室当班长。2007年退休。
听他讲自己,像一条沙海里的掘地龙,开一台推土机,激起滚滚沙尘。轰轰隆隆,一块条田诞生了;轰轰隆隆,又一块条田诞生了。从机器上走下来,全身是土,眉毛挂满土,鼻孔淤满土,嘴巴里粘满土。不是土龙是什么?一天当土龙,天天当土龙,当了二十多年土龙,怎么可能不病?他的青春岁月,平展展地躺成一片绿洲,当然值得自豪。
他说,爸爸是木工班长,各个连队的工具,机关的办公桌椅,全是木工班八九个人做的,一年四季忙得不得了。木工班离团部几十米,团长政委和他关系好,经常叫去家里吃饭。团里人都喊他老钟高!老钟高!年年先进。他经常当先进,奖状贴一墙,不像现在得了奖会发东西。他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不在乎什么东西。
钟明昌的语气里,透着以父亲为傲。老钟高人好,领导待他好,所有人待他好,我想还有个原因,对一位勤勤恳恳的老兵,人们的尊敬里,也会有同情的成分吧。
我问他当初母亲为什么没有来?这个问题触动了他,讲话的声音低沉了许多。
1954年,公家发函去,让家属来新疆。因为路太远,她妈妈不敢走。1959年,爸爸回去接家属。大哥有两个小孩,嫂子身体不好,妈妈要管孙子,不能立即来,就接来了他和姐姐。
过两年妈妈身体也不好了,没几年就去世了。说到这里,他眼里泪花闪闪。
他说来到新疆,爸爸对他特好,但他想家。经常哭,偷偷地哭,不敢让爸爸知道。
从贵州遵义凤冈县来到四十七团,万里之遥,深居在沙海里的一个小点。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就算长大成家,遇到过多少事情,问过多少个“怎么办”,他说不清楚。我看过钟高的档案。
生于1911年,7岁放牛,11岁种地,15岁当木匠,20岁卖油,编筐子,25岁重做木活。36岁,做木工活的路上被抓壮丁,在军队搞后勤,给卫生队背箱子。当时全家12口,母亲、弟弟、妻子、五个子女、长子结婚有两个孩子。成分中农,有30亩地,房子三间,牛一头。
一个勤劳持家的手艺人,突然消失了。一大家子,老老少少,慌乱成了什么样子呢?他一步一步离家而去,心里是怎样的牵挂?战争局势快速转变,一个人裹在时代的洪流里,像一片树叶,一粒沙,命运根本不能自主。一年之间,他从大西南到了大西北。1948年10月,成了解放军的一员。从玉门关到阿克苏,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和田,成为英雄部队里的一位功臣。
1949年,他是三营部的炊事员。黄诚政委称NspHfF4cW7+OLCY1u6NTQA==“火头军”为“火车头”,他们走在行军序列前面。部队行军一天,到晚上宿营,要开水有开水,要洗脸水有洗脸水,洗过了就开饭,吃完饭就睡觉。炊事员刷锅洗碗收拾停当才能休息。第二天要比其他人早起,忙完一顿早饭,拆锅扒灶,路上的负担比别人重。晚上又要先到宿营地垒灶做饭烧水,提前做好一切。1800人成功穿越沙漠,炊事员应当记大功。
三营发展成了四十七团,成为驻守沙海,平暴维稳最牢固的一颗钉子。钟高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他是木工班长,其实是一位“将军”,一位统领工具的将军。在那个凭借体力与沙海肉搏,改造自然的时代,人们手上的工具是多么重要啊!木工和铁匠,是两路工具方面军的“司令员”,他们统领木与铁,让这两路工具的军队完美结合,交到战士手上,形成改造自然的战斗力。他带领一个班,把一棵失去生命的树变成大有作为的工具。
钟高67岁仍在工作,经常加班到深夜两三点,有时忙得饭都顾不上吃。1985年,74岁才离开木工班,1990年身患癌症去世。
钟明昌拿出爸爸的照片。有一张半蹲在地上,修一只胶质车轮,这张照片还保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的墙上。
钟明昌的妻子王青也是沙海老兵的第二代,1949年10月生于甘肃平凉,5岁进疆。父亲王积才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和田,转业成为团场职工,再没有离开过四十七团,在团里一直赶大车,1991年去世。
王青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她家兄弟姐妹七个,母亲是家属没工作,每到下半月,家里揭不开锅,到处借粮。一家九口人住一间芭子房,门口垒个炉灶做饭。那种房子,芦苇扎成把子,用木头穿在一起,糊上泥巴。房顶不结实,不能多糊泥,留下缝隙,刮风进土,下雨流泥。小虫子小动物是家里的“常住居民”。
钟明昌说,那种房子其实挺好的,就是容易着火。他家有一年过年正在做红烧肉,铁皮烟筒烧红,把房顶的苇把子烧着了。邻居们一起救火,拿水浇灭,房顶开个洞,找东西盖上。肉烧熟了照样吃。说到这里,他又笑起来。
2012年,他们住进京昆小区现在这套房子。84.5平方米,花了4.4万元。搬进了新楼房,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啥也不缺,啥也不少。
两个孩子,儿子老大,在和田地区电力公司工作,女儿在喀什工作,孩子们过年时回来一次。
他说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再老了,走不动了,就去敬老院。
他们从小离开家乡,在这一片新开拓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繁衍后代。父母留在这里,他们也留在这里,这片土地就有了根基。
责任编辑去影宁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