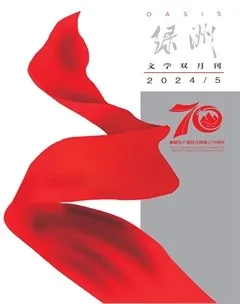峥嵘岁月
2024-10-02赵天益
岁月流韵
我们老家把乌鸦叫老鸹。我家后院墙外有一棵大槐树,每年春天都有三五对老鸹在树上育雏,叼来树枝筑窝,衔来食物喂雏,从天亮到天黑,看来很是辛苦。我们这些小孩子,每到天近黄昏,便数着它们一只只从野外归来,看它们滑翔着落到树枝上,心中就漾起暖暖的温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离开学校西出阳关闯天山,来到准噶尔大漠南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机耕农场开荒创业。荒地是一望无际的大苇湖,四处冒着水泡的沼泽地,一汪汪泉眼深不见底,一条条泉沟如蟒蛇一般在芦苇丛中蜿蜒穿流。
我们在青年垦荒连孙天恩连长带领下,选一处高阜扎营,搭芦苇棚,挖地窝子,建造最初的家。高阜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老榆树,合抱粗,参天高,树上有很多老鸹窝。听人说,这里是老鸹的世袭领地,谁也说不清它们在此生活了多少世代,繁衍了多少子孙,家族到底有多大。它们傍晚归巢的时候,嘎哇嘎哇的聒噪声能传出三五里。早晨张开翅膀飞去的时候,黑压压一大片,遮蔽半边天。老鸹住在树上,我们住在树下,互不侵犯,相安无事。我们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老鸹窝”,后来搞地名普查时,觉得此名不雅,便改为北泉镇,就是现在石河子总场场部所在。
我们青年垦荒连以老鸹窝为中心,挖渠排水,四向开荒,东到山丹湖,西到活海子,南到望月坪,北到泉水地。驻地一出门就是芦苇沼泽,浩浩渺渺,无边无际。住的“房子”是用苇把子拱起来的,上面盖一层厚泥遮风防雨;睡的“床”是用苇把子捆扎起来铺成的,上面再垫一层麦草;用的“桌子”是用苇把子搭建的,上面放一块木板。那时候干活,一日三餐都在野外吃,大家很少带碗筷,以苇叶为碗,苇茎当筷,几乎成了我们的习惯。夏天中午酷热难耐,我们割来一捆芦苇,搭起凉棚小憩。沼泽洼地蚊虫成灾,我们常被叮咬得满身疙瘩,又痒又疼。每到夜晚,我们便聚几堆芦苇燃起篝火,驱赶恶蚊。上下工往返于水坑湿地,我们侧身割一把苇子填垫其中,脚在上面一点便跳了过去……芦苇对于我们这些垦荒队员来说,如同布帛菽粟,不可缺少。
然而,芦苇之于我们,如顽敌在垒,势在必克。为了变沼泽为良田,必须消灭芦苇。我们按照农田水利规划,开挖大型排干渠,破坏芦苇的生存条件。在挖渠排水中,我看到芦苇的根系是那么发达,纵横交错,上下牵连,一层压一层,层层相叠。在一方泥土中能挖出12公斤左右的苇根,粗细相接长达五十多米。这并不是个别情况,而是全苇湖的普遍现象。我还看到苇湖表层的“草泥炭”,有一米多厚,重量却很轻,能在水中漂浮起来。对此我们感到非常奇怪,便去请教场部生产科刚从八一农学院毕业的农业技术员吴凤藻,他告诉我们:这是大自然的一种规律,是千百年来沼泽苇湖中的芦苇根生茎,茎护根,缠缠绕绕,自生自灭,腐茎败叶年深日久结积而成。它们一旦风化为土壤,能使农田的肥力倍增。
在开垦荒地时,拖拉机翻起白花花的苇根布满一地,我们就一根一根把它从泥土中拽出来,直勒得双手起泡渗血。我们班的“机灵鬼”李昌修,聪明好学,遇事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在开荒除草中他搞了个小试验,把一截鲜活的芦苇根摆放在田埂渠边上,风吹日晒半年之后,再埋进土里,第二年春天竟奇迹般发芽吐绿……就这样,为了生活,我们利用芦苇;为了开荒造田,我们消灭芦苇,消灭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生活。
那个时候,农场的道路还没有修通,交通十分不便。特别是化雪后的春天,运输常被积水阻断,食物运不进来,全连人被困在大苇湖里,断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一次,我们断粮三天,全靠野菜、芦芽苇根充饥。晚上有人爬树掏乌鸦蛋煮了吃,抓乌鸦用火烤了吃。乌鸦肉颜色乌黑,有一股焦胡味,不好吃。那时候肚子饿,吃起来不觉得,现在想起来都反胃。尽管如此,大家情绪却不低落,因为知道困难是暂时的,对生命构不成威胁。晚上,我们躺在苇棚里,头冲着门,饿着肚子欣赏徐徐升起的月亮。班长陈健说,月亮绿莹莹地从大苇湖里爬出来,像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的。我们知道,自断炊以来,他心情不太好,由于吃不饱肚子,班里开荒的功效上不去,影响劳动竞赛夺红旗。
我们连团支部书记周志斌是个文化人,有主意,有点子,是年轻人拥戴的“头儿”。有一天刚下夜班,已是上午八九点钟,他却独自坐在苇湖泉沟边发愣。我赶忙走过去想问个究竟,他却神秘兮兮地悄声对我说,他想抓几条鱼让大家尝尝,并示意我放轻脚步,不要弄出动静来。原来他在观看一对鲤鱼在浅水里游弋,鱼尾巴搅得水里的芦苇蒲草哗啦啦响。这时周志斌来了劲,麻利地脱下衣服,只穿一条短裤慢慢下到泉沟,手举着铁锹走到蒲草丛中,等待那两条鲤鱼的到来,并向我夸下海口说:“你先回去生起火,准备好调料,中午等着吃烤鲜鱼。”结果,他的诺言落空,那天中午不但没抓来鱼,他的脊背上却被蚊子叮咬得全是红疙瘩。
当天晚上,劳累一天的人们都进入梦乡,周志斌却坐在油灯下,脱下身上穿的背心,剪下新买来的袜子,又缝又补,在做捕鱼的工具,一直搞到下半夜才睡觉。天刚麻麻亮,他揪住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快起床,跟我到泉沟里取鱼去。我懵懵懂懂跟着他来到泉沟边,只见他下到水里,猛地用力拔起一截苇秆,苇秆上拴着一根细绳,牵起绳子后往外提出一个网兜来,竟有大半兜活蹦乱跳的金色鲤鱼。目睹此情此景,我高兴得拍手称绝,赞他赛过梁山泊智多星吴用。用自制“渔网”捕鱼的创举,在连队不胫而走,大家争相效仿,这不仅填饱了人们的肚子,还活跃了连队的气氛。
在沙漠变绿洲,苇湖变良田的过程中,我们与乌鸦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以致发展到我们必须驱逐它们、捕杀它们、消灭它们,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
我们在老鸹窝盖住房,砍伐老榆树作梁檩。新建的房屋红瓦粉墙,一片崭新,却不顾乌鸦们流离失所,没有栖身之地。它们啄食我们播入土壤中的种子,是严重的破坏行为。连长一声令下,第二天条田里便竖起一个个稻草人。稻草人身穿旧军装,头戴破草帽,手执长长的柳条秆子,秆头吊一只死乌鸦或一条旧布条。风一吹动,执秆的稻草人便不停地转动,惊吓得乌鸦们不敢贸然落脚,只好饥肠辘辘地飞离。
雪后的冬天,乌鸦们在野外觅不到食物充饥,便明目张胆地飞回村庄,袭击我们的粮场,暴食我们的苞谷、小麦。看场的老兵鸣锣驱赶,它们一轰而起,飞上树梢,锣声一停,转眼又落满场。饥饿使它们变得胆大妄为,不顾生死与看场老兵搞“拉锯战”,你进它退,你退它进。惹得老兵们咬牙切齿,按捺不住心中怒火,终于起了杀心。他们用“1059”农药拌上苞谷、小麦,制成毒饵诱杀它们。就这样,中毒的乌鸦一批批死亡。这个办法立竿见影,每次都取得胜利。
那年秋冬之交,我们农场发起一场消灭乌鸦运动。那场运动现在说起来滑稽可笑,而在当时却神圣得笃信无疑。当时备战正紧,经常传出这里有信号弹升空,那里有敌人电台“嘀嗒”作响,某地发现敌特踪迹……对敌斗争的弦上得紧紧的,紧得若再上一圈就会绷断。那时我在浇水班浇水,实行两班倒,白班夜班轮流上。秋末的一天,军代表在全连职工大会上讲,连队东北方向,玛纳斯河拐进荒原那一带,连日来,到太阳快要落山时,发现有降落伞出现,提醒大家提高警惕,遇到可疑的人和事要及时报告。会后,还特地将浇水班的人留下来,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现在大田里的高秆作物都砍倒了,空降的敌特分子白天隐蔽起来,晚上出来活动。上夜班的浇水班要特别注意,遇到坏人一要报告,二要奋力捉拿,就是牺牲也在所不惜,革命群众会记住你们的。”听他那口气,敌特分子一定会撞到我们铁锹的刃口上。
头天夜里,平安无事,第二天、第三天夜里一如既往,除了看到一只狐狸在月光下捕捉田鼠,连一个人影也未发现。第四天换成白班,异常情况发生了。那天我和班长在六号条田浇水,太阳快落山时,班长惊呼:“快看,降落伞……”不知是紧张,是激动,还是害怕,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遥远的东北方向,果然有一个黑伞状物体在飘忽下降。班长命令我紧紧盯住“降落伞”,他飞也似地跑回连队报告去了。
“降落伞”时而上升,时而下降,时而向东旋,时而向西旋,忽忽悠悠竟然旋到我的头顶上来。我看得千真万确,不由得大为惊诧,它根本不是什么降落伞,而是一群乌鸦在翻飞。这是乌鸦的习性,年年秋末如此。眼前这群乌鸦少说也有上千只,结群在空中盘旋,忽如乌云一片,忽如无柄大伞。这群该死的乌鸦真是胆大包天。我嘴上骂着,心里却在犯嘀咕,怎么办?如实告诉军代表,他会不会说我在涣散军心,消蚀斗志,麻痹群众思想,弄不好会遭到一顿批判,况且当下又无人作证。
那天晚上,附近的武装值班连队全部出动了,扑向玛纳斯河滩搜捕从“降落伞”上下来的“特务”。灌木丛、芦苇地,沟沟坎坎挨着查,排着找,自然是一无所获。军代表追问我降落伞到底落到什么地方?我思索再三,还是实话实说了,他一听愣了神,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又有人来报告说,他们也看到是一群乌鸦在飞旋,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从此之后,玛纳斯河滩再也没有闹过“降落伞”事件了。不久,连队传达上级一个通知,说乌鸦是头号害鸟,糟践粮食,祸害庄稼,是“备战备荒”的破坏力量,一定要彻底消灭它!
没有了老鸹,没有了老鸹窝,关于老鸹的故事,在这里再也不会发生了。
远方的团场
远方的团场,心爱的连队,在广袤无垠的准噶尔大漠南缘,是我永远怀念的第二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来自五湖四海的军垦战士,聚集在屯垦戍边大旗下,在生产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之地,化剑为犁,掘地为庐,开创史无前例的基业,创造出沙漠变绿洲,戈壁变良田,荒原建新城的人间奇迹。
远方的团场,禾苗覆盖大地,原野一望无际。地平线上,天山横空出世,雪峰在碧空下逶迤,防护林带折射出一抹淡淡的新绿。西边一群骏马奔驰流动,东边羊群里不时传出粗犷的吆喝声,受惊的鸟儿从林间飞出,在素缟上画出一幅鲜活的丹青。
团场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令我魂牵梦绕,牵挂于心。那是当年全团动员,人人参战,上山伐木,用土窑烧砖修建的大礼堂。在这里看电影只收一毛钱,《白毛女》《朝阳沟》连续放映十几场,场场爆满,挤破头抢买电影票的场景恍若昨天。礼堂左侧绿树丛中那座大木桥,横架在自然泉沟上的彩色栅栏,当时最为豪华,是团机关工作人员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也是一个景点,早早晚晚有许多人来此摄影留念。如今团部迁入新址大楼,这座桥也就很少有人走动。
建场初期我们用的大都是原始工具,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砍来杨树、柳树枝条编制筐子、背篓、抬把、耙地耱子、装粮食晒棉花的大笆。我们住的地窝子、干打垒、土块房的门窗,睡的床铺皆用柳条编织而成。团场人顺口溜说:“柳条子门,抬把子床,地窝子里娶新娘。”冬天备耕、备料、运肥、拉沙大会战,马拉人拖的爬犁上,固定的筐子也是树条编成。道路两旁红旗招展,田间地头人欢马叫,你追我赶,好不热闹。
连队排干渠马号旁的铁工班,苇棚下盘着一座铁匠炉,班长石老三带着班里几个兵,既管喂马放马,又要打制和修理全连的生产工具。每次从这里经过,老远就能听到铁锤敲击铁砧的叮当声。被熊熊炭火烧软的铁块,让他们摆弄得像炉膛里的烈焰,一会儿工夫,一把镰刀、铁锹、砍土曼或是一张锄头倏然成型出炉。
连部路北一块平坦的戈壁上,老军垦们丈量出长宽,向垂直方向掘进,待挖到一人多深时,根据住人多少,留出床铺,饭桌用的土墩,从侧面挖出一条斜坡作出入通道,再用树条编成大方笆,铺上芦苇麦草,略微拱起来,糊上一层厚厚草泥,顶端留一个方口装上玻璃当天窗,地窝子便大功告成。夏天三四十度三伏天的酷暑,却凉爽怡人。寒冬三九天滴水成冰,烧起少许柴禾温度能保持许久。如今高楼侧畔杂草丛生的地窝子已萎缩成一段历史,一种象征。
连队那口自流井,涓涓清流常年不断注入旁边的大洼坑里,形成一个涝坝,四周绿树成荫,是连队人聚会和游走的好去处。冬天湖面结冰,是个天然滑冰场,一群小孩在这里嬉闹,有穿冰鞋溜冰的,有坐在冰爬犁上用两根铁筋或木棍,如划桨般溜冰的。女职工和家属们拿了蔬菜或衣服来井边洗濯,手指冻得红萝卜似的。夕阳时分,暮归的羊群、牛群弥漫过来,翘着鼻翅尽情豪饮,直到肚子膨隆鼓胀,在牧工兄弟的口哨声中入圈进栏。
那时连队尚未通电,晚上黑黢黢,但每个宿舍里都有煤油灯的亮光。自制的袖珍煤油灯里冒着缕缕青烟,橘红色火焰微微跳动,为地窝子里带来一片光明。结束一天的劳动之后,连里还要点名讲评和政治学习,几盏罩子煤油灯高悬于大食堂的屋梁上,亮光闪烁,交相辉映。指导员读报讲时政要闻,连长评讲当天工作,布置明天任务,技术员进行农业技术讲座培训,文化教员领大家唱歌活动,我们的日子过得倒也充实有味儿。
我们连的电话机人称“摇把子”。一个乌黑油亮的方盒上架着一个弯月形话筒,方盒左边便是摇把子。一根硬邦邦的黑线,把两节“易拉罐”大小的电池与黑盒子连接在一起,通向团部总机。打电话时用右手握住摇把使劲摇几下,然后再拿起话筒向总机“喂,喂”一番,告诉他想要连线的对方,再由总机接线员帮你接通,才能与对方喊破嗓子似的说上话。电话机每连只有一部,还有专人管理登记,谁要想打电话,需连领导批条子,可金贵着呢!
龙泉渠畔那一行行苍老的沙枣树,看上去就像满脸皱纹的老者,拄着拐杖静静地站立着,默默注视眼前浸润自己血汗的条条农田。林带里的沙枣树绿荫下,是我们一伙年轻人休息天嬉戏的地方。在那物质奇缺的年代,甜甜的沙枣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甜蜜,这是大自然给军垦人的馈赠。在新疆,兵团团场是种植沙枣树最多的地方,它抗盐碱,阻风沙,不畏酷暑严寒,有着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像极了兵团这个坚强无畏的群体。
畜牧班的大胡子陈班长,领着班里几个年轻人,揣着几瓶烧酒和一盒方块糖,顺着渠道来到库尔别克毡房前。这位哈萨克族牧工夏天进山牧羊,冬天回到连队,看到老朋友,赶忙迎进毡房。当他们脱下鞋子在铺着花毡的炕上刚刚坐定,女主人便把馕和油炸馓子端上炕桌,不停地躬身给客人们斟满酥油奶茶。羊肉在锅里炖着,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诱人的香味从毡房的天窗溢出。酒足饭饱之后,库尔别克顺手操起冬不拉弹唱起来,虽然听不太懂歌词,但唱给人的感觉是辽阔草原上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的深厚友情。
每到春节前夕,连队便决定每班抽出一名年富力强的小伙子组成临时杂务班,由副业班长领着磨豆腐、生豆芽、做洋芋粉条,让人高兴的还有杀猪宰羊。芦苇搭起的作坊里热火朝天,忙里忙外的人们整日里汗流浃背。寒冬腊月的屠宰场上,热气腾腾,人声鼎沸,一群小孩子跑前跑后追赶着看热闹。鲜亮的猪肉、羊肉和头蹄杂碎,除留够职工食堂备用外,由司务长按人头分给职工和家属,让劳碌了一年的人们过个欢乐年。
入冬后大雪纷纷扬扬地下起来,黄昏时分终于渐止。万里晴空默默地注视着西部边陲这片开拓于大漠戈壁上的绿洲,注视着用忠诚和坚毅铸就的军垦群体。团场连队炉火通红的屋子里,其乐融融的兵团人坐在电视机前,欣赏着纷繁众多的节目,注视着普天之下的大事要闻。
雪落大地
那些年农场人过冬天,看什么摸什么都是冰冷的,唯有看雪摸雪是温暖的,绒绒的雪花用手一碰就化。农场人看雪是棉被,能盖住土地不挨冻。所以,农场人过冬特别盼望下雪,盼望给寒冷的大地盖一床棉被,不要冻坏大地上的生命,尤其是那纤细的麦苗。
最知时节的雪是及时雪,及时下在“三秋”以后,土地尚未封冻之前。没风没火的日子,神不知鬼不觉的夜里下了一场雪,第二天早晨推门一看,白茫茫一片,把大地覆盖得严严实实。
其实,每年的初雪都是有征兆的,而且是多兆同现。首先是撒野了整个夏秋的麻雀,提前半天飞回家,先在屋檐下、草垛上、墙洞里找好栖身的地方,然后贪婪地觅食。它们成群结队地绕着连队、村庄转,群起群落,不肯离开场院、道路、房前屋后的空地,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将嗉子填得鼓鼓的,那些按时进窝的老公鸡老母鸡,迟迟不肯进窝,咯咯咯地围着主人要粮食吃,或挤在草地、墙角逮虫子吃。还有我们人,夜里睡觉热了蹬被子,暖洋洋到天亮不觉得冷。早晨一开门,啊,铺天盖地下了一场大雪,不免自言自语地说:“怪不得夜里有些热,下雪不冷化雪冷嘛!”
下雪有下雪的事情要做。不一会儿,就听值日排长“嘟嘟”吹哨子,接着喊:“各班起床以后扫雪,扫完雪休息。”休息,真是个好消息!很快,呼呼啦啦的扫雪声,响遍连队的旮旮旯旯。
要是哪一年雪少,下雪小或者下雪晚,全连的人都会着急。连长带头发愁:“这天气是怎么了?咋还不下雪,再不下雪冬麦要冻死了。”男女老少都盼雪,一天朝天上看好多遍,看雪在哪儿。从理智盼到不理智,开始看着风向盼,瞧着云彩盼,眺着早霞盼,盯着晚霞盼。盼不来,就异想天开地说:“要是有那么一天,天随人愿,要雪即雪,要雨即雨,该多好啊!”
记得那年冬天,我去参加农场召开的一个生产会议,到会的全是营长连长,他们都是抓生产的行家里手,齐聚一堂,十分活跃。室内献计献策,室外大雪纷飞。主持会议的老场长显出从未有过的高兴,指着窗外的大雪说:“瑞雪兆丰年,今年天时有了,就看我们人的了。”
天上的飞雪,老场长的神采,与会人们的精气神,一时激起我的灵感,即兴写了一首小诗,其中几句是:
山白,岭白,田野白,
雪花漫天撒,
老场长伸手接一把,
闻一闻,舔一舔,
啊,面包味儿真够大,
笑令天公:下,下,下。
小诗共五节,先是刊登在师部的报纸上,后又发表在一家杂志上。有位读者看后说这首诗描绘了一幅瑞雪图,是农场备耕的泼墨画。
那年冬天雪少。田间麦苗裸露,面临冻旱,有大面积死亡的可能。我们农场的无霜期短,庄稼一年只能种一季。一季麦子半年粮,麦苗冻死了,来年吃什么?事关生计大事,人们盼雪的心情又焦灼起来。期望着天上早下雪,下大雪。人们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听广播,打开入户的小喇叭,听气象预报有没有雪。
真没料到,那年的12月5日下午,在天气预报称无雪的情况下,竟然纷纷扬扬下起了雪,大片大片的雪花撒向原野,落进村庄,不到半天时间,地上的雪已积了十来公分厚。大家聚在屋檐下欣赏雪,议论雪。心细的人觉得有点蹊跷,说这雪是从哪里来的,下雪怎么还伴有雷声?心粗的人想事简单,说话直接:“这还用问,雪是天上下的,雷是天上打的,这叫‘冻雷’。”这些都是雪里的闲话,怎么说都无所谓,谁也不当回事儿,嘴上快活就行。
第二天雪霁日出,我到场部办事遇见人武部的丁部长,说他要到各连队去调查雪情。我有些纳闷,便跟丁部长说,以往这项业务都是农业生产部门办的,怎么这次你也干上调查雪情的事呢?丁部长笑着对我说,你们说的冬天打雷,那是我们民兵值班连打的炮,这场雪是我们迫降的,叫人工影响天气。这项作业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人武部负有跟踪调查的责任。他还告诉我,昨天下午到夜间,值班连用“三七”高炮和土火箭,发射碘化银降雪弹1930多枚,才把这场雪打落下来。人工降雪是一项“系统工程”,气象、人控、电讯、驻地解放军一齐出动,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打火箭炮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几天以后,师部报上发表一条消息说,这次人工降雪效果显著,可保全垦区60多万亩小麦安全越冬。消息十分喜人,种田人多年的美丽梦想,开始变成了现实。
远去的赶车人
1955年秋天,我随河南建设边疆学生大队来到兵团,我被分配到农八师机耕农场(今石河子总场)四连,指导员郭锡庚把运输班长周大龙叫到连部介绍说,这是新来的赵天益同志,连里决定把他交给你们班,他是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娃娃,由你亲自带他进行劳动锻炼,这是政治任务。从此我便跟着周班长干活。
周大龙班长是军垦老兵,甘肃陇东人,大高个子,浓眉大眼,体魄健硕,一身犍子肉,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待人亲切和善,赶车上路时总爱吼两嗓子秦腔,是全连叫得响的马车驭手。运输班有七八辆大车,多是牛拉木轮车,班长赶的是一辆“槽子车”。这种马车与后来农场的两个胶皮轱辘马车完全不同,有四个木质轮子并镶了铁箍。在几十年前那个开荒建场的艰苦岁月里,从师部所在地的石河子到场部,再由场部到连队的开荒点上,所有粮食、种子、油盐一应生活生产物资的运输,全靠这辆槽子车。
我们四连位于玛纳斯河西岸一个叫沙梁子的荒原上,春天风大碱更大,白花花的盐碱滩,风起一片灰蒙fUwGuy90o5uMGgVdhM/aYKBWc6O7Ydc+c5if4mRFVA0=蒙。赶车的周班长嘴唇裂着许多小口子,不断有血珠儿挂在上面。夏天的荒漠戈壁上,石头能晒得裂开缝,他渴得嗓子眼里冒青烟时,只能在半路苇湖滩的泉眼里喝上一肚子水,啃上几口窝窝头。隆冬季节,风雪弥漫的荒野里,他的马车与风雪融为一体,只有鞭梢上的红绳绳给茫茫雪原凭添一点儿生气。
在那些年月里,周班长和他的马车究竟拉运了多少物资,为那些远在戈壁大漠里开荒造田的人们捎带办了多少好事,谁都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从未想过这些,他只把酸甜苦辣全部倾注在他心爱的马车和那两匹老马上。他的槽子车常洗刷得纤尘不染。他长年累月辛苦奔波,人活得很实在,很踏实,他带领的运输班年年都被评为先进班组。记忆中每晚全连职工点名讲评大会上,赵文德连长总是表扬周班长,说他是从不歇脚的革命老黄牛,号召全连职工向他学习。
当我离开家乡来到军垦农场即将接受第一个寒冬考验的前夕,全班人都从周班长那里领到一双毛茸茸、沉甸甸、似靴非靴的物件。看到我目光中有些困惑,老班长用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这叫毡筒,是个宝贝,在新疆过冬没它不行。”毡筒!我的脑海里第一次有了它的印象。
那年冬天,周班长带我赶着槽子车,到离连队三四十公里外的北沙窝拉运柴火,农场职工取暖要烧柴,食堂做饭要烧柴。那时气候比现在恶劣得多,冬日里北风呼啸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滴水成冰,赶车到戈壁滩上拉运红柳、梭梭柴是常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周班长用没有挂面儿的羊皮大衣紧紧裹着身子,尖顶大皮帽子放下两个大耳片儿,只剩下鼻子和眼睛在外,穿着毡筒的两条长腿,随着车子的颠簸而不停地摆动。天气酷冷,他呼出的热气在眉毛、胡子和皮帽子上结成了冰霜,他却不声不响地大口吸着又粗又长的莫合烟。
临出发前,班长招呼我一定穿上毡筒。我嫌它又笨又重,沉甸甸地穿着不便走路,仍然穿着从老家带来的棉鞋。没有多久,我没穿毡筒的左脚脚底板冰凉透心,从脚趾尖到脚跟像虫爬似的难受,后来慢慢不疼了,没有知觉了。而我的右脚又开始钻心地疼,我一时忍耐不住便低声呻吟起来。
“咋啦?小伙子!”周班长忙掐灭莫合烟问我。我说脚冻了,疼得厉害。他立马从车前挪过身来,一摸我的脚,“啊”一声说,我看你小子是存心不打算要这两只脚了,这么冷的天为啥不穿毡筒?
槽子车在雪地里戛然而停。周班长麻利地脱掉我双脚上的棉鞋,把我的左脚塞进他的皮大衣里,并使劲地揉搓起来。这是一双父兄一般的肥厚大手,我的左脚慢慢有了知觉。这时,周班长用力脱下他双脚上的毡筒,把我两只脚塞进去。而我那双薄棉鞋则紧紧巴巴地套在他的脚上。
我平生第一次穿上曾不愿穿的毡筒。当我的双脚穿进毡筒的那一瞬间,一股暖流沿着裤腿升腾上来。随之冻得僵硬的肌肤在暖融融的热流中渐渐舒展开来,血液在周身缓缓流动起来,厚厚的毡筒阻隔了刺骨的寒流。自此,在农场的那些日子里,这双毡筒一直陪伴着我。
也就因为这一次,我可亲可敬的周大龙班长,由于我的过失,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两个脚指头。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老班长在那个彻骨的寒冬里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着刀割似的疼痛,他与我有着同样的血和肉啊!第二年秋收之后,我被调到厂部政治处组织股工作,老班长赶着那辆槽子车依依不舍地送我到场部报到。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如今毡筒已不多见,早已走进历史。我与毡筒有缘,与早已不在人世的老班长更有缘,是他和他的毡筒在我人生起步的节点上,给我启迪与力量,大漠雪原上那深深的毡筒印迹,成了我终生怀念。
责任编辑蔡淼宁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