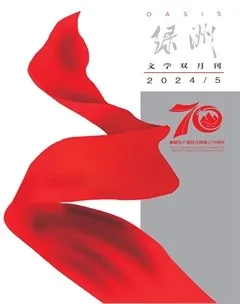此情棉棉无绝期
2024-10-02丰收
“你老家在哪儿?”在我生活过的农场、居住的边地小城石河子。在新疆,这是一个经常会被别人问到,我也经常会问别人的问题。当有人问我时,我的眼前就有了那片大得望也望不到边的棉花地……
我顺着垄沟寻找地里摘棉花的母亲。听着棉荚催熟的开裂声响,远远望见扎着头巾,拖着棉花包往地边棉堆走的母亲。快要跑到母亲身边时,母亲直起腰招呼我,“来,帮帮妈……”把花兜里白花花的棉花倾倒在棉堆上,母亲说,“多好的花呀……”笑脸也像一朵开裂的棉花。母亲打着补丁的布衫汗碱结成了壳,已经潲成灰色的蓝头巾和露在头巾外的头发上,粘满了白绒绒的飞花,皴裂的双手缠满了胶布。
望不到边的棉花地在天山北坡、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地名“莫索湾”界域。已有四、五辈先人埋在沙土下的当地百姓习惯把这地儿叫“西营城”。19世纪70年代,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新疆。新疆各族百姓自发组织民团,屯田筑城,练兵保家。光绪元年,左宗棠舆榇亲征,以摧枯拉朽之势驱逐阿古柏,收复南北疆。天山北坡留下了西营城、野马城、马桥子城这些个历史记忆。父亲告诉我,他们开发莫索湾时,梭梭红柳萋萋荒草下,前人耕种的垄沟渠埂还看得清楚。少先队过夏令营,在西营城废墟挖岀了一筐筐铜钱,还有高脚铜灯台。铜钱、高脚灯台结满了绿色铜锈。前人种熟的土地成全了不怕辛劳吃苦的父母,当年播种,麦子、苞米、棉花大丰收。眼见着大“解放”装满一麻包一麻包粮食、棉花,一辆接一辆排着队从南干渠六号遇水叠桥,一路往东。母亲说,运去口里救命。外运的麦子、苞米、棉花一年比一年多,梭梭林子、红柳林子一年比一年小。冬天打荒,一堆一堆梭梭、红柳烧红了夜空,也烧疼了我们小小的心。长满琵琶柴、铃铛刺、骆驼刺、风滚草的梭梭、红柳林子是我们玩耍的天堂。风滚草是我们逮蚂蚱的帮手,窜来窜去的小沙蜥是我们的玩伴。梭梭枝条隐隐一抹绿色,把春天的信息最早带给我们。母亲让我仔细看看梭梭树,母亲说,为了减少水分蒸发,梭梭舞动的叶片退化成了细细的枝条,梭梭树半边迎风的身子总是伤痕累累,那是长年累月抗击风沙留下的伤疤。直面风沙的梭梭树,护卫着棉花地、苞米地,一树花也开得明艳亮丽,红色花蕊夹有淡淡杏黄,黄色花蕊夹有娇柔水红,一树树梭梭花点染得戈壁荒漠几多生机!母亲说,梭梭花是沙漠的花仙子。
梭梭开花,播种棉花,种了棉花种苞米和甜菜。忙过春播,母亲和左邻右舍的阿姨抓住夏管前一小段时间,打理一家人的吃穿用度。新疆夏天的夜有月亮的时候多,明月出天山。太阳还挂在半空里呢,月亮就急急地爬了上来,眼对眼,这是别的地儿很难见到的景观。我们喜欢月亮地,常听母亲说,“今儿的月亮长眼!”母亲和阿姨们借着明晃晃的月光,把从不长庄稼的碱滩盐泡子挑回的盐碱土,倒进一个装在柳条筐的草袋子里,一遍遍水淋,隔一夜,淋到桶里的水澄清了,用淋岀的盐水炒萝卜白菜,饭菜有了添香的咸味儿。
到西营城之前,我随父母离开了迪化城(那时候乌鲁木齐还叫迪化)。扬子江路的家搬到了一个大苇湖边上的小李庄。
小李庄是进疆部队最早的屯田点,方圆数百里,只有一户李姓人家,得名“小李庄”。“七七事变”时只有16岁的父亲与三位风华正茂的同学投笔从戎。父亲枪林弹雨一路西行,耿介拔俗顶撞部长,从新疆军区运输部发配到新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修渠引水开荒造田。自此,父亲就在沙漠与绿洲的拉锯战中摸爬滚打,终老一生。
童年的记忆里总是在搬家。戈壁滩种出麦子、棉花,苹果树开花坐果,又该搬家了,去另一处戈壁荒滩引水开荒种树种庄稼。一座小城刚有了点儿城的身姿容颜,又去一处沙漠边开基始祖建新城。父亲母亲是绿洲的拓荒者,也是精神漂泊者。时代变迁社会动荡的大潮中,一个人的命运如一柄飘零的落叶。豫东夏邑县会亭集小酆庄始终是父亲意念中叶落归根之所。离老家一个甲子,耄耋之年的老父亲执意回老家要在老宅废墟上盖房。那些个炉火相伴的冬日寒夜,母亲心念着娘家屋后的杏树行子,窗下纺车。我读初二时,眼见母亲俯身抱着姥姥寄来的自己织的大白布,泪流满面。
无论怎样地游牧新疆大地,也走不出胡杨、白杨护卫着的农田绿洲。
只要绿洲在,生活就会继续。绿洲于我,已不是瀚海背景下的地理存在,它已是根深蒂固的具象指认:小李庄、西营城、宿星滩。是那片大得望也望不到边的棉花地。
《乌苏县志》有记:“乌苏城北百六十里,宿星滩。”乌苏,新疆名城,天山北坡连东西贯南北的战略重镇。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登临乌苏城楼北眺,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边缘屯田点呈二十八星宿排列,得名“宿星滩”。说是左宗棠西征时所为,先人天眼。星移斗转,荒僻边远的宿星滩渐渐隐没岁月深处。20世纪50年代初,又一队军人踏进这片西陲边地时,二十八星宿排列的屯田点苍凉得只在日光里依稀可辨。我下乡时,这里却叫了“苏兴滩”。许是寄寓“复苏”“振兴”的时代热情,或是谐音渐变随了世风。宿星滩,原始方式拓植出一片片绿洲的,大多是走了西口的移民。尤以河南、甘肃人多。地方苦,沙梁后面还是沙梁,碱滩地连着碱滩地。来这儿的人也都住了下来,男婚女嫁地有了小子闺女,落地生根。相比小李庄、西营城,在宿星滩的十年我对绿洲农场有了魂灵通透的血脉之亲。一泡尿从东头流到西头的场部官道,官道右边“猪肉西施”掌门的肉铺子;转过街角的门市是宿星滩的热闹处,回头率超高的售货员“白妮”,1956年从河南小禹州支边进疆,知书达礼,祖上的荫泽;胡杨、梭梭、红柳装点的“森林公园”,宣传科跑腿的小春子拉弦子唱小曲,他喜剧开锣悲腔收场的男欢女爱把宿星滩的青春男女搅得转转了好些年;农场西北角那处一到阳春三月就是骚哄哄的配种站,自然而然成了农场青年荷尔蒙催萌性启蒙的田野课堂……古往今来,商贾行旅,走西口的汉子婆姨,讨活命的“盲流”“劳改”,哪一个开口不是一部人世传奇?如一粒随风而去或是借水而动的种子,上承霜气,下接地气,就那么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就那么“湖南庄子”“河南庄子”“六户地”“十户滩”地繁衍蓬勃开来,五湖四海,南腔北调,混血的绿洲大地化育青春,不经意间的耳闻目睹,春天升腾的地气,冬日蕴藏的热流,经久不衰地记忆,在那么一个时日突然就鬼使神差地从库存的某个角落蹦跶出来……
2007年春节前夕,我从北京赶往广州。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高峰相邀,为纪念王震将军百年诞辰的纪录片撰写文本,借春节将军亲属齐聚深圳,访谈将军生平,多些感性体验。
落地羊城,分明感觉广州已经装裹在喜洋洋的节庆里。
广东人无论家境如何,春节都会置办花木,装点门庭宅院。“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庭、宅兰桂齐芳,花开富贵,寄寓对来年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花木千种,象征财富火旺的金橘必不可少。
广东人对春节的重视,还强烈地表现在合家团圆,尽享天伦,远在天涯也要千里万里赶除夕的年夜饭。
广州文友问我,大老远春节跑广州写王震?你和他什么关系?再大的事也要十五过后再去做嘛!
每当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都禁不住向西北望,望我们的天山,心儿已飞回那方辽阔的疆域。
我没见过王震。他离开新疆那年,我还不满两岁。对他我却不陌生,他人生的一部分已融入新疆大地,而我长于斯,至今还厮守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我们在新疆长大的兵团第二代,对王震的感情很复杂。
不少“口里人”眼里,这片疆域边远、蛮荒。
我们原本也是“口里人”。因为王震,我们成了“口外”的新疆人,他和我们的关系千丝万缕。
因为他,我们的父亲到了新疆。父辈眼里,他是号令三军、说一不二的统帅,是老旅长、司令员。是他率领着我们的父辈突破“北纬44度不种棉”植棉禁区,建设了关系国家棉花战略安全的优质棉生产基地;是他身先士卒立军令状,与陶峙岳将军,与张仲瀚、陶晋初,与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教授各司其责,2万亩棉花地亩产201公斤,创全国棉花单产最高纪录;是他1951年就从苏联引进单行采棉机……因为他,我们的母亲远嫁塞外……因为他,天山南北有了收获棉花的土地,也有了喝天山雪水长大的我们。无论我们认为这公平还是不公平,我们已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
荒原变绿洲的漫长过程中,父亲渐渐衰老,母亲也无可奈何地失去了青春。他们对故乡的记忆,己渐渐变得模糊和抽象,而新疆的家业却更为具体和牵挂。他们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此生此世他们无法离开新疆,也渐渐被家乡的亲人淡忘……
只有在岀了大事的日子里,他们才又被记起。上世纪闹饥荒的年月,一车皮一车皮麦子、苞米东行入关救灾;1962年中苏西部边境爆发震惊世界的边民叛逃事件,没有领章帽徽的兵团战士在几千公里的中苏边境打下水泥桩,拉起铁丝网;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兵团”开着一辆辆老“解放”打头,第一个把弹药、给养送上喀喇昆仑神仙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公民很难知道发生在这个特殊区域内的事情。这些事儿,大都和“国家”“民族”有关联。
说到这里,我可以告诉朋友们:这就是王震和我们的关系。
篝火很遥远了……篝火并不遥远。
庄稼绿了黄,黄了绿,开都河畔哈拉毛墩坎土曼挖出的万亩土地收获了几季庄稼后,第一犁掌犁人谢高忠率队挺进塔里木,夜宿乌鲁克荒原。篝火冲散了南疆春夜的寒气,如水的月光下,谢高忠问战士们,“我们去塔里木干什么?”战士们七嘴八舌,这还用问吗?开荒种地。谢高忠说:“不对!我们去建设白银王国!”三五九旅的老兵、南泥湾大生产的劳动英雄谢高忠告诉战士们,他们的传奇师长张仲瀚告诉他,乌兹别克是苏联的棉花种植基地,号称苏联的“白银王国”。“我们要开发的塔里木,和乌兹别克在同一纬度,无霜期长,日照时间长,水土资源丰富,我们要在塔里木建设中国的‘白银王国’!”
战士们知道,国家急等着用棉花,棉花是纺织工业的原料。上海、青岛的棉纺厂因为没有棉花停产了。医疗、化工、国防领域,棉花也有它的不可替代性。北疆的战友们已经突破了“北纬44度不种棉”的植棉禁区,日照长、积温高、水土资源得天独厚的南疆也定能建设起来我们的“白银王国”!那一夜,明月下的篝火与战士们的激情一起燃烧!
她靠在那棵最大的胡杨树下,静静地离去了,好似睡着了一样。一片又一片金黄的叶片飘落枝头,陪伴着她。
“我也是王震招来的兵啊,他是我的湖南老乡,他是浏阳北盛乡跪马桥的。”1951年3月15日,她是忘不了的,这是她参军进疆的日子。她家屋后不远处有一片胡杨林子,林子边,她开辟了小小一片菜园。从湖南老家到了天山南边地名“吾瓦”的兵团农场,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棉花地、棉花苗、棉花,和棉花缠磨了一辈子。从1984年起,就没人要求让她再去厮守了一辈子的棉花地,她却还是一年年奔地里的苦营生。春天定苗夏天打顶秋天拾花。她有自己的目标:一季最少拾250公斤棉花。腰,还有腿,都不像以前那么听从她的指令了,只好带着一个小马扎坐着摘。今年她已经摘了251公斤,一朵一朵揪。一朵棉花4—5克重,251公斤要揪多少朵?她今年的目标是要揪回来500公斤的……她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她甚至走不回家了……最后,还是当年栽种的胡杨送她远行。
我们应该记住她的名字:湖南参军进疆女兵陈淑惠。
一个不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的普通农工张斗兰,却留下了永载兵团史册的纪录:她种植的21.3亩棉花地亩产皮棉200.9公斤,创造了陆地棉单产全国纪录。张斗兰的棉花,距吉尼斯世界纪录仅差5.1公斤,而吉尼斯纪录是在3亩——不到张斗兰栽种面积七分之一的地块上创造的。
金秋收获季节,中国棉花学会11位专家专程来到张斗兰的棉田。青枝绿叶白絮,从条田这头到那头,齐整整一片,专家们喜形于色地赞叹:“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棉花!”团长对张斗兰说,这都是中国搞棉花的权威。权威是和常人不一样些,观察棉花好仔细!地边边看一阵,地中间看一阵,一棵一棵地数,结了多少桃子,开了多少朵花。看完了,数过了,有人就说,这棉花单产要上200公斤!来的权威都很兴奋。一个头发白了的老头紧紧握住张斗兰的手,很激动地说,我搞了一辈子棉花,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棉花。这个白发老头是中国棉花学会会长。会长向张斗兰要了一株棉花,这株棉花结了38个棉桃,全都开得白白的。会长拔这株棉花时十分小心,38朵花一朵一朵用纸袋套好,包扎好,然后又把一整株包起来。这时,张斗兰已经对会长有了些好感,这人侍弄棉花比我还仔细些呢。
听着专家们的赞叹,张斗兰禁不住流泪了。女人的眼泪包含太多内容,冬去春来,日出日落,压碱播种,治虫收获……一双茧花叠着茧花、血口压着血口的手,记录了多少农人的艰辛和创造。
陈顺礼先生有“中国长绒棉之父”誉称。
1953年春天,在春播地里,陈顺礼收到王震将军邮寄的一包长绒棉棉种“莱特福阿金”,自此,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的陈顺礼再没离开过阳光灿烂的塔里木盆地,一辈子从事一项工作:长绒棉育种。
1950年初春,陈顺礼已经完成了毕业论文,再有一个多月就要毕业典礼了,“王震招兵”的消息传到了学校,陈顺礼从学校赶到长沙,报名参军,跟随王震将军到了塔里木。如果他不参军,如果他不学农,王震将军的长绒棉种就到不了他手里,他去哪里当“长绒棉之父”。这些个“如果”,是陈顺礼的老伴马环日后说的。
国家急需长绒棉,交通运输、机械制造、军事工业……长绒棉是特种原料。国家同时在海南岛、云南、新疆试种。学名“海岛棉”,故乡在非洲尼罗河流域的长绒棉偏偏选中了远离大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种植长绒棉,中国没有现成的路走,只有大田选育一条道,一块条田500亩,一株一株寻找那些变异株。大千世界物事一理,自然界里棉花和人一样,总有长得高大英俊、智商又高的人。陈顺礼就是在棉花地里寻找那些天赋灵气的变异株。再播下这些变异株的种子,开始新一轮选拔。这是大海捞针式的苦活,风风雨雨,烈日酷暑,几个玉米面发糕一壶水就是陈顺礼的一天。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陈顺礼选育出5000多株母本!
1959年,中国有了长绒棉“胜利一号”品系,单产比引种品种提高了一倍,霜前花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迪托夫教授告诉王震:“司令员朋友,我要向你祝贺,我已经看到了中国长绒棉的希望。”
1965年,中国有了长绒棉“军海一号”品系,成为中国长绒棉推广面积最大的主栽品种。于是在长绒棉种植业界就有了“埃及尼罗河,中国塔里木”的说法。
陈顺礼前辈的老伴马环告诉我,陈顺礼去世前,夜晚常常梦里哭醒,马环和女儿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马环白天看护,女儿夜晚看护。陈顺礼是夜里辞世的,弥留之际,陈顺礼泪流满面对女儿说,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她奶奶。他是小儿子,湖南人叫满伢子,母亲最疼爱这个小儿子,父亲去世早,寡母带大他太不容易。为了棉花,陈顺礼没有探过一次亲,老母亲过世正是棉花播种,没有回去……等了一年又一年,等自己也老了,病了,想起了老母亲……能安慰陈顺礼的,只有他的长绒棉。
兵团棉花大面积丰收,采摘成为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瓶颈。自20世纪80年代始,每当霜重秋浓时节,成千上万河南、山东、甘肃……的“棉客”,就像候鸟一样奔向天山南北。乌鲁木齐火车站人潮滚滚,东来的列车几乎趟趟满员,都是乘专列来新疆拾棉花的大闺女小媳妇。
棉花机械采收不亚于一次农业革命,从选育适采品种开始,规范栽培模式,后期加工配套成龙……系统工程;机械采收对棉花品种的衣分、纤维强度、抗病抗旱性能要求更高,甚至对棉株株型也有要求。最好的采棉机美国制造,人家不会为了我们的种植模式改变机械设计,只有我们的品种、栽培模式适应成熟定型的采收机械。为了推动兵团棉花机械采收,时任兵团党委书记、政委郭刚连续三年国庆假期前往七师车排子垦区、八师莫索湾垦区、十师夏孜盖垦区棉田实地调研。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机采棉不只是解决了一个拾花劳力的问题,降低生产成本的问题,它解放了人。拾过棉花的都知道,那是软绵绵的强劳动,机采棉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
机械采棉,促进了新疆不亚于地膜种植的又一栽培技术革命——节水灌溉,只有滴灌能够满足采棉机无埂无渠的工作要求。
1994年,又一个霜重花浓的收获季节,谢高忠前辈邀我去塔里木。棉花地头、胡杨树下,老人家话说当年。明月,篝火,老兵们“白银王国”的憧憬,如今已是现实。兵团棉花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水准雄居中国第一。新疆已经发展成为关系国家棉花战略安全的优质棉花生产基地。
“想一想啊,这些个事儿好像就是昨天……一眨眼,三代人了……”前辈的话让我心生凄然,是啊,人生苦短……
翻过年,春夏交替的5月17日,敬爱的谢高忠前辈仙逝……老人家魂归天山,没有回山西崞县老家。
1993年4月4日,中国这片最大的疆域,多少双眼睛等待着一架飞机的到来……
1993年3月12日15时34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震逝世。遵照王震将军的遗愿,这架专机运送他的骨灰撒归天山。将军生前多次袒露心迹:“骨灰撒在天山,成为新疆大地的一粒。”
在这一天,遍布天山南北166万平方公里,一个名叫“兵团”的地方,他的300万人众和许许多多从那个年月走过来的“老新疆”,还在等待着另一个人。这个人自1966年离开新疆,再没有回过新疆。在“兵团”和“老新疆”的心里,这个人的形象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化、疏离,反而因这一方水土的壮丽历程被诗化、雕塑得更加高大、挺拔、亲切。在他们的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忘记过这个人——张仲瀚。
今天,他终于随同王震将军魂归天山。这是将军的遗嘱:“仲瀚无儿无女,和我一起回新疆吧!”
这更是他的夙愿,早在1949年秋天,王震问张仲瀚是想去新疆呢,还是随贺老总南下入川,张仲瀚选择了前者。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张仲瀚对探视他的好友故旧说:“如果我一生中有过最伤心的事,那就是迫使我离开了新疆。”
生不能还,魂归天山。
乌鲁木齐光明路十五号大院,挺拔的白杨,刚露出芽尖的青青小草,铺陈出一派肃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兵团领导,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老部下和来自社会各界的群众,列队兵团机关礼堂前,迎接灵车到来。
当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出现在人们眼前,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啜泣声……开发建设新疆的将士们向他们的良师益友默默地致以最后的军礼。白发稀疏,热泪湿襟,牵出渐渐走进历史的激情岁月,牵出人世真情……
苍天有灵,大地哀恸,纷纷扬扬的清明雨寄托着无尽的哀思和怀念。
载着张仲瀚骨灰的银燕凌空而起,一捧花瓣,一捧骨灰……
天山,天赐之山——雄奇俊美的骨架,定位高天阔地的新疆。
钟天地灵气,聚日月光华,纳百川魂魄,育一方生灵。
以百万年历史,见证沧海桑田,西域古今。
今天,浩浩云海环揽巍巍雪峰,银装素裹,承接英魂。一捧花瓣,一捧骨灰……银燕飞临石河子绿洲,这是您梦牵魂绕的地方。一捧骨灰,一捧花瓣,飘飘洒洒,回归绿洲大地的每一块田垄,每一方阡陌……融入新城每一道绿树垂荫的街巷……在这里,有您转战南北的老战友、老部下;在这里,拓印有您垦荒岁月的足迹;在这里,记录着您荒原夜话绿洲情怀……
您回来了,回到了您阔别多年日思夜想的故乡。兵团人,都有两个故乡,一个是老根绵延不绝的地方,一个是为之奉献了一切的新疆。
2007年11月4日,一声嘹亮的啼哭告诉我们,己然不算小的家族又添了一个侄孙女。给孩子报户口时,侄女没听奶奶的话,籍贯一栏她给女儿填写了“新疆石河子市”,而不是奶奶说的“河南省柘城县”。那是奶奶爷爷的老家。这个河南的“老家”离她太过遥远了,她心里,留有童年记忆少年足迹的石河子才是自己的“老家”。刚诞生的这个婴孩,已是石河子第四代“军流苗裔”。一个人,除了生物的DNA外,还有地理的DNA,它就是故乡。我们儿女的地理DNA,已不再是山东惠民、湖南宁乡、河南商丘……无论父辈怎样的乡音不改,兵团第二代第三代的老家都是天山南北的绿洲大地。
多美啊!面对秋日的胡杨林,你才能顿悟老祖宗为啥把秋唤作“金秋”!与千年一梦金镀真身的胡杨林相辉映的是一片连着一片绿叶难隐的“太阳红”——红枣林子!黄河水孕育出的大红枣儿不远千里万里,根脉源远流长伸展到了天山之南的塔里木盆地。和我们一样,它是异乡亦是故乡。最有气势的还是霸蛮得连天接地的棉花地!如此,才不负天赐之山的境界,才不负大地绿洲的格局——我的新疆老家。
责任编辑惠靖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