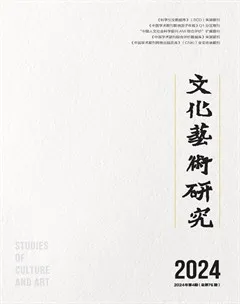感知过去,书写历史:斯蒂芬·巴恩与凯伦·朗的对话a
2024-10-01斯蒂芬·巴恩凯伦·朗文陈书焕



摘要:艺术史的“历史感知”(sense of the past)如何形成和发展?“后退几步”何以作为审视20 世纪艺术准则?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断裂”的吗?尼采曾经提出对历史的态度有怀古式的(antiquarian)、纪念式的(monumental)和批判式的(critical)。 这三种都不完全正确,也不完全错误。维柯的螺旋式历史观曾经把反复回到原点的回环运动看作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要素之一。如果从空间角度考察螺旋运动,那么螺旋式的历史不仅涉及某个时间点、某个时候的地点,还涉及空间。空间可以有时间属性。由此需要思考“空间再现”“唤起过去”时的“牛耕式转行书写”;思考“器物”(apparatus)对人性造成怎样的影响;思考“奇珍”(curiosity)如何令物品“回望”人类,从而不仅成为一个历史概念,更成为一种推动性概念,一种看待和思考事物的方式;思考“从事媒介批评的古物学家”意味什么;进而思考“历史写作”何以可以视为一种“历史诗学”。
关键词:斯蒂芬·巴恩;历史感知;空间再现;奇珍;历史诗学;艺术史
中图分类号:J1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24)04-0097-13
凯伦·朗:我想从20 世纪60 年代谈起。那时你正进行关于具体艺术(concrete art)的写作,同时还关注动态艺术(kinetic art)、比较批评、历史和其他很多领域。但在你最初发表的关于具体艺术的论著中,你提到“定义是危险的”。我认为那是本次访谈恰当的起点,因为从一开始,你就不居于一门学科,而是居于学科之间。是否可以谈谈你思想形成的过程?
斯蒂芬·巴恩:好的。我从1964 年开始说起,那时我刚刚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首先我必须承认——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常让我想起这个讽刺的事实——美国人说我不是“科班出身”的艺术史家。的确,我不是。我这代人中的许多学者都不是。在那之后,艺术史广为传播,各分支纷纷涌现。1964 年对我来说很关键,那时我读了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的《木马沉思录》(Meditations on a Hobby Horse)。我在剑桥大学修了“传统”的历史学学位,但这本书向我展示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并不直接与我的历史和史学史的研究有关,但与今天的艺术息息相关。那一年,白教堂美术馆(The Whitechapel Gallery)举办了劳森伯格(Rauschenberg)大展;我还在当地的安格利亚电视台中短暂出镜,讨论这次展览。我对展览印象深刻,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劳森伯格和再现》("Rauschenberg and Representation")。在这篇文章中,我讨论了“再现”为何对劳森伯格而言不可或缺。我回应了贡布里希的《木马沉思录》,他提出将“再现”理解为“替代”,而非“类比”。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
那年晚些时候,我带着博士导师的祝福去了巴黎。我的导师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爵士(Sir HerbertButterfield)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的名字在今日可能不意味着什么,但在当时,他是剑桥大学最重要的现代思想史历史学家之一。早在20 世纪30 年代,他就写了《辉格派的历史观》(The Whig View ofHistory),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指出,辉格派的观念是一种态度,它不仅对历史进行删减,使历史抽象化,还宣扬一种历史写作,用当代的方式来论述所有问题。在巴特菲尔德看来,从麦考莱勋爵(Lord Macaulay)及其后继者,到当今的剑桥学者,大多都秉承这种历史观。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必须是具体的,我们必须以具体的形式回顾过去。他可能是剑桥大学唯一愿意指导,也确实指导了我的博士论文的人,因此,我的论文在历史写作的层面上,完全是受到巴特菲尔德的影响。
1964 年秋,我动身去巴黎,巴特菲尔德给了我两个很棒的建议。第一个是:“和那位老太太交朋友!”你一定会很疑惑。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研究对象—— 19 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政治家德·巴朗特男爵(Prosper de Barante),其家族城堡仍然归家族所有。现任巴朗特男爵夫人每年夏天都住在那里,他们家族还保存了全法国最好的——确切地说是第二好的——私人图书馆。于是之后几年,我每年夏天都去探访巴朗特城堡,沉浸在丰富的史料中。巴特菲尔德给我的第二个建议也许不算是建议。在给我的一封长信中,他提到了“历史意识”(historical-mindedness)的重要性。他在这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既考察了当代德国史学,又考察了更早的德国历史著作。在当时的英国历史学家中,他是为数不多的拥有欧洲视野的学者。在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中,人们常接触到“历史意识”这个概念。就艺术史和其他历史研究而言,文艺复兴是一个典范时期,人们对旧日的迷恋自此而始。但是我猜巴特菲尔德想说的是,关注1800 年左右的这个时期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在这个时期,历史感知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发展起来。
迈克尔·本特利(Michael Bentley)最近出版的巴特菲尔德传记(The Life and Thought of HerbertButterfield: History, Science and God)引用了巴特菲尔德写给我的那封信,并将其与巴特菲尔德就该主题进行的吉福德讲座(the Gifford Lectures)联系起来。根据本特利的说法,巴特菲尔德后来认为这些讲座是失败的,因为他打算证明“历史感知”(sense of the past)是历史学发展的产物。我是不支持这个假设的,尤其是从我作为艺术史家的研究出发。我的结论是,这两种与历史联系的模式是渐近的(asymptotic)。它们可能会平行,也可能不会,但永远不会相遇。
但我追随巴特菲尔德最初的直觉,试图发展这个想法。在哈佛大学举办研讨会时,这实际上让我陷入了困境。我是应诺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的邀请参加这次会议,而文艺复兴艺术史大家约翰·谢尔曼(John Shearman)正好坐在观众席上。我谈论了法国画家弗朗索瓦- 马里乌斯·格拉内(François-Marius Granet)和他在拿破仑镇压修道院后在罗马完成的那些令人惊叹的画作。他说,他试图用绘画“恢复往日那种甜蜜的平静”。我提出,这种心绪本质上是由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断裂所造成的,以往从未出现过。约翰·谢尔曼对这个观点很愤怒,他认为,文艺复兴才是现代历史感知形成的真正时期,我却想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但我认为,我们既能承认文艺复兴的重要性,也能关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某个时期,在当时的法国和世界各地,历史感知开始变得更为具体。
朗:是的。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绝妙地捕捉到了那种意识。在村里的颁奖典礼上,一位老妇人被推上领奖台,胸前被挂上一枚奖章,尽管她并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场景中,历史感知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官方”的、一锤定音的。
你在历史和艺术史的研究中,是如何平衡文学艺术中的历史感知和历史学中的历史感知的?你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渐近关系?
巴恩:需要“脚踏两条船”。我想起了最近一次会议上别人向我提的问题,当时我谈论了19 世纪早期平版印刷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它在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中对历史的记录能力。有人问我:“这种对历史的记录是否反映在了史书中?”
我可以说,并非如此。事实上,是小说家而非历史学家充分利用了平版印刷这一新技术。司汤达在《帕尔马修道院》(La Chartreuse de Parme)有一个精彩段落,描写年轻的法布里斯·德东戈(Fabricedel Dongo)拼命想要在滑铁卢战役中作战;与之对应的是奥拉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描绘战斗场景的出色石版画,与早期的全景战场图截然不同。
当然我也可以回答,从《克里奥的衣裳》a 这本书开始,我就注意到了插图在历史书写中扮演的角色。奥古斯丁·蒂埃里(Augustin Thierry)的《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England by the Normans)在后续版本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插图,成了一本相关视觉材料的“图集”。这不单是出版商的圈钱行为。读者在读文的同时也读图,读沙龙里的油画,也读杂志里的木版画。阅读历史文本时,他们也希望读到图,而出版商满足了他们。我在《克里奥的衣裳》中指出,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这股浪潮中保持清醒。他的史书里没有插图,因为这些书思考的对象,就是人们根据历史事件创作的那些视觉遗产。
朗:让我们回到贡布里希的观点,将“再现”理解为“替代”(representation as substitution)。我认为你是在论及具象诗(concrete poetry)时谈到这一观点的。b 这让我想到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到的“再现”。你似乎深受尼采的影响,不知是出于你的导师还是你自己的兴趣。你在著作中采用了不少尼采的观点,例如“后退几步”(taking a few steps back)。它似乎和你谈到的“历史感知”产生了共鸣。
巴恩:是的,我确实同时谈到了当代诗学。1964 年,我去爱丁堡拜访了伊恩·汉密尔顿·芬莱(Ian Hamilton Finlay)。我为此写了一篇短文《具象诗中的交流和结构》("Communication and Structurein Concrete Poetry"),它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木马沉思录》中的一篇文章,其中探讨了“语义空间”(semantic space)的概念。[1]从此我开始写一些具象诗歌,逐渐取代了我对地形学水彩画(topographicalwatercolors)的兴趣。在我看来,人们可以把印刷文字作为素材,结合它们的形状和布局来创作,虽然不一定会比我以前画的那些风景画更形象,但一定非常独特。我把这些具象诗歌做成了明信片,后来又由我的朋友鲍勃·卓别林(Bob Chaplin)做成了丝网印刷。我们在 1980 年举办了联展,展出了历史学和地形学的艺术作品。
现在说说我对尼采的兴趣。正如你所说,尼采让我受益无穷。《历史的用途和滥用》(Use and Abuse of History)是我最常参考的,它的核心是三种对历史的态度:怀古式的(antiquarian)、纪念式的(monumental)和批判式的(critical)。当然,这三种都不完全正确,也不完全错误。
尼采说,怀古式的历史“呼吸着发霉的空气”,但是这并不是全部。他也尊重自己的祖先,尊重他们的故居等。“发霉的空气”让我想到我的另一个偶像——瓦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司各特说,一个好的废墟“就像一块上好的斯蒂尔顿奶酪”,他对历史的兴趣近乎食欲。
纪念式的历史与过去的伟大成就有关,体现在那些德国历史的奠基者身上。批判式的历史对尼采是最重要的,这本来就是他自己的态度。
这三种对历史的态度都非常有用,我可以举一个在我的研究中出现的例子。2010 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举办了一场关于霍勒斯·沃波尔的草莓山庄(HoraceWalpole's Strawberry Hill)的展览,我相信有很多人看过。当时,我应邀为展览的精美图录写了一篇沃波尔的介绍[2]。作为一个18 世纪的人,沃波尔让研究者头疼,但他预见了“浪漫的室内装饰”——借用克莱夫·温赖特(Clive Wainwright)的书名。a 在社会地位、审美趣味上,沃波尔是个大人物;在收藏界,他是一名先驱者。但他也同时关注詹姆斯一世时期,在他看来,直到英国内战前的这个时代,中世纪才真正告终。沃波尔兴趣广泛,这些兴趣看似互相冲突。我一直在思考其中的原因,直到我想到,应该用尼采的三种态度来解释这个问题。你可以同时看到纪念的、怀古的和批判的——或者说讽刺的——历史态度,从这幅丰富的画卷中,我们或许可以理解沃波尔的多种成就。
作为史学史家,我在一个成熟的领域工作,它让我感到无比沉闷。我读了无数的书,它们却没有关注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人们为什么对过去着迷?历史感知是什么时候在记载中出现的,又是如何发展的?我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才搞明白这些问题。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历史学家,而不想凭空捏造理论。当我读到米什莱写的一个脚注时,我得到了启示。那是20 世纪60 年代晚期,当时我已取得了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做的是预备性研究,但仅此而已。我在书中读到:“当今时代的历史学家——巴朗特、蒂埃里和我自己,形成了一个循环。要理解其中之一,你必须理解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句话仅仅是米什莱信中的一个脚注,我猜没什么人真正注意过它。但我由此开始设想这样一种循环:一二三, 二与一相连,三与一和二相连,形成一个系统。同一时期,我读了克劳德·列维-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生食与熟食》(The Raw and the Cooked),它以一个美妙的《序曲》开篇,其中谈到了音乐。他把作曲家分成三种:“代码”“信息”和“神话”,巴赫、贝多芬和瓦格纳。他举了一系列例子来解释这个结构性的观点:代码、信息和神话形成了一个循环。正如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说的“话语的不同功能”(different functions of discourse),这个循环有着语言学的基础。
在此,我突然意识到一种处理米什莱循环的方法。它是雅各布森所说的那种循环吗?我在197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检验了这个想法。[3]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回还”(ricorso)这个概念。米什莱对辩证法没有特别的兴趣,对正题、反题和合题明显不感兴趣,但他的思考方式常常是循环的。他以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为例子,在我看来,维柯是论证循环式或者螺旋式历史观的典范。他把这种反复回到原点的回还运动看作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要素之一。
朗:是的,这质疑了发展的历史观。有了回还,我们就有了螺旋式(spiral)的历史。尼采也谈到了螺旋,它不仅是回到原点,更是一种扩展。如果我们从空间角度考察螺旋运动,那么螺旋式的历史不仅涉及某个时间点、某个时候的地点,还涉及空间。空间可以有时间属性,可以包含过去、现在,近的时间和远的时间。
巴恩:是的,有段时间,我花了很大力气研究空间再现(spatial representation)。1967 年,我出版了一本国际具象诗选集,是世界上最早的具象诗选集之一,在排版上花费了很多心思。到了20 世纪70年代早期,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委托我为他主编的“现代艺术文选”丛书编一本关于建构主义史的文集。丛书和文集都汇集了各国文献。在我编辑《建构主义传统》(The Tradition ofConstructivism, 1974)的过程中,我觉得有必要在空间上呈现它的发展史:建构主义运动始于俄罗斯,随着瑙姆·加博(Naum Gabo)和拉斯洛·莫侯利- 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等艺术家移民他国,运动有了国际性的影响力,一直延伸到美国。[4]我的朋友菲利普·斯特德曼(Philip Steadman)为本书设计了一幅建构主义发展示意图,它有时也被称为《建构主义西进》("Constructivism Moves West"),常与现代主义发展史的其他示意图一起出现,例如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的著名图表a。事实上,这幅《建构主义西进》最近又在理查德·柯斯特拉涅兹(Richard Kostelanetz)1975 年的选集《随笔集:论述的其他形式》(Essaying Essays: Alternative Forms of Exposition)的新版中出现了。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我还先后担任《20 世纪研究》(20th Century Studies)的副主编和主编,编辑了一系列关于结构主义、法国新小说、俄国形式主义等的论文集。1976 年,在我负责的最后一期合刊中,我把一组至今仍有价值的文本编在一起,起名《视觉诗学特刊》("Visual Poetics")。其中有我的文章,有艺术家维克多·布尔金(Victor Burgin)的文章,还有许多来自不同传统的理论家的文章——中欧符号学家让·穆卡罗夫斯基(Jan Mukarovsky)和马克斯·本泽(Max Bense)、法国学者于贝尔·达米施(Hubert Damisch)、马尔塞林·普雷奈(Marcelin Pleynet)和让·路易·舍费尔(Jean-Louis Schefer)。他们的作品仍对我有着重要意义。
我对历史的和当代的维度都感兴趣。你问这些维度应该占据什么样的空间?是否占据了多种空间?这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后来,我决定做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很容易失败。我写了一本书——《真葡萄藤》[5],从古希腊一直写到今天的历史,围绕一系列主题:对象的再现——从宙克西斯(Zeuxis)画的葡萄到后来的静物画;自我的再现,以描绘纳西索斯的画为例;最后是历史的再现,我考察了“真十字架”(True Cross)的传说。它可称是西方最宏大、最复杂的史诗,从中衍生出无数优秀的艺术作品,从中世纪到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和亚当·埃尔斯海默(AdamElsheimer),一直延续到18 世纪。
我用尼采的一段话来表达我的观点,出自《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 Too Human)。尼采对历史的态度是“爬梯式”的,实际上这里有两个比喻。尼采说,唤起过去(invoke the past)是一个类似于牛耕地的过程——“牛耕式转行书写(boustrophedon)”。你从左写到右,转个弧形的弯,再从右写到左,依此类推。我觉得这是螺旋式运动的另外一种说法。尼采还使用了“梯子”的概念。他说了一句久久萦绕在我心头的话:“想要看得远,不是靠站在梯子的顶端。想要看得远,靠的是后退几步。”在审视20 世纪的艺术时,这一直是我的准则。从1900 年开始审视20 世纪的艺术,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起点,况且这不久前还是我们生活的世纪,这使得它不仅是现代的,更是当代的。可是如果局限在这个时期,你就会对现代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等各种问题产生偏见。所以“后退几步”,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概念上,都能让我们看得更远。
朗:我想起了你对“没有间断”(no short breaks)的评论和你著作中对它的展现。历史时期的“间断”,或者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间断”,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的概念。回过头来看,你质疑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定义。例如,你的书《现代主义的道路》(Ways around Modernism)起初着眼于马奈,又突然转向安格尔,认为他的画作看重图像的复制和繁殖,令我们重新考虑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定义。
巴恩:是的,我从一个简单的命题开始:如果我们不考虑现代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就没法知道如何对待和理解后现代主义。[6]悖论在于:一方面,我们在谈论现代主义时,必定要谈论马奈;另一方面,在马奈作画的时候,图像在“指数增殖”——虽然我不想用简单的术语来定义它。无论是以最初的版画形式,还是以后来的照片形式,画家开始对复制自己的作品感兴趣。然而,他们不是现代主义者,或者说大多数不是现代主义者,或者说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者。阿道夫·古皮尔(Adolphe Goupil)是法国19 世纪推广当代艺术的先驱,他也是我关注的焦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另一种历史,比起仅仅关注沙龙绘画,这种历史更加多元化、更有影响力,它影响了我们的观看之道。几年前在洛杉矶、巴黎和马德里举办的杰罗姆(Jean-Léon Gérôme)大展等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杰罗姆的主要画作通过其岳父古皮尔离开法国、来到美国,成功地培育了一种图像的文化,并被好莱坞发扬光大。这不仅是画作流通的问题。正如那场展览所示,杰罗姆和古皮尔为作品制作了大量印刷复制品。因此,就像在《平行线》(Parallel Lines)一书中一样,我在《现代主义的道路》中感兴趣的是,如何把现代主义“修正”为历史的一个注脚,把它和图像复制的历史和现代视觉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7]
朗:马奈观摩了大量油画,也大量致敬和借鉴了油画的复制品。如果我们将传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循环,其中二借鉴了一、三借鉴了一和二,这样是否有助于修正“先锋”这一刻板的术语?
巴恩:我想说,任何说法都比这个陈旧的军事隐喻要好!当然,我们现在离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在1970 年的立场已经很远了。当时他写道,先锋派“一枝独秀”并“完全掌握了‘局面’”。我喜欢三元的模型,列维·斯特劳斯的代码、神话和信息就是例子。但我认为,我们还需要从更宽泛的视角进行研究。从那个视角来看,我们不仅在讨论话语模式的继承,还在谈论弗洛伊德式的那种“被压抑物的回归”。换句话说,那些地下的、被忽视的话语常常改头换面,令我们感到困惑。后现代主义也许只是它们的继承者,而不是什么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朗:重新看待后现代主义,让我们的重点从“反讽”转向“奇珍”(curiosity)。您之前已经研究了自近代早期以来的奇珍,当时奇珍[和珍奇柜(curiosity cabinets)]一跃成为收藏的核心概念。不过,考察奇珍是如何塑造和颠覆了后现代主义,似乎是个不错的思路……
巴恩:是的。我对奇珍产生兴趣,部分是因为我所处的环境。比如,英国现存最好的奇珍收藏位于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档案馆,是1680 年去世的约翰·巴格雷夫(John Bargrave)的遗物。这些藏品包括他访问罗马时带回的红衣主教肖像集和注解(虽说有伤风化)。这些都收藏在我所生活的城市,参观很方便。奇珍在当下的发展,与其在历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息息相关。在追溯其发展时,我注意到了克日什托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的著作。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奇珍。波米安也研究过福柯,他最早的一些作品——尚未被翻译——是对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的直接回应。他认为奇珍是介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一种“过渡体系”,但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如今再说什么“知识体系”(epistemes)就显得太福柯了。这个问题我越想越觉得不寻常:奇珍源于福柯所说的“文艺复兴知识体系”,将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进行比较,比如海底有什么,山顶有什么。这种认知习惯本质上是将自然视为上帝的计划,所有的巧合和类比都是它的表现。然而,17 世纪的科学精神否定了奇珍,因为奇珍依赖于对特例的观察。我记得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话,他说把一棵果树种在墙的北侧,就是一种奇珍。换句话说,当你把果树种在它没法结果的地方,就成为一种奇珍,也即违背自然的。对特例的注重也是违背理性的,因为科学是通过总结案例、实验测试和推导出一般规律来进步的。
我与波米安对奇珍的发展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奇珍实际上并没有随着科学的兴起而消失,而是以其他形式出现,其中一种形式是古物收藏(antiquarianism)。二者动机相似,但具体的历史方向不同。与17 世纪的旅行者巴格雷夫相比,古物收藏迷恋特定的物品,其中带有更多的情感甚至情绪,而巴格雷夫却与他的藏品保持距离[8][9][10],这些都影响了当下对奇珍的呈现。例如,超现实主义是一种对物的崇拜,它既是对现代主义的建构主义潮流的反击,又延伸到如人类学等的其他领域。在今天,我们可能会误将某些潮流视为超现实主义的产物,而事实上,将它们理解为新瓶装旧酒的奇珍更为确切。
我记得和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谈过这件事。福斯特和《十月》(October)小组的成员曾评论过一些艺术作品,认为它们并不是艺术,而是民族志(ethnography)。他对“奇珍的回归”很感兴趣,并引用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的观点——艺术只需要“有趣”。这与奇珍的动机相似,而与主流的传统美学及高雅艺术不同。19 世纪,查尔斯·布兰克(Charles Blanc)创办了《美术公报》(Gazette des Beaux-Arts)(图1),当时的“美术”涵盖了建筑、绘画、雕塑、版刻和园艺等艺术。《美术公报》的副标题是《欧洲艺术和奇珍邮报》(Courrier européen de l’art et de la curiosité),涵盖了远东的奇物和“伍德伯里照相印版”(Woodburytype)——这些也属于奇珍。那个时期给非高雅艺术留有余地,就连波德莱尔的文集也题为《美学探奇》(Curiosités esthétiques)。奇珍和古物收藏的传统给许多当代艺术甚至现代艺术带来了启发。最近我接到一项任务,探讨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的装置作品“盒子”与奇珍的关系。阅读格林伯格对康奈尔作品的早期评论,会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康奈尔在超现实主义谱系中的位置。被分类到这个流派,让康奈尔非常不安,他甚至曾写信给阿尔弗雷德·巴尔,恳请把自己描述为“美国建构主义者”。放眼更古老的艺术形式,我们反倒能更好地理解现代主义艺术。
朗:这表明奇珍不仅是历史概念,更是一种推动性概念,一种看待和思考事物的方式。《美术公报》用“奇珍”来为中国、日本等地的物品分类,展示了一种空间边界,暗示了什么东西在“艺术”的概念之外,这也是你所写到的。关于将奇珍作为推动性概念,我认同你的观点;这种兴趣部分源于奇珍在“已知”和“未知”之间的位置,以及它对既有艺术观念——包括我们对艺术的想象——的挑战。艺术是一种不受理论束缚的“培根式”(Baconian)的事实,而奇珍提供了我们需要的刺激。奇珍让我们不断推翻既定观念、进行新的探索,这正是你在写作中所做的。
巴恩:奇珍的主客体关系与以往不同。在普通的主客体关系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有明确区别:客体是完全可知的,主体拥有或支配客体。相比之下,奇珍之物会回应,邀请我们书写它的故事,这也是我提到约翰·巴格雷夫的原因。他会在储物柜中放一把短剑,说“这是17 世纪威尼斯暗巷里用来杀人的短剑,你可以看到藏着毒药的机关”。我们也可以依此编出一些轶事:巴格雷夫一定是通过他的熟人英国驻威尼斯大使亨利·沃顿爵士(Sir Henry Wotton)了解到,伟大的威尼斯牧师、科学家,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差点被一位被反宗教改革教宗派来的耶稣会士暗杀。
在当代艺术家中,也有人这样观看物品,甚至被物品诘问。其中一位是科妮莉亚·帕克(CorneliaParker),她从弗洛伊德的沙发上提取了纤维,尽管得到了许可,但还是引发了轩然大波。物不一定难以定义,但一定难以捉摸。帕克讲述了关于某物的故事,而你也有兴趣听。在美国的一场展览中,她展示了电影《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中米娅·法罗(Mia Farrow)穿的睡裙。你看到长廊尽头的玻璃屏风后面有一条裙子,奇怪的是,越是靠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玻璃后面的裙子就越模糊,看起来仿佛在远离。当你走近时,它就在那儿,却几乎看不见。在我看来,这是艺术家/ 材料、艺术家/ 作品、主体/ 客体关系的一个有效范式。在此,我们再次涉及这种倒转的、歪斜的关系。
朗:本雅明有句名言:“光晕(aura)回头看着我们。”我认为这是暗示其难以捉摸。他反对像艺术史家和历史学家那样,把物品人格化、去主观解读物品,而不是让它自己说话。
说到本雅明,让我们转向他对“起源”的论述。在你的著作中,我看到你将起源视为时间中的一个点。从德国的观点出发,我认为本雅明对起源的观点是在历史中突然涌现,而不是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你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质疑了将时间视为“箭头”、历史在不断进步的观点。相反,我们可以想象历史是“放射形”发展的,一切皆有可能。
巴恩:我很久以前读过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也很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认为,本雅明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把他放在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解。《德国悲剧的起源》有着镶嵌画般的结构和关于话语和再现的精彩序言。书中的短文很吸引人,但如今需要批判性的审视。比如,《摄影小史》("Little History of Photography")充满洞见,但翻译发表在法语杂志《摄影研究》(Études Photographiques)上后,读者可以发现很多错误,因为本雅明根本没亲眼见过文中提到的许多资料和作品。换句话说,本雅明的写作环境与我们今天不同,我们比他对摄影了解得更多。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失去了意义,但我们必须牢记这一前提。本雅明最广为人知的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有一个问题:它已成了罗兰·巴特所说的“套路”("doxa")a。我们常说的进化观、发展观,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篇文章中来的。例如他指出,平版印刷术是视觉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但很快就被摄影取代(supersede)——“取代”这个德语单词的字面意思是“飞越”(flown over)。就像传统上将1863 年沙龙视为现代主义的起源一样,摄影也被认为是“原版”和“复制品”间的分水岭和危机之兆。
现在看来,我觉得它小看了事情的复杂性。它把摄影的发明和发展简化成一种简单的进化叙事。据说画家保尔·德拉罗什(Paul Delaroche)说过:“从今天起,绘画已死。”实际上,他从未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最早出现在一份狂热的民族主义出版物中,距离德拉罗什去世已久,我尚未发现它在之前的文献中出现过。德拉罗什培养了许多重要的摄影师,如古斯塔夫·勒·格雷(Gustave Le Gray)、查尔斯·尼格尔(Charles Nègre)和亨利·勒塞克(Henri Le Secq),并撰写了一份关于摄影如何帮助画家的报告。根据目前的信息,德拉罗什早在1838 年秋就参观过达盖尔(Daguerre)的工作室。因此,赫尔穆特·格恩斯海姆(Helmut Gernsheim)在摄影史中将这句评论与1839 年8 月19 日巴黎科学院与美术学院会议(Academies of Science and Fine Arts)联系起来是完全不可信的。
关于本雅明对19 世纪印刷文化的看法,我认为这是20 世纪20 年代一位鉴赏家的观点。在《开箱整理我的藏书》(Unpacking My Library)中,本雅明提到一位无名艺术家,称他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版画家。现在我们知道本雅明指的是谁,但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个人并非最为著名。这种误解源于19 世纪本雅明那代人对版画失去了兴趣,他们认为它注定消亡。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19 世纪法国和世界各地的版画形式,形式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形式与市场、沙龙和学院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本雅明和他那一代人,比如查尔斯·艾文斯(Charles Ivins),都构建了关于视觉文化的迷思,它们经不起推敲。
朗:是的,你确实拓宽了我们对19 世纪以及复制技术的理解。让我们再谈谈那篇教条主义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我认为,其中对失去光晕的恐惧源于对物品“回望”能力的恐惧,以及对人类丧失艺术感受力的恐惧。因此,本雅明不仅担忧绘画在被复制时失去与人共鸣的能力,还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器物(apparatus)会对人性造成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仍未解决的问题。奇珍的重要性在于,它令物品“回望”人类。
你刚才提到的那些“经不起推敲的视觉文化迷思”让我想起了罗兰·巴特。他的作品充满人性,对世界的好奇跃然纸上:关于我们如何构建世界、认知客体,并用它们编织神话。您很早就阅读了巴特,并向英语世界介绍他。你能对我们讲讲这段经历,告诉我们它如何影响了你的思考吗?
巴恩:我很高兴你提到巴特。我应该是第一个把他的文章翻译成英文的人。这篇文章是《结构主义的活动》("The Activity of Structuralism"),首发于1963 年,我们把它发表在剑桥的《形式》(Form)杂志1966 年第一期。后来,我在《时代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述巴特的《明室》(La chambre claire),这是一部摄影研究的伟大作品,在他去世前几天出版。我得到他的授权,翻译了《历史的话语》("The Discourse of History"),发表在1981 年的《比较批评》(Comparative Criticism)年鉴,那期的主题是“修辞与历史”(Rhetoric and History);巴特的那篇文章紧挨着我自己的论文《作为动物标本师的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 as Taxidermist"),这篇后来成为《克里奥的衣裳》这本书的第一章。换句话说,巴特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仍未减弱a。
最近,我在写关于伊恩·汉密尔顿·芬莱最早建造的花园时,想到了约翰·迪克森·亨特(JohnDixon Hunt)和我本人引用过的、巴特1963 年论文中的一个重要段落,讨论芬莱对古代的看法。回顾我们在20 世纪60 年代的通信,我们当时确实在讨论那篇文章,这点我可以证实。《历史的话语》一文的结语指出,“从现在开始,历史的标志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如何理解”,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曾经,我认为这不过是个乌托邦式的声明,但现在我逐渐认同了它。
我非常欣赏巴特的另一个方面是他避免使用“套路”。这个词上文已经出现过,它无疑是巴特学术探索的缩影,推动他进入许多研究领域。我们不一定总能理解他,但他的追求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朗:在此有许多可以讨论的,但现在让我们回到尼采和古物学。对你来说,古物学一直很重要,无论是恢复它的完整意义,还是尼采在《历史的用途和滥用》中将古物学比作一棵扎根于地下的树。尼采指出,古物学对古老和传统之物的熟悉和热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这个世界上舒适自处的状态。他说批判式的历史很重要,因为古物学家对过去的热爱也会让他看不清现在。然而,如果批判式的历史走得太远,就可能根除过去,在根源上切断过去。作为一个通过“过去”理解“现在”的人,您显然不愿如此,虽然您也使用这种批判性的历史观。您是否愿意谈论一下这点?
巴恩:好的。这让我想起了一位老朋友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对我的评价,他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媒介研究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将我描述为“从事媒介批评的古物学家”(media-critical antiquarian)。这在德语中可能好听点,但它仍是“从事媒介批评的古物学家”。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这里的“古物学家”有福柯式“考古学家”的意味,只不过挖掘的是话语而不是文物。“媒介批评”中“媒介”是广义的,其范围比任何一个视觉艺术领域都要广得多,而“批评”是至关重要的。
在20 世纪70 年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著作。在我完成关于《历史话语中的循环》的文章后,我想,这个循环是否存在?会有人对我的研究感兴趣吗?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爵士(Sir Edmund Leach)和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对这篇文章以及刊发此文的1970 年《20 世纪研究》期刊表示了好评。然而,我不知道艺术史乃至历史学领域是否有人对此感兴趣,很长时间不知道该向哪里投稿。我投给《艺术史》(Art History)杂志的第一篇文章被编辑约翰·奥尼恩斯(John Onians)退稿,他说:“试想一下,如果你最可怕的敌人正在阅读这篇文章,他们会怎么想!”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回复。我把文章投给了其他编辑。不久之后,海登·怀特于1973 年出版了《元史学》(Metahistory),并邀请我加入他主持的卫斯理学院人文中心。通过怀特,我结识了其他从事史学史批判分析的美国学者,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莱昂内尔·戈斯曼(Lionel Gossman)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自那以来,我开始在卫斯理学院主办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杂志发表文章,该期刊一直对我很友好。
怀特帮我开展了对博物馆的研究。在卫斯理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验证这些想法后,我于1978 年在《历史与理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两个法国博物馆的比较研究[11]。这篇文章后来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除了法语。然后,我开始思考话语“循环”的不同阶段,并对怀特的“反讽”概念产生了兴趣。在19 世纪早期至中叶的英国文化圈,人们对古物学持有一种反讽或嘲弄的态度。19 世纪30 年代,霍勒斯·沃波尔的藏品挂牌出售,附有一份精美的目录,封面是约翰·里奇(John Leech)的绘画。人们受邀前来取笑这些物品的荒谬。这个以反讽结束的循环似乎是无休止的。后来,我重新阐述了对博物馆和博物形式的想法,并写了一篇关于“反讽式的博物馆”的文章[12]。这篇文章最早在德国发表,人们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尤其是相对化的古物和反讽化的纪念。可以说,我们不能天真地退回到古物学阶段,但古物学之树必须根深蒂固。这是一种平衡的做法,博物馆通过展览和陈列,来展现这种平衡。博物馆记录了我们观察和理解过去的方式,就像琥珀保存了苍蝇。在博物馆的设计和建造中,这些需求将不断得到审视。
朗:在写作中,你深入历史语境,打破既定观点。当你思考物品与历史的关系时(这是我们艺术史家本来就应该做的),物品开始回望你。我觉得在你的写作中,你对历史语境和物品非常了解,以至于它们自己提出问题,而你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则带着一种历史敏感性去回答。
巴恩:希望如此,但我常常需要补充历史语境。举两个例子。首先,我研究过现代史学史的一句“神圣”的格言——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如实直书”(as it really happened/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如何理解这句话?当然了,需要讨论翻译的准确性,比如要如何理解“实”(really)这个词。但我认为这句话的语境是约克郡乡绅查尔斯·沃特顿(Charles Waterton)的动物标本制作术。在此之前,人们只是把骨头填到动物尸体上对应的位置,结果骨架变得扭曲,皮毛变得皱巴巴的,搞得一团糟。沃特顿取出动物的骨头,用氯化汞浸泡动物尸体(他也用它定型自己的礼帽),然后从内部塑形,做成稳定逼真的标本。这是玛丽·雪莱写下《弗兰肯斯坦》的时代。对“逼真重现”的愿望和实现愿望的技术,是天主教乡绅(沃特顿)和新教牧师后裔(兰克)之间的共同点。
另一个例子更有趣。1862 — 1863 年,现代主义出现了。1863 年发生了什么?落选者沙龙(Salondes Refusés)曾展出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图2)。这个事件很重要,不是吗?的确,这幅画很迷人,历久弥新。但我在波尔多一家古董店发现了一个甜点盘(图3),上面的图案画着两位女士在公园里面对面站着,写着“1862 年和1863 年”。一位女士穿着宽大的裙撑,另一位穿着直筒连衣裙,戴着软帽。画面中的两位先生,一位穿得很严实,戴着小礼帽,另一位穿着宽松外套。这画很有趣,因为里面的人物并不知道现代主义始于1863 年,但一些变化已经发生,比如人们的着装风格和休闲活动。第二位女士和她松松垮垮的裙子,还有她的男伴,可以直接移植到《草地上的午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语境问题可能会让你抓狂,但总有平行事件或偶然发现向你提供语境。你只需要碰巧、幸运地找到它们,并注意观察。
朗:如你所说,看似遥远的事物实际上可能具有核心意义。最后,请你谈谈诗学。除了奇珍和俏皮(playful),你的作品中还流淌着诗意。我心目中的诗学观念是一种形成和塑造,作为历史学家,不拘于既有的观念和定义,引入之前从未使用过的材料,将历史写作视为一种诗学,形成一家之言。
巴恩:确实如此。从20 世纪70 年代初开始,我就对诗学非常感兴趣。部分原因是,我最早用法语发表的文章是为《诗学》(Poétique)写的,这份期刊秉承了罗兰·巴特的精神。巴特为创刊号提供了一篇精彩的短文《从哪里开始?》("Où commencer?")——“你从哪里开始研究诗学?”当时的编辑是杰拉德·热内特(Gérard Genette)和茨维坦· 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我和他们都有联系。我很高兴能参与这项事业,所以把1976 年编的那期杂志也称为“视觉诗学”。在《克里奥的衣裳》中,我汇集了自己早期关于历史再现的文章,并在引言中表示,我希望创造一种“历史诗学”(historicalpoetics)。选择“诗学”这个术语,一方面是由于它当时很时髦。这样就不必谈论修辞,因为修辞和比喻性语言往往被视为旁门左道或者花里胡哨,是一种给事实涂脂抹粉的方式。传统意义上,学习修辞是为了锻炼口才,在论坛或讲台上说服人们。那并不是我想要暗示的含义。
当时,我发现列维- 施特劳斯的学生、人类学家丹·斯佩伯(Dan Sperber)提出的“认知修辞”(cognitive rhetoric)很有趣,那也可以称为是一种诗学。这种修辞,不论是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传统的角度,都不仅仅是对“中性语言”(neutral language)的偏离——中性语言充分表达了含义,不需要补充。对于斯佩伯来说,交流取决于修辞,而修辞不仅是装饰,还是心理过程和交流过程的组成部分,对于激发观众和读者的反应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认为对语言的使用,也即“语言的诗学”,是至关重要的,这可能源于我很久之前学习拉丁语的经历,那是一种组织陌生语言的训练。语言的组织训练不仅在我们写作时,也在我们谋篇布局时起着主导作用,这一切汇成了诗学。
彼得·伯克评论过我的一本书,认为我作为散文家是最出色的。我觉得那是个误解。但我确实重视书籍的谋篇布局,尤其是章节的构成。我关注插图的质量和风格,这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得以实现。我即将出版的《杰出的图像》(Distinguished Images)[13]可能比我以前写的任何一本书都“诗意”(poetic)。当然,我希望它也能吸引那些对19 世纪法国印刷文化感兴趣的人。
参考文献:
[1]Bann, Stephen. "Communication and Structure in Concrete Poetry"[J]. Image, 1964.
[2]Bann, Stephen. "Historicizing Horace"[M]. Horace Walpole's Strawberry Hill. Ed. Michael Snodin. New Haven: Yale UP, 2009. 117-133.
[3]Bann, Stephen. "A Cycle in Historical Discourse: Barante, Thierry, Michelet"[J]. 20th Century Studies 3, 1970.
[4]Bann, Stephen, ed. The Tradition of Constructivism[M]. New York: Viking, 1974.
[5]Bann, Stephen. The True Vine: On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Western Tradi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9.
[6]Bann, Stephen. Ways around Modernism, Theories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Visual Art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7]Bann, Stephen. Parallel Lines: Printmakers, Painters and Photographer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M]. New Haven: Yale UP, 2001.
[8]Bann, Stephen. Under the Sign: John Bargrave as Collector, Traveler, and Witness[M].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4.
[9] Bann, Stephen. "Travelling to Collect: The Booty of John Bargrave and Charles Waterton" [M]. Travellers' Tales: Narratives of Home and Displacement. Ed. George Robertson, et al. London: Routledge, 1994. 155-163.
[10] Bann, Stephen. "Scaling the Cathedral: Bourges in John Bargrave's Travel Journal for 1645" [M]. Monuments and Memory: Made and Unmade.Ed. Robert Nelson and Margaret Oli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3. 15-35.
[11]Bann, Stephen. "Historical Text and Historical Object: The Poetics of the Musée de Cluny"[J]. History and Theory,1978(17).
[12] Bann, Stephen. "Das Ironische Museum"[M]. Geschichte sehen: Beiträge zur Beiträge zur Ästhetik historischer Museen. Ed. Jörn Rüsen,Wolfgang Ernst, and H. Th. Grütter. Pfaffenweiler: Centaurus, 1988. 63-68.
[13]Bann, Stephen. Distinguished Images: Prints and the Visual Econom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M]. New Haven: Yale UP, 2013.
(责任编辑:孙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