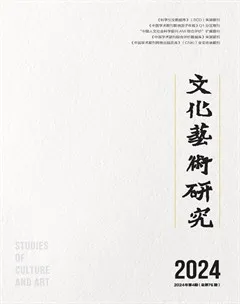自由与超越: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存在主义美学
2024-10-01甘莅豪
摘要: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出发,探讨2024 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学创新及其对人类的价值,可以看到:相较于东京奥运会以“物哀共情”模式展示的悲情美学,巴黎奥运会开幕式通过存在主义的“自由与超越”理念进行艺术表达,体现了对现代奥运开幕式观念的突破与超越。开幕式中的多个场景,包括巴黎城市剧场、新浪漫主义三人行、变装皇后秀、跑酷表演及艺术作品的创新展示等,都表达了一种萨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哲学。由此,巴黎奥运会不仅深入探讨了后疫情时代人类存在的意义,深刻反思和谴责了人类战争行为,展示了在荒诞情境中人类的无畏勇气和无限创造力,同时也彰显了对于自由与多元价值的积极追求。进而言之,如果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如儒家和道家的自由观念引入讨论,不仅可以丰富对存在主义美学的理解,也可为处理自由与规范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指向了一条兼顾个体自由表达与社会和谐一致的奥运会开幕式观念发展路径。
关键词: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存在主义;美学;萨特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24)04-0001-09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全球新冠疫情“悲情”语境和日本“以悲为美”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创新性地采用了“物哀共情”模式。这一模式立意高远,既深度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也展示了日本的创新精神,更塑造了一个关注弱者、包容多元、和谐共存的现代文明国家形象。[1]然而,东京奥运会的这种模式,虽然强调了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呼唤人类在全球疫情肆虐之际重新审视自身的渺小与脆弱,却也引发了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新一轮反思。随着新冠疫情的阴影逐步退去,人类迫切需要从悲伤与隔离带来的负面情绪中走出,重新发现自身的力量与价值。在此背景下,2024 年巴黎奥运会肩负起了全新的使命。
受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 保罗·萨特思想的熏陶,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突破了东京奥运会的“物哀共情模式”,转而强调“自由与超越”的存在主义美学。[2]这一美学观念的核心在于“存在先于本质”,即人类并非受制于规定的自在状态,而是时刻处于一种自为状态,需要通过自由选择和积极行动来定义和改变自己的本质与命运。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类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上,总与万物格格不入,但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得以通过对自身存在的积极反思和行动来表达真正的自由。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正是以此哲学为指导,通过艺术表现、仪式设计和象征意义,传达人类在绝望中坚持生存的乐观理念,倡导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它召唤人们,即使在危机与困境面前,也要努力超越现状,勇敢定义自身的本真存在。
一、否定与虚无:诸神已死
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深受尼采的影响,特别是在否定上帝的观念上。尼采以他的著名宣言“上帝已死”,标志着传统的基督教价值体系和理性价值观的崩溃。[3]萨特不仅继承了这一思想,还进一步发展了无神论的观点,认为上帝的概念是人类为满足需求而创造的构造,随着人类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自由,上帝这一概念便日渐消亡。在萨特看来,上帝的存在实际上剥夺了人的自由,使人陷入无能的境地。通过否定上帝,萨特强调人的存在不再依赖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而完全由人自身决定和创造。也就是说,人在出生时没有固定的本质,只有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逐渐塑造自己的本质。这种观点将人的存在视为一种不断自我创造的过程,而不是由某种超自然力量预设的。这种自我创造的过程赋予了人类以无上的尊严,因为除了人的宇宙以外,没有别的宇宙。人类不再需要依赖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定义自身,而是可以通过自身的意志和行动来创造自己的存在。[4]
在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一幕名为“Festivité(节日庆典)”的表演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讨论。该场景通过展示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价值观,涉及跨性别模特及舞者等多种表演形式,传达了丰富的时尚风格和个性表达。其中,法国演员菲利普·卡特里内(Philippe Katerine)臃肿虚胖的中年男性身躯几乎赤裸地从舞台的盘子中出现,将一种略带“恶心”的表现形式与呼唤和平的信息相结合,呈现名为“Nue(裸体)”的歌曲,给出了“如果我们赤身裸体,会不会有战争?答案可能为否,因为当你赤身裸体时,你不能藏枪或匕首”的追问和答案,从而用荒诞否定荒诞,对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和加沙战争进行了戏谑式的谴责,并进一步贯彻了历届奥运会呼唤和平的理念。
由于这个表演的镜头画面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在视觉构造上有相似之处,这一幕遭到不少保守人士批评。开幕式的组织者对此进行了辩解,指出这一幕的灵感实际上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众神盛宴。具体来说,组织者强调,开幕式的表演是受到了17 世纪荷兰画家扬·比利耶特(Jan Harmensevan Biljert)的作品《众神的盛宴》的主题和表现形式的启发,菲利普·卡特里内的造型是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形象相呼应,而头戴光环的肥胖女性则是对画中太阳神阿波罗的一种戏拟表现。
显然,这一解释可以被看作是开幕式对传统宗教的一种否定和对众神的一种嘲讽表达。这种表达方式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萨特存在主义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暴行的反思,本届奥运会则是对新冠全球危机和俄乌战争、加沙战争的回应,两者都是在人类经历巨大灾难后的产物。它们共同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质疑:“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无端地死去?”
其实,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菲利普·卡特里内通过其独特的表演,展现了酒神式的快乐和对“人”的深刻理解。他的造型灵感部分还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虽然这一造型引发了观众的不适,但更重要的是它传递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完美的神并不存在,只存在有缺陷的人。该思想鼓励人们勇敢面对无神的世界,并在其中寻找人类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这一幕不仅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致敬,更是对人类创造力和自由的庆祝。它也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在面对新冠病毒等天灾时,我们应该坚信人定胜天的力量;在面对所谓崇高和神圣时,我们不能忽视其荒诞的本质。也就是说,菲利普·卡特里内提醒我们——世界很荒诞,我们要快乐。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所谓的正义理由,特别是发动战争的理由,往往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们应该以更加理性和客观的态度看待世界,不要被某些所谓神圣的表面光环所迷惑。
这种对诸神的否定是萨特哲学的核心,也是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与其共鸣的地方。尼采宣布“上帝已死”时,试图揭示没有了上帝,人类失去了寻求外在意义的依靠,必须面对生活的本来面目,并且在这种直面中找到自我超越的动力。萨特同样强调,没有了上帝,人反而获得了塑造自己、创造自己的真正自由。他认为,人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个没有先验意义的世界,并且在这种面对中创造出自己的生活意义和价值。萨特的这种思想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主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因为没有任何外在的权威可以告诉个体应该如何行动,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这种责任感是萨特哲学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要求个体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要勇于承担自由的重担。在这个意义上,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不仅呈现了对诸神的否定,更是一种对人类理性和自由的高度肯定,展现了一种无神论的快乐和彻底否定的自由精神,不仅挑战了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为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提供了具象认识。通过继承和发扬尼采和萨特的思想,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面对荒诞世界的勇气和智慧。
在否定上帝之后,萨特意识到,一旦上帝死去,人类将面对一个无意义、无目的的世界,这种情境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和恐慌。萨特将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两种。自在的存在指的是那些不具备意识的事物,它们的存在与其本质完全一致。而自为的存在指的是人类,因为人类具备意识,因此其存在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由于人类的本质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不断形成和流动的,因此人类的本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源自虚无。然而,萨特并不认为虚无是消极的。他认为,正是这种虚无赋予了人类行动的自由和可能性。这种自由不仅使人类摆脱了传统价值观的束缚,也使人类重新获得了创造自身的能力。显然,萨特的虚无主义并不是一种悲观绝望的世界观,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可能性的哲学。他认为,虚无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没有意义,而是意味着一切意义都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通过面对虚无,人类可以超越传统和自身的局限,创造出全新的、自为的存在方式。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选择在塞纳河上举行,不仅打破了奥运会开幕式在体育场内进行的惯例,更通过一系列富有创意的设计打破了多种观念和框架,体现了人类对自由和创新的追求。这场开幕式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了存在主义的“虚无”概念,展现了打破禁锢、重新定义的精神。
首先,将城市作为开幕式舞台。巴黎奥运会组委会将整个城市作为开幕式的舞台,运动员们乘坐160 艘船沿着塞纳河徐徐入场,从奥斯特里茨桥出发,经过城市中心的著名景点,最终在埃菲尔铁塔附近的耶纳桥停下。这个创意不仅提供了绝佳的视觉体验,也改变了人们对奥运会开幕式通常在体育场内举行的传统观念,将城市变成一个开放的剧场,让观众不仅能欣赏到体育赛事,还能感受到巴黎的独特魅力。包括在本次奥运会期间,著名的地标建筑巴黎大皇宫成为击剑等项目的比赛场地,这一安排打破了建筑功能的思维定式,将一座多功能的展览馆转变为竞赛场所,让观众重新审视建筑的用途。对建筑空间的灵活利用和创新思维,不仅让人们对建筑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也为未来的多功能场地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些大胆的突破和创新,让人们重新思考开幕式的形式和内容,也让开幕式成为一次城市与运动、历史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其次,跑酷穿梭于城市房屋之间。跑酷作为一种突破城市建筑和道路布局限制的运动,完美契合了存在主义的精神。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跑酷选手戴着面纱和兜帽,手持火炬飞跃一个又一个场馆,展现了无限的自由和无畏的精神。这种突破性的表演,通过打破城市建筑和道路布局的框架,象征着人类追求自由和突破自我的精神。这种表演方式让观众感受到了运动的激情和自由的魅力,也让人们重新思考城市空间的可能性和多样性。
再次,卢浮宫内的油画人物出框。演员们扮演的卢浮宫内的油画人物,在火炬的照耀下纷纷“出框”,这一创意打破了画框的限制,也颠覆了观赏者与被观赏者的传统关系。这些名画人物不仅从画框中跳出,还在塞纳河边欣赏开幕式,打破了艺术品只能被人欣赏的固有观念。油画人物的复活和互动,赋予了静态艺术品以生命和动态,不仅让观众耳目一新,也为人们思考艺术的本质和观看艺术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
接着,将名画放置在塞纳河中。开幕式后程,卢浮宫馆藏名画在塞纳河水中若隐若现,打破了观众室内观看名画的传统习惯,不仅使艺术品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也让观众在欣赏名画的同时享受河边的美景。这种打破空间限制的展示方式,让艺术走出博物馆,走向公众,展现了艺术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不仅让艺术更加亲民,也展现出艺术展示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小黄人偷走名画《蒙娜丽莎》的情节,同样打破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展现出独具创意的法式幽默。这一情节不仅是对经典艺术作品的调侃和再创作,也反映了现代动画艺术和传统油画艺术的融合与创新。开幕式通过幽默的表现形式,将经典艺术与现代流行文化相结合,传递出对艺术的包容和开放态度。
最后,“火车出站”破框而出。该场景创新性地让世界上第一部公开放映的电影,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中的火车从银幕中破框而出,在历史和当下、现实与想象层面展示了电影艺术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力量。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以这一经典镜头作为转场,将观众的视线从室内带到塞纳河岸,展示了运动与科技、现实与虚拟的完美融合。这种打破框架的创意,不仅让观众感受到电影的魔力,也让人们再次思考和定义“何为电影,电影为何”。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当火炬手穿越大剧院时,演员们正在排练的剧目是《悲惨世界》中的一幕,描绘的是法国七月革命的激烈斗争场景,画面致敬的则是19 世纪法国绘画大师德拉克洛瓦的巨幅油画《自由引导人民》。这幅画表现了1830 年法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历史时刻,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同时,塞纳河堤岸边,手捧头颅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形象也令人印象深刻。在大革命中,皇室贵族被送上断头台,意味着人类皇权和神权统治旧时代被淘汰,共和新时代的到来。将革命、战斗、死亡、断头台等传统意义上的血腥内容搬上“合家欢”的开幕式舞台向全世界展示,这看似不合时宜,但也恰恰反映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打破禁锢的存在主义美学思想。
总而言之,巴黎奥运会开幕式通过一系列否定性和突破性的设计,展示了存在主义“虚无”概念下无所顾忌的自由与创新精神。无论是将城市作为剧场、在大皇宫内举办体育赛事,还是跑酷穿梭城市、卢浮宫油画人物出框等,这些创意都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和框架,展现了现代社会对自由、创新和自我突破的追求。
二、自由与选择:他人即地狱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在于自由,他认为,自由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目的。通过否定上帝和填充虚无,萨特重新定义了自由的意义,并强调人类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不仅创造出自身的本质和价值,也为自己的一切选择和行为负责;不仅影响到自身的存在,也影响到他人的存在。萨特认为,人类的自由并不是一种被动的状态,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创造过程。自由意味着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和行动,超越传统的束缚,创造出全新的存在方式。自由不仅使人类摆脱了传统价值观的束缚,也使人类重新获得了创造自身的能力。通过强调自由,萨特不仅为人类重新定义了存在的意义,也重新定义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
在2024 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众多惊艳场景中,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塞留馆)内的亲密爱情故事无疑是一个独具匠心的亮点。这一幕的主角是一女两男,他们在图书馆中上演了一场纠缠与分离、爱与文艺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存在主义美学的自由选择的内涵。这一段故事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庄严氛围中展开。图书馆内珍藏了大量的艺术书籍、手抄书、地图、版画、摄影作品等,而这三位主角拿出的书籍也颇具深意,包括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安妮·埃尔诺的《简单的激情》、斯利马尼的《性与谎言》、拉迪盖的《肉体的恶魔》、德拉克洛的《危险关系》、莫里哀的《华丽的情人》、马里沃的《爱情的凯旋》等。这些法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描绘了不同层次的爱情、欲望和人性。选择这些作品,不仅突出了法国文学的深厚底蕴,也为三人纠缠、冲突、接受、容纳、融合的爱情故事提供了文化背景。在两男一女奔跑场面里,观众还可以看到法国经典电影《祖与占》和《法外之徒》的影子。这两部电影被看作是法国20 世纪50 年代末兴起的新浪潮电影的翘楚,致力于打破传统电影的叙事方式和美学观念。通过致敬这些文学作品和电影,开幕式不仅向全球介绍了法国文化,更是在表达一种突破传统、追求自由、接受他人的精神。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每个人都有在虚无中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正确看待他人的目光和评价。开幕式上的这段爱情故事,通过纠缠与分离,表现了每个人在面对复杂情感时的自由选择和承担责任,继而走向一种新型的彼此尊重、接受和融合的过程。在存在主义的视角下,人并不是被动地存在,而是通过选择和行动来定义自己的存在和意义。开幕式上的这三位主角,正是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通过各自的选择,展现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世界的多元性和自由选择的力量。
此外,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这一存在主义哲学概念,也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斗争,特别是通过“凝视”实现的客体化过程。[5]在巴黎开幕式上,《法国变装皇后秀》(Drag Race France)变装皇后皮什(Piche)和节目评委妮基·多尔(Nicky Doll)在德比利人行桥上的走秀正是从这一视角阐述了存在主义美学。
首先,走秀的本质是一个展示过程,变装皇后们通过服饰、姿态和表演,呈现自我。这种展示不只是简单的自我表达,更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宣告:“这是我,我是独特的。”然而,变装皇后们在展示自己的同时,也承受着无数双眼睛的审视与评判,这种目光有时是欣赏的,有时则是批判的。在观看者的凝视下,变装皇后们的主体性可能被削弱,成为了被观看的对象,犹如传说中人们在美杜莎的凝视下化为石头,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
其次,变装皇后们的走秀,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意在挑战传统性别观念和社会规范。在他人的目光下,变装皇后们的表现能否被真正理解和接受,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变装皇后们若过分依赖观众的认同,可能会陷入自我质疑和痛苦之中。全球观看者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偏见,目光中可能蕴含着误解、排斥甚至敌意,正如萨特所言,不能正确对待他人的评价将陷入地狱。
最后,萨特的观点也提醒我们,要争取自由,摆脱他人目光的束缚。变装皇后们的勇敢走秀,是对自我主体性的肯定,是对自由的追求。他们通过表演,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和本质,拒绝被简化为他人目光中的客体。尽管可能要面对不理解和偏见,但他们依然选择自由地表达自我,这本身就是对“地狱”的一种抗争。由此,变装皇后们的走秀,也是一种对他人凝视的反击。他们将自身的主体性展示在公共场合,通过艺术和表演,将观看者从简单的凝视中解放出来,迫使他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性别与身份问题,反思自己的思维定式,进而接受并包容他者的多元存在。这种互动虽然包含了冲突和矛盾,却也蕴含了可能的理解和共鸣。
综上,从“他人即地狱”的角度来看,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变装皇后们的走秀环节既是对他人目光的挑战,也是对自我主体性的肯定。他们通过这一场景,不仅展示了个人的独特性,也在冲突和理解中寻找和构建了一种自由主体间的新型关系。
显然,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学观念不仅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理想,更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该观念认为,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和行动,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存在和价值。人类不仅要追求个人的自由选择,更要正确处理他人的自由选择,并在冲突中接纳与包容他者,从而追求共同的自由和幸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不仅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理想,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追求[6],因为它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并为人类创造出全新的价值和意义。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发展,这一点在异质化和差异化主体日益增多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三、超越与救赎:爱的礼赞
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以及自我超越的过程,这些概念通过反思、否定、行动、超越和自我救赎等多个方面展现出来。[4]232-286 在这一美学体系中,超越与救赎成为理解个体存在的关键。首先,反思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基础,它要求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状态进行深刻的自我审视。在反思过程中,个体处于一种既非完全自在(存在于事物之中),也非完全自为(自主意识)的虚无状态。其次,否定则是反思的结果,是个体对自身现状和外部世界的质疑和拒绝。萨特指出,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否定,它既承认世界上存在某种事物,又通过改变这些事物的存在将其否定。因此,否定是一种实现,即通过对现有状态的否定来赋予行动的意义。再次,行动是萨特存在主义中个体实践自由的主要方式。通过行动,个体不断超越自身的现状,追求新的可能性和目标。最后,超越性在此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个体通过不断地选择和行动,来超越当前的自我状态,追求未实现的目标,即否定自在,通过自为趋向新的自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超越的过程,由认识和行动来实现。由于自在本身不与自为维系任何关系,因此个体必须通过自身的认识和行动来追求和实现这种超越。这种追求和实现的过程永远在进行,个体在超越中力求统一自在和自为,但这种统一永远无法彻底实现,因为两者本质上是异质的。
显然,在萨特的存在主义中,自我不仅是个体存在的核心,也是超越和救赎的主体。个体通过自我反思和否定,被赋予自由特性,并通过行动不断超越现状,从而实现对自我的不断重构。尽管这种重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孤独感和焦虑感,但正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超越中,个体找到了救赎的可能。当然,救赎在萨特的存在主义中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拯救,而是一种通过自由选择来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这种救赎是反抗性的,是对现有确定性(如宗教、社会规范、习俗、观念、道德、肉身等)的质疑和拒绝。
进言之,萨特存在主义美学的超越与救赎体现了对自由、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深刻探讨:通过反思和否定,人成为自由本身;通过行动和超越,个体不断追求新的可能性;最终,通过对自我不断的重构和对现有确定性的反抗,个体实现了自我的救赎。
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指导下,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在这种不断超越和追求中展现出一种充满激情的生命力,虽然这种生命力充满了荒谬感和孤独,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比如本次奥运会开幕式象征性的意象人物——席琳·迪翁、冉·阿让、卡西莫多,以及歌剧院的魅影,展现了自我超越和自我救赎的主题。这些角色正是通过不断地反思、否定、行动和超越,实现了对自我存在的追寻和救赎,体现了萨特存在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
席琳·迪翁在被诊断出罹患僵人综合征后,依然选择在2024 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登台演唱《爱的赞歌》。这种选择显示了她对困境的否定和对自身存在的反思。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强调,自我反思是个体意识到自身自由的基础。在面对疾病带来的限制时,席琳·迪翁通过反思认识到自己依然拥有选择的自由,并拒绝被疾病定义。她的演唱行为是对疾病的否定,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超越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她冲破了身体的限制,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和救赎。她的演出赋予了《爱的赞歌》新的积极意义,展示了个体在困境中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
而《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通过反思自己的过去和接受卞福汝主教的善意,意识到自身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这种反思使他能够否定过去的犯罪身份,追求新的高尚生活。在他成为市长和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冉·阿让通过不断的行动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他对芳汀和珂赛特的照顾不仅是对自己过去错误的补偿,更是对自我存在的重新定义。萨特认为,超越是自为趋向自在的过程。冉·阿让通过善行和道德实践不断追求理想的自在,尽管这种统一永远无法彻底实现,但是,他的救赎之路展示出存在主义中个体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实现精神救赎的过程。
《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在被社会排斥的情况下,通过对爱斯梅拉达的无私的爱和保护,展示了对自身存在的反思和对外界评价的否定。卡西莫多的选择和行动体现了萨特存在主义中的自由意志和超越性。他拒绝被自己的外貌和社会的偏见所定义,通过无私的行动展现出内在的善良和纯真。卡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的保护和牺牲可以看作是他自我救赎的过程,是他超越自身困境和社会排斥的体现。尽管他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他的灵魂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升华,这也展示了存在主义中个体在面对孤独和荒谬时,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实现精神升华的可能。
《歌剧魅影》中的魅影生活在社会的边缘,通过对克丽斯汀的爱恋和音乐创作,展示了他对自我处境和社会排斥的否定。他对克丽斯汀从强烈的控制到最终的放手,体现了存在主义中的反思、否定和行动的升华。魅影最终选择成全克丽斯汀和拉乌尔的幸福,是对自己内心痛苦和执念的超越,是他自我救赎的重要时刻。通过这一自我反思和自由选择,魅影实现了自我的成全,也实现了从孤独、痛苦到精神自由和崇高的转变。
总之,通过席琳·迪翁、冉·阿让、卡西莫多和魅影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萨特存在主义美学中超越与救赎的理念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体现。开幕式通过这些代表性人物向全球观众展示了法国的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宣AZL2mHUtW3JrLQdIKJQqldhBDbwYXUxLsSGoQyl0AMs=示了人类在面对荒谬和孤独时,通过自我救赎找到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可能性。也正是这种宣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继东京奥运会之后,在面对新冠疫情的痛苦记忆,以及俄乌战争和加沙战争的荒诞现实下,将人类奥运会开幕式理念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东京奥运会时人类面对无常世界的无力感,到巴黎重新吹响大写“人”的号角,弘扬反抗一切、昂扬向上、改变一切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批判与反思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以其大胆、创新的存在主义美学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这种美学融合了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通过展示多样性、个体主义以及对传统规范的挑战与解构,呈现了一种新颖的文化视角。开幕式试图表达自由和自主的理念,旨在打破常规,倡导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和自由表达。然而,这种极端的个体自由观也引发了显著的批评和反思。批评者认为,开幕式中的一些表现,如极端的个体主义、对传统伦理观的挑战和对LGBTQ+ 群体的高度突出,忽视了奥林匹克精神中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核心价值。许多人表示,这些表演形式不仅令人瞠目结舌,更是对传统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一种冲击和挑战。批评者指出,过分强调个体自由和自我表达,可能导致社会规范的瓦解和文化的混乱,甚至人类的灭亡。这种观点认为,存在主义美学在强调个体与他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冲突时,忽视了和谐与共生的可能性,进而会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对立。
首先,存在主义美学根基在于“诸神已死”和“宏大叙事的崩溃”,崇尚个体生命最深层的自由意志,可能落入巴别塔故事中的分歧与隔阂。存在主义美学否定传统宗教和文化的神圣感,强调个体在无意义的世界中孤立无援。尽管这种观念能够激发个体的自由和创新,但也可能导致去中心化、去秩序化,引发文化的断裂和社会的混乱。这种文化碎片化可能引发对文化和价值的深度质疑与社会分裂。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的表现形式,比如对诸神的反讽、对传统婚恋观和性别观的解构,虽然确实新颖且富有冲击力,却也很容易引发宗教人士和普罗大众的不适,从而削弱奥林匹克精神中所强调的团结与合作。
其次,存在主义美学不反对用荒诞、丑陋和不敬对抗经典美学和传统秩序,导致这种对抗虽然能够体现艺术的反叛精神,但也可能过犹不及,引发争议。奥运会开幕式作为一项集体仪式,本应体现尊重与和谐,目的是表现体育精神中的团结和公平;而存在主义美学的一些表现方式可能缺乏对这种核心价值的尊重,过度的艺术反叛和对挑战传统的情节,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引发恶心和不适,从而间接削弱了奥运会利用公共景观传达共同价值观的效果。
再者,存在主义美学的个体主义和反叛态度可能导致对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极端漠视。在“自我为中心”自由观念的影响下,个人行为和艺术表现可能会对自然差异、社会规范和公共利益有所忽略。虽然这种态度能推动艺术创新,但在公开场合出现时可能引发强烈的反感,从而欲速则不达,反而促成了反对阵营的出现与凝聚,无法形成彼此尊重的差异性存在,甚至造成社会的分裂。
最后,存在主义美学强调个体与他人关系中的冲突而非弥合,这也与奥林匹克的团结理念形成对立。萨特的存在主义虽然也重视差异化共存,但其根基在于认为个体之间的关系充满冲突,强调“他人即地狱”,聚焦于个人在他人目光和评价中的孤立感和痛苦感,并被迫积极应对,从而改变自我和他者,再进而改变世界。然而,奥林匹克精神提倡的是不同国家、文化和个体间的团结与合作,寻求美满、共融与和谐。存在主义美学的冲突性理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这一集体理念。
事实上,对自由的理解本身就有多个层次,中国传统的自由思想或许能够为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提供参照。从儒家和道家的自由观来看,萨特存在主义美学的弊端在于其过于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自我超越,而忽视了人际关系和自然、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儒家认为,自由并非无拘无束地行动,而是在道德自律和社会和谐中实现的一种内心状态。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强调个体通过自我约束和遵守社会礼仪来修炼自身,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由不是脱离社会责任和人际关系的孤立状态,而是个体在与他人和社会和谐相处中定义自我本质和道德目标的能力。道家的自由观念则更侧重于个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认为,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对“道”的理解与顺应,即通过“无为而治”来实现自然状态下的平和与自在。庄子特别强调,通过超越物质欲望和摆脱社会规范的限制,个体能够达到“逍遥游”的境界,这是一种心灵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超脱。在这种观念下,l1cNIE5305wo5bzVJ6hH0vFeMxbC5w6T3PbYqBlEs8Q=自由成为一种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和存在方式。[7]
显然,2014 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在展示存在主义美学强大创新性的同时,也暴露了其过于强调个体自由和破坏传统规范的弊端。对此,儒家和道家的自由观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人类处境的路径:在追求个体自由的同时,也要重视道德自律、社会和谐和自然统一。这些古老的智慧可以在个体与社会、自由与规范之间找到更加平衡和谐的路径,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和幸福。
奥林匹克精神自诞生以来,始终反映着人类对未来的思考和追求。从1996 年亚特兰大的“世纪庆典”,到2004 年雅典的“欢迎回家”,再到2008 年北京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每一届奥运会的口号都深刻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与时代精神。2022 年,北京成为历史上首个“双奥之城”,其提出的“一起向未来”口号,激励着正处于变局中的世界团结一心,共同面对挑战。如今,巴黎奥组委提出“奥运更开放”的口号,既是对全球的邀请,也是对共同前行的期待。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复兴以来,已发展成全球性的体育盛会与文化盛宴,其核心理念在于奥林匹克文化所蕴含的包容性和超越性。这种理念与人类社会对美好未来的共同追求不谋而合。无论是面对纳粹主义的威胁、难民危机的挑战,还是疫情及其他全球性问题的困扰,奥运会始终以体育的精神和力量促进人类的团结与进步。国际奥委会将“更团结”纳入奥林匹克格言中,就是为了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巴黎奥运会“奥运更开放”的口号不仅承载着历史的回响,更指引着未来的航程,象征着一种超越差异、敞开胸怀的心灵。某种意义上,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所传递的“天下一家”“以和为贵”理念,也许能够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所体现的存在主义“冲突”“创新”理念进行互文对话,并实现有效融合。它们如同两股相异却和谐的旋律,奏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响曲。尽管这两者在形式上各有风采,但本质上都在探寻共鸣与和谐的奥义。巴黎的呼唤是开放的邀请,融入广袤无垠的世界;而北京的智慧则是共处的美德,彰显求同存异的真谛。通过这种对话与融合,未来的奥运会开幕式或许能够在展现创新性的同时,兼顾传统规范与社会和谐,从而为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超越与救赎带来不同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甘莅豪. 从狂欢到共情: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国家形象修辞——一种体育景观观念史的视角[J]. 文化艺术研究,2021(5).
[2]伏爱华. 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07.
[3]弗里德里希·尼采. 快乐的科学[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4]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萨特. 他人就是地狱[M]. 关群德,等,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6]萨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 周煦良,汤永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7]邓晓芒. 什么是自由?[J]. 哲学研究,2012(7).
(责任编辑:孙婧)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2024QKT001)的阶段性成果。